《四川文學(xué)》2024年第1期 | 甫躍成:守護(hù)者(組詩)
《午飯后經(jīng)過一處工地》
工地里出來的幾個(gè)中年人
戴著黃色安全帽,穿著綠色反光背心,
蹲在馬路邊曬太陽。
有的抽煙,有的看手機(jī),
有的閉著眼睛靠在樹下,什么也沒看。
他們不說話。
除了我,沒有人經(jīng)過。
枝頭的殘葉微微晃動(dòng)。萬籟俱寂。
這是一個(gè)冬日的正午。
我心懷感激卻不知為何。他們的心情
是否也有相似之處?
我從他們身旁經(jīng)過。煙草的味道。
隱隱的呼嚕聲。打在他們身上的陽光
與打在我身上的,應(yīng)是同一種。
《滴水聲》
天明之后我再也沒有聽到滴水聲,
而那些滴水聲,幾乎讓我失眠了一夜。
它們那么密集、響亮,近在咫尺,
仿佛水珠滴進(jìn)了我的腦仁,
把我粗糙的記憶,也敲平了一塊。
黑暗之中我找不著那些水,
但是白天,我多想跟它們碰上一面。
奇怪的是,我再也沒有聽到滴水聲,
它們居然不辭而別,沒留下任何
蛛絲馬跡。早上起床,拉開窗簾,
我沒找著落水的屋檐、接水的篷布;
雨后的世界渾身濕透,也幫助它們
抹去最后一點(diǎn)來過的證據(jù)。那些滴水聲
是怎么來的?怎樣的源泉、路徑、落差
在那個(gè)特定的夜晚,造就了那些聲響?
我收拾行李,離開賓館,沒入人群。
后來我去過無數(shù)城市,住過無數(shù)房間,
聽到過無數(shù)的流淌、滲漏,總能見到
滴水的痕跡。但是那家賓館
很多年了,我再也沒有回去過。
《對(duì)屠宰鋪的六只羊的正面觀察》
前肢吊住。后肢吊住。
剝了皮,開了膛,
掏空下水,內(nèi)臟,腹腔打理得
干干凈凈,露出兩排
整齊的肋骨。
從這個(gè)特殊的角度,我不偏不倚,
與那只羊,正面相對(duì),總覺得是
與一面鏡子正面相對(duì)。仿佛我在
展示隱私,我在推銷
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自己。
它兩眼圓睜,神情呆滯,
當(dāng)然并不快樂,但也看不出
如何痛苦。大約我也是這副面容。
但它畢竟只是畜生,何況還是
死掉的畜生。它哪里會(huì)像
人類這樣,在頭顱正面
層層疊疊地,生長著無數(shù)盾牌。
舒一口氣,我向右挪了一步。
那只羊的左肩上,便層層疊疊地
現(xiàn)出六張臉來。
《老科學(xué)家》
老科學(xué)家死了四十多年,他的妻子還活著。
我們?nèi)グ菰L老科學(xué)家,沒有遇到。
我們問他的妻子,得知他正在四十五年前的
某間實(shí)驗(yàn)室里,做電纜補(bǔ)償實(shí)驗(yàn)。
這會(huì)兒正在做,還沒有結(jié)束。
也不知他做完實(shí)驗(yàn)后,會(huì)不會(huì)
走上四十五年的路程,回到我們中間來。
他就站在歷史中的某個(gè)點(diǎn)上,忙他的事;
但因?yàn)樘h(yuǎn),具體位置,連他妻子
也弄不明白。只留下我們,這幫串門的,
守在歷史之外,他們夫妻的客廳里,說著
他的逸事,左等右等,等了足足一個(gè)下午。
《滅蚊記》
毫無疑問,這是意義非凡的一握。
他向空中撈了一把,
死死攥住,確保捏死了那只蚊子。
這些天來,那只蚊子
總在他耳邊飛來飛去。在黑暗中。
在寂靜里。在他解除了所有武裝的當(dāng)口。
它肯定是故意的。它從來不在
他埋頭工作的時(shí)候來,也不在他
跟朋友喝酒聊天的時(shí)候來。
打蛇打七寸,它深知他的薄弱環(huán)節(jié),
瞅準(zhǔn)了,就痛下狠手,從他剛爬上床
就圍住他,一直到他再次逃進(jìn)人群之中。
這下好了。那只蚊子
終于栽在他的手心。勝負(fù)已定,
一切都將到此結(jié)束,一切都將重新開始。
出于謹(jǐn)慎,他又反復(fù)攥了幾把,
仿佛書里說的,扼住了命運(yùn)的咽喉。
起身,開燈,不無激動(dòng)地
攤開手掌,他只看見一片空無。
《守護(hù)者》
他問我能不能幫他守著三輪車,
好讓他把兩個(gè)包裹,送到臺(tái)階上面的那棟樓去。
當(dāng)然沒有問題。只是有些意外。
他只跟我見過幾面,知道我住在這個(gè)小區(qū),
但不知道具體位置。他對(duì)我的了解
僅限于一串號(hào)碼,以及地址欄里的
一個(gè)網(wǎng)名。他憑什么,對(duì)我這么信任?
突然有了惡作劇的沖動(dòng)。
如果我把三輪車開走,他怎么辦?
如果我順手藏起幾個(gè)小巧的包裹,他死無對(duì)證,
又怎么辦?他憑什么認(rèn)為,我不會(huì)這么做?
而我真的沒這么做。
我甚至心頭一暖,漸漸地有了
一種守護(hù)正義的使命感。十分鐘后,我望見他
出現(xiàn)在臺(tái)階頂部,滿頭是汗,憨笑著
朝我跑來,像老家的一個(gè)親戚。
《生產(chǎn)記》
她說她錯(cuò)過了孩子出生的過程。
從昏迷中醒來,剛一睜眼,借助天花板上
一面碩大的鏡子,她就目睹了
那血肉模糊的場(chǎng)面。她細(xì)細(xì)分辨著
那被切開的:一層,兩層,三層。
鮮紅的剪刀。鮮紅的紗布。鮮紅的
來回穿梭的針線。
那個(gè)腹腔,跟她先前見過的
并不一樣。她對(duì)我說,她見過的
從來不像這么凌亂。它們總是
被打理得干干凈凈,掛在肉鋪的鐵鉤上,
等著一個(gè)上好的價(jià)錢。
她不明白她為什么會(huì)躺在這里,
也不明白,那開膛的事件
又跟她有什么關(guān)聯(lián)。但這想法只有一瞬。
她對(duì)我說,醫(yī)生的右手
在拿刀的同時(shí),還能麻利地
用手套套住左手。然后兩手互換工作。
“橫著剖,還是豎著剖?”
沒等她回答,十個(gè)指頭,活動(dòng)著關(guān)節(jié),
已在手套下躍躍欲試。
直到一陣嬰兒的啼哭,把她從昏迷中
拽了回來,把她從別的世界
拽了回來,并將一個(gè)撕爛的空腔
塞進(jìn)了她的腹部。這讓她覺得
作為母親,她錯(cuò)過了孩子出生的過程。
作為父親,我錯(cuò)過的,還要更多一些。
我只看見她被推進(jìn)手術(shù)室,再從手術(shù)室里
被推了出來。
《死亡是個(gè)漸漸的過程》
父親告訴我,磚廠李全
有次從窯頂滾下來,鋼筋扎破肚皮,
后來手術(shù),腸子被割去兩米。
隔壁老六,年前做彩超,
意外發(fā)現(xiàn),腰子無緣無故地
少了一個(gè)。還有裝了假腿的鄭叔,
切了苦膽的二舅,甚至一些
我隱約記得名字的同輩。
父親是在我
問起他斷指的康復(fù)情況時(shí)
說起這些的。那么多人
都在變得殘缺不全,并且越缺越多,
越缺越多。所不同的
只是父親缺在明處,而他們
缺在暗處。
還算不錯(cuò)。截至目前,
我保留著全部零件。唯有腰椎
偶爾疼痛,大約是蓋到父親胸前的
那些黃土,蓋到了這里的緣故。
《女孩和她的姐姐》
她把媽媽叫作姐姐,這是近一年的事。
這是在她想要一個(gè)妹妹,沒有得到我們的回應(yīng)
之后發(fā)生的。爸爸媽媽是兩個(gè)人,
而她是一個(gè)。她多么需要一個(gè)小姐妹
跟她搭積木,過家家,用太空沙
捏各種神奇的形狀。
多么簡單。她僅僅是要
一個(gè)妹妹。實(shí)在沒有,弟弟也行。
她不明白為什么,添一個(gè)妹妹
竟有那么多考量,必須精打細(xì)算,評(píng)估財(cái)力、
人手、假期、房屋面積。
她不明白那么多玩具、繪本,只要她喜歡,
爸爸媽媽都給她買了;而一個(gè)妹妹,他們居然
糾結(jié)了這么多年。作為對(duì)策,從爸爸這里,
她搶走了媽媽,讓她充當(dāng)她的姐姐。
“姐姐。”她從臥室跟到廚房。
“姐姐。”她從廚房跟到客廳。
有時(shí)我真想奔過去,
抱住這對(duì)孤單的小姐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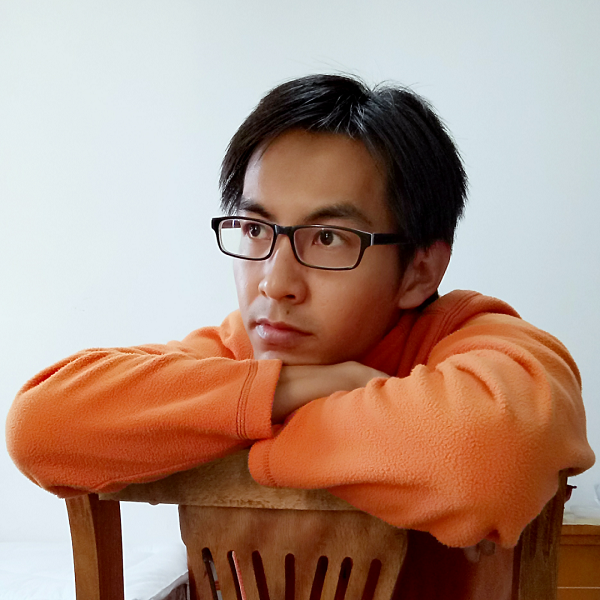
甫躍成:1985年生于云南施甸,現(xiàn)居四川綿陽。曾獲詩探索·中國春泥詩歌獎(jiǎng)、“四川十大青年詩人”稱號(hào)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