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電影,不妨先“閱讀”導(dǎo)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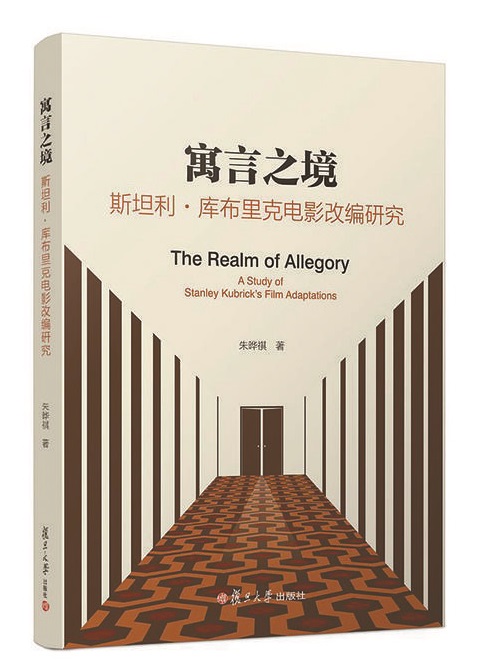
《寓言之境:斯坦利·庫(kù)布里克電影改編研究》 朱曄祺 著 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出版
電影從未像今天這樣焦慮于自身的原創(chuàng)性。從端莊素凈的文字到閃爍流盼的影像,這中間不僅是導(dǎo)演媒介轉(zhuǎn)譯手法的魔幻再現(xiàn),也是導(dǎo)演竭盡全力捍衛(wèi)電影作者身份的一種博弈。最近看到的這三本著作,《寓言之境:斯坦利·庫(kù)布里克電影改編研究》《經(jīng)典之后的銀幕奇景:好萊塢中生代導(dǎo)演研究》以及《法國(guó)“作家電影”流派研究》從不同角度為我們展現(xiàn)了導(dǎo)演研究的一些新方法和新動(dòng)態(tài),為讀者匯聚起了一種多元共生的電影閱讀經(jīng)驗(yàn)。
庫(kù)布里克:一個(gè)寓言型讀者
作為“導(dǎo)演中的導(dǎo)演”,斯坦利·庫(kù)布里克一直是一個(gè)神話般的存在。他的成就不僅引來(lái)詹姆斯·卡梅隆和史蒂文·斯皮爾伯格的交口稱譽(yù),甚至連伍迪·艾倫這樣的導(dǎo)演也不得不坦陳自己對(duì)他的敬意。確實(shí),庫(kù)布里克作品題材各異,形態(tài)迥然,議題深邃。可以說(shuō),他的作品兼具怪誕的娛樂(lè)性與迷宮般的思辨渴求,并因此成就了一種晦澀迷人的整體風(fēng)格。遺憾的是,現(xiàn)階段關(guān)于他的研究大多止步于傳統(tǒng)的導(dǎo)演傳記層面,甚而是以訛傳訛的八卦趣味,而未能精準(zhǔn)回答這種風(fēng)格背后的精神成因和作者技巧。這正是《寓言之境:斯坦利·庫(kù)布里克電影改編研究》令人眼前一亮的地方。區(qū)別于以往導(dǎo)演研究的普遍思路和范式,作者朱曄祺別出機(jī)杼,選擇了從庫(kù)布里克作為文學(xué)-電影改編者的角色介入,跳出了“作者電影”的習(xí)慣性窠臼,轉(zhuǎn)而從文學(xué)文本追蹤溯源,試圖重新探討有關(guān)庫(kù)布里克創(chuàng)造性的深層秘密。
在我看來(lái),本書(shū)至少在三個(gè)層面上做出了有益嘗試。首先,它重新定義了“作者電影”的范疇。眾所周知,自弗朗索瓦·特呂福1954年在《電影手冊(cè)》上公布自己有關(guān)作者策略的思考之后,“作者電影”常常被用來(lái)強(qiáng)調(diào)電影導(dǎo)演在創(chuàng)作上的獨(dú)立性以及作品的獨(dú)屬氣質(zhì)。那么當(dāng)面對(duì)庫(kù)布里克這樣一位視文學(xué)改編為創(chuàng)作重要契機(jī)的導(dǎo)演時(shí),作者理論該如何生效?我想,這正是朱曄祺決意從文學(xué)改編這個(gè)“非原創(chuàng)性”的源頭嘗試探討庫(kù)布里克作品創(chuàng)造性的出發(fā)點(diǎn)。那就是,將庫(kù)布里克視為一個(gè)寓言型讀者,并以此建構(gòu)他的作者身份。這就過(guò)渡到了文學(xué)-改編電影的標(biāo)準(zhǔn)判斷問(wèn)題,也即這本著作的第二個(gè)亮點(diǎn)。一直以來(lái),“忠誠(chéng)觀”都支配著文學(xué)-改編電影的創(chuàng)作標(biāo)準(zhǔn)。羅伯特·斯塔姆甚至認(rèn)為從精神分析角度來(lái)看的話,“電影改編就是俄狄浦斯,象征性地殺死了作為‘父親’的源文本”。而朱曄祺巧妙避開(kāi)了這一陷阱,將目光轉(zhuǎn)移到作為創(chuàng)作策略的改編行為本身,專注于探討導(dǎo)演在轉(zhuǎn)換“非語(yǔ)言體驗(yàn)”過(guò)程中如何激發(fā)電影的媒介優(yōu)勢(shì),自然而然地將媒介轉(zhuǎn)譯問(wèn)題引入了導(dǎo)演研究,從一個(gè)更大的媒介場(chǎng)域中印證了庫(kù)布里克獲得“新的看待世界的視角”這一過(guò)程。
《寓言之境》的第三個(gè)亮點(diǎn),或許也是最具抱負(fù)的一點(diǎn)就是,作者試圖通過(guò)將庫(kù)布里克定義為一個(gè)寓言型讀者,繼而在德勒茲運(yùn)動(dòng)-影像和時(shí)間-影像的哲學(xué)理路中為導(dǎo)演建構(gòu)起一種寓言-影像,即“肯定影像自身的矛盾性和差異性,讓原作、陳套、刻板印象和輿論常識(shí)都再次回到零度”。當(dāng)然,“回到零度不是為了摧毀和消解,而是為了在非零和的互動(dòng)中實(shí)現(xiàn)一種朝向未來(lái)、充滿活力的創(chuàng)造”。必須坦承,就庫(kù)布里克晦澀迷人的整體風(fēng)格和原著文本之間的“斷裂”而言,我確實(shí)感知到了朱曄祺所說(shuō)的寓言-影像,那是導(dǎo)演對(duì)原作文本和影像不確定性的一種積極回應(yīng)。這也是為什么我們對(duì)庫(kù)布里克改編作品總是持有一種混沌激撞的視覺(jué)印象,但對(duì)故事的感知卻總是恍如夢(mèng)游一般綿軟無(wú)力的原因。不過(guò),就書(shū)中寓言-影像的邏輯推演而言,我以為所涉理論之間仍有很多縫隙尚待填充。這是一本能夠?qū)﹂喿x發(fā)起挑戰(zhàn)的著作,當(dāng)然會(huì)伴隨著不斷解惑的快感。也可以說(shuō),就它的研究對(duì)象而言,這本書(shū)的行文風(fēng)格與庫(kù)布里克作品的整體風(fēng)格頗為般配:晦澀迷人,欲罷不能。
諾蘭:好萊塢最后的電影作者
《經(jīng)典之后的銀幕奇景:好萊塢中生代導(dǎo)演研究》選擇了克里斯托弗·諾蘭、戈?duì)枴ぞS賓斯基以及達(dá)倫·阿羅諾夫斯基三位導(dǎo)演作為管窺好萊塢中生代導(dǎo)演群體創(chuàng)作現(xiàn)狀的一個(gè)切口。正如書(shū)名暗示的那樣,三位導(dǎo)演的創(chuàng)作實(shí)踐構(gòu)成了相對(duì)保守的好萊塢主流敘事之外的一道銀幕奇景,令讀者從不同題材、風(fēng)格和價(jià)值取向中領(lǐng)略到了電影創(chuàng)作的多元形態(tài)和創(chuàng)作潛能。確實(shí),通過(guò)作者對(duì)幾位導(dǎo)演創(chuàng)作路徑的詳盡分析,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歐美電影文化之間的傳承與互動(dòng)。諾蘭作品中困頓糾結(jié)的個(gè)人英雄主題、維賓斯基反英雄的角色塑造,以及阿羅諾夫斯基對(duì)灰色人性的反復(fù)摹寫(xiě),都能在庫(kù)布里克的作品中找到回聲。最重要的是,沿著書(shū)中提供的線索,好萊塢中生代導(dǎo)演與昔日“新好萊塢”導(dǎo)演作品的精神地圖逐漸顯影。那種由“消費(fèi)社會(huì)所孕育,并從消費(fèi)社會(huì)提倡和反對(duì)的價(jià)值中誕生的現(xiàn)代性”,通過(guò)不同的角色發(fā)出了各自的呼聲。可以說(shuō),他們的作品持續(xù)不斷地發(fā)酵著“作者電影”的獨(dú)特魅力,并力圖在后現(xiàn)代文化語(yǔ)境中為“作者電影”賦予新的意蘊(yùn),那就是“藝術(shù)價(jià)值與商業(yè)價(jià)值的自覺(jué)趨同”。
正如羅伯特·考克爾所言:“電影不僅是娛樂(lè)物,而且是工業(yè)和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對(duì)于三位中生代導(dǎo)演來(lái)說(shuō),如何將嚴(yán)肅的社會(huì)議題和人類(lèi)深邃神秘的精神世界鑲嵌進(jìn)基于類(lèi)型的好萊塢主流盈利框架,同時(shí)還要在形式風(fēng)格上做到清晰可辨,首先就是要尊重和恪守被驗(yàn)證過(guò)無(wú)數(shù)次的好萊塢電影工業(yè)經(jīng)驗(yàn),然后才可以觸及風(fēng)格化的“作者”符號(hào)。以諾蘭來(lái)看,圍繞著造夢(mèng)(《蝙蝠俠》系列)、尋夢(mèng)(《記憶碎片》)與盜夢(mèng)(《盜夢(mèng)空間》)這一不斷重復(fù)的抽象主題,使得他在技巧上形成了以碎片化剪輯、非線性敘事以及低密度暗黑冷峻的影像(對(duì)夢(mèng)境的營(yíng)造)為特征的整體風(fēng)格。而他一直堅(jiān)持實(shí)景拍攝,堅(jiān)持使用傳統(tǒng)膠片,拒絕使用數(shù)字中間片來(lái)調(diào)色的“固執(zhí)”習(xí)慣,也為作品整體上賦予了一種“不妥協(xié)”的作者氣質(zhì)。但它經(jīng)由碎片化剪輯和高度視覺(jué)化的夢(mèng)境再現(xiàn)所形成的那種大開(kāi)大合的節(jié)奏,又極其精準(zhǔn)地?fù)糁辛嗽诤蟋F(xiàn)代文化語(yǔ)境里浸淫已久的觀眾口味,使得“作者電影”這個(gè)概念從法國(guó)新浪潮時(shí)期那種對(duì)形式技巧的僭越?jīng)_動(dòng),演變?yōu)橐环N融合了幾許“作家電影”氣質(zhì)的混合物(諾蘭承認(rèn)《盜夢(mèng)空間》里有好幾處情節(jié)“碰巧”與《去年在馬里昂巴德》相似)。無(wú)怪乎斯皮爾伯格直言諾蘭“是好萊塢最后的電影作者”。我想,通過(guò)這幾位中生代導(dǎo)演的實(shí)踐,好萊塢主流電影已經(jīng)確認(rèn)了它的自我更新意識(shí)和推陳出新的能力。
“作家電影”:將文學(xué)表達(dá)不了的用影像再現(xiàn)
盛柏則在《法國(guó)“作家電影”流派研究》中仔細(xì)辨析了“作家電影”和“作者電影”的區(qū)別。對(duì)于一個(gè)深受20世紀(jì)中葉“存在主義”和柏格森“直覺(jué)主義”影響而導(dǎo)致的富于心理意識(shí)特征的電影流派來(lái)說(shuō),“作家電影”獨(dú)有的哲思意蘊(yùn)與內(nèi)斂氣質(zhì)和新浪潮時(shí)期“作者電影”在形式上的激揚(yáng)狂放大相徑庭。它對(duì)戲劇化敘事模式的摒棄、對(duì)情節(jié)套路的淡化、對(duì)角色線索的交錯(cuò)處理、對(duì)旁白的偏愛(ài)、對(duì)時(shí)空?qǐng)鼍暗奶S式剪切等處理,使得觀影過(guò)程猶如在一個(gè)私密的內(nèi)心世界里夢(mèng)游,成功地在電影世界里復(fù)制了類(lèi)似文學(xué)閱讀的沉浸經(jīng)驗(yàn),一度為“作家電影”贏得了聲譽(yù),也將電影與文學(xué)的關(guān)系推到了話題中心,歷史上第一次為電影媒介賦予了文化深度——電影從此不再是一個(gè)膚淺的娛樂(lè)產(chǎn)品。譬如在面對(duì)《廣島之戀》這樣的作品時(shí),觀眾即便全神貫注參與進(jìn)去也仍然不得要領(lǐng)。在那一刻,電影仿佛由熱媒介又變身為冷媒介了。看起來(lái),“新小說(shuō)”派的作家們雖然拿的是導(dǎo)筒,卻仍然是按照文字去思維。不知道曾經(jīng)提倡將攝影機(jī)視為一支自來(lái)水筆的亞歷山大·阿斯特呂克對(duì)此會(huì)作何想。
事實(shí)上,無(wú)論是“作家電影”還是“作者電影”,他們都在各自不同的立場(chǎng)上強(qiáng)調(diào)電影作品的原創(chuàng)性,表面的差異背后或許是對(duì)媒介表達(dá)可能性的某種焦慮。正如盛柏觀察到的那樣:“‘作家電影’流派的導(dǎo)演們并不是為了電影而拍電影,而是將文學(xué)表達(dá)不了的東西用影像再現(xiàn)出來(lái)。”如果我們將這個(gè)判斷放在上世紀(jì)中期視覺(jué)文化開(kāi)始呈井噴之勢(shì)的語(yǔ)境中(正好是“作家電影”群體的創(chuàng)作高峰),或許更容易理解“作家電影”隱含在意識(shí)流影像中的不安與糾結(jié)。正像他們對(duì)旁白的過(guò)分倚重所導(dǎo)致的“影像與聲音的堆砌”最終對(duì)電影本體美學(xué)的傷害那樣,“作家電影”留給我們最寶貴的遺產(chǎn)之一可能就是重新思考電影與文學(xué)的關(guān)系。倘若阿蘭·羅伯-格里耶所言屬實(shí),即小說(shuō)和電影“是截然不同的兩種物質(zhì)形態(tài)”,因而需要為他們的電影創(chuàng)作出專屬的劇本的話,那么當(dāng)我們回望庫(kù)布里克寓言式的改編策略,或許就更容易理解他作品中的“作者”屬性:創(chuàng)造性的媒介轉(zhuǎn)譯與激進(jìn)形式的完美結(jié)合。
概括而言,以比較閱讀的經(jīng)驗(yàn)來(lái)看,這三本著作圍繞電影的作者屬性和電影與文字的媒介屬性,角度各異,殊途同歸,共同指向了一種多元共生的電影經(jīng)驗(yàn),大致勾勒出了當(dāng)下導(dǎo)演研究的一種新視界。期待中國(guó)導(dǎo)演研究也能涌現(xiàn)更多在方法論和研究視角上獨(dú)具一格的新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