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之書》:自由的言語包含說出和思考這個世界的全部可能
《不安之書》是葡萄牙國寶級詩人費爾南多·佩索阿用二十余年以不同異名創(chuàng)作的百余篇日記體散文隨筆,由后人收集編纂而成的一本奇書。最早曾由作家韓少功于20世紀(jì)90年代從英語譯為中文,書名叫《惶然錄》。
本次出版的《不安之書》以著名佩索阿學(xué)者熱羅尼莫·皮薩羅的編訂本為底本,從葡萄牙語全文譯出,還原了佩索阿創(chuàng)作的階段性特征和這位文學(xué)巨匠的人生心路歷程,寫出了現(xiàn)代人內(nèi)心的種種感受,展現(xiàn)了人性的孤獨和決絕之美,以動人的詩意和哲理引起我們的共鳴。本文摘編自熱羅尼莫·皮薩羅為該書所作的導(dǎo)讀。
在以“旋渦,旋風(fēng),在生活流動的膚淺中!”(第246篇)開頭的篇章里,一個由池塘、河流和小溪組成的“水之意象”在我們面前構(gòu)建起來,這個意象的出發(fā)點,是視野中的人群,他們“在(里斯本)市中心的大廣場上”穿行,像“多彩而莊重的水”一樣。對敘述者而言,這個由人群組成的“水之意象”在“大廣場”流淌著——他還補充道,“因為我想到快要下雨了”——與“這一不確定的來來往往”巧妙契合,也就是說,與生活如水流和回流的感受相契合。復(fù)數(shù)形式的“來來往往”?是的,對此他這樣解釋:
在寫最后這句話的時候,我覺得它準(zhǔn)確地說出了它所定義的東西,我想也許有必要在我的書出版時,在“勘誤”下面加一欄“非誤”,然后寫上:“這一不確定的來來往往”,第幾頁,的確如此,形容詞單數(shù)搭配名詞復(fù)數(shù)。(第246篇)
佩索阿終究沒有寫下這些“非誤”,但是,如果他真的寫出來,我們會更容易明白《不安之書》究竟是怎樣充滿這些能夠引起陌生感的語句——并不僅僅因為語法上的搭配——同時也能明白,《不安之書》是如何得益于作者的語言意識,從而形成富有音樂性和夢幻感的散文風(fēng)格的。在本文中,我并不想證明《不安之書》的偉大在于它有一定數(shù)量的、不那么正統(tǒng)的語句,也不想證明這些語句必然提升了某些篇章的價值(正如若熱·德·塞納所說,“有些篇章是最優(yōu)美也最有穿透力的葡萄牙語散文”)。我想說的是:“非誤”計劃表明了本書語言的一種高深意義;《不安之書》的散文值得研究,因為是它定義了這部作品,并彰顯出作者的特色。福樓拜說“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佩索阿則通過(或不通過)半異名作者貝尓納多·索阿雷斯宣稱:“很大程度上,我就是我寫的這篇散文。”(第322篇)此外,任何對《不安之書》文本的反思(越來越以創(chuàng)作計劃和“非誤”概念為引導(dǎo))都包含對該書的編訂工作進行審視,因為很多時候,編訂者除了確定文本,還會修改原文。
在寫下“這一不確定的來來往往”的同一天(1930年4月25日),佩索阿還創(chuàng)作了另一段文字,其顛覆程度不亞于前者:
廣場東邊比另一邊有更多的外地人。好像鋪著地毯的閘門,那些波浪狀的門向上降下,不知為什么,正是這樣的一句話向我傳達了那個聲音。也許因為門降下的時候才更能發(fā)出那個聲音,但是此刻它們正在上升。一切都是可以解釋的。(第246篇)
可以注意到,那些門(窗?)不但反邏輯地向高處降下(佩索阿還用鉛筆加了一條注釋:“也許因為門降下的時候才更能發(fā)出那個聲音”),而且是“波浪狀的”(onduladas),一個出人意料的形容詞,和“鋪著地毯的”(alcatifadas)一樣,兩者還押韻。《不安之書》的語句尋求貼合并傳達多重感受,常用一種有韻律的散文來表達,與詩歌建立了明顯的一致性。讓我們在同時代的一段筆記中(1930年3月23日前后)回顧《不安之書》的詩藝:“把馬拉美的感性放在維埃拉的風(fēng)格中;在賀拉斯的軀體中像魏爾倫一樣做夢;在月光下成為荷馬。”(第230篇)也可參見《不安之書》五篇中的第一篇,“貝爾納多·索阿雷斯著”,由佩索阿于1931年發(fā)表在《發(fā)現(xiàn)》雜志上,開頭如下:
作為藝術(shù)形式,比起韻文,我更偏愛散文,理由有兩個。其一是個人原因,我沒有選擇,我無法用韻文寫作;其二則是放之四海皆準(zhǔn),而且我完全相信,這不是前一個理由的影子或偽裝,所以我有必要將它拆解,因為它觸及藝術(shù)全部價值的深層意義。
我把韻文看作一種中間性的東西,一種音樂向散文的過渡。和音樂一樣,韻文受到韻律法則的限制,即使不是規(guī)律韻文那生硬的法則,也仍有著類似謹(jǐn)慎、強制、壓迫和懲罰的自動裝置。在散文中,我們自由說話。我們可以添進音樂節(jié)奏,但還能思考。可以添進詩性節(jié)奏,但還能處于它們之外。一個偶然的韻文節(jié)奏不會阻礙散文;一個偶然的散文節(jié)奏則會將韻文絆倒。
在散文中囊括著整個藝術(shù)——一方面因為在言語中包含整個世界,一方面因為自由的言語包含說出和思考這個世界的全部可能。(第331篇)
異名作者里卡多·雷耶斯和阿爾瓦羅·德·坎波斯在其他文字中延續(xù)了這場爭論,佩索阿生前未曾發(fā)表這些文字,他去世之后,它們才在《私密筆記和自我闡釋》(1966年)和《有待認(rèn)識的佩索阿》(1990年)中得以發(fā)表。我不參與這場被《不安之書》擴展并復(fù)雜化的爭論,但我想強調(diào)的是,對佩索阿/索阿雷斯來說,散文是獲得自由的化身:“在散文中,我們自由說話”;“自由的言語包含說出和思考這個世界的全部可能”。這種自由,不管真實或是表面,都是《不安之書》試圖要推向極致的。在與上述引文同年代的一個文本中,作者尖銳地回應(yīng)了“沒有人讀我寫的東西,那又怎樣?”這個問題,他說:“我寫我自己,是為了從生活中散心”,其中,“我寫我自己”(escrevo-me)用的是動詞“寫”(escrever)不尋常的反身形式。而他怎樣寫作?在怎樣的散文中散心?
佩索阿以一貫的清醒認(rèn)識到,一個作者的創(chuàng)作部分地取決于一種心理特征和風(fēng)格的創(chuàng)造——就像后來福柯理論化的那樣。
如果我們從語言學(xué)的角度審視《不安之書》,它就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創(chuàng)作中的作品”(work in progress),類似詹姆斯·喬伊斯那些最偉大的作品。在現(xiàn)代主義著作的“勘誤”下面,存在著多少個“非誤”呢?
在用打字機寫下“這一不確定的來來往往”的同一天(1930年4月25日),佩索阿為他的散文,即本書作者的散文,留下了一段深思。此處作部分摘錄:
今天,在感受的間隔,我對我使用的散文形式進行了深思。事實上,我是怎么寫作的?[……]
下午我分析自己,發(fā)現(xiàn)我的風(fēng)格系統(tǒng)有兩個原則作為支撐,于是我立即以正宗優(yōu)秀古典作家的樣子,將這兩個原則定為我整個風(fēng)格的總體性基礎(chǔ):完全準(zhǔn)確地以感受到的東西來描寫感受——如果感受是清晰的,就清晰地寫;如果是隱晦的,就隱晦地寫;如果是混亂的,就混亂地寫;理解語法是一種工具,而非法律。
假設(shè)我們面前有一個男子氣的姑娘。一個普通人會這樣說她:“那姑娘像個小伙子。”另一個普通人,離意識到說話即是表述要近那么一些,會說:“那姑娘是個小伙子。”再來一個,同樣意識到何為表達的義務(wù),但又更傾心于準(zhǔn)確性(這可是思想的放蕩),會說:“那小伙子。”而我則會說 “她那小伙子”,打破語法規(guī)則中最基礎(chǔ)的那條,即名詞和形容詞性單詞的性數(shù)必須一致。[……]
語法上的分類雖然是正當(dāng)?shù)模彩翘摷俚摹1热纾褎釉~分為及物和不及物;然而,懂得表述的人,很多時候需要把及物動詞轉(zhuǎn)化成不及物動詞,才能將他所感受到的東西拍照下來,而不是像普通的人形動物,只會在暗處張望。如果我想說我存在,我會說“我是”。如果我想說我是以單個的靈魂存在,我會說“我是我”。但如果我想說我是以指向自身、塑造自我的個體而存在,與自身一道,行使自我創(chuàng)造的神圣職責(zé),我怎能不立刻將動詞“是”轉(zhuǎn)化成及物動詞呢?這樣一來,我將以勝利的、反語法的姿態(tài),至高無上地說出:“我是著自己。”(Sou-me)僅憑兩個小詞,我可不就說出了整個哲學(xué)。這難道不比連說四十多句廢話要好很多嗎?還能對哲學(xué)和語言表達提出比這更苛刻的要求嗎?
讓不懂得如何思考所感的人去遵循語法吧。[……](第247篇)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佩索阿很早就設(shè)定了這兩個原則。第一,“完全準(zhǔn)確地以感受到的東西來描寫感受”,這也是他在《頹廢文學(xué)》(1909年前后)一文中提出的觀點之一,該文的副標(biāo)題為“關(guān)于馬克斯·諾道[《退化》]一書的筆記”,文中寫道:“正如埃德加[·愛倫]·坡指出和踐行的那樣,有必要區(qū)分隱晦的表達和表達的隱晦。為隱晦的事物提供清晰的表達是一種藝術(shù),不是將事物本身變得明白,而是將事物的隱晦性變得明白。”第二,“理解語法是一種工具,而非法律”,這是在未來主義宣言中被強化的一條原則,也是葡萄牙現(xiàn)代主義第一階段(1909—1915)的精神,雖然佩索阿在《不安之書》中從“沼澤主義”和其他現(xiàn)代主義文本風(fēng)格演變成辦公室小職員的晚期散文風(fēng)格,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阿米耶爾和馬拉美,塞薩里奧·韋爾德和卡米洛·庇山耶,荷馬或賀拉斯,以及安東尼奧·維埃拉神父(“葡萄牙語之皇”),或者,如果我們想一想《弗拉迪克·門德斯書信集》的話,也得益于埃薩·德·凱羅斯。
《不安之書》中圍繞1930年這個軸心的文章是那么多,佩索阿也似乎感到有必要解釋他為什么以這種方式寫作:
歸根到底,所有文學(xué)都努力使生活變得真實。眾所周知,哪怕當(dāng)人們行動而不自知時,生活在其直接現(xiàn)實中,是徹徹底底不真實的;田野,城市,概念,都是徹底的虛構(gòu)物,是我們那復(fù)雜的自我感知所生的女兒們。所有的印象都不可傳遞,除非我們將其變成文學(xué)性的。小孩子是非常文學(xué)性的,因為他們說的是自己感受到的東西,而不是根據(jù)他人所說的、人應(yīng)該感受到的東西。有一次我聽到一個小孩子,他想說自己在哭泣的邊緣,他說的可不是“我想要哭”,那是成人才會用的表達,是愚蠢的;相反 ,他說的是“我想要眼淚”。這句話完完全全是文學(xué)性的,如果一位著名詩人說得出這句話,一定也會引以為傲。它是如此毫不猶豫地提到熱淚的出場,那即將沖破意識之眼瞼的、化成水的痛苦。[……]
表達!懂得如何表達!懂得通過書寫的聲音和智識的圖像來存在!這一切才是人生的意義所在:此外都不過是男男女女,假設(shè)的愛情和虛構(gòu)的驕傲,消化和遺忘的托辭,蠕動的人類,好像昆蟲,當(dāng)石頭被抬起時,暴露在沒有意義的藍天那抽象的巨石之下。(第266篇)
“表達!懂得如何表達!”,佩索阿如此呼吁;懂得通過“書寫的聲音”存在是如此重要,此外還要加上懂得通過“智識的圖像”存在的價值。《不安之書》充滿了這樣的圖像。在本文開頭,我提到里斯本的大廣場上由池塘、河流和小溪組成的“水之意象”,在同一個片段中,我清晰地記得,視野中的電車好像“可移動的火柴盒,大大的黃顏色的,小孩子會把燒過的、歪歪斜斜的火柴棍插在上面,做成一根糟糕的船桿”(第246篇)。還有很多這樣的影像,許多都不可磨滅。因此,《不安之書》是里斯本城最令人驚嘆的肖像畫,一系列詞語和影像疊加累積,在讀者的視象中交織、互補。作者在第一階段的文本中說道:“這本書展現(xiàn)靈魂獨特的狀態(tài),從所有側(cè)面剖析,從所有方位考察。”(第49篇);這一靈魂狀態(tài),更確切地說,是一個辦公室職員的靈魂狀態(tài),他的生活和精神以“里斯本”作為“關(guān)鍵地址”,全部“用大寫的字母”寫成(第248篇)。
在《不安之書》中,幾乎所有事物都指向新的、暗示性的現(xiàn)實。作者解釋說,“每一件事物向我暗示的,并非它是影子這一現(xiàn)實,而是它是通往現(xiàn)實的道路”;以午后的星星公園為例,它讓作者想到“一座古老的公園,在靈魂幻滅之前的那個世紀(jì)”(第158篇)。在另一段文字中,作者解釋如何努力變換自己所看到的東西,以及如何讓風(fēng)景像音樂般勾起視覺意象:
我使風(fēng)景產(chǎn)生音樂的效果,喚起視覺意象——這是狂喜狀態(tài)所能獲得的奇妙且最艱難的勝利,因為引發(fā)浮想的載體與被喚起的感覺同屬一種秩序。類似的最高成就,是在某個景觀與光線都不甚明朗的時刻,當(dāng)我望向索德烈碼頭,竟清楚地看見它變成了一座中國寶塔,塔頂四角掛著奇怪的鈴鐺,好似滑稽的帽子。這座奇特的寶塔是畫出來的。它高聳于綢緞織成的界面,我不知道這空間如何能長久地存在于可怕的三維世界里。(第61篇)
這個圖像和其他類似的圖像,由不同元素堆積而成,比作者“不經(jīng)意的靈魂”中那些消極“展開”(第204篇)的、簡單的夢中風(fēng)景要豐富得多。《不安之書》似乎不過是一系列“并不連貫而我也不期望能連貫的印象”(第222篇),圖像可以給出這樣的印象,作者也頻頻嘗試灌輸這種感覺。然而,有時候,《不安之書》顯得更加不連貫,組織更松散;這時尤其不應(yīng)該忽略那個賦予作品整體性的運作機制:通過無數(shù)圖像來完成敘述,而不是通過相對罕見的事實或事件(比如理發(fā)師“右手邊椅子上工作的同事”之死)。在《不安之書》中我們看到的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圖像揮灑,通常這在詩歌中更加常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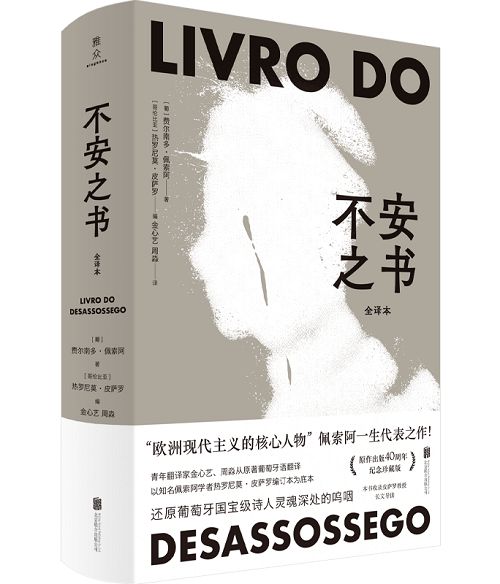
《不安之書》,[葡]費爾南多·佩索阿著,[哥倫]熱羅尼莫·皮薩羅編,金心藝、周淼譯,雅眾文化·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2022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