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間奇聞到兒童讀本,差距有多大? 繞到門后看看格林童話的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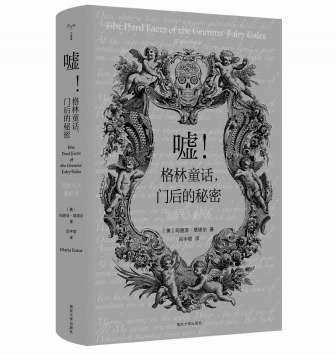
《噓!格林童話,門后的秘密》 (美)馬里亞·塔塔爾 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
人類生來愛故事,編故事與聽故事皆熱愛。
當(dāng)我們尚在襁褓中,母親便擁著我們邊搖邊聊,像在喃喃自語,又好似在說故事給我們聽。懷里的小嬰兒就像聽懂了,手舞足蹈地拼命回應(yīng)。等我們長(zhǎng)到兩三歲,每晚講睡前故事就愈發(fā)變得順理成章。所有故事里,當(dāng)然最愛童話,伴著“再讀一遍”的口頭禪,我們數(shù)不清聽過多少遍《小紅帽》與《白雪公主》。長(zhǎng)大了,再回想這些童話故事,情節(jié)依舊在那里,記憶中,仍殘存著媽媽的軟語與體香。
童話故事與母親,帶給了我們對(duì)世界最初的認(rèn)知。
美國(guó)著名童話學(xué)者、哈佛大學(xué)教授瑪麗亞·塔塔爾,潛心研究格林童話多年,對(duì)童話的演變與發(fā)展頗有心得。她的《噓!格林童話,門后的秘密》是一本向成年人介紹格林童話的專著,正如書名所言,如果說格林童話的大門是向孩子們敞開的,那么作為大人,我們或許有必要繞到門后,看看童話的背后的秘密,以便在鬼靈精怪的小讀者提出問題時(shí),我們始終保持清醒頭腦,告知他們世界上凡事都存在兩面性,童話里的故事也不例外。
表面上,童話里那些諄諄教導(dǎo)的話像是說給孩子聽的,但合上書,每個(gè)成人是否能從童話里捕獲一個(gè)真實(shí)的自我呢?就像圣埃克蘇佩里的《小王子》中,小王子與玫瑰的情感,真的能用單純的彼此馴服就抵達(dá)長(zhǎng)久來解釋清楚呢?讀童話故事,成年人的收益也許會(huì)比兒童更多。
眾所周知,格林童話是世界童話中的先驅(qū)與佼佼者。作者“格林兄弟”當(dāng)然不是一個(gè)人的名字——哥哥雅各布出生于1785年,弟弟威廉比哥哥小一歲,兩人都是德國(guó)19世紀(jì)著名的歷史學(xué)家、語言學(xué)家,他們花費(fèi)了很大的精力做民間故事與古老傳說的搜集與整理工作。這里,我們看到了一個(gè)很重要的信息:格林兄弟并非是文學(xué)創(chuàng)作者,而是歷史與民俗研究專家。他們的作品在德國(guó)被稱為《兒童與家庭童話集》,是銷量?jī)H次于《圣經(jīng)》的暢銷書。
那么,格林童話是如何由屬于民俗學(xué)范疇的民間故事轉(zhuǎn)變成充滿文學(xué)性的童話故事的呢?塔塔爾在本書的第一部分“兒童文學(xué)?”里進(jìn)行了詳細(xì)闡述。她明確表示,格林兄弟所做的所有收集整理,甚至可以說在“格林童話”的各個(gè)版本之間,進(jìn)行了幾度純潔化的工作,以便達(dá)到兒童的閱讀標(biāo)準(zhǔn),但其中不存在文學(xué)原創(chuàng)工作。所以,最初的“格林童話”并不是為孩子們寫的,而是百姓間口口相傳的“奇聞異事”。
西班牙女作家伊蓮內(nèi)·巴列霍在《書籍秘史》里提到,在發(fā)明文字之前,人類社會(huì)就是一個(gè)口傳社會(huì)。山魯佐德用給蘇丹國(guó)王講故事來穩(wěn)住他那顆要?dú)⑷说男模@件事要堅(jiān)持一千零一夜啊,可見講述故事帶來的情感舒緩與安撫效果不可估量。
但作為民間故事,你知道格林童話的初版里有多少“少兒不宜”嗎?塔塔爾表示,“性與暴力”在收集來的故事里隨處可見。比如在《千匹皮》中,女主人公的父親一心想同自己的親生女兒結(jié)婚,導(dǎo)致女兒不得不從家中逃走,前往樹林。而在第二版的《灰姑娘》里,竟然有灰姑娘兩個(gè)姐姐的眼珠被鴿子啄瞎的情節(jié)。
格林兄弟之所以保留這樣的情節(jié),源于他們對(duì)文本故事性的認(rèn)知。他們認(rèn)為那時(shí)的民間故事多數(shù)來自于家庭生活,而“性與暴力”是家庭最常見的沖突。然而,兒童并不反感暴力,反而似乎對(duì)暴力情節(jié)有無法抑制的迷戀,這大約來自于孩童對(duì)自身生活的不安全感,抑或從“物競(jìng)天擇”的角度來看的求生欲。
不過暴力不能單純地歸結(jié)為惡,置身于童話中去解讀,還包括神靈與魔鬼的較量。如此看來,或許對(duì)孩子們還是有一定意義的。但面對(duì)公眾的批評(píng),威廉還是背著雅各布對(duì)收集來的故事進(jìn)行了“刪改與加工工作”。然而,純潔化后的童話的確不如之前的民間故事那么吸引人了,銷量也不容樂觀。從第二版到第三版出版,格林兄弟忍受了十八年的清苦生活。
從民間故事重塑成童話故事,格林兄弟經(jīng)過了從聽到讀、從口語到書面語言的轉(zhuǎn)變,以及在情節(jié)上的大規(guī)模修改。但其中最大的問題是,民間故事具有歷史傳承的差異,以及各地理區(qū)域的不同特征。比如德國(guó)的《小紅帽》與俄羅斯的版本就不完全一樣,而那個(gè)吃掉小紅帽的野獸,可能是狐貍,也可能是大灰狼。從二十世紀(jì)初起,民俗學(xué)家開始采用“歷史-地理法”的分類模型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收集民間故事。不得不說,格林兄弟的這些前期搜集工作對(duì)民俗學(xué)研究是有推動(dòng)作用的。
雖然不能說格林童話千篇一律,但可以發(fā)現(xiàn)它的撰寫與編排是有規(guī)律可循的。這一點(diǎn),熟悉格林童話的讀者都知道。在本書作者塔塔爾看來,童話故事里總有一個(gè)無知的父親,但他卻具有著善良與謙虛的品質(zhì),無論他是國(guó)王還是農(nóng)民。但是,所有吸引人的故事都發(fā)生在母親與孩子們身上。
格林童話里的女性多樣化,是值得我們關(guān)注的一點(diǎn)。“她”,既可以是無處不在的“鵝媽媽”——據(jù)說這位鵝媽媽是所有年長(zhǎng)農(nóng)婦的代稱,旨在用母鵝咯咯咯咯的叫聲來形容母親喋喋不休地講故事,也可以是兇惡的王后,還可以是無知的小紅帽和后知后覺的白雪公主。
但最重要的是,最初格林故事插畫中的女性形象都是與紡錘或紡車共同出現(xiàn)的,直到十九世紀(jì)才逐漸消失。與我國(guó)民間故事不同,這種勞作的形象在故事中絕不是為展示女性的勤勞,而是通過各種暗示來說明紡織勞動(dòng)會(huì)傷害身體,就像講故事會(huì)傷害嗓子一樣。如果女性具有一種技藝,那一定是通過傷害外表得來的,而那些美貌女主人的華美禮服,必然是辛苦勞作的成果。如何從苦工變王后?不是沒有通路,但要借助超自然的能力獲得,那就是魔法。童話的邏輯是驚人的,但格林兄弟還是固執(zhí)地輸出從民間收集來的價(jià)值觀。
正如塔塔爾在本書結(jié)尾所說,“在格林童話中,真的恐怖與其說是‘受害-報(bào)復(fù)’類故事,不如說是那些‘違犯-懲罰’類警世故事。這些故事總是以成年人的智慧戰(zhàn)勝孩子的好奇、違抗或頑皮為結(jié)局。”如果她的話是對(duì)的,那么讀童話,可不是越讀越天真,而是越讀越老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