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理解式的閱讀 ——評(píng)《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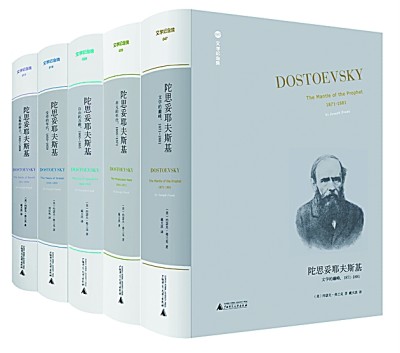
《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卷本 約瑟夫·弗蘭克 著 戴大洪 譯 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
當(dāng)一個(gè)作家變成了一門專門的學(xué)問(wèn),這首先意味著他具有了某種經(jīng)典性。但在這樣的經(jīng)典作家當(dāng)中,更有一些作家具備了“全人類性”的特質(zhì),他們的創(chuàng)作早已經(jīng)不能被書齋里的“文學(xué)”這個(gè)定義所局限,他們是思想者,他們對(duì)人類未來(lái)共同命運(yùn)的憂思、猜想和思想進(jìn)路當(dāng)屬于新世紀(jì)的全人類。其中,俄羅斯文豪費(fèi)·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無(wú)疑是位居前列者。
同樣,如果一個(gè)學(xué)者終其一生研究一個(gè)作家,并且真的極為投入,這首先意味著價(jià)值的認(rèn)同,這樣的學(xué)者或許并不鮮見(jiàn)。但我們也應(yīng)當(dāng)承認(rèn),其中有的學(xué)者在更高意義上實(shí)現(xiàn)了這種認(rèn)同:這已經(jīng)是一個(gè)生命對(duì)另一個(gè)生命的體認(rèn),心甘情愿將自己的生命時(shí)光用于理解、闡釋、傳播另一個(gè)來(lái)自遙遠(yuǎn)時(shí)空的人的思想,這主要產(chǎn)生于一種信念——他們有著一致的目標(biāo),他的詮釋將幫助人們理解一個(gè)偉大作家的思想在當(dāng)代語(yǔ)境下的深刻意義。
表面上看來(lái),作為學(xué)界著名的學(xué)者,身為普林斯頓、斯坦福兩所名校榮休教授的約瑟夫·弗蘭克似乎不過(guò)做了一個(gè)研究俄羅斯文學(xué)的大學(xué)教授應(yīng)該做的事情,只不過(guò)他做得更突出、“學(xué)術(shù)成果”更多,獲得的大獎(jiǎng)名頭更大罷了。然而只要是認(rèn)真讀過(guò)一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讀者,就會(huì)發(fā)現(xiàn)這部著作已經(jīng)不止于作家研究,甚至不止于文學(xué)研究。這不僅因?yàn)樗捏w量(中文版僅第五卷就厚達(dá)1128頁(yè))——看似龐然大物實(shí)則空洞貧乏的“學(xué)術(shù)著作”比比皆是——它簡(jiǎn)直就是一部清晰的十九世紀(jì)俄羅斯社會(huì)思想發(fā)展史,作者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和創(chuàng)作完全融入了這個(gè)大背景,這就使得《罪與罰》《群魔》《卡拉馬佐夫兄弟》等著作的故事、情節(jié)和主人公有了一個(gè)很大的“景深”。這非常有利于幫助讀者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藝術(shù)形象。
陀氏的小說(shuō)是一種“思想之書”,居于其核心的是人的思想意識(shí)。這意味著對(duì)個(gè)體的人的自由意志的珍視。正是基于這種意義,陀氏的文學(xué)才如巴赫金所說(shuō)是“對(duì)話”的,而不是“獨(dú)白”的,因?yàn)楠?dú)白小說(shuō)哪怕寫了一萬(wàn)個(gè)出場(chǎng)人物,他們都被禁錮在某種整齊劃一的思想意識(shí)中。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都有自己獨(dú)立的“聲音”。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shuō)對(duì)于未經(jīng)訓(xùn)練的讀者來(lái)說(shuō)具有很大的難度,或許“多聲部性”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作者的聲音、主人公的聲音經(jīng)常被混為一談,叛逆主人公的“聲音”也經(jīng)常被當(dāng)作荒腔走板;即便對(duì)于專業(yè)研究者來(lái)說(shuō),對(duì)于陀氏作品中思想意識(shí)的認(rèn)識(shí)也存在著很多分歧。而當(dāng)我們?cè)谝粋€(gè)恢宏的思想史背景下來(lái)考察的時(shí)候,就意味著我們也有可能參與到這場(chǎng)思想對(duì)話中去。
如果用一句最簡(jiǎn)單的話來(lái)概括,這場(chǎng)思想對(duì)話的核心就是在貧困時(shí)代(筆者借用海德格爾語(yǔ))人們?yōu)槭裁纯赡埽约坝檬裁磳?duì)抗虛無(wú)。這也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給予全人類的贈(zèng)禮,盡管這是一份提前了很多年的禮物。在閱讀前四卷的過(guò)程中,筆者一直在猜想,弗蘭克將會(huì)在何處收筆。第五卷名為《先知的責(zé)任》(The Mantle of the Prophet,中文版譯名調(diào)整為《文學(xué)的巔峰》),結(jié)尾的情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盛大的葬禮。作者用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在為圣彼得堡大學(xué)和別斯圖熱夫女子高等教育課程的講座上的一句話結(jié)尾:“他比任何人都更準(zhǔn)確地理解人類的精神理想,比任何人都更自覺(jué)地為實(shí)現(xiàn)這些理想而奮斗,他還通過(guò)布道比任何人都更有力地影響他人。當(dāng)代俄羅斯民族的這個(gè)精神領(lǐng)袖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維約夫的這段話盡管是在當(dāng)時(shí)的“俄羅斯使命”語(yǔ)境下說(shuō)的,有一定的針對(duì)性,但是仍然指出了陀氏之于“全人類未來(lái)”的啟示意義。這種啟示在于對(duì)代表歷史理性的“歐幾里得世界”的揭示,特別是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宗教大法官”的傳說(shuō)不啻于對(duì)下一個(gè)世紀(jì)人類災(zāi)難的預(yù)言,并且成為當(dāng)代反烏托邦/敵托邦文學(xué)的濫觴。但是這個(gè)故事真正的意義蘊(yùn)含在佐西馬長(zhǎng)老的回應(yīng)中。弗蘭克在書中用了近200頁(yè)的篇幅(還不算前面的準(zhǔn)備部分)對(duì)《卡拉馬佐夫兄弟》進(jìn)行了詳細(xì)解讀,尤其是“宗教大法官”的部分。
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畢竟是個(gè)非常復(fù)雜的作家。他的寫作有時(shí)候令人想起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shuō)”:為所有人而又不為任何人。這種筆法勢(shì)必導(dǎo)致大量的誤解甚至攻擊。此外,他的某些言論也并非無(wú)可指摘,例如他涉及猶太人的文字。面對(duì)這樣一個(gè)人物,弗蘭克的寫作態(tài)度是明智的,他沒(méi)有以陀學(xué)專家自居,而是仿佛一個(gè)細(xì)心的、富有好奇心的讀者,展開(kāi)了一種理解式的閱讀,在容易引發(fā)歧義、匆匆下結(jié)論的地方,尤其謹(jǐn)慎而仔細(xì)地展開(kāi)考察。
和前四卷一樣,弗蘭克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與社會(huì)思潮交織在一起展現(xiàn)。在這一卷中我們看到這一時(shí)期,俄國(guó)民粹派運(yùn)動(dòng)如何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定程度上進(jìn)行了和解,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用小說(shuō)創(chuàng)作對(duì)其進(jìn)行回應(yīng)。其中民粹派運(yùn)動(dòng)核心人物米哈伊洛夫斯基在關(guān)于俄羅斯民族的“根基”這個(gè)問(wèn)題上與陀氏部分地達(dá)成了一致。社會(huì)運(yùn)動(dòng)領(lǐng)袖們不再將陀思妥耶夫斯基當(dāng)作“反動(dòng)勢(shì)力”的代表,相反,他作為民族精神代言人的地位越來(lái)越清晰可見(jiàn),直到1880年春天他在普希金紀(jì)念活動(dòng)上的演講使其聲譽(yù)達(dá)到了頂峰。同時(shí),弗蘭克也給我們展現(xiàn)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民粹派截然不同的立場(chǎng),他將陀氏在民粹派雜志《祖國(guó)紀(jì)事》上發(fā)表的《少年》稱作“特洛伊木馬”,揭示了民粹派思想中的漏洞。在這一卷中,弗蘭克也有意識(shí)地將《作家日記》卷入了這種交織當(dāng)中。《作家日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個(gè)人的雜志,發(fā)表他自己的小品、政論文,也有精妙的短篇小說(shuō)(例如《永恒的女性》),可以看作是世界作家中最早的“自媒體”之一。弗蘭克沒(méi)有集中論述《作家日記》的史略,而是指出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民眾之間的一個(gè)非常重要的思想紐帶,《作家日記》最后一期(1881年1月號(hào))在他寫作生涯的最后一天完成,又在他下葬的當(dāng)天出版,人們?nèi)滩蛔⑦@種巧合視為某種“啟示”的意義,但弗蘭克提示道:我們應(yīng)當(dāng)念念不忘,他的文學(xué)成就遠(yuǎn)遠(yuǎn)超過(guò)了他的社會(huì)—政治幻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許是世界文學(xué)史上最難理解的作家之一,弗蘭克這種“掰開(kāi)揉碎”、娓娓道來(lái)的解讀,對(duì)普通讀者、專業(yè)研究者來(lái)說(shuō)都有極大的幫助,他這種娓娓道來(lái)建立在對(duì)原著文本(弗蘭克研究的底本為蘇聯(lián)科學(xué)院三十卷俄文本)和大量重要的俄、英文參考文獻(xiàn)的消化、吸收上。中文五卷本的出齊,將對(duì)國(guó)內(nèi)“陀學(xué)”研究大有裨益。
(作者:張曉東,系北京師范大學(xué)俄羅斯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