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男孩:種族問題和美國歷史
1900年,一座名為“亞瑟·G.多齊爾男子學(xué)校”的教養(yǎng)院建立,該校也是美國佛羅里達(dá)州的第一座少管所。多年后,一支大學(xué)考古隊意外地發(fā)現(xiàn)了這所學(xué)校的一處墓地,才將此地掩蓋了一個多世紀(jì)的罪惡公布于眾,該校因此于2011年正式被查封。作家科爾森·懷特黑德看到相關(guān)報道后,以此事件為原型,寫出了《黑男孩》一書。圖書出版后,熱度不減,并于2020年斬獲“普利策小說獎”。
據(jù)當(dāng)時的新聞報道,在亞瑟·G.多齊爾男子學(xué)校的校園內(nèi)挖掘出許多具非裔美國人的尸骸,且有證據(jù)表明,遇害者死于謀殺,并有明顯的受虐痕跡。《黑男孩》以此為切入點(diǎn),故事情節(jié)展開于一個名為“尼克爾”的學(xué)校里的一片“隱秘墓地”。無疑,尼克爾的原型就是亞瑟·G.多齊爾男子學(xué)校,懷特黑德雖然也創(chuàng)作過非虛構(gòu)作品,但這一次,他創(chuàng)作的是一部小說,需要動用“虛構(gòu)”的力量。
為了寫好這部小說,懷特黑德對此事件展開了深入的調(diào)查,他后來告訴記者:“我越是深入此書的創(chuàng)作,就越感到壓抑和憤怒,恨不得拿著汽油和火把沖到那個地方去。”想必讀者在接觸這類題材時,首先激起的肯定也是憤怒和壓抑。但作者在小說中顯然沒有囿于這些。除去這些,怎樣引起讀者的反思,并將它以小說的虛構(gòu)性體現(xiàn)出來,才是寫作的關(guān)鍵。

普利策小說獎得主科爾森·懷特黑德
小說的虛構(gòu)性遠(yuǎn)非更換了學(xué)校的名字這么簡單。《黑男孩》的英文原名為“Nickel Boys”。“Nickel”一詞一語雙關(guān):其一,指的是小說中那所學(xué)校的名字;其二,Nickel原意是“五分鎳幣”,小說點(diǎn)明了其用意:“這里的男孩之前總說這里之所以叫這個名字,是因為他們的命連五分錢都不值”。作者突出的是來到這所學(xué)校的男孩的命運(yùn)之卑賤。除去“尼克爾”一詞之外,更值得關(guān)注的“男孩”(Boys)在原文中是復(fù)數(shù)。
小說的時代背景設(shè)定在“吉姆·克勞法”被廢除的年代。吉姆·克勞具體指涉何人,在美國歷史上眾說紛紜,其中一種說法認(rèn)為,所謂的“吉姆·克勞”是一個名叫賴斯的白人在舞臺上扮演的南方黑人角色。這個白人故意將自己的臉抹黑,學(xué)著黑人的姿態(tài)跳舞,一時間成了美國街頭巷尾喜聞樂見的娛樂節(jié)目,久而久之,“吉姆·克勞”就成了黑人的代名詞,更成了黑人文化的符號。后來美國政府通過了各種針對黑人的種族隔離法案,這些法案被統(tǒng)稱為“吉姆·克勞法”。甚至在特定的時候,“吉姆·克勞”就是“種族隔離”的代名詞。直到20世紀(jì)60年代,伴隨著民權(quán)運(yùn)動的展開,“吉姆·克勞法”才得以廢除。懷特黑德將小說設(shè)置在歧視性法案被廢除的年代,真正想要觸及的還是他一貫關(guān)心的主題:種族問題和美國歷史。換言之,復(fù)數(shù)的男孩都是一個人:“吉姆·克勞”,他們都是生活在特定歷史時期的一類人。
此外,小說開始于一場意外的考古發(fā)現(xiàn),雖然如前文所說,這一設(shè)定有具體的真實事件為依托,但作為小說的場景,也可視為帶有明顯隱喻性的一個“原初場景”。考古挖掘的不是稀世珍寶,也不是輝煌的過去,而是一段被掩蓋的屈辱史。對于所有死者來說,他們或許連生前的名字都無法保留,只有一個復(fù)數(shù)的稱呼:尼克爾男孩。非裔美國人生前是“吉姆·克勞”,死后是一個集體性的稱呼,他們被代表,被掩埋,消失在歷史中。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懷特黑德也在進(jìn)行一場考古活動,他要將小說嵌入歷史和現(xiàn)實之中,賦予死者以姓名的尊嚴(yán),并給予屈辱的“吉姆·克勞”以血肉的正義,進(jìn)而迸發(fā)出更深層的真實,就如同他的偶像加西亞·馬爾克斯一樣。
值得指出的是,“吉姆·克勞法”被廢除的年代也是黑人在紐約哈萊姆區(qū)進(jìn)行文學(xué)藝術(shù)復(fù)興的年代。著名黑人詩人蘭斯頓·休斯在《哈萊姆》這首詩中曾寫過這樣的詩句:“延時實現(xiàn)之夢會變得怎樣?是否會如暴曬下的葡萄般變得干枯?”盡管隨著民權(quán)運(yùn)動的興起,黑人能在文學(xué)藝術(shù)上發(fā)聲,但他們自己的歷史和屈辱,依舊如同烈日下的葡萄那樣,因為被遺忘而脫水、縮小,即便無法被徹底去除,也會漸漸成為一個隱沒的黑點(diǎn)。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科爾森·懷特黑德是在通過小說,不斷給這顆脫水的葡萄注入水分:打破“吉姆·克勞”的符號性,并喚醒被人遺忘的死者。
主人公埃爾伍德的家庭本身就是一個需要進(jìn)行挖掘的“考古現(xiàn)場”,他的父母、外祖父等家庭成員的經(jīng)歷本身就是美國歷史的沉淀。作者通過寥寥數(shù)語,勾起黑人持續(xù)在美國遭受歧視的過往。埃爾伍德因一個偶然的機(jī)會,獲得了一份禮物——馬丁·路德·金的演講唱片,從而成了有望打破家族命運(yùn)的人。絕非巧合的是,作者在賦予改變埃爾伍德擺脫命運(yùn)之偶然的同時,也給了他墮入厄運(yùn)的突然:埃爾伍德僅僅因為搭車而被認(rèn)為是偷車賊,從而進(jìn)入了尼克爾教養(yǎng)院。偶然得到的幸運(yùn),突如其來的荒誕,這兩點(diǎn)使埃爾伍德身上最顯著的特質(zhì)——堅定——得以放大,這不僅僅構(gòu)成了這部小說的敘事內(nèi)驅(qū)力,也成了人物身上最具個性的特質(zhì)。只不過,這種特質(zhì)如果被無限放大,整部小說就會顯得僵硬,人物就會顯得單一,似乎有以一種符號打破另一種符號之虞。但小說的另一個主人公特納的出現(xiàn)無疑化解了這一潛在的缺陷。與埃爾伍德相比,特納世俗、隱忍,甚至有些得過且過的意味,他不僅能在噩夢般的教養(yǎng)院里擁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并無數(shù)次地躲過可能的處罰,還時不時地給埃爾伍德的認(rèn)真和堅定潑冷水。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一點(diǎn)恰恰也拯救了埃爾伍德。兩個人在尼克爾結(jié)識、互相了解的過程,也代表著黑人群體中對待暴行的兩種態(tài)度逐漸融合的過程,這不僅讓讀者可以在這兩個人身上安插自己的視角,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沉痛的故事背景帶來的壓抑感,也讓小說的情節(jié)顯得跌宕起伏,展現(xiàn)出了科爾森·懷特黑德的小說創(chuàng)作才華。
此外,更值得指出的是,這兩個人最后的“結(jié)合”更具有小說主題上的升華。懷特黑德并非想鼓吹要從尼克爾逃出來,需要堅定的勇氣和善于周旋的頭腦的結(jié)合,而是想要突出一種“轉(zhuǎn)變”。埃爾伍德的堅定使得他擺脫了家庭的命運(yùn),也逃離了尼克爾的厄運(yùn),換言之,讓他避免成為另一個“吉姆·克勞”。而他在“特納”身上的“復(fù)活”,不僅讓特納繼承了他的堅定(這對特納來說是最大的改變,細(xì)心的讀者可以對比小說最后幾章作者語言風(fēng)格的改變),而且讓自己不至于最終成為一名死者,遁入被遺忘的角落。這種轉(zhuǎn)變借由小說寫作特有的人稱轉(zhuǎn)變來完成,無疑是小說中最為高光的一筆,在主題和形式上進(jìn)一步凸顯了懷特黑德用文學(xué)關(guān)懷現(xiàn)實的情懷。
懷特黑德曾在采訪中對《時代周刊》的記者說,他希望通過寫作這部小說,喚起最廣泛的人群對種族問題的關(guān)注。他說:“政客們迎合人們最基本的偏見……因為利用人們的恐懼以及人們身上非理性的弱點(diǎn),比做一些對人們有利的事更有力量。當(dāng)那些詭計多端的人想方設(shè)法地劃分他們的州,以剝奪有色人種的選票時;想方設(shè)法地關(guān)閉某些投票站,使人們很難抽出時間去登記或投票時,我們也在一起……”
由此可見,復(fù)數(shù)的“男孩”既指一個人身上的他們,也指他們身上的一個人;既指生者存有死者未盡的使命,也指死者蘊(yùn)含生者改變未來的秘密;既指你,也指他,更指我們。
本文為《地下鐵道》作者科爾森·懷特黑德新作《黑男孩》的譯后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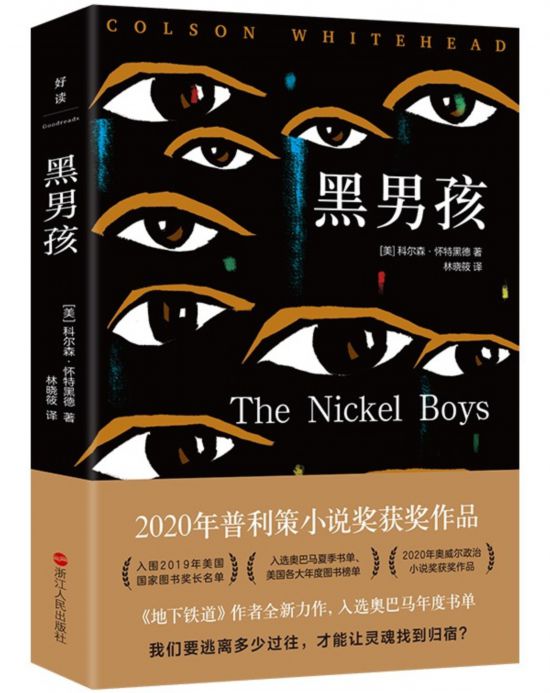
《黑男孩》,【美】科爾森·懷特黑德/著 林曉筱/譯,浙江人民出版社·好讀文化,2022年7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