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松導(dǎo)讀《蠅王》:文學(xué)為我們當下的生存,提供了一種注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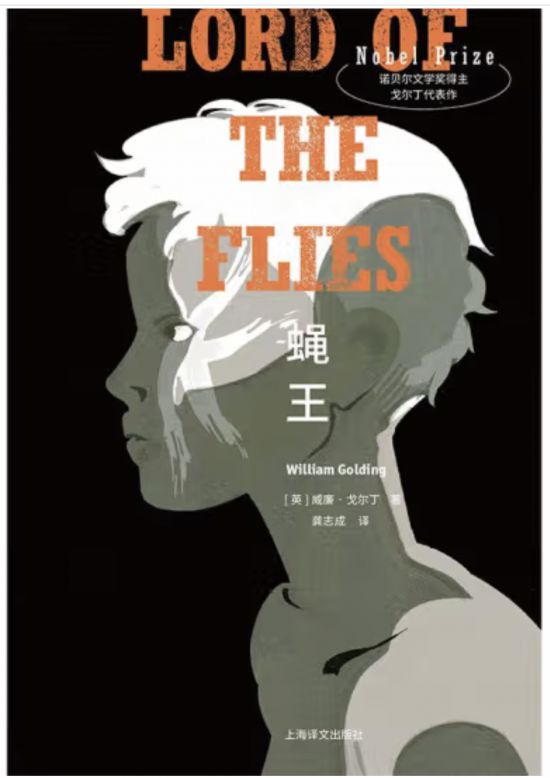
去年是威廉·戈爾丁誕生一百一十周年。上海譯文出版社今年再版《蠅王》這個書。編輯讓我寫導(dǎo)讀。我不敢寫。怎么可以為這樣一本獲諾貝爾文學(xué)獎的書寫導(dǎo)讀呢?這是純文學(xué)作家、主流文藝批評家,或者哲學(xué)家和社會學(xué)家要做的事情。我只是一個科幻小說作者。我想最多叫讀后感,而且只是科幻的讀后感。當然也有人把《蠅王》這個書,歸于大概念的科幻范疇,因為它描寫了核戰(zhàn)爭,可能整個世界都毀滅了,然后剩下一個只有孩子的孤島。他們在這個島上重新搭建文明,頗有技術(shù)性,但也同時構(gòu)筑野蠻,讓我想到一些以原始社會為題材的科幻。《蠅王》寫的是一個假設(shè)性的未來,也可以是一種反烏托邦、敵托邦的類型。但是它是真實的,讀后覺得是確實發(fā)生了的。有幾個意象讓我難以釋懷。
一是孩子,或者未成年人。小說描寫了一個由孩子組成的世界。書中主角都是孩子。他們逃至荒島,形成新的集體,又大致分成兩個派別,形成對峙和攻防,有點像我們小的時候打群架那樣。應(yīng)該說,孩子代表的是未來,同時也代表過去。因為他們沒有接受完整的文化教育。從生物演化來看,從受精卵到嬰兒,反映了幾十億年間整個生物演化過程,比如最開始像魚,最后才有人形。在卡爾·薩根那里,人類行為受到爬蟲復(fù)合體、哺乳動物腦和新皮質(zhì)的支配。其中爬蟲復(fù)合體是最古老的,新皮質(zhì)是人類進入文明黎明期后才漸漸出現(xiàn)的。那么這三者在合作又斗爭。爬蟲復(fù)合體就是人類的幼年。人性中我們稱作邪惡的,或者說獸的那部分,在小說中,反映為野獸,或者豬頭上的蒼蠅,便是這個東西。這也是暗喻人類社會,還沒能真正走出童年。因此島上的各種殺伐顯得是那么自然。
其實也有很多書和電影是以此為內(nèi)容的,像阿瑟·克拉克寫了《童年的終結(jié)》。而在《大逃殺》里,孩子為了生存而互相殺伐。最近那個《魷魚游戲》也是如此。其他的還有盧基揚年科的《四十島騎士》、劉慈欣的《超新星紀元》以及卡德的《安德的游戲》,也都充滿類似的“小將式”殘酷。所以這是戈爾丁對于文明的理解。我們的本能沖動,我們野蠻的一面,始終在對抗著文明的部分,這可能是一種危險,但也或許就是人類演化的動力。孩子們在競爭中,最后還是生存了下來,雙方都磨煉出了本事。在這個過程中小將們完成了對異己者的清除。整個《蠅王》讀下來,更像是一場游戲。人離不開游戲,但沉湎在里面是令人恐懼的。現(xiàn)在很多孩子學(xué)編程,老師講,二十年后五種孩子將不會被淘汰,一是對事物有好奇心的孩子,二是有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能力的孩子,三是懂得管理情緒的孩子,四是擁有延遲滿足能力的孩子,五是學(xué)習(xí)能力強的孩子。但在《蠅王》中,我看到,不會被淘汰的,是能斗狠的孩子,是能威脅對方生命的孩子。
《蠅王》告訴我們,對于一些民族而言,暴力和仇恨貫穿了歷史和未來。人類在無休止爭斗。這是恒定不變的主題。但唯其如此,愛才不會消失。因為我們太愛自己了,我們太自私了。這是由基因決定的。為了愛自己,才必須愛他人,或者裝出來愛他人。這使得未來仍然是不明朗的,繁麗外表下有著毀滅的光影。但為了活下去,抗爭也是一個主題。人要從噩夢中掙逃出來。實在不行還可以選擇自殺。但《蠅王》里沒有人自殺。他們可能選擇了妥協(xié),或者寄望于成人的解救。最后坐軍艦來到島上的成人好像上帝那樣的救世主。但如羅伯茨所言,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實是幾位自居為超人的政客所造成的生靈涂炭之變局,而戰(zhàn)爭的結(jié)束又催生了新的獨裁者。救世主對人類的危害,既是戰(zhàn)爭等政治動亂,也是如上帝般用精神和知識束縛人類。救世主的沖動與法西斯的行徑何其接近。只有用意志逃離或使自己死亡,才能打破這一僵局。
二是核武,或上帝之火。《蠅王》講的是原子戰(zhàn)爭的背景。馮·丹尼肯在他的書中指稱《圣經(jīng)》中所多瑪和蛾摩拉的毀滅,是緣于外星來的核火。那么蒼蠅王這個魔頭,在我看來便是核武的象征。它喻意人類發(fā)掘出了物質(zhì)中的超級力量,要扮演上帝的角色。《蠅王》是戈爾丁在二戰(zhàn)之后寫的。作者本人參與了戰(zhàn)爭。我認為他寫的是人類世的問題。
什么是人類世?在地質(zhì)學(xué)上,依據(jù)所對應(yīng)地層的生命特征將地球四十六億年的歷史分成了前后兩個部分:前面是沒有明顯生命跡象的隱生宙,后面是有了明顯生命痕跡的顯生宙。顯生宙又根據(jù)動植物形態(tài)的重大變化劃分出三個代,分別是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人類生活的地質(zhì)時期是顯生宙新生代第四紀的全新世。但諾貝爾化學(xué)獎得主保羅·克魯岑認為,如今人類已不再處于全新世,而是進入一個叫做人類世的新時期。這個時期的特征是人類操控了地球演化的進程。人類世可能是由十八世紀末人類活動對氣候及生態(tài)系統(tǒng)造成全球性影響開始的。這個時間節(jié)點正與戈爾丁的同鄉(xiāng)詹姆斯·瓦特在一七八二年改良蒸汽機的時機吻合。而二〇一九年科學(xué)家在澳大利亞進行科考期間,在坎貝爾島取樣,發(fā)現(xiàn)一棵北美云杉上面記錄了數(shù)次原子彈試驗產(chǎn)生的放射性碳,其放射性元素峰值出現(xiàn)在一九六五年十月至十二月之間。由此又把人類世開始的時間確定為一九六五年。
這是一個劇變時期。人類創(chuàng)造出比歷史上所有時期加在一起還要多得多的物質(zhì)財富。我們開始登陸月球和地外行星,走出太陽系。我們發(fā)動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并掀起地球第六次生物大滅絕的浪潮。短短一百年不到人類第一次擁有了可以自我毀滅以及毀滅整個地球的手段,包括核武器、納米技術(shù)和生物科技。它們建立在二十世紀相對論和量子論的創(chuàng)建以及DNA雙螺旋結(jié)構(gòu)的發(fā)現(xiàn)上。這構(gòu)成現(xiàn)代文明的基礎(chǔ),也把人類帶向后人類。人類開始再造自身及地球。《蠅王》中孩子們在島上的行為,他們使用火,搭建房屋,獵殺動物,獵殺人類,反映的都是這個。他們釋放了能力,也釋放了惡魔,正走向自我毀滅。正如澳大利亞國立大學(xué)微生物學(xué)教授、人類消滅天花病毒的功臣弗蘭克·芬納所稱,人類可能在一百年內(nèi)滅絕,人類世將終結(jié)。《蠅王》描寫了自有生命以來這顆星球上出現(xiàn)的最大恐懼。如何面對并戰(zhàn)勝這種恐懼,是這本書發(fā)出的警示。
三是自然,或者存在。盡管是人類當?shù)溃匀唤缫廊活B固地存在著,它體現(xiàn)在那個外在于我們的巨大物體上面。我以前忽略了《蠅王》中對大自然的描寫,再讀時才深深為它震撼,不禁想到核戰(zhàn)爭的另一面——亦即或許只有用核戰(zhàn)爭,才能消滅掉人類這只叮在腐肉上的蒼蠅,讓地球恢復(fù)到從前的自然狀況。戈爾丁對自然的描寫真是精彩絕倫,比如:“正午發(fā)生了各種稀奇古怪的事情。閃閃發(fā)亮的海面上升著,往兩邊分開,顯出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許多平面;珊瑚礁和幾株緊貼在礁石較高處的矮棕櫚樹像是要飄上天去,顫動著,被撕開來,像雨珠兒在電線上滾動,又像在排列古怪的許多面鏡子中被折射。有時候,在原先沒有陸地的地方隱約出現(xiàn)了陸地,而當孩子們聚精會神地注目時,陸地又像個氣泡似的一晃就不見了……中午,各種幻影融進天空;在那上面,驕陽如怒目俯視著。然后,到傍晚時分,蜃景消退下去,海平面又回復(fù)了水平方向,又變成藍藍的,夕陽西下時,海平面輪廓清晰。那是一天中又一個比較涼快的時候,但嚇人的黑夜也就要來臨了。夕陽西沉以后,黑夜君臨島上,好像把一切都撲滅了;群星遙遠,星光下的茅屋里傳出了一陣陣騷動聲。”這樣的描寫在《蠅王》中比比皆是。這不能簡單歸于英國小說的傳統(tǒng),而更有著作者的沉思。
我們生存在一個難以理解的自然體中。我們是神秘宇宙的一分子,由地球這個孤島載著在茫茫大海中航行。這究竟是有目的的,還是沒有目的,而僅僅是偶然的?讀罷《蠅王》會產(chǎn)生這樣的迷惘之問。作為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將,我們怎么面對這個奇異的世界?我們怎樣才能做到不被拋棄、不自我毀滅,也不被宇宙中更強大的力量毀滅?我們是否要減少一些狂傲自負,而養(yǎng)成敬畏心和謙虛心?這樣的主題,在從瑪麗·雪萊到威爾斯那里也好,在從克拉克到巴拉德那里也好,都有體現(xiàn)。英國不僅是科幻小說的發(fā)祥地,還是科學(xué)革命、工業(yè)革命的發(fā)源地。在這塊土地上產(chǎn)生了牛頓、達爾文和霍金。因此《蠅王》這本書也是在叩問我們的存在。在編程學(xué)習(xí)中,老師會告訴孩子:“創(chuàng)作作品并不難,首先你得定角色,先看角色有幾個,再看角色是什么。想想他們干什么,最后再定怎么做。”因此我們要把握好怎么去創(chuàng)造角色。我們不僅是游戲的創(chuàng)造者,同時也是這場游戲中的角色。我們走的每一步都關(guān)系著我們在宇宙中的存亡。讀罷《蠅王》這部小說,我更愿意去仰望浩瀚的星空并思考內(nèi)心的道德了。
這是我的三點感觸。它們是以非常文學(xué)的方式從我內(nèi)心中自然滋生的。因此我覺得在這個科技成了第一現(xiàn)實的時代,在這個物質(zhì)為王的時代,文學(xué)藝術(shù)的意義是不會殞滅的。它是對抗吃人蒼蠅的武器。文學(xué)是什么時候產(chǎn)生的已不可知。我覺得文學(xué)跟生存是有關(guān)的。估計在更早的時候,文學(xué)便發(fā)生在成年猿人在山洞里給孩子講故事的時候,而這跟用火的發(fā)明有關(guān)。沒發(fā)明用火之前沒有這樣的環(huán)境。原始社會人類壽命十幾二十歲,但他們已經(jīng)懂得通過講故事把經(jīng)驗傳遞下去。到后來就產(chǎn)生了喬叟、莎士比亞、蕭伯納和狄更斯。《蠅王》的文學(xué)性是很強的。它把故事用絕妙的意象表現(xiàn)出來。小說的描寫和敘事足夠精致,包括孩子們五彩繽紛的行為,還有那些猶如夢境的對話,反反復(fù)復(fù)像在不停循環(huán),還有野獸、島嶼和大海的意象。《蠅王》也表明,文學(xué)要關(guān)注當代的重大問題。在破碎化的時代,要有統(tǒng)合性的關(guān)注。像最近戈爾丁的同鄉(xiāng)伊恩·麥克尤恩寫的《我這樣的機器》和石黑一雄寫的《克拉拉與太陽》,都是這樣的。文學(xué)為我們當下的生存,提供了很好的一種注釋。《蠅王》使得我對劇變時代的文學(xué)懷有信心和期待。
韓 松
2022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