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張祥龍:哲人遠(yuǎn)行
2022年6月8日晚上10點50分,張祥龍先生因病逝世,享年73歲。張祥龍先生是我國當(dāng)代著名哲學(xué)家,以現(xiàn)象學(xué)、儒家哲學(xué)和東西比較哲學(xué)研究聞名于世,他對中國文明懷有極其深厚的感情,對中華文化復(fù)興具有強(qiáng)烈的歷史責(zé)任感,其著述文章對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批評亦多有啟迪。
張祥龍先生治學(xué)嚴(yán)謹(jǐn),學(xué)貫中西,會通古今,在東西方哲學(xué)比較、現(xiàn)象學(xué)和儒家哲學(xué)等領(lǐng)域造詣深厚,成就斐然,他的學(xué)術(shù)思想氣象恢弘,自成一家。在現(xiàn)象學(xué)研究方面,張祥龍先生以海德格爾哲學(xué)為起點,融入中國傳統(tǒng)體道方法,別開生面,推動了海德格爾哲學(xué)與中國思想的結(jié)緣,促進(jìn)了海德格爾的中國化。他對現(xiàn)象學(xué)的研究極富新見,在漢語學(xué)界乃至國際現(xiàn)象學(xué)界都卓然自立。長年來張祥龍先生在比較哲學(xué)研究領(lǐng)域進(jìn)行了卓越的探索,為深化哲學(xué)的理解和各文明哲學(xué)之間的對話,帶來了諸多啟發(fā),開創(chuàng)了包括印度哲學(xué)在內(nèi)的東西方哲學(xué)比較的新思路。張祥龍先生積極探索中國哲學(xué)研究的新范式。他早先以現(xiàn)象學(xué)方法研究先秦諸子,后逐漸轉(zhuǎn)向并集中于儒家哲學(xué)研究,旁參印度古學(xué),參酌現(xiàn)代西方哲學(xué),體大思深,發(fā)人未發(fā),成為儒學(xué)思想當(dāng)代建構(gòu)的重要代表人物。
《中西印哲學(xué)導(dǎo)論》(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22年5月)一書是張祥龍先生最后出版的著述之一,該書源于張祥龍先生在北大同名課程的講稿,是一本帶有普及性的哲學(xué)導(dǎo)論,在比照和互文中呈現(xiàn)不同文明的哲學(xué)特質(zhì)。經(jīng)出版方授權(quán),中國作家網(wǎng)特遴選其中《先秦真知觀》一章部分文字發(fā)布,謹(jǐn)表紀(jì)念。
——編者按

張祥龍先生(1949.08.14-2022.06.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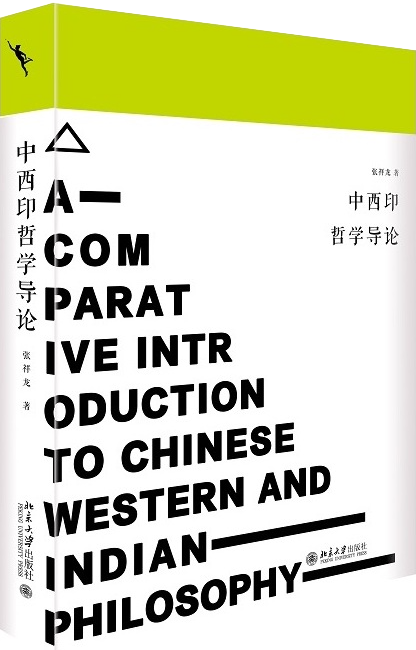
《中西印哲學(xué)導(dǎo)論》,張祥龍 著,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22年5月
設(shè)想一下,如果持另一種終極實在觀,即不同于西方傳統(tǒng)哲學(xué)的核心觀點(主張終極實在是不變的存在本身),而是認(rèn)為終極實在是處在變易之中的,那么整個知識論的格局會有什么改變呢?當(dāng)然會有巨大的轉(zhuǎn)變!而我們以前也看到了,這正是中國古代哲學(xué)的主流觀點。如果終極實在處于變易之中,那么主客之間的所謂異質(zhì)性就不那么硬性了。正因為整個存在的根基處是正在變化著的,于是就可以設(shè)想,所謂主體和客體是這存在的不同變體,它們正在參與同一個生成過程(比如陰陽大化過程),因而可以達(dá)到相互融合,或者說它們只是一個既行且知的過程的不同表現(xiàn)而已。這恰恰就是中國古人對真知識的看法。
所以這個主客異質(zhì)導(dǎo)致的無公度性問題,在中國古代很不突出,因為終極實在本身就是一個發(fā)生的和相互理解的過程。我們可以先看一個例子。《莊子·秋水》(《資料》,第213頁左)講了一個寓言(這本書里充滿了寓言),它是這么說的:“莊子與惠子[惠施]游于濠梁之上”,濠就是濠水,在今天安徽鳳陽縣附近,梁就是橋。他們兩位,即莊子跟惠施,是好朋友、諍友,碰到就一直辯論。這二人站在橋上,莊子看見水里有魚兒在游,就說:“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你看這魚在水里游得多么快樂呀!惠施馬上反駁:“子非魚,安知魚之樂?”你又不是魚,你怎么知道魚是快樂的?“你怎么知道[‘安知’]……?”這就是認(rèn)知的問題,而惠施特別強(qiáng)調(diào)主體跟客體的異質(zhì)性對認(rèn)知的阻障作用。莊子說:“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魚的快樂?以彼之矛反過來攻擊他。惠施馬上反駁:“我非子,固不知子矣”,我不是你,當(dāng)然我就不能知道你;但是“子固非魚也”,也就是:有一點我是不會搞錯的,即你肯定不是魚;“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因此,你不知道魚之樂是毫無疑問的了。這里惠施的論辯好像占了上風(fēng),邏輯上更進(jìn)了一層。看莊子怎么說,他現(xiàn)在已經(jīng)被逼到絕境了。“莊子曰:請循其本。”讓我們回到原本處吧。你向我發(fā)問道:“‘汝安知魚樂’云者”,你問我“你是怎么知道魚是快樂的?”等,那么就表明,你“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你本來就已經(jīng)知道我知道魚之樂了,只是在問我是怎么知道的(這里好像有點兒詭辯,但其中的道理見后邊分析)。那么我就告訴你,“我知之濠上也”,我站在這濠水橋上就知道水中魚是快樂的了。
這里莊子論辯的要點在哪里呢?就在這“請循其本”,即讓我們追蹤到我們辯論的根本處。那什么是此辯論的根本處呢?當(dāng)然是思想語言的交替使用和相互理解。你問我怎么知道魚之樂的,我回答;你懂了我的回答,于是再問;我懂了你的問題,于是再答。你既然能問我,我也能答你,說明我們有一種非常根本的語言上的和意義上的交流,也就是某種相互認(rèn)知。你以為:我不是你(我非子),你也不是我(子非我),我們就相互“不知子”或不知曉對方的意愿或意思了嗎?不是的呀!在某種意義上我是你的客體,你也是我的客體,我是主體,你也是個主體,但是我們居然可以通過語言乃至其他途徑(比如表情和手勢)而發(fā)生有效暢快的交流和相互理解。那么,即便我不是魚,魚也不是我,你怎么能斷定我和魚之間沒有一種根本的、在主客分離之前的交流呢?我與你可溝通,那么我也可以在這橋上與水中的魚兒溝通啊!這是莊子更深的含義和論證。表面上莊子是在抓話語間的“你怎么知道”這個話頭,但是里邊有深意。也就是說在主體與客體、主體與主體分離之前,我們已經(jīng)處在了某種相互糾纏、交融的狀態(tài)中,所以我們才能夠進(jìn)行語言和意義的交流。那誰能斷定在我們跟魚之間、我們跟萬物之間沒有一種根本的糾纏和交流呢?這是一個反映中國古代認(rèn)知觀特點的很犀利的論辯例子。于對話當(dāng)場層層深入,絲絲入扣,首尾回蕩,頗有些禪宗對話的味道,只是理路更清晰細(xì)密。
所以,中國古代關(guān)于真知問題的關(guān)鍵不在于主客的靜態(tài)相符。也就是說,對于中國古哲人來講,認(rèn)識真理主要不是克服主客異質(zhì)而達(dá)到普遍必然性的問題,而是一些動態(tài)的問題。也就是要在有無相交纏的生成之處,來理解、對付、預(yù)知生成變化的結(jié)構(gòu)、趨向、節(jié)奏和樣式。
中國人確實很實際,一切哲理都源自實際生活經(jīng)驗,可是中國人的實際不是說不要理論,關(guān)鍵是其理論走向與西方不一樣。就此而言,中國古代認(rèn)識論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怎么突破“時障”。我們生活在現(xiàn)在,怎么突破現(xiàn)在與過去,尤其是現(xiàn)在與未來之間的那個屏障,讓我們的認(rèn)知和思想能夠穿透過去,尤其是能夠走向未來,預(yù)知事態(tài)發(fā)展,這才叫真知。中國古人最看重的恰恰是這種知識。
這種突破時障、朝向?qū)淼臅r幾(機(jī))化特點,在《周易》中表現(xiàn)得十分明顯,而無論是孫子、老子還是孔子,概莫能外。傳統(tǒng)西方這一面,我們已經(jīng)看到,那些知識形態(tài)、認(rèn)識論形態(tài)想找到的是普遍必然的規(guī)律,用它們來規(guī)范人生和世界。這種知識就不是預(yù)知活生生的未來,而是要制造未來。人為自然立法,科學(xué)改造了整個世界,把我們的未來全部重新塑造。中國古代的哲理不是這樣的。它認(rèn)為自然的變化、整個人生態(tài)勢的變化本身就有合理性,我們不但要跟著它走,還要知道它本身是怎么回事。這與西方的認(rèn)識論是大不一樣的。
在這樣的知識中,時幾(機(jī))、事態(tài)、記憶或者說是變化的樣式,比如往返等,都是最受關(guān)注的。時幾是時機(jī)之源,而“幾”恰恰是《周易》特別強(qiáng)調(diào)的。“知幾其神乎!”(《周易·系辭下》)認(rèn)知的要害和神髓就是要“知幾”。“幾”是“動之微,吉之先見[現(xiàn)]者也”(同上)。這里“吉”指預(yù)兆,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這個勢頭,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存在的勢態(tài),但是還沒有見諸明顯的形式,也就是還沒有被實現(xiàn)為可把握的存在者。有無正在交織著。“動之微”,指非常微妙的變動,但是這個“動”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一個趨向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很多人都看不到它,只有真智者,也就是中國古人認(rèn)為的那些得到了真知識的人,才能夠看到此“幾”。這是中國古代知識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即感知和追隨那朝向未來的趨向,具有很強(qiáng)的時間性、時幾(機(jī))性。但是為了朝向未來,就須特別重視過去,能夠回溯以前的、古代的事情,在一圈圈的回旋中獲得沖向未來的動勢,而且,只有找到這種回旋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你對歷史的回顧才能幫你知道未來。因為歷史有重復(fù)之處,但更有出新之處,必須領(lǐng)會了時幾的微妙結(jié)構(gòu),才能真正突破時障。
除了這突破時障、朝向?qū)淼臅r幾化特色,中國古代知識論的第二個特點,就是用勢。“勢”和“幾(機(jī))”基本上是相通的。“勢”往往是無形的。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山上的一個堰塞湖,或一塊大石頭處于懸崖邊上,它們就有一種向下之勢,但它還未被實現(xiàn)出來。如果你認(rèn)識到了,并善于運(yùn)用它,例如你有本事把敵人引到它下面,而你自己處于上面,再加上山道相當(dāng)狹窄而無法躲避的話,那幾乎就贏定了。或者說,時值冬日,但過幾天將有反常的東南風(fēng),誰要事先知道了,像《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那么現(xiàn)在還完全無形的風(fēng)勢到那天就會以時機(jī)化的方式實現(xiàn)出來,憑之而摧毀敵方幾十萬大軍,改變歷史走向。《孫子兵法》就是探討怎么能把自己放到那個優(yōu)勢位置,而把敵人放到那個劣勢位置,則我就能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一到那種情況,敵人只能投降,不然的話,巨大的石頭從上面滾落下來,人的求生本能就使之要躲開,也就相當(dāng)于投降了,于是當(dāng)即拿下。
所以我剛才問那個同學(xué):戰(zhàn)爭之術(shù)是不是有不戰(zhàn)而勝的境界?很多西方的戰(zhàn)略家,比如克勞塞維茲,就不承認(rèn)有這樣一個境界,認(rèn)為戰(zhàn)爭永遠(yuǎn)是打出來的。當(dāng)然,事先誰謀劃得好、安排得好,就可以創(chuàng)造得勝的機(jī)會,但是不戰(zhàn)而勝這個境界怎么可能呢?敵人來就是跟你打的,怎么會不打就投降呢?我看我國軍事科學(xué)院寫的《孫子兵法》評論,有的就認(rèn)為此境界無法理解,是《孫子兵法》中的神秘主義傾向。當(dāng)然也不是完全否認(rèn),但是從道理上無法理解。這里我們看到了中國古代認(rèn)知的一個重要特點,即通過“勢”來認(rèn)識真相,因為這真相處于變化之中。
其實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就生活在“勢”里邊。你想想你的24小時是怎么度過的?幾乎絕大多數(shù)的時候都不用反思,順勢而行。你們在聽我講話,我根本不會注意到我發(fā)音的時候這個喉頭是怎么震動的,話就講出來了;你們也不去分辨我語音中的音素,囫圇個兒地就明白了我的意思。走路,抬腿就走;騎自行車,蹬上乘勢就騎。勢態(tài)根本不用反思,如果你還要去思考、細(xì)察,說明出了問題,比如你的車的車胎沒氣了,或者車鏈子掉了,或者你的身體哪兒不舒服了,以至無法用勢。
第三個認(rèn)知特點就是技藝化。中國古代認(rèn)識論中更看重的是“技”和“藝”,而不是邏輯分析、形式推理和抽象理論的建構(gòu)。當(dāng)然也有理論,陰陽五行就是很高深的理論,某種意義上也很抽象,但它是活的,一定要體現(xiàn)在活生生的生發(fā)和維持的過程之中。所以孔子要以六藝來教學(xué)生,同樣可以想見,老子和莊子教學(xué)生,也是憑借技藝而活潑多姿的。你去看《莊子》,其中“庖丁解牛”“梓慶造”等,講的都是手藝人,通過精絕的手藝而得道,此外還有或顯或隱的氣功修煉的技藝。佛家則重打坐參禪。這是印度傳來的技藝,即瑜伽的變式。關(guān)于瑜伽,以后我們會專講。但是中國的禪宗對參禪的技藝加以變化,不一定非要坐禪了。坐禪修行當(dāng)然也可以,但只是開悟法門之一。嬉笑怒罵,搬柴擔(dān)水,機(jī)鋒對談,棒打刀削,只要能夠開啟智慧、擺脫執(zhí)著,讓你進(jìn)入人生思想的生動過程中的,皆是禪機(jī)。
由于這個緣故,在中國古代知識論的視野中,對變化的發(fā)生結(jié)構(gòu)、時機(jī)生熟和實現(xiàn)樣式的關(guān)注幾乎是高于一切的。比如其中的一個變化樣式就是往來或循環(huán)。我們以前講到《周易》中至簡至易的結(jié)構(gòu)——陰陽結(jié)構(gòu),憑借這么簡單的區(qū)別性特征來實現(xiàn)它的具體含義時,要通過大量的往來、循環(huán)來表現(xiàn),所以中國古人對于循環(huán)結(jié)構(gòu)非常敏感。如果它只限于形式上的循環(huán),那就沒什么意趣了。中國人覺得《易》講的天地四時的循環(huán),或過去未來之間的某種循環(huán),比如按陰陽五行結(jié)構(gòu)進(jìn)行的循環(huán),越循環(huán)越能出新意。《周易》說:“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一闔一辟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周易·系辭上》,《資料》,第128頁右)又說:“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周易·系辭下》)日月、陰陽往來的時間構(gòu)成中,隱藏著往來循環(huán)的微妙結(jié)構(gòu),因而含有無窮的“神以知來”的可能。
因此,中國古代知識論的要害,就是要知變化之道。“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周易·系辭上》)什么是“真知識”?就是知曉變化的道理和樣式。“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周易·系辭上》,《資料》,第127頁左)一位君子要想有所作為,要采取行動,就要去詢問《易》以知變易的趨向。“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yuǎn)近幽深,遂知來物。”(同上)《易》回應(yīng)此君子的蓍問,如響應(yīng)聲,不管何種非對象化的隱幽事態(tài),都可曲折透入而知將來之物。所以“往來”的根子在時幾,往指過去,來即將來。“知來物”正是要害。“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同上書,第128頁右)《周易》的神妙就在于可憑之明了天下之至變。于是在這兒擺弄擺弄那五十根蓍草,算將起來,實際上是算入了時幾的微動處,就能夠預(yù)測未來。現(xiàn)在的網(wǎng)絡(luò)小說,不少是“穿越”式的,也就是當(dāng)代的一個人,比如一名特種兵、一位工程師、一個大學(xué)生,憑借某種機(jī)緣回到了過去,在三國、宋朝、明朝、清朝乃至抗日戰(zhàn)爭時期大顯身手。而這些主角兒之所以能干出一番改變歷史的大事業(yè),就是因為他預(yù)知了未來。但這只是文學(xué)的虛構(gòu),不僅從技術(shù)上做不到,而且還忽略了一個問題,即如果他改變了歷史,那么他本人還能不能存在呢?很危險呀。未來影響了過去,而改變了的過去也會影響未來呀。但《周易》卻是真真實實地“彰往而察來”,靠的不是取巧,而是進(jìn)入非定域的感通之幾。“《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干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同上)。《易》的思維與觀念化思維很不同,它在后者的意義上是“無思”“無為”,但又完全時機(jī)化,被情境觸動后,就“感而遂通”天下之事。因為它進(jìn)入了陰陽不測的神妙處,即可深入幽深事理而探究對象事物的幾微征兆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