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儀:從民族救亡烽火中走來的美學家

蔡儀(1906—1992),1906年6月出生于湖南攸縣。出生時取名壽生,后自名南冠。1931年在《東方雜志》發(fā)表小說《先知》時,用筆名蔡儀,此后一直沿用。幼時,隨父親學習《詩經(jīng)》《左傳》。1921年,考入長沙長郡中學。1925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在北大期間開始接觸新文學,并初步接受了進步的革命思想,1926年冬加入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在這一時期也開始了新文學習作,加入“沉鐘社”。1927年夏,北京處于奉系軍閥高壓之下,南方革命形勢高漲,蔡儀休學南歸,不過并沒有接上組織關系。思想苦悶中,于1929年秋東渡日本,先后在東京高等師范學校哲學教育系、九州帝國大學日本文學系學習。在日期間,參加了唯物論研究會的討論,閱讀馬克思、恩格斯有關現(xiàn)實主義的理論文章。1937年夏,在九州帝國大學學分修畢,回到北平即投身抗敵救亡活動。1939年以后,到重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及文化工作委員會工作。后因政治宣傳工作暫停,轉入文學理論研究,寫作《新藝術論》《新美學》。在皖南事變后,蔡儀表達了入黨請求。1945年9—10月間,再次提出入黨。同年12月,得到黨組織批準,正式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自1946年開始,蔡儀分別在上海大夏大學、杭州藝術專科學校、華北大學二部、中央美術學院教課。后來根據(jù)在華北大學二部講授新文學運動的課程講稿出版了《中國新文學史講話》。1953年10月,調到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這一時期,因回應呂熒在《文藝報》上的文章參加美學討論,1958年完成《唯心主義美學批判集》,1959年完成《論現(xiàn)實主義問題》,此外主編有《文學概論》《文藝理論譯叢》《古典文藝理論譯叢》。20世紀80年代后,除改寫《新美學》外,主要精力在推動馬克思主義美學發(fā)展,編輯《美學論叢》以及普及美學知識。

蔡儀的一生貫穿了20世紀中國最為跌宕起伏的一段歷程。他幼年時,正值辛亥革命。青年時期,他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加入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而后留學日本。日本軍國主義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后,蔡儀投身到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全民族抗戰(zhàn)中。正是在民族救亡的烽火中,蔡儀成為一名堅定的共產(chǎn)黨人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馬克思主義是他一生的學術追求和生命體認。
積極投身革命事業(yè)
1925年,蔡儀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當時,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落潮、新文化陣營走向分化的時期。大批青年學生受李大釗的影響,走出校門宣傳馬克思主義,投身革命活動。受此氛圍影響,蔡儀與同學一道到北大附近的工人夜校宣傳、講課。這是蔡儀思想形成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時期,從“舊學”轉到“新知”。蔡儀幼年由父親發(fā)蒙,熟知舊學,他名字之一的“南冠”即取自《左傳》中的楚人鐘儀故事,“楚囚,君子也。言稱其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其人風骨一直深藏于蔡儀心中,在他的小說和詩歌創(chuàng)作中多有流露。不過,他是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和馬克思主義思想洗禮的新一代學人。在《八十感懷》詩中,蔡儀曾回憶道:“六十年前舊紅樓,授我新知慰我愁,指我人生新道路,終身努力苦追求。”
1927年,北京處于奉系軍閥的反動統(tǒng)治之下,革命陷入低潮。特別是“四二八”慘案之后,局勢更加惡化。蔡儀休學南歸,繞道天津、上海赴武漢,嘗試找到黨組織。他到達武漢時,時局已發(fā)生變化,當時武漢的革命也處于危機中。蔡儀未能與黨組織取得聯(lián)系,只得暫時回到湖南老家。在他留居故鄉(xiāng)的1929年6—7月,湘鄂贛三省的反動派調集了五個團的兵力,并糾集平江、瀏陽等地的反動武裝,對湘鄂贛革命根據(jù)地發(fā)動“會剿”,屠殺革命群眾三萬多人。這一時期,正是湘鄂贛革命根據(jù)地的困難階段。蔡儀在家鄉(xiāng)教書期間,被當?shù)剀婇y當作共產(chǎn)黨嫌疑犯抓了起來。后來,他創(chuàng)作的小說《先知》中有這一段經(jīng)歷的影子。這篇小說借卞和的故事,既寫他得不到理解郁憤而死,更用諸多筆觸描寫卞和始終堅定自己的信念而不渝。這篇小說的風格和人物讓人聯(lián)想起蔡儀早年參加的“沉鐘社”。其創(chuàng)刊號首頁引用了吉辛的名句“我要工作啊,一直到我死亡之日”。魯迅評價“沉鐘社”的作品時,曾說:“將真和美歌唱給寂寞的人們”,卻也是“飽經(jīng)憂患的不欲明言的斷腸之曲”。這斷腸之曲不是感傷的、猶豫的,而是沉靜而熱烈的,因而魯迅稱贊“沉鐘社”為“中國最堅韌,最誠實,掙扎得最久的團體”。小說《先知》主人公的形象雖然愁郁,卻并不彷徨,這是來自作者蔡儀面對民族憂患中的自覺和自省。
1929年秋,蔡儀東渡日本,先在東京高等師范學校學習,后在九州帝國大學學習。蔡儀留學日本,并不是因革命低潮期而避走書齋,《蔡儀傳》中曾形容這一時期的蔡儀“尋找組織,尋找革命之心不死”。在此期間,他接觸了大量馬克思主義研究和宣傳的書籍,為后來的理論研究工作打下了堅實基礎。不過,令蔡儀始終懸心的是民族存亡。1937年夏,他在九州帝國大學修完學分后回到北平。
隨著抗日戰(zhàn)爭的爆發(fā),蔡儀即放棄尋找學術界的工作,將全部精力投入北平文化界的一些抗敵救亡活動中。北平淪陷后,他到了長沙、武漢,協(xié)助呂振羽辦湖南文化界抗敵后援會,負責教務。湖南文化界抗敵后援會是我們黨領導的抗戰(zhàn)初期湖南最活躍、影響最大的民眾抗日團體。1939年初,因薛岳接替張治中來湖南,堅持反共、打擊進步勢力。隨著文化界人士相繼離開,湖南文化界抗敵后援會等救亡團體也被瓦解。蔡儀與進步文化人士一道來到重慶,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工作。第三廳受中共南方局領導,主要工作是團結社會名流、組織群眾、宣傳抗日救亡。由于蔡儀曾經(jīng)留日,懂得日語,因此他與九州帝國大學的同學余瑞熹一起,被分配撰寫和編輯政治、文化方面的《敵情研究》小冊子,從日本報刊上編輯整理重要信息,提供給上級部門。同時,他們每月編寫抗日反戰(zhàn)的傳單和宣傳品,并應雜志約稿撰寫敵情分析文章。從湖南文化界抗敵后援會到第三廳的敵情研究,在回國之后的兩三年間,蔡儀并沒有從事美學和文學理論的專業(yè)研究。他后來回憶道,“當時腦子里都是抗日,可以說是全力以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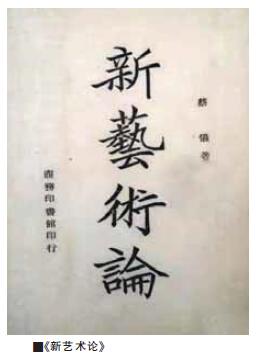
構建馬克思主義美學理論
1941年初,蔡儀向黨組織負責同志表達了入黨的愿望,當時正是皖南事變發(fā)生后不久。與1927年時的選擇一樣,越是在革命危難之時,蔡儀越是堅定地投入革命行動。皖南事變發(fā)生后,第三廳被迫改組為文化工作委員會,已經(jīng)不能繼續(xù)在重慶公開進行政治宣傳工作。為適應形勢的轉變和發(fā)展,周恩來提出“有研究能力的人,盡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坐下來搞點研究,抓緊時間深造自己,深入研究幾個問題,想寫點什么書趕快把它寫出來”,“等革命勝利了,要做的事情多得很呢,到那個時候,大家更忙啦,你們想研究問題、寫書,時間就難找啦!”(《南方局黨史資料——文化工作》(六),重慶出版社1990年版)因此,蔡儀不再做“敵情研究”,而是回到曾經(jīng)關注的文學理論研究領域。他以在日本留學期間所習得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恩格斯現(xiàn)實主義文章中的理論闡發(fā)為基礎,1942年寫出了《新藝術論》。郭沫若將該書的第一章《藝術的內容和形式》刊發(fā)在《中原》創(chuàng)刊號,接著在第二期以《藝術相關的諸屬性》為題發(fā)表了其他幾節(jié),并親自向商務印書館推薦出版。1944年,蔡儀完成《新美學》,該書的序言開篇寫道:“舊美學已完全暴露了它的矛盾,然而美學并不是不能成立的……這是以新的方法建立的新的體系。對于美學的發(fā)展不會毫無寄與吧。”多年以后,我們讀來仍能感受其中的激烈,寓于平淡的文字中,更顯得堅決。這里的“新”,指的就是馬克思主義。在當時國統(tǒng)區(qū)的政治高壓下,書名不能直接用馬克思主義。《新藝術論》在當時國統(tǒng)區(qū)的青年讀者中有很大影響,畫家李可染曾邀請蔡儀到他任教的重慶國立藝術專科學校與進步學生座談,因為這些學生讀過《新藝術論》后想當面向作者請教一些問題。后來蔡儀編輯《青年知識》的念頭就是由此而萌發(fā),想要為青年朋友們做些事情。
對于《新藝術論》,今天的一些研究者認為蔡儀受到了日本美學家甘粕石介的影響,評述的重點落在體系性而非原創(chuàng)性,而對該書中關于馬克思主義之于文藝理論、美學領域的革命性的論述卻很少提及。《新藝術論》《新美學》一以貫之的立場是堅持唯物主義認識論,以唯物主義作為美學研究的根本方法論指導。這兩部書不僅是學科意義上的開創(chuàng)之作,更應該被理解為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進行理論斗爭的一次重要嘗試和實踐。《新美學》序言中提出了鮮明的理論立場,這往往被理解為不同陣營之間的批判,即針對朱光潛為代表的觀念論美學。其實,這樣的解讀并沒有充分地體察蔡儀在20世紀40年代理論思考的真實狀態(tài),蔡儀與同時代的左翼理論家有一個明顯的差異:當時他很少寫文學批評,也沒有直接介入某些論爭。
居于蔡儀思考中心的,與其說是對“舊”的批判,不如說是對于“新”的探索:馬克思主義究竟意味著什么?對于中國新文學的困境和出路而言,馬克思主義又意味著什么?他選擇的是更為深遠也更為艱苦的理論思考和理論斗爭。這一選擇的意義,要從新文學發(fā)展脈絡來把握。20世紀20年代的革命文學論戰(zhàn)具有重要的開創(chuàng)性,它闡揚了文學的階級性和革命性,并且?guī)恿笋R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文藝理論的翻譯介紹。在革命文學論戰(zhàn)后,魯迅和馮雪峰主持翻譯出版了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藝術與社會生活》和盧那察爾斯基的《藝術論》《藝術的社會基礎》等。這不僅是出于對知識的興趣,更有現(xiàn)實的需要,革命文學的困境需要在理論上正本清源。20世紀30年代初期,中國左翼聯(lián)盟的成立雖然使得新文學運動有了有力的組織,但對于文學理論的建設并沒有太多深入。理論建設上的弱點于“第三種人”的論爭中呈現(xiàn)得最為明顯,這一困境也促使左翼文學陣營更為自覺地思考革命文學的理論根基。
唯物主義美學觀念之所以能夠在20世紀30年代的左翼理論界迅速發(fā)展,與救亡圖存的現(xiàn)實需要密切相關。1937年,周揚發(fā)表《我們需要新的美學——對于梁實秋和朱光潛兩先生關于“文學的美”的論辯的一個看法和感悟》,提出“新的美學已不是研究抽象的美的學問,它應當指出美的要求不是藝術作品的最后根源,它本身,就和藝術作品一樣,是歷史的社會的產(chǎn)物,這是新美學和舊美學的根本不同,也就是前者和后者訣別的起點”。盡管這篇文章并沒有詳細論述新美學的特質,也沒有構建起嚴密的邏輯體系和范疇體系,但非常堅定而自覺地以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來解釋美的問題。蔡儀在《新藝術論》最后一章論及藝術美時,提出了“美到底是什么?”并且初步形成了“藝術的美就在于藝術的典型,藝術的典型形象就是美的典型形象”“美就是典型,典型就是美”等論點。1944年他寫成的《新美學》一書,是20世紀中國最早的、系統(tǒng)性的、唯物主義的美學專著。從1937年到《新藝術論》和《新美學》的問世,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美學在較短時間內就達到了很高的水平。
《新藝術論》《新美學》開宗明義地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作為美學研究的根本方法指導,只有以此立足才能奠定“科學的美學”。這一時期,左翼文藝理論家呼喚新舊美學的“訣別”“決裂”,這固然出于現(xiàn)實斗爭的考慮,更為重要的是要為革命文學運動夯實理論基礎,而理論思考的嚴謹性和徹底性與實際斗爭中的復雜性是兩個不同的層面,容不得一絲含混。這個徹底性,集中體現(xiàn)在哲學上的物質存在與主觀意識的關系這一基本問題上持唯心的還是唯物的立場。蔡儀認為,“美學上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分,正如哲學上的這種區(qū)分一樣,是由美學思想本身的性質決定的,決不是別人強加給它的。因而這是事實的本然,是承認或不承認的問題,而不是道德的說教,不是應該或不應該的問題。誰要否認,誰要反對,自然有其自由”。《新藝術論》《新美學》將哲學的基本問題帶入美學和文藝理論領域,改變了20世紀30年代以文藝心理學為主導的美學的討論方式。這是蔡儀美學思考中一以貫之的顯著特點,從根本的哲學論點說起,闡述什么是哲學上的、什么是美學上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這一大是大非問題。在20世紀50年代的美學大討論中,蔡儀的一篇文章的標題即為《論美學上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根本分歧》。以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來看待社會、分析藝術活動,重視客觀性,美是一種客觀的認識對象,藝術創(chuàng)造最后是要讀者看到現(xiàn)象背后的本質規(guī)律,這也構成了20世紀中國美學歷程中的一個特點。暫不細論具體觀點上的得失,單就這一大是大非問題,蔡儀的美學思想在馬克思主義美學、在中國美學的發(fā)展進程中是有歷史功績的。

探索唯物主義美學體系
蔡儀雖然并不直接參與理論論爭,但是他觀察到,20世紀30年代介紹進來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大體上僅僅闡明文學理論的根本法則,很少涉及文學的實際問題如創(chuàng)作方法,而這些是左翼文學運動中面臨的實際問題。更為重要的是,當時理論界雖然把握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基本概念,但是對于這些基本概念怎樣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怎樣運用于中國新文學運動方面尚無法正確理解。這是產(chǎn)生宗派主義偏向和文學理論方面的教條主義的主要原因。蔡儀在寫作《新藝術論》時,有意識地加強了對這些問題的論述。有的研究者對比了《新藝術論》和蘇聯(lián)學者維諾格拉多夫的《新文學教程》,認為二者的基本觀點是一致的,但蔡儀對問題的論述則要詳盡得多。詳盡的部分是在典型問題、世界觀與創(chuàng)作方法以及現(xiàn)實主義問題等方面。蔡儀對這些問題的辨析并不照搬唯物主義的哲學條款,而是以新的理論立場和方式呈現(xiàn)出新的解釋力。因此,盡管《新藝術論》有明確的思想文化立場,但在這種辯證思維基礎上構建的文學論,與以往人文主義立場的文學論或早期無產(chǎn)階級立場的文學論相比,都更富有包容性和整體性。
蔡儀在20世紀40年代的理論工作中,就自覺地聯(lián)系20世紀中國革命文藝的實踐經(jīng)驗做理論上的反思,這一研究路徑一直貫穿到20世紀60年代的《文學概論》的寫作中。蔡儀在《文學概論》中對社會主義時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多有具體的分析。例如,他對如何理解文藝的工農(nóng)兵方向、如何理解繼承與創(chuàng)新的關系、如何理解革命現(xiàn)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等創(chuàng)作實踐中所提出的理論問題,都有精辟的論述。這既是蔡儀理論工作的獨特性,也是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題中應有之義。蔡儀也曾做過另外一種嘗試,即文學史的寫作。抗戰(zhàn)勝利后,他從重慶回到上海,而后于1948年底到達華北解放區(qū),在華北大學二部國文系講授新文學史,在此基礎上寫作完成了《中國新文學史講話》。蔡儀介紹說:“它不是敘述一般新文學史運動的史實,只是考察幾個新文學史上的問題;卻想通過這幾個問題,去認識新文學運動的大致情形。”“這幾個問題”分別是新文學運動和革命運動的關系、新文學運動的團結和斗爭、新現(xiàn)實主義的精神、大眾化的傾向。與文學史寫作常常依托的作家、作品、思潮、流派等不同,蔡儀的“這幾個問題”是理論思考的節(jié)點。從對“這幾個問題”的提煉中,我們能夠看出蔡儀已經(jīng)開始嘗試走出馬克思主義文論的議題和概念范疇,從18—19世紀歐洲語境中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經(jīng)驗走出來,更為深入地植根于中國新文學發(fā)展的歷史性中。《中國新文學史講話》的寫作方式雖然是文學史式的,但是寫作脈絡中的歷史唯物主義也是蔡儀美學思考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與學生的談話中,蔡儀多次談到,研究美學史,重要的是不能從概念出發(fā)或者從西方美學套解。唯物主義美學并不僅僅是基本哲學立場的顛倒,而是全面系統(tǒng)地對古今中外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規(guī)律的總結。20世紀80年代之后,蔡儀的精力主要放在《新美學》的改寫以及馬克思手稿的闡釋和爭論,并沒有直接研究中國美學史。在《新藝術論》中,蔡儀更多地引證了中國傳統(tǒng)文論、畫論中有關筆法、技巧、藝術創(chuàng)作規(guī)律的有關理解,與“藝術的認識”一章中較多的抽象辨析相比,“藝術的表現(xiàn)”一章更多地融入了自己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對于同一時期左翼文藝實踐的批評也更為明顯。在《文學概論》的寫作中,他也自覺地將中國文論作為重要參照。《文學概論》寫作的一個重要背景是20世紀60年代的中蘇論戰(zhàn),國內形勢從“一邊倒”開始轉向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對于包括《文學概論》在內的大學文科教材的編輯工作,周揚明確提出建立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號召,“我們現(xiàn)在是要按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回過頭來總結中國的文藝遺產(chǎn)和五四以來的文學經(jīng)驗,再從中得到我們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的理論”。這是周揚一直以來思考的問題,在中蘇分裂的大背景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努力更多地呈現(xiàn)為與蘇聯(lián)文藝學教材切割,突出民族特色。《文學概論》在大的框架方面,由蘇聯(lián)教材的三大塊(文學本質、作品分析和文學發(fā)展)改造為五論:本質論、作品論、創(chuàng)作論、批評鑒賞論和發(fā)展論。創(chuàng)作論,尤其是批評鑒賞論,是蘇聯(lián)教材所沒有的,是來自中國傳統(tǒng)文論和文學經(jīng)驗的總結。
在蔡儀探索的唯物主義認識論的美學、文學理論體系中,中國美學史的研究一直處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尤其需要特別辨析的是,蔡儀對于中國美學和詩學思想的重視,并不是因為20世紀60年代要求突出民族特色的歷史氛圍,而是更多出自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考慮。中國傳統(tǒng)的文藝思想,不僅僅是蔡儀的思想資源,也是唯物論的思考框架得以形成的對話者;而20世紀中國的文藝實踐乃至政治實踐,不僅僅是蔡儀理論思考的歷史背景,還是他的思考對象。蔡儀對于左翼文藝實踐的反思,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與同為左翼陣營內部的理論家之間的緊張感,并不弱于與當時被稱為“自由主義”的文藝理論家之間的論戰(zhàn)。與傳統(tǒng)文論、與新文學之間的這兩層對話關系,構成了《新藝術論》對于“藝術創(chuàng)作過程”的思考基礎。蔡儀的理論工作中所呈現(xiàn)的多重線索提示我們,不應固守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經(jīng)典”與“譯介”的靜態(tài)的理解模式,而要全面地、歷史地理解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fā)展脈絡的“理論原創(chuàng)性”。
蔡儀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不是出于書齋里的閱讀,而是同中華民族的革命與救亡息息相關,20世紀的風云激蕩始終主導著蔡儀的人生選擇和學術選擇。1977年夏,何其芳因病離世。蔡儀在悼亡詩中寫道:“遠赴延安革命鄉(xiāng),委身黨國換戎裝。即將畫夢抒情筆,當作為民抗敵槍。四十年間勤戰(zhàn)斗,無窮心力付文章。尚余修史選詩業(yè),此愿未償劇可傷。”在美學和文藝理論的許多重大問題上,他們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交往密切,感情非常深厚。這首悼念詩簡略回顧了何其芳的生平,尤其將回顧的起點放在延安,這不僅有對何其芳的追懷,也飽含著對他們共同選擇的革命道路的體認,那是一代從民族救亡的烽火中走出來的詩人、學者、戰(zhàn)士,孜孜以求、矢志不移的革命者。在這樣的精神歷程中,蔡儀直到晚年仍然認為美學研究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要有現(xiàn)實性,“美學或文學理論的研究,直接關系于文學藝術的創(chuàng)作和批評,直接關系于人民精神的美育和生活的美化,毫無疑問是文化科學一個重要部門”。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