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yán)肅的游戲”:你只是得到,你并未選擇

作家的油畫像 Astrid Kjellberg-Juel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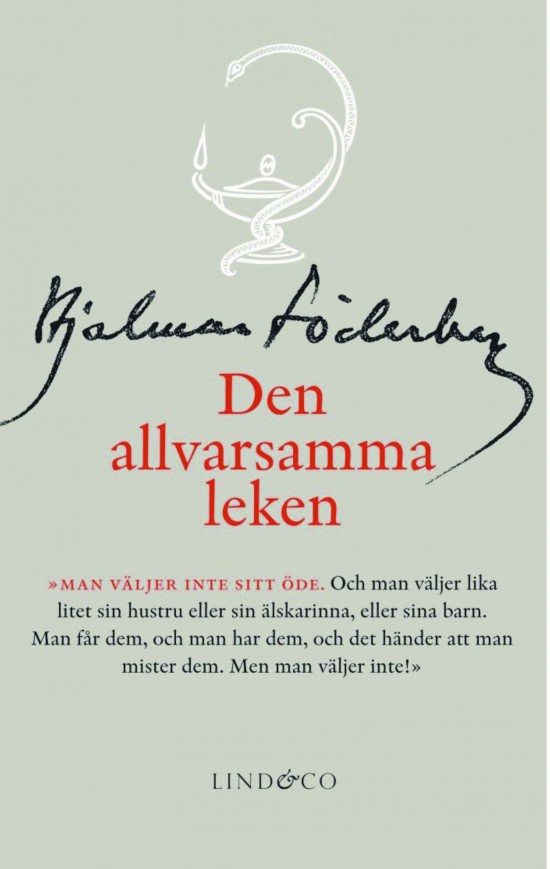
《嚴(yán)肅的游戲》瑞典語版
在他生命后來的階段里,瑟德爾貝里會想起1906年的那個(gè)秋天,他稱之為煉獄。他覺得自己走過了一條長長的、彎曲的地下通道,越來越窄,后來他必須爬著,他找不到出口,也看不到一丁點(diǎn)光亮。有一天他照著鏡子,他才30多歲,可他覺得自己老了,每一天都老一歲。
雅爾瑪爾·瑟德爾貝里(Hjalmar S?derberg 1869-1941)是瑞典最偉大的現(xiàn)代作家之一。他生于斯德哥爾摩的一個(gè)公務(wù)員家庭,是小說家、劇作家,也曾在斯德哥爾摩當(dāng)記者。
雖然母親曾為他的文學(xué)志趣憂心,他的從文之路頗為順暢,20歲前后便開始在《每日新聞》等報(bào)刊發(fā)表短篇小說、詩歌和評論。他一生著有《錯(cuò)覺》(1895)、《馬汀·別克的青春》(1901)、《格拉斯醫(yī)生》(1905)和《嚴(yán)肅的游戲》(1912)這4部中長篇小說,約90篇短篇小說,《雅特露德》(1906)等3部戲劇。在一場嚴(yán)肅的婚外情游戲后,他拋開對詩歌、文學(xué)和情色的幻覺,南下哥本哈根,在那里寫時(shí)事評論并研究基督教史。
寫了又寫的情與愛
無法找到第二個(gè)瑞典作家像瑟德爾貝里這樣不厭其煩地在文本中啟用情愛素材。他有一則膾炙人口的短篇小說,題目就叫《親吻》,寫女孩和男孩初吻前微妙的心理活動,他寫得更多的是幻滅的情與愛。
瑟德爾貝里筆下的情愛,炙熱而執(zhí)著時(shí)仿佛宗教體驗(yàn),比如格拉斯醫(yī)生的單相思,雅特露德對愛的執(zhí)念,前者是地下的潛流,后者是地表的激流。“愛,它到底是什么?”雅特露德也說不清,相反,她覺得愛是個(gè)奇怪的字眼兒,聽來古怪,不像真正的瑞典語。愛,它到底是什么,若拿它說明父母對子女的憐惜,意思不含糊。若將其聚焦于情侶,則無論用什么語言來解釋,都會讓人迷失在語詞里吧。
雅特露德需要完滿的愛,三個(gè)男人都沒法讓她滿意,她似乎注定要處于孤獨(dú)之中。《錯(cuò)覺》的男主人公、一名醫(yī)學(xué)院學(xué)生游走于女人之間,拋棄一個(gè),讓另一個(gè)懷了孕。《馬汀·別克的青春》的內(nèi)容部分基于童年記憶,是瑟德爾貝里在文學(xué)上的一次突破,包含對兩性關(guān)系和生命意義的探討。《格拉斯醫(yī)生》以世紀(jì)之交的日記鋪展出一起謀殺案,牧師的婚內(nèi)強(qiáng)奸、海爾嘉的婚外通奸、格拉斯的單相思都讓瑟德爾貝里看來越發(fā)像書寫情愛的專業(yè)戶。1940年代,有評論家將瑟德爾貝里的最后一部小說《嚴(yán)肅的游戲》稱為“我們的文學(xué)中最好的愛情小說”,這一說法近百年來被看作贊譽(yù),可它也一定會誤導(dǎo)出對《嚴(yán)肅的游戲》的表面化閱讀。
瑟德爾貝里的情色故事并非純白色。即便《親吻》那樣的純愛素描,也沒用單線條,而是加入了時(shí)而敵對的心理活動。而《嚴(yán)肅的游戲》里作為背景的夏日戀曲中有海水的波光和星星的閃亮,是全書最純粹而浪漫的篇章,可還有些別的。有嫖妓經(jīng)歷的阿維德在親吻莉迪亞的瞬間,懷疑莉迪亞已非處女之身。莉迪亞與阿維德10年后的舊情復(fù)燃里沒有羅密歐和朱麗葉的純粹,一次次交歡,阿維德期待身體外更深的連接而求之不得。像是畫一個(gè)不曾畫完的圈,像證明對當(dāng)下存在狀態(tài)的不滿,唯獨(dú)不像純愛。
瑟德爾貝里本人的婚外情既為他提供了海爾嘉、雅特露德及《嚴(yán)肅的游戲》的女主人公莉迪亞的原型,也提供了故事。就像瑟德爾貝里過早拋開文學(xué)一樣,他一面將情色作為觀察和描摹的對象,一面層層剝開情色的外皮。那些攤開的外皮無言地暗示,情色是人活著會經(jīng)過的試煉之一,它在一些瞬間幫人超越日常的絕望,它給人不同時(shí)期的狀態(tài)著色,而最根本的,它只是讓人理解存在的滋味。瑟德爾貝里一再書寫情色,終究是寫它如何現(xiàn)出原形、灰飛煙滅。
嚴(yán)肅的游戲
單從情節(jié)看,《嚴(yán)肅的游戲》說了一段陳腐的婚外情事。年齡相仿的莉迪亞和阿維德在夏日海島相愛。阿維德不愿過早受拘束,不確定這段情和以往的有何區(qū)別,不能在經(jīng)濟(jì)上支撐婚姻。秋天到了,雖說對莉迪亞日思夜想,他卻沒去找她,而讓命運(yùn)決定一切。可當(dāng)他聽說19歲的莉迪亞嫁給51歲的名學(xué)者時(shí),感到了撕心裂肺的痛。日子是往前走的,命運(yùn)將阿維德放進(jìn)一樁不錯(cuò)的婚姻,并且他過得很幸福。
夏日戀情只是一道背景,真正的故事10年后才開始。那時(shí)秋已走遠(yuǎn),在寒冷的冬夜,阿維德和莉迪亞偶然重逢、舊情復(fù)燃。不久,莉迪亞離了婚,到斯德哥爾摩獨(dú)居,她完全無意和阿維德做夫妻,而是周旋于幾個(gè)情人之間。阿維德不堪面對真相,踏上南下的列車、遠(yuǎn)離傷心之地。
小說人物幾乎都有原型。莉迪亞的原型叫瑪瑞爾·馮·普拉騰,19歲時(shí)結(jié)婚,30歲時(shí)離開55歲的貴族丈夫和11歲的兒子,在20世紀(jì)初從南方北上斯德哥爾摩追求文學(xué)夢。她以一封女粉絲的信搭建起與風(fēng)頭正健的“馬汀·別克”的聯(lián)系。兩人的婚外情從1902年持續(xù)到1906年。瑪瑞爾同時(shí)與另幾位作家有或長或短的桃色關(guān)系。這個(gè)摩登女性對瑟德爾貝里構(gòu)成毀滅性打擊。得知情敵之后,他不得不立刻逃離丑聞,逃離故鄉(xiāng)。《嚴(yán)肅的游戲》因此常被讀作一個(gè)男人因?yàn)閷σ粋€(gè)尤物的激情而自我破碎的故事。可或許這只是誤讀。
叫“莉迪亞”的森林寧芙
1922年夏,在《嚴(yán)肅的游戲》出版10年后,瑟德爾貝里收到一封來自莉迪亞· 斯蒂勒女士的信,她發(fā)表過一兩首詩歌,問大作家是否因此才對這個(gè)姓名有印象,借用到自己的小說里。大作家對這奇怪的巧合吃驚不已,他回復(fù)說,莉迪亞來自賀拉斯的文字。
賀拉斯詩集里有不少情詩,莉迪亞出現(xiàn)在四首詩里。詩里的“我”以局外人姿態(tài)描述莉迪亞的情感故事,又時(shí)時(shí)藏不住情緒化表達(dá)。詩歌講述一名男子迷戀莉迪亞,以至忘記了職責(zé),愛使他嫉妒,流出最苦的膽汁。到第三首,嫉妒發(fā)展為復(fù)仇的欲望,莉迪亞老了,不像從前那般令人垂涎。最后一首詩里的對話透露,“我”和莉迪亞也有過一段情。“我”想知道,愛情的鐘聲若有機(jī)會再次為往昔的情侶敲響,會怎么樣。可如今,莉迪亞身邊有另一男子,詩人正與金發(fā)的克洛伊在一起。賀拉斯問,若古老的維納斯回來了,金發(fā)的克洛伊給扔了出去,一扇門為莉迪亞重新敞開,會怎么樣?在很大程度上,《嚴(yán)肅的游戲》演繹了為莉迪亞重開一扇門的故事,阿維德金發(fā)的妻子達(dá)格瑪成了現(xiàn)代小說版的克洛伊。
賀拉斯的莉迪亞是凱撒和奧古斯都時(shí)代詩歌里常見的喜怒無常而嫵媚誘人的女人,總周旋在暴風(fēng)雨般的情人關(guān)系里。古羅馬的莉迪亞來到北歐的自然和文學(xué)環(huán)境下是個(gè)什么樣呢。和莉迪亞偷情日久的阿維德有一天給自己斟上一杯酒,在書房里來回踱步。妻子就在門外,而他想起幾行詩來:“可這顆心,叫森林寧芙偷走了的,/他再也拿不回來。/他的靈魂在月光下逐夢,/他沒法再愛一個(gè)配偶。”男人非要投入寧芙那巨大的誘惑不可,盡管將無法再愛一個(gè)人類的妻子。
重歸斯德哥爾摩的莉迪亞不再是夏夜的天真少女,她不在父親膝下,也不在丈夫跟前,她的第一個(gè)婚外情人不是阿維德。成了阿維德的情婦后,她和其他男子發(fā)生了關(guān)系,其中一個(gè)在圣誕節(jié)早晨自殺,因?yàn)椴痪们埃?dāng)阿維德在莉迪亞那里過夜時(shí),這人按了門鈴,吃了閉門羹。相比于有一個(gè)私生子,對妻子不忠的阿維德,按當(dāng)時(shí)社會的邏輯,阿維德只是陷入了中產(chǎn)階級男子的生活常規(guī),莉迪亞則被看作對男性有殺傷力的蛇蝎美人。這一看法隨時(shí)代的發(fā)展不斷改變。1973年,有女作家出版小說,采用了莉迪亞的視角,并將故事挪到20世紀(jì)中期。
無論如何,阿維德也在莉迪亞那兒吃閉門羹后,一天,他看著自己的幼女,竟冒出這樣的疑問:“我的孩子,你長大后,會是個(gè)達(dá)格瑪,誘惑一個(gè)男人同她結(jié)婚……還是說變成個(gè)莉迪亞,誘惑一個(gè)又一個(gè)男人,從不安頓下來,直到年老和死亡帶來結(jié)束……”
你只是得到,你并未選擇
創(chuàng)作之初,瑟德爾貝里將《嚴(yán)肅的游戲》定名《莉迪亞的錯(cuò)》。若將小說情節(jié)狹義地誤解為婚戀糾葛,卷入糾葛的所有人都犯過錯(cuò)。這游戲里有一條以情愛之名包裹著的欺騙鏈條。莉迪亞的丈夫不該用富貴“買下我作為合法的情人。懷孕和孩子則不在他的規(guī)劃之內(nèi)”;達(dá)格瑪不該用謊言讓阿維德就范; 阿維德和莉迪亞不曾忠實(shí)于夏日戀情,各自成婚后不曾忠實(shí)于婚姻。當(dāng)然莉迪亞對道德觀做出的挑戰(zhàn)最大,在阿維德看來,是莉迪亞“勾引”了男人,還讓其中一個(gè)送了命。
感情糾葛里的錯(cuò)只在表面,深處是命運(yùn)里無法避免的錯(cuò)。許多要素出現(xiàn)在生命路的兩邊,像樹上的果子,人以為可以自主地摘取它們,卻往往是不得不如此,一定會如此。
有人曾詢問瑟德爾貝里,書名到底是偏于“嚴(yán)肅”,還是“游戲”,得到的回答是兩者一樣重要。
地產(chǎn)大亨的女兒達(dá)格瑪對阿維德有興趣,報(bào)社同事麥克爾說:“小心!從前是男人找女人,那是舊風(fēng)俗。如今女人來找男人,而且不擇手段!”阿維德很快就對誘惑投降,她給他提供年輕和美麗,不接受便是傻瓜。與阿維德上床之前,達(dá)格瑪問:“你愛我嗎?”“當(dāng)然,”他回答:“我愛你。”阿維德覺得,不這么說無法開始床笫之歡。“愛呀愛的……他已失去自己的第一顆心。他認(rèn)為要7年才能長出一顆新的來。可一個(gè)人自然的沖動沒有休眠,遠(yuǎn)遠(yuǎn)沒有。”幾乎每一晚,她都潛入他的公寓。即便如此,阿維德一再表示不會結(jié)婚。最后,達(dá)格瑪跟他哭訴,父母得知了兩人的關(guān)系而震怒,她只好說他倆已秘密訂婚。阿維德上門賠罪,做了這一家的女婿。多年后,他才明白,父母震怒和秘密訂婚的戲碼是達(dá)格瑪自編自導(dǎo)的。
麥克爾提醒過阿維德:你利用她以及她對你的愛滿足自己的欲望,那是人之常情,可這樣做也很卑鄙……你不想結(jié)婚,你沒錯(cuò),你結(jié)不起。可問題不是你想怎么樣,而是會發(fā)生些什么!你不選擇,你并不選擇你的命運(yùn),正如你并不選擇父母和自己……正如你并不選擇妻子、情婦或子女。你得到、擁有,也可能失去他們,可你并不選擇他們!”
那不存在的湖泊
莉迪亞問阿維德:“你能告訴我嗎,陶擬澤湖在哪兒?”阿維德覺得耳熟,卻又想不起來是在哪里聽過或讀過:“我怕是不知道,我猜它在德國或瑞士的某個(gè)地方。怎么,你打算去那兒?”莉迪亞說:“想去,非常想,要是我能找到它在哪兒。”他倆接著有如下的對話:
“那應(yīng)該不會太難。”
“恐怕很難,”她說,“昨晚我失眠了,想著《當(dāng)咱們死人醒來時(shí)》里的一段。始終聽見腦子里有句話:可愛的,可愛的是陶擬澤湖的生活!而后我想,我猜,并沒有那樣的湖,可也許那正是它如此可愛的原因。”
“哦,這樣啊,我想你說得對,那樣的湖一定不容易從地圖上找到。”
事實(shí)上,在嫁給名學(xué)者之前,莉迪亞給阿維德寄去一張小卡片,上邊畫著秋色中的水面,又說她真想到遠(yuǎn)方去。那遠(yuǎn)方的湖一定不會出現(xiàn)在人所生活的環(huán)境里。可愛的湖,它在易卜生的那出戲里和美好往昔一同出現(xiàn),是存在著幸福的地方。莉迪亞想到那里去,不像要返回過去,更像要獲得眼下和未來的幸福。
幸福在哪里呢,在哪里?它就在阿維德和達(dá)格瑪?shù)幕橐隼铩?/p>
阿維德和達(dá)格瑪從命運(yùn)中得到的婚禮于1904年2月10日舉行。那一天報(bào)童奔走在街頭,于暴風(fēng)雪里高喊:號外號外,俄羅斯、日本交戰(zhàn)!顯然這不是瑞典常見的有六月新娘的明媚婚禮,這場婚禮安排在暴風(fēng)雪之日,婚禮的主角未必不是瘋著,天瘋著,世界瘋著,像一場大鬧劇里套著小鬧劇。
然而,在關(guān)于阿維德和達(dá)格瑪婚姻的段落里,集中出現(xiàn)了三次和幸福相關(guān)的表述:“阿維德和達(dá)格瑪在一起過著非常幸福的生活”,“阿維德和妻子過著開心的日子”,“除此之外,他們非常快樂地生活在一起。而歲月流逝。”這恐怕就是命運(yùn)中的許多婚姻的狀況,沒多少人會自尋煩惱,把腦袋伸進(jìn)“除此之外”的袋子里,看里頭有些什么。
十年后,阿維德和莉迪亞在斯德哥爾摩歌劇院偶然相遇,中場休息時(shí),他倆的手伸出來,找到彼此。沉默。而后,她低聲說:“你幸福嗎?”他沉默了片刻回答:“我想沒有人真正幸福,可不管怎么說你得繼續(xù)活著,盡己所能。”“沒錯(cuò),”她說,“我猜你做得到。”他們沒再說什么。阿維德以自己的語言詮釋了瑟德爾貝里以世俗標(biāo)準(zhǔn)頒給他的幸福獎(jiǎng)狀。
煉獄和地下通道
十年后,他倆共度一夏,像是對海島夏日做遙遠(yuǎn)的呼應(yīng)。在同床共枕前,莉迪亞說:“這一個(gè)夏天里我倆的日子再不會有了,永遠(yuǎn)也不會了……”阿維德覺得他們能永遠(yuǎn)相愛,莉迪亞拿眼睛笑了笑:“能,當(dāng)然能,永遠(yuǎn)并且始終,至少直到明天早晨!”如此,她率先點(diǎn)穿了情愛的虛幻,而她也早已用追逐其他情人的行動來粉碎愛的幻覺。
情愛閃耀著絢麗光芒時(shí)或能讓人戰(zhàn)勝自身的殘忍、狡猾和欺騙,然而這不意味著情愛中不含殘忍、狡猾和欺騙。情愛的魔力消散時(shí),那些大大小小、有意無意的殘忍、狡猾和欺騙顯現(xiàn)出來,像融雪下的一切。情愛會變,靈魂是,人也是,在變幻著的時(shí)間和環(huán)境中變化。人在生長,靈魂在生長,從軟到硬,從單純到渾濁。仲夏夜,少年格拉斯親吻了初戀,而在醫(yī)生的回憶里,那個(gè)時(shí)空是失落的天堂。也是夏夜,10年前阿維德和莉迪亞在星星閃亮?xí)r親吻,10年后,他倆從偷情的狂喜跌入冷漠的背叛,這一前一后恍若隔世。
瑟德爾貝里并未局限于所處時(shí)代對男女的雙重標(biāo)準(zhǔn),他無法改變社會的傾向性,但他最大限度地贊美了女性,無論雅特露德、海爾嘉或莉迪亞,都是男士仰慕的對象。海爾嘉無辜而美好,雅特露德執(zhí)著而熱烈。瑟德爾貝里不太理解的是莉迪亞,從阿維德的視線看去,10年后的莉迪亞矛盾而冷漠。而她們都是瑪瑞爾的化身。
因?yàn)槠拮拥募膊『徒?jīng)濟(jì)壓力,瑟德爾貝里婚姻的院落里火星四濺,和瑪瑞爾的情事如火上澆油。瑟德爾貝里自述這段情是自己一生中最具決定性的事件。而瑪瑞爾在信中跟人表示,她從未愛過作家本人,只愛上了馬汀·別克。
《嚴(yán)肅的游戲》對死亡的激情做了防腐處理。如果說斯特林堡和他筆下的男人多以仇恨結(jié)束和女人的關(guān)系,瑟德爾貝里和他的男主人公們多以分手和傷痛來了斷。《嚴(yán)肅的游戲》將自己扮成情色悲劇,可它不過是訴說生而為人的悲哀。婚外情本身并未對婚姻產(chǎn)生致命的作用,出了大問題的是阿維德和莉迪亞的情愛本身,它從夾雜謊言的真情演繹到滿是謊言的假意。這是世上不少人與事的狀態(tài)。這不意味著人得否定一切,只意味著并非一切都是人以為的模樣。摘樹上的果同時(shí)是自愿的和被迫的。人生中的不少抉擇和行動與此相似。
“在他生命的后來的階段里,阿維德會想起1908年這個(gè)秋天,他稱之為煉獄。他覺得自己走過了一條長長的、彎曲的地下通道,越來越窄,后來他必須爬著……他找不到出口,也看不到一丁點(diǎn)光亮……突然,他覺得自己老了。似乎每一天都老一歲。”情色所鋪的常常是這樣的煉獄和地下通道。
苦澀而彷徨的男子們
瑟德爾貝里時(shí)常聚焦世紀(jì)之交和現(xiàn)代化大潮中缺乏行動力的男子,來自韋姆蘭鄉(xiāng)間的阿維德是其中的代表。阿維德對都市現(xiàn)代性時(shí)有困惑,身處保守的中產(chǎn)階級傳統(tǒng)和新時(shí)代女性的夾擊之間。他在經(jīng)濟(jì)上不夠獨(dú)立,不能隨心地娶他所愛的女人,又無力抵御富家千金的誘惑。記者身份增加了他的自信,卻無法消除他的困頓,他效力的報(bào)社本身因經(jīng)濟(jì)原因處于風(fēng)雨飄搖之中,而又竭力報(bào)道著世界的風(fēng)風(fēng)雨雨。阿維德順?biāo)浦鄣赝瓿闪藢橐黾盎橥馇榈倪x擇,像無以果腹的人摘下長在必經(jīng)之路邊上的果子,他選又沒得選,卻早晚得選。這人看上去苦澀而彷徨,自作自受、自相矛盾,也正因?yàn)槿绱耍牌鹾狭巳说钠毡槿觞c(diǎn),促生了作品經(jīng)久不衰的生命力。
小貓雅各布和美德
瑟德爾貝里的文字率真而優(yōu)美,沒有同時(shí)代作品難以擺脫的道德宣講。也給讀者充分留白,開放的文本和他對事物難免懷疑的態(tài)度相當(dāng)吻合。關(guān)于道德,瑟德爾貝里寫過這樣的插曲:
“兒時(shí)的我對善惡還挺了解,后來忘了。兒時(shí)我確信小貓抓老鼠很乖,嘴里叼著小鳥走來就太淘氣,我對這些就跟知道二二得四一樣確信……記得某年夏天我們住在鄉(xiāng)下,那是個(gè)星期日,我們受邀去教區(qū)長家就餐。餐桌擺在花園里。突然……黑白斑點(diǎn)的小貓雅各布?xì)舛ㄉ耖e地走來,嘴里叼著只小燕雀。教區(qū)長震怒,起身在整個(gè)花園里追逐小貓,好將美德鞭打到它罪惡的皮毛里。與此同時(shí),烤鴨涼了。貓爬到了一棵樹上,牧師帶著懸而未決的案子走回來:實(shí)在抱歉,朋友們,我急躁;看到貓將它那食肉動物的牙齒咬在無辜的小鳥身上,我內(nèi)心十分不安。給我夾塊鴨肉,親愛的媽媽!”
帶著對道德的模糊性的洞察力,瑟德爾貝里從不對道德問題做簡單的回答。當(dāng)他不得不直面這些難題時(shí),往往用詼諧和諷刺來應(yīng)對。那并不意味著圓滑和失真,有時(shí)反因?yàn)楸普娑@得尖銳,就比如阿維德在海島夏夜親吻莉迪亞時(shí)的那段關(guān)于處女貞操的聯(lián)想。
被嚴(yán)肅對待的虛無
在留下的照片或圖畫上,瑟德爾貝里總一臉嚴(yán)肅,像一個(gè)命中注定的苦惱人,偏這苦惱人嚴(yán)肅地跌入了一場玩不起的游戲。
瑟德爾貝里很欣賞中國詩歌,有人因此覺得他的精神世界里有著從中國文化中感染的些許特色,比如說帶著憂郁的宿命論。
處女作小說《錯(cuò)覺》的黑白線描看似簡單卻意味深長,不乏幽默,基調(diào)冷而悲,其后的作品里的諸多元素、主題,對人生懷疑的態(tài)度都已深埋下去。像土里的水仙花球,一旦三月春暖便冒出綠葉、開出相同又不同的花。男主角難定生活方向,站在深淵邊。他也想走向大眾認(rèn)可的幸福和成功,可這條路上荊棘叢生。
接著的幾部小說都涉及男主人公不被祝福的愛情,不愿適應(yīng)主流模式、又不得不隨波逐流的無奈,都書寫了人與存在的搏斗。
《馬丁·伯克的青春》的憂郁里時(shí)而閃過清冽的思想光亮。馬丁本想成為詩人和自由思想者,而冬夜凍結(jié)了詩歌、幻想和青春。瑟德爾貝里以食物置于冰上給粘住作比,又寫到,“我曾渴望在巨大的激情之火中燃燒。它從沒來過,要么是因?yàn)槲也慌浍@得這么大的榮譽(yù)。”后來馬丁懷疑這樣的火更像快樂之火,火卻不是他的元素。他只和冰雪相關(guān),“一旦真正的春天的太陽進(jìn)入我的生活,我很快會腐爛”。最終,馬丁走入永不消散的冬霧。小說帶著瑟德爾貝里內(nèi)心的悸動呈現(xiàn)了幻滅。
《格拉斯醫(yī)生》讓一名醫(yī)生坦露一生中的重要經(jīng)歷和情感。年已30歲,渴望崇高的愛情又一日日被空虛吞噬。年輕而美麗的牧師太太海爾嘉向醫(yī)生坦白婚內(nèi)強(qiáng)奸、無法離婚的隱情,希望醫(yī)生幫她找個(gè)借口,好擁有身體的獨(dú)立。格拉斯醫(yī)生很快明白海爾嘉的情人是誰, 卻沒停止對海爾嘉的單戀。牧師讓醫(yī)生給弄死了。牧師的消失并不意味著活著的人的難題消失,海爾嘉遭到情人背叛,對格拉斯醫(yī)生內(nèi)心的掙扎一無所知。一切結(jié)束時(shí),除了寒冬和空虛,再沒有別的。
青春片段還未從記憶里消失,現(xiàn)實(shí)婚姻無法消除靈魂的困頓。阿維德幾乎是個(gè)不錯(cuò)的男人,工作勤懇、對他人友善,按生活慣性對待妻子,但他找不到更大的生活意義,和莉迪亞的偷情成了一管麻醉劑。他背叛妻子又被情人背叛。從一場游戲中醒來,他發(fā)現(xiàn)周圍是可怕的虛空。
《格拉斯醫(yī)生》里運(yùn)作的是離奇的謀殺情節(jié),在《嚴(yán)肅的游戲》里,情色以軟刀子殺人,但整個(gè)故事距日常世界很近而更具普遍意義。它的動人之處還在于對夢想和現(xiàn)實(shí)的雙重遠(yuǎn)離,對是與非的不置可否。
瑟德爾貝里曾企圖尋找兩個(gè)靈魂和兩個(gè)身體完全融合的情愛。斯特林堡讓愛情變成一場權(quán)力爭斗,瑟德爾貝里則讓男女在生命的舞蹈中相吸相斥,曲終人散而見生之虛空。
如幻如夢、無法駕馭,情色如此,人生和世界亦如是。《嚴(yán)肅的游戲》里個(gè)人情感的虛無只是大世界虛無的一個(gè)縮影。在更大的世界里,報(bào)社隨時(shí)有倒閉的危險(xiǎn),挪威鬧著和瑞典脫鉤,歐洲彌漫著戰(zhàn)爭風(fēng)云。世界是一個(gè)更大的虛空,這是瑟德爾貝里傳達(dá)的嘆息,他的思想和感知并不積極,卻是真實(shí)的、現(xiàn)代的、因而能傳至久遠(yuǎn)的。他和他的男主人公一樣與世界有天生的游離,而這樣的他也是同時(shí)代人忠誠的記錄者和敏銳的心靈觀察者。帶著壓抑的悲哀和不情愿的宿命感,看穿了謊言和幻覺的他,曾于斯德哥爾摩的石子路上,在克拉拉教堂的鐘聲里踽踽獨(dú)行。
想做社會的靈魂
情色和人生問題上的幻滅感沒讓瑟德爾貝里徹底遁入書齋,比懷疑和幻滅更強(qiáng)大的是他的真誠和勇氣。1922年問世的第三部戲劇《命運(yùn)之時(shí)》以一次大戰(zhàn)為背景,包含對戰(zhàn)爭爆發(fā)機(jī)制的分析,描繪了人文主義與民族主義、軍國主義的斗爭。1930年代,瑟德爾貝里呼吁世界沉睡的良心,反對狂熱主義和好戰(zhàn)思想,強(qiáng)調(diào)納粹主義意味著文明的最終衰落。瑟德爾貝里對1930年代德國事態(tài)的洞察引人矚目,如阿維德年輕時(shí)夢想成為的那樣,他被譽(yù)為社會的靈魂。他對納粹主義和好戰(zhàn)思想的警惕,在今日仍有現(xiàn)實(shí)意義。
瑟德爾貝里過早拋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對世界文學(xué)來說是一大損失。從翻譯語種的數(shù)量、圖書借閱量、再版數(shù)、影視和舞臺上的亮相頻率看,瑟德爾貝里的小說是瑞典乃止北歐文學(xué)中最具生命力的。他寫出了瑞典文學(xué)中最完美、最溫婉,深刻而敏銳的書頁。文本折射著時(shí)代,不機(jī)械、不被動,以文學(xué)虛構(gòu)調(diào)動了自身的觀察和體驗(yàn)。他的記錄自然流暢又暗藏精巧構(gòu)思,讓夏和冬都傳達(dá)出象征的意義。在他年僅30歲前后留下的文字里有許多難以復(fù)制的成分:明澈如赤子,詩意和激情如青年,洞察人的虛偽和生的虛幻如垂暮老人。他描摹時(shí)代畫卷,人的行動和情感和國內(nèi)外時(shí)事、和斯德哥爾摩的建筑和四季互為生命的證人。克拉拉教堂的鐘聲今猶在,阿維德和達(dá)格瑪走過的橋也在,莉迪亞挽著未婚夫走過的動物園島上的小徑仍是個(gè)最美麗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從1890年代初開始,瑟德爾貝里出色地翻譯了不少詩歌和小說。這些詩人和作家包括敏感的J.P. 雅各布森、頹廢而審美的波德萊爾、懷疑論者海涅、古典自然主義者莫泊桑。瑟德爾貝里仿佛按自身的色調(diào)挑選了他們。我總覺得那個(gè)尖刻而銳利的麥克爾和看似懦弱的阿維德是瑟德爾貝里的兩面,麥克爾談起混亂的意大利局勢時(shí)說:“我們活在一個(gè)好戰(zhàn)的時(shí)代,兄弟。奸淫,奸淫,永遠(yuǎn)是戰(zhàn)爭和奸淫,別的什么都不時(shí)髦,莎士比亞這么說。今日依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