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xiǎn)的關(guān)系》:法國(guó)大革命序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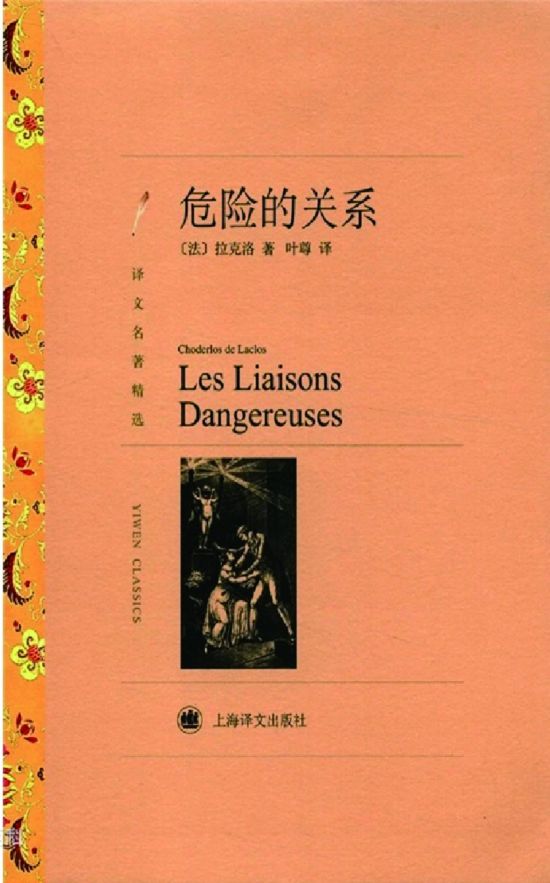
2013年“巴士底紀(jì)念日”(Bastille Day)當(dāng)天,法國(guó)媒體評(píng)選出文學(xué)史上與法國(guó)大革命主題相關(guān)的十大杰作:狄更斯《雙城記》排名第二,榮登榜首的是拉克洛《危險(xiǎn)的關(guān)系》(Les Liaisons Dangereuses)。
《危險(xiǎn)的關(guān)系》(1782)是法國(guó)文學(xué)史上一部“奇書”,也是作者肖代洛·德·拉克洛(Choderlos de Laclos,1741-1803)平生唯一一部小說。這部小說的創(chuàng)作素材,據(jù)曾在拿破侖軍隊(duì)擔(dān)任軍需副官的文學(xué)家司湯達(dá)考證,主要源自行伍出身的拉克洛所部駐扎在法國(guó)東南部小鎮(zhèn)格勒諾布爾的一段生活經(jīng)歷——當(dāng)?shù)氐摹澳贻p人時(shí)常從他們富有的情婦那里接受饋贈(zèng)。他們用這一筆收入為自己添置華麗的服飾,并有余力包養(yǎng)另外一些較為貧困的情婦”。因此,拉克洛才有機(jī)會(huì)對(duì)上流社會(huì)的婚姻情感生活進(jìn)行近距離的深入觀察。不僅如此,小說中描繪的男女逐愛的種種攻防計(jì)策,多半也和小說家本人的軍事專業(yè)息息相關(guān)——1792年,法國(guó)大革命領(lǐng)導(dǎo)人丹東任命拉克洛為行政委員,負(fù)責(zé)改組共和國(guó)炮兵部隊(duì)(青年拿破侖為其麾下一員)。該部在與“反法同盟”首次較量的決定性戰(zhàn)役——瓦爾密(Valmy)戰(zhàn)役中表現(xiàn)勇猛,成功擊潰普奧聯(lián)軍,拉克洛一戰(zhàn)成名。
返回巴黎后,受貴族友人引薦,拉克洛出任攝政王奧爾良公爵的私人秘書,后者號(hào)稱思想開明,贊同革命,是波旁王室的“另類”。在此期間,拉克洛不僅對(duì)宮廷權(quán)謀及貴族生活有了更為全面的了解,同時(shí)也有機(jī)會(huì)結(jié)識(shí)米拉波、塔列朗等政治領(lǐng)袖——可惜他本人作為奧爾良公爵“代言人”提出的改革方案無一被采納。大革命期間,拉克洛兩度被捕入獄。第一次是1793年,他被誣告“里通外國(guó)”,極有可能以“叛國(guó)罪”判處死刑。幸而此時(shí)前線戰(zhàn)事吃緊,需要用到他不久前發(fā)明的一種威力無比的空心炮彈,于是他被釋放,去軍中充當(dāng)教官,“戴罪立功”。然而大約半年后,他再度被捕,因?yàn)樗欣实荣F族流亡美國(guó)之前,成功說服奧爾良公爵之子路易·菲利普(后繼位查理十世,加冕為法國(guó)國(guó)王)一同前往。如此一來,為奧爾良公爵家族出謀劃策的拉克洛自然難脫干系——后得丹東援手,才僥幸逃過一劫。大革命期間,拉克洛前后共被關(guān)押13個(gè)月。出獄后,他第一時(shí)間向公安委員會(huì)提交《論戰(zhàn)爭(zhēng)與和平》的備忘錄,主張收復(fù)法國(guó)失地,無果。此后,拉克洛心灰意冷,退出政壇,直到拿破侖稱帝,他才得以東山再起。他被提拔為準(zhǔn)將,率部加入意大利軍團(tuán),于1803年不幸染疾身亡。
從表面來看,《危險(xiǎn)的關(guān)系》與作者跌宕起伏的人生閱歷似乎并無直接關(guān)聯(lián)。小說以書信體形式,刻畫路易十五時(shí)代末期上流社會(huì)的一樁驚天丑聞,或更準(zhǔn)確地說,是由兩樁陰謀交織勾連所造成的一出人間悲劇:巴黎名媛梅爾特伊侯爵夫人意欲報(bào)復(fù)喜新厭舊的熱爾庫(kù)爾伯爵,寫信請(qǐng)求老情人瓦爾蒙子爵出手相助——后者正企圖勾引年輕貌美的修道院院長(zhǎng)夫人都爾維爾。一方面,熱爾庫(kù)爾伯爵拋棄侯爵夫人后,有意迎娶富家女塞西爾。塞西爾對(duì)年長(zhǎng)的伯爵無感,但對(duì)風(fēng)流倜儻的當(dāng)瑟尼騎士一見傾心——在侯爵夫人暗中撮合之下,兩位年輕人悄然展開地下戀情。而另一方面,院長(zhǎng)夫人無力抵擋瓦爾蒙的連環(huán)計(jì),屈身成為他的情婦,但不久便察覺這位浪蕩子并非出于真愛而只是習(xí)慣性玩弄與淫狎——傷心之下,她遁入修道院,抑郁而亡。故事結(jié)尾,瓦爾蒙至侯爵夫人處,欲與之重續(xù)前緣,卻意外發(fā)現(xiàn)其臥榻已由當(dāng)瑟尼騎士捷足先登。在隨之而來的一場(chǎng)決斗中,瓦爾蒙被刺,臨終前將與侯爵夫人共同陰謀策劃的往來書信悉數(shù)公之于眾。侯爵夫人身敗名裂,被上流社會(huì)永久驅(qū)逐。
書信體是18世紀(jì)流行的小說樣式。孟德斯鳩《波斯人信札》和歌德《少年維特的煩惱》在文學(xué)市場(chǎng)大獲成功,同時(shí)也吸引了更多讀者的關(guān)注。此外,拉克洛在本書卷首所引用盧梭的《新愛洛伊斯》,以及書中院長(zhǎng)夫人的枕邊讀物——英國(guó)傷感小說鼻祖塞繆爾·理查森的《克拉麗莎》也同樣采用書信體裁。相對(duì)而言,后兩本書——尤其是《克拉麗莎》——對(duì)拉克洛無疑影響更大。小說同名女主克拉麗莎性格忠貞,但終究未能抵御浪蕩子的誘惑,同意與其私奔,結(jié)果卻無端遭遇強(qiáng)暴,傷心絕望而死。理查森以描畫人物心理見長(zhǎng),但論及小說的謀篇布局及敘事手法,拉克洛明顯要?jiǎng)俪鲆换I。
《危險(xiǎn)的關(guān)系》全書由12位大小人物總共175封書信構(gòu)成,正如拉克洛手中的一副紙牌——上流社會(huì)的紙牌游戲(card game)的確是書中反復(fù)出現(xiàn)的場(chǎng)景——他縝密計(jì)算各色人等在每一局交鋒中的得分失分,并以此決定他們的出場(chǎng)順序及篇幅長(zhǎng)短。比如他筆下的男主瓦爾蒙戲份最足:這位青年貴族既是花花公子,又是劍術(shù)高超的武士,他相信勾引是一門“戰(zhàn)爭(zhēng)”的藝術(shù),因此僅僅占有肉體毫無樂趣可言——他的目標(biāo)是要將對(duì)方從意志到精神徹底摧垮,讓她徹底淪為自己的玩偶。以他的標(biāo)準(zhǔn),被勾引者越是不甘順服,越能激發(fā)他的斗志,而美貌貞潔的院長(zhǎng)夫人恰好便成為他的理想獵物。值得注意的是,拉克洛對(duì)待小說人物,既不像盧梭那樣雄辯理性——試圖通過道德說教感化讀者,也不像理查森那樣傷感濫情——通過描寫不幸身世打動(dòng)人心。相反,他不動(dòng)聲色,仿佛一名冷酷無情的訓(xùn)練官操演他的士兵。作為一名精通軍事防御工事營(yíng)造的炮兵將軍,同時(shí)也是深諳宮廷政治斗爭(zhēng)技巧的資深政客,這樣的排布和演練對(duì)小說家而言可謂毫不費(fèi)力,只要保持他一貫?zāi)恢弥摹氨旧奔纯伞H蘸蟛ǖ氯R爾評(píng)價(jià)《危險(xiǎn)的關(guān)系》時(shí)斷言:“這本書要是能燃燒,只能像冰一樣燃燒”——正表明詩(shī)人對(duì)拉克洛這位“不可靠敘述者”客觀中立態(tài)度的認(rèn)同和欣賞。
或許正是作者這樣一副事不關(guān)己高高掛起的態(tài)度,激起了道德人士對(duì)本書的強(qiáng)烈憤慨。本書不僅有色情小說常見的“露骨”描畫(僅此一項(xiàng)便足以將它查封),而且頗具無神論色彩——宗教與道德緊密相連,而本書通篇沒有哪一位人物具備道德責(zé)任感。更要命的是,本書外表描畫男女私情,其實(shí)是影射宮廷政治——作者本人是大革命前期臭名昭著的“陰謀家”,慣于造謠生事,四處煽風(fēng)點(diǎn)火,與活躍政壇的其他一些小冊(cè)子作家(如米拉波)一樣居心叵測(cè)。
對(duì)于任何一部意圖難以界定的文學(xué)作品,最簡(jiǎn)單粗暴的方法便是將它打上“色情”標(biāo)簽而后封禁銷毀。與拉克洛同時(shí)代的薩德侯爵(年齡相差一歲)幾乎每一部作品都難逃厄運(yùn)——這些“色情”小說大多在監(jiān)獄中完成,作家本人最后也老死于巴士底獄。對(duì)拉克洛極為仰慕的19世紀(jì)文學(xué)大師司湯達(dá)的《紅與黑》以及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也同樣長(zhǎng)期遭到封殺。與上述文學(xué)名著命運(yùn)相似,出版不久,《危險(xiǎn)的關(guān)系》在巴黎被查封,罪名是“違背公德”“傷風(fēng)敗俗”。盡管時(shí)至今日,本書已取代盧梭《新愛洛伊斯》堂而皇之步入法國(guó)文學(xué)經(jīng)典,其印數(shù)也遠(yuǎn)超《紅與黑》《包法利夫人》《茶花女》以及《追憶似水年華》等名著,但在近200年時(shí)間內(nèi),這部一度暢銷(首印2000冊(cè)兩周內(nèi)售罄,在當(dāng)時(shí)堪稱現(xiàn)象級(jí)事件)的文學(xué)經(jīng)典卻始終與讀者“緣慳一面”,令人不勝唏噓。
平心而論,盡管書中不乏性愛描寫——比如侯爵夫人設(shè)計(jì)誘惑巴黎一名風(fēng)流騎士,待他黑夜闖入閨房后又控告他非禮,甚至還有同性之愛——比如侯爵夫人與純情少女塞西爾互生情愫,但總體而言,作者并未像色情作家那樣大肆渲染,而只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這既體現(xiàn)出小說家駕馭題材的能力,更反映出他的文學(xué)品位。舉個(gè)例子,侯爵夫人在致瓦爾蒙信中透露:與騎士共浴愛河之前,她需要通過閱讀色情小說提升“性趣”——而她所讀的并非坊間流傳的薩德,而是另一位小說名家小克雷比永(Crébillon fils)的色情政治諷喻(erotic political satire)作品《索法》(Le Sopha)——小說家本人曾因著文嘲諷當(dāng)朝大臣紅衣主教羅昂(Cardinal de Rohan)而被判監(jiān)禁。從這個(gè)角度看,正如評(píng)論家所說,與其說拉克洛近于薩德,不如說他更近于盧梭。
米蘭·昆德拉在關(guān)于“小說的藝術(shù)”講座中曾指出,《危險(xiǎn)的關(guān)系》一書中人物別無所求,“唯有尋歡作樂”——或許這也是本書被指為“道德感缺失”的一個(gè)主要原因。以聲名狼藉的侯爵夫人(波德萊爾稱之為“撒旦式的夏娃”)為例,她生活放蕩,人格卑劣,其人生信條為“愛情只是尋歡作樂的一個(gè)借口——即淫蕩的代名詞”。她善于操控他人(男女通吃),為達(dá)目的不擇手段,堪稱貴族階層道德敗壞之典型。拉克洛通過這一人物形象展現(xiàn)貴族的腐朽沒落和荒淫無恥,用他自己在本書“序言”中的話說,“揭穿道德敗壞者用來腐化有德者的伎倆,這是為社會(huì)風(fēng)尚的純潔凈化立了一功”。換言之,他的本意是要像先賢塞萬提斯一樣,做一篇警世的教育小說——可惜世人誤會(huì)了他的良苦用心。
此處便涉及本書題旨之爭(zhēng)的核心問題,即這部小說更大的問題“不在其淫,而在其誨淫”。在批評(píng)家看來,拉克洛刻意將侯爵夫人描畫成“女唐璜”的形象——在中世紀(jì)以來的歐洲文學(xué)傳統(tǒng)中,唐璜是始亂終棄、戰(zhàn)無不勝的浪蕩子原型,而侯爵夫人的一大“愛好”恰好也是先讓男人拜倒在石榴裙下,而后再將他一腳踢開,從中獲取絕對(duì)征服的快感。與唐璜津津樂道的愛情冒險(xiǎn)(羅曼司)相比,侯爵夫人的“玩火”行徑不僅踐踏男性尊嚴(yán),而且也是對(duì)傳統(tǒng)社會(huì)價(jià)值觀的徹底“顛覆”——這樣的指控,顯然要比“有傷風(fēng)化”的罪名嚴(yán)重得多。
似乎對(duì)“含沙射影”“誨淫誨盜”之類攻訐之詞早有預(yù)判,拉克洛在“序言”中明明白白作出交代,并告誡讀者請(qǐng)勿對(duì)號(hào)入座——本書中“有好些人道德品質(zhì)如此敗壞,很難想象他們?cè)谖覀冞@個(gè)世紀(jì)中生活過。我們這個(gè)世紀(jì)是哲學(xué)的世紀(jì),智慧的光芒普照每個(gè)角落,眾所周知,我們所有的男人都是循規(guī)蹈矩、彬彬有禮的,我們的女人個(gè)個(gè)都是雍容持重、端莊嫻靜的……我們的意見是,如果這部作品里敘述的事件是真實(shí)的,那么這些事件只能發(fā)生在別的地方,別的時(shí)代。”如果說作者卷首引用盧梭的“正風(fēng)俗論”——“我目睹了當(dāng)代的習(xí)俗風(fēng)尚”——僅僅是掩人耳目,則此處的告白無異于宣告此地?zé)o銀。
正如歷史教科書所言,大革命的爆發(fā)與法國(guó)的社會(huì)等級(jí)制度密切相關(guān)。作為權(quán)貴的第一等級(jí)(教士僧侶,如書中修道院院長(zhǎng))和第二等級(jí)(貴族領(lǐng)主,如書中瓦爾蒙子爵以及當(dāng)瑟尼騎士)屬于特權(quán)階層,他們擁有世襲的爵位(通常附帶城堡或莊園等大塊地產(chǎn),以及大筆年金),并在其領(lǐng)地上建立起自己的“獨(dú)立王國(guó)”——憑借特權(quán),他們總能從法律中找出漏洞,合理“避稅”,從而得以盡享優(yōu)渥生活,肆意揮霍浪費(fèi)。相反,整個(gè)法蘭西王國(guó)的財(cái)政收入都只能依靠對(duì)第三等級(jí)(如書中受瓦爾蒙救助的農(nóng)夫,以及女仆)的剝削和壓榨。貴族無所事事,華服盛裝出席貴婦名媛的晚宴或許是他一天當(dāng)中最緊要的事務(wù)——如何體面優(yōu)雅地打發(fā)一天(或一生)的時(shí)間可能是他全部的生活目標(biāo)。而第三等級(jí)的平民大眾終日勞碌卻食不果腹,并且時(shí)時(shí)有遭遇權(quán)貴凌辱的危險(xiǎn)(如《雙城記》中的馬內(nèi)特醫(yī)生),因此貴族與平民的仇恨愈演愈烈,階級(jí)矛盾也日益加深,大革命一觸即發(fā)。
這也是《危險(xiǎn)的關(guān)系》最重要的歷史和時(shí)代背景——“危險(xiǎn)的”不僅是男女關(guān)系,更是等級(jí)關(guān)系。作為大革命前后歷史的參與者和見證者,拉克洛不可能真正超然物外,對(duì)迫在眉睫的“危險(xiǎn)”熟視無睹。他的友人米拉波在報(bào)刊發(fā)表雄文《論逮捕密札與國(guó)家監(jiān)獄》,矛頭直指臭名昭著的“國(guó)王密札”(即空白逮捕令),向王權(quán)絕對(duì)專制發(fā)出挑戰(zhàn)。拉克洛身在體制內(nèi),無法像摯友一樣直抒胸臆,而他更欣賞的是同時(shí)代另一位著名文人莫夫爾·安杰維勒(Mouffle d'Angerville,或譯當(dāng)熱維爾)的反諷筆法——后者著《路易十五的私生活》(Vie privée de Louis XV),以史家的紀(jì)實(shí)手法將君主(及情婦)和廷臣的腐敗、國(guó)家財(cái)政的揮霍、以及民眾的深重苦難一同展現(xiàn)在世人面前。與之相似,拉克洛也以“紀(jì)實(shí)”的筆法,揭露宮廷貴族的生活糜爛和道德淪喪。
對(duì)封建王權(quán)及舊制度(Ancien Régime)的擁護(hù)者而言,這顯然屬于別有用心的顛覆和解構(gòu)。正如作家本人在書信中所說,大革命前夕,“宮廷”一詞不再像路易十四時(shí)代那樣令人肅然起敬、望而生畏:經(jīng)過小冊(cè)子作家的大肆渲染,生性暗弱的國(guó)王路易十六及縱情享樂的王后安托瓦內(nèi)特雙雙淪為笑柄——尤其是關(guān)涉王后與羅昂紅衣主教的“鉆石項(xiàng)鏈?zhǔn)录敝螅癖妼?duì)于沿襲數(shù)百年的法國(guó)君主制可謂好感全無,封建王權(quán)已呈搖搖欲墜之勢(shì)。照拉克洛的看法,18世紀(jì)中期之前,法國(guó)朝野上下僅有少數(shù)人具備革新思想,期待一場(chǎng)革命風(fēng)暴,而18世紀(jì)80年代前后,由于各類啟蒙思想讀物及地下宣傳手冊(cè)的散播(奧爾良公爵府邸四周的咖啡館乃信息中心),革命思想已深入人心,而正是這一思想觀念的變遷最終引發(fā)了法國(guó)大革命。由此,波德萊爾作出如下研判,沒有什么能比這類“有傷風(fēng)化”的小說“更能說明和解釋法國(guó)大革命”。從這個(gè)角度看,拉克洛《危險(xiǎn)的關(guān)系》堪稱是當(dāng)之無愧的“法國(guó)大革命序曲(prelu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