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禁區(qū)”到暢銷:川端康成作品在中國

在中文世界對川端康成的標準化簡介中,“日本新感覺派作家”是出現(xiàn)頻率最高的標簽之一。所謂“新感覺派”,是受到歐洲現(xiàn)代主義文學強烈影響而最早出現(xiàn)在日本的現(xiàn)代主義文學流派,主要形成于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藝術上強調運用象征和暗示手法,表現(xiàn)人在瞬間的主觀感受。
川端康成與橫光利一通常被認為是日本新感覺派作家雙璧,然而支撐起新感覺派的其實多數(shù)為橫光利一的作品。川端康成對這一文學運動的主要貢獻是用一篇論文(《新進作家的新傾向解說》)奠定了理論基礎,他在創(chuàng)作實踐上只有早期幾篇小說符合典型新感覺派的美學氣質。
早在1926年,川端康成就發(fā)表了成名作《伊豆的舞女》,1934年開始發(fā)表代表作《雪國》,1968年因其“敏銳的感受,高超的敘事技巧,表現(xiàn)日本人的精神實質”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相比谷崎潤一郎、芥川龍之介等同時代的日本文學大師,川端康成在中國的譯介其實相當晚近,直到1980年代才開始大規(guī)模地翻譯介紹。
早期的零星介紹
川端康成一生從未到過中國,不像谷崎潤一郎、芥川龍之介都曾在民國年間赴中國旅行,并且留下許多相關文字。1949年前的中國對于川端康成的了解十分有限。
偽滿洲國時期發(fā)行的刊物《華文大阪每日》1940年第4卷第10期上,署名為“許穎”的作者發(fā)表了《當代最有絢爛風格的作家川端康成》一文,詳細介紹了川端康成其人其文,以及他和同輩作家群體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的異同,例如把他和橫光利一比較:“川端康成沒有似橫光利一那般雄厚的意志,而他則有強烈的抒情氣質,橫光的作品有建筑構造之穩(wěn)重的意味,川端的作品則是流動的,而又閃著光。這是因他更多具有詩人玄微奧妙的感覺。故此,橫光利一的強力,與那多般的成就,是足能代表著新感覺派特色的全部,而比較川端康成立在前面,則僅成為蔥郁的林木中之一株了。”
即使今天看來,這篇1940年的評論文章對川端康成的文學史定位可謂相當準確,指出他盡管經(jīng)歷了諸多日本現(xiàn)代文學流派運動,但始終不為時尚風氣所轉移,而且抓住了川端康成自成一家的美學特質:
作者所有的作品,看去都極似美好的牧歌,但其間總有一絲哀感貫注著。那是來自少年時代所影響的宿命的自覺、冷漠的人生觀,時而漂浮著虛無懷空之感。孤獨感是任何作者所不能免的,自身生活的郁結,經(jīng)文學的思索,而凝成一個觀念。“花”在作品中便常是象征化了的媒介物,舞女、雛妓等類人物的命運,都是這般弱的小花朵,榮華的時日和生命能有多久,一種不吉的預感,散伏各處,作者從美麗的花束上,看到將歸寂滅的面貌,而作者的悲哀,亦正是因他有看穿過去的利眼。
遺憾的是,刊發(fā)這篇文章的《華文大阪每日》雜志是抗戰(zhàn)時期日本侵略者為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唱贊歌而創(chuàng)辦的,以政治宣傳、文藝創(chuàng)作與評論為主,偏重文學創(chuàng)作。《華文大阪每日》創(chuàng)刊于1938年11月1日,起初為半月刊,1944年1月改為月刊,歷時七年,共刊行141期。該刊在日本本土編印,由大阪每日新聞社、東京日日新聞社聯(lián)合編輯(后改由大阪每日新聞社單獨承辦),專門在中國東北、華北、華中地區(qū)發(fā)行。

1935年《文藝畫報》第3期載“世界文壇漫畫巡禮”中的川端康成漫畫:“川端康成的神經(jīng)愈來愈尖銳連犬語也懂得了”
1942年,著名編輯、出版家范泉翻譯了川端康成的隨筆選集《文章》,該書作為“復旦大學中文組讀物叢刊”第三種由復旦出版社發(fā)行。在譯者“前記”中,范泉交待了自己選譯這本小書的緣由:
口語體的文章,對于文語體的文章而言,可以說是一種激烈的革命。但口語體的文章本身,應當不斷地革命,因為都市生活等等漸漸地變得繁忙,以目前為止的文章來表現(xiàn),那是不可能的,或至少是很難抵達理想的完美的境地。于是需要新的文章論的介紹和建立,需要討論關于言語和文章的新問題。
本書的作者便從言語心理學的見地發(fā)掘了新的文章論。他不單說出了這種學說底理論的經(jīng)路,并且還把現(xiàn)代日本作家的表現(xiàn)和文章,用嶄新的看法來批評和研究,企圖能觸及文章論和表現(xiàn)論上的問題。
老作家們的文章為什么總覺得有一種陳舊的感覺呢?無名作家或新作家的文章,為什么總令人嗅到新鮮的香味和調子呢?再進一步地說,老作家們應當怎樣繼續(xù)不斷地去發(fā)掘他們文章的新鮮的香味呢?新作家們應當怎樣確切把握著他們活的言語的吸收和創(chuàng)造呢?
雖然范泉翻譯的《文章》是民國年間出版的唯一一部川端康成作品集,但其中關于作者本人的介紹付之闕如,再加上是文藝理論類的書籍,故而在傳播川端康成方面影響微弱。到1945年左右,范泉又翻譯了幾本日本文學著作,包括吉江喬松《綠的沉默》、島崎藤村《初戀》和中野重治《孩子和花》,他本來準備把這三冊連同川端康成《文章》一起,輯為“現(xiàn)代日本小品譯叢”,交付世界書局印行,可惜后來因故未能印成問世。

《文章》,范泉譯,復旦出版社,1942年
改革開放初期的突破
1968年底,川端康成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的音樂會堂領取了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繼泰戈爾之后第二位獲得此獎的亞洲人,也是第一個獲得此獎的日本作家。瑞典學院常務秘書安德斯·奧斯特林在授獎詞中指出川端康成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兩點意義,“其一,川端先生以卓越的藝術手法,表現(xiàn)了具有道德倫理價值的文化思想;其二,川端先生在架設東方與西方之間的精神橋梁上,做出了貢獻。”

川端康成領取1968年諾貝爾文學獎,并發(fā)表著名演說《美麗的日本與我》
彼時處于“文革”時期的中國對這一重大文化事件的報道近乎空白,何以至此?周朝暉在《川端康成哪去了?》(載《讀書》2016年第4期)一文中曾有說明,原來“文革”開始后不久,川端康成、石川淳、安部公房、三島由紀夫四個日本文壇重量級作家在《東京新聞》刊發(fā)聯(lián)名宣言,對“文革”表達抗議,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川端康成被列入“黑名單”也就不難理解了。
三島由紀夫是川端康成交往多年的密友,信奉日本武士道和軍國主義精神,1970年他試圖闖入自衛(wèi)隊嘩變的計劃失敗后剖腹自殺。就在三島自殺的17個月后,1972年4月16日,川端選擇用口含煤氣管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沒有留下任何遺言,以至于川端自殺原因成為不解之謎。
1978年,中國迎來改革開放的同時,和日本簽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自此開啟兩國蜜月期,文化界的合作交流日益增多,川端康成及其作品才開始逐步“解禁”,從而被國內的日語譯者大量譯介。
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7月出版侍桁翻譯的《雪國》,是改革開放之后國內出版的首部川端康成作品,內含《雪國》《伊豆的舞女》兩個中篇小說。1985年,侍桁又和金福合作,繼續(xù)在上海譯文出版社推出了《古都》的譯本。

《雪國》,侍桁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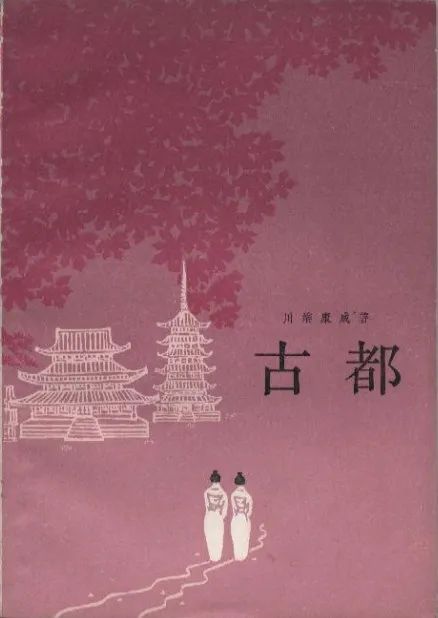
《古都》,侍桁、金福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
侍桁(1908-1987),原名韓侍桁,生于天津,早年曾留學日本,與魯迅交好。上世紀30年代,韓侍桁寫有大量文藝作品和批評文章,一度參加“左聯(lián)”,后轉向“第三種人”。在1930年代初文壇關于“第三種人”的論爭中,韓侍桁站在“第三種人”一方,與“左聯(lián)”文人展開爭論,從而被魯迅指責搞“第三種文學”。
韓侍桁與日本現(xiàn)代文學結緣甚早,1929年春潮書局就出版了他選譯的《現(xiàn)代日本小說》,只不過彼時川端康成剛在日本文壇嶄露頭角,故而未有篇目選入。作為翻譯家,韓侍桁在民國年間最重要的貢獻莫過于譯出了丹麥文學史家勃蘭兌斯的巨著《十九世紀文學之主潮》(現(xiàn)多譯為《十九世紀文學主流》),前四卷由商務印書館在1936到1939年間陸續(xù)出版,后兩卷則未能印行成書。1949年后,韓侍桁先后在齊魯大學、上海編譯所、上海譯文出版社供職,為外國文學翻譯事業(yè)做出了卓越貢獻。
改革開放初期,同為老翻譯家的川端康成譯介者,還有李正倫。李正倫生于1918年,河北樂亭人,大連語言學校日語科畢業(yè),歷任中央文化部電影局秘書科翻譯,中國電影出版社外國電影編輯室編輯、翻譯、副譯審等職,在日本電影文學劇本翻譯方面成就顯著,主要譯作有《蛛網(wǎng)宮堡》《七武士》《羅生門》《生死戀》《故鄉(xiāng)》《人的證明》等近百部。
1984年,中國電影出版社出版了李正倫翻譯的《古都》,該書被收入“外國影片研究叢書”,內容除了小說原著外,還有據(jù)此改編的同名電影劇本。1980年上映的日本電影《古都》,由市川崑導演,女星山口百惠在其中一人分飾孿生姐妹兩角。山口百惠1974年曾出演由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改編的同名經(jīng)典電影,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紅極一時,《古都》也是她的謝幕之作。
《古都》之外,李正倫在1990年代還接手了川端康成《天授之子》(漓江出版社,1998年)、《美好的旅行》(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1999年)的翻譯工作。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譯介熱潮
1981年韓侍桁翻譯的《雪國》出版兩個月后,山東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由葉渭渠、唐月梅翻譯的《古都·雪國》。與韓侍桁、李正倫等老一輩翻譯家相比,生于上世紀30年代左右的葉渭渠、唐月梅伉儷顯然能在新時期的翻譯事業(yè)上投入更多精力,而他們也正是從翻譯川端康成起步,逐漸成為國內日本文學研究和翻譯界的領軍人物。在多年后的一篇訪談中,葉渭渠回憶了他第一本川端康成譯作出版前后的情形:
我翻譯川端文學,是從70年代末開始的。當時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擔任亞非文學組組長,編輯部決定出版一套“日本文學叢書”,我將《川端康成小說選》作為一卷列入計劃中,主管領導沒有反對,但擔心會引起非議。因為改革開放伊始,人們的觀念還沒有完全開放。此前川端康成是個禁區(qū),有風險。我說:“既然有風險,我來譯好了。”這就是我翻譯川端文學的開始。后來山東人民出版社約我和老唐(葉先生的妻子,唐月梅教授)翻譯川端的作品,我沒敢推薦 《千只鶴》,我就推薦了《雪國》《古都》。我們1979年已翻譯出來,結果在出版社足足拖了一年多。因為有人認為《雪國》是寫“五等妓女”,給妓女唱贊歌的。出版社最后要撤《雪國》,只出《古都》。我們堅持寧愿退稿,也不撤《雪國》,因為《雪國》無論在藝術上還是在影響上都遠大于《古都》。出版社不愿放棄這個選題,于是請示了當?shù)爻霭婢郑@準后又發(fā)生書名排序問題。這個本子定名《古都·雪國》,就是為了淡化《雪國》。(《讓學者回歸學者 學術回歸學術——訪日本文學專家葉渭渠先生》,載《文匯讀書周報》2005年10月1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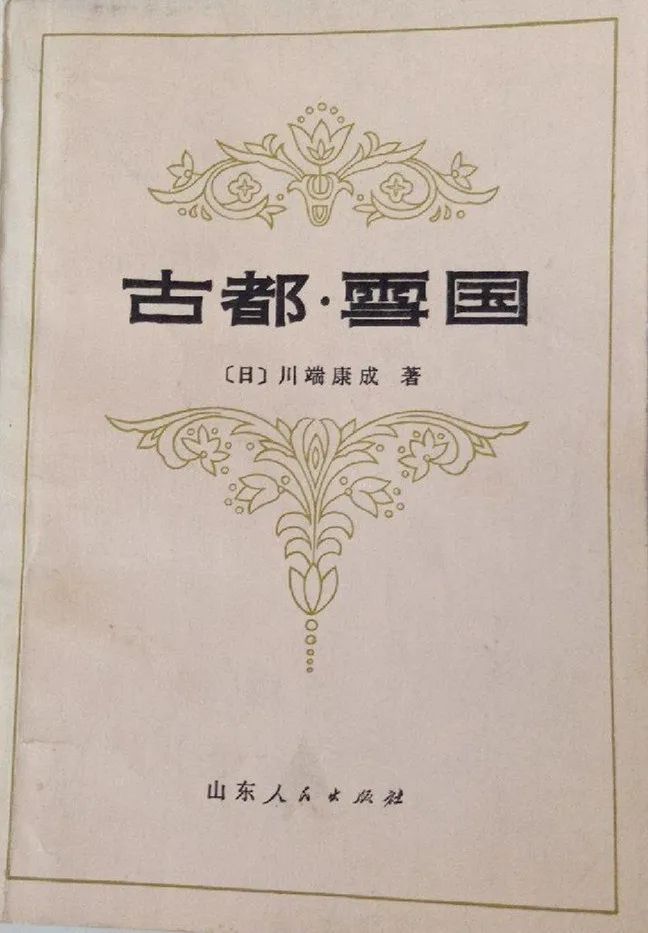
《古都·雪國》,葉渭渠、唐月梅譯,山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
上述提到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川端康成小說選》直到1985年才正式面世,隨后葉渭渠再接再厲,又接連翻譯出版了《川端康成散文選》(百花文藝出版社,1988年)和《川端康成談創(chuàng)作》(三聯(lián)書店,1988年)。
進入1990年代后,葉渭渠、唐月梅伉儷基本包攬了川端康成作品在國內的譯介,整個1990年代,葉渭渠一共主編了四套川端康成作品叢書。第一套是十卷本的《川端康成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二套是三卷本的《川端康成集》(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三套是十卷本的《川端康成作品》(漓江出版社,1998年),第四套是兩卷本的《川端康成少年少女小說集》(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1999年),僅1996年就有兩套川端康成作品集同期出版,當時國內出版市場和讀者對于川端康成作品的饑渴程度可見一斑。

葉渭渠主編《川端康成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與此同時,關于川端康成的傳記和研究著作也呈現(xiàn)井噴之勢,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相關著作包括葉渭渠《川端康成評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何乃英《川端康成》(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譚晶華《川端康成評傳》(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6年)、張國安編著《執(zhí)拗的愛美之心——川端康成傳》(世界圖書出版公司,1996年)、喬遷《川端康成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年)、葉渭渠等主編《不滅之美:川端康成研究》(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1999年)……
葉渭渠2010年因心臟病去世,在他去世的前幾年里,還跟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前編輯同事、蕭乾的夫人文潔若因舊事重提而打了一場筆仗,到最后雙方撕破臉皮、互揭老底,公事私怨間雜其中,搞得很不光彩,孰是孰非,在此不予置評。但客觀地講,葉渭渠早年頂住壓力,敢于突破“禁區(qū)”譯介川端康成和三島由紀夫的作品,這一功績應該是有目共睹。
在早期川端康成中譯本序列中,還有一位譯者的譯本不得不提,即高慧勤翻譯的《雪國·千鶴·古都》(漓江出版社,1985年),收入“獲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叢書”。這套由漓江出版社策劃的叢書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持續(xù)推出,對中國當代眾多詩人、作家產生了深遠影響。
高慧勤(1934-2008)畢業(yè)于北京大學東語系日文專業(yè),也是川端康成、芥川龍之介在國內的重要譯者,她的丈夫就是一個多月前剛去世的著名法語譯者羅新璋(1936-2022)。2000年,高慧勤主編的《川端康成十卷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精裝發(fā)行。

《雪國·千鶴·古都》,高慧勤譯,漓江出版社,1985年
對中國當代作家的影響
經(jīng)過如此大批量、高密度的譯介,時至今日,川端康成早已躍升成為國內知名度最高的日本現(xiàn)代作家之一,甚至進入中學語文課本,被所有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生熟知。不過,深刻受到川端康成作品滋養(yǎng)的,還要數(shù)余華、莫言等中國當代作家。
若論國內作家中誰曾對川端康成推崇備至,余華極有可能排名第一。在余華談閱讀的隨筆散文中,多次提及自己從事寫作之初如何迷戀川端康成:
我是1983年開始小說創(chuàng)作,當時我深受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影響,川端作品中細致入微的描敘使我著迷,那個時期我相信人物情感的變化比性格更重要。我寫出了像《星星》這類作品。這類作品發(fā)表在1984年到1986年的文學雜志上,我一直認為這一階段是我閱讀和寫作的自我訓練期,這些作品我一直沒有收入到自己的集子中去。
由于川端康成的影響,使我在一開始就注重敘述的細部,去發(fā)現(xiàn)和把握那些微妙的變化。這種敘述上的訓練使我在后來的寫作中嘗盡了甜頭,因為它是一部作品是否豐厚的關鍵。(《我的寫作經(jīng)歷》,收入《沒有一條道路是重復的》,作家出版社,2012年)
1982年在浙江寧波甬江江畔一座破舊公寓里,我最初讀到川端康成的作品,是他的《伊豆的舞女》。那次偶爾的閱讀,導致我一年之后正式開始的寫作,和一直持續(xù)到1986年春天的對川端的忠貞不渝。那段時間我閱讀了譯為漢語的所有川端作品。他的作品我都是購買雙份,一份保藏起來,另一份放在枕邊閱讀。后來他的作品集出版時不斷重復,但只要一本書中有一個短篇我藏書里沒有,購買時我就毫不猶豫……川端的作品籠罩了我最初三年多的寫作。(《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遺產》,收入《沒有一條道路是重復的》,作家出版社,2012年)
我曾經(jīng)迷戀于川端康成的描述,那些用纖維連接起來的細部,我說的就是他描述細部的方式,他敘述的目光無微不至,幾乎抵達了事物的每一條紋路,同時又像是沒有抵達,我曾經(jīng)認為這若即若離的描述是屬于感受的方式。川端康成喜歡用目光和內心的波動去撫摸事物,他很少用手去撫摸,因此當他不斷地展示細部的時候,他也在不斷地隱藏著什么。被隱藏的總是更加令人著迷,它會使閱讀走向不可接近的狀態(tài),因為后面有著一個神奇的空間,而且是一個沒有疆界的空間,可以無限擴大,也可以隨時縮小。(《溫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收入《溫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作家出版社,2012年)
對于川端康成最初的這份迷戀,一直被余華記在心間。在2005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兄弟》中,他甚至讓自己虛構的人物與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相遇,這一情節(jié)安排也可以看作是余華對文學偶像的一次戲謔的致敬:
那時候趙詩人和劉作家還在做著文學白日夢,他們知道李光頭弄來了一批日本西裝,立刻跑到了李光頭的倉庫里,扎進了堆積如山的垃圾西裝里。劉作家花了三個小時找到一套“三島”西裝;趙詩人也不示弱,他花了四個小時找到一身“川端”的西裝。我們劉鎮(zhèn)的兩大文豪得意洋洋,見了人就掀開他們的西裝,讓人看看里面“三島”和“川端”的姓氏,他們告訴劉鎮(zhèn)的無知群眾,“三島”和“川端”可是兩個了不起的姓氏,日本最偉大的兩個作家就姓“三島”和“川端”,一個叫三島由紀夫,一個叫川端康成。他們說這些話的時候紅光滿面,好像他們穿上“三島”和“川端”的西裝以后,就是我們劉鎮(zhèn)的三島由紀夫和川端康成了。
如果說余華只是被川端康成無微不至的細部描寫所感染,那么為莫言打開“高密東北鄉(xiāng)”文學世界的短篇小說《白狗秋千架》則直接受到川端康成《雪國》的啟發(fā)。1999年,莫言的長篇小說《豐乳肥臀》在日本翻譯出版后,他首次訪問了日本,并在一系列演講中提到川端康成對他這一代中國作家的影響。在東京的駒澤大學發(fā)表演講時,莫言坦陳:
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我從川端康成的小說《雪國》里讀到了這樣一個句子:“一只黑色壯碩的秋田狗,站在河邊的一塊踏石上舔著熱水。”我感到眼前出現(xiàn)了一幅鮮明的畫面,仿佛能夠感受到水的熱氣和狗的氣息。我想,原來狗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寫進小說,原來連河里的熱水與水邊的踏石都可以成為小說的材料啊!
我的小說《白狗秋千架》的第一句就是:“高密東北鄉(xiāng)原產白色溫馴的大狗,流傳數(shù)代之后,再也難見一匹純種。”這是我的小說中第一次出現(xiàn)“高密東北鄉(xiāng)”的字眼,也是第一次提到關于“純種”的概念。從此之后,一發(fā)而不可收,我的小說就多數(shù)以“高密東北鄉(xiāng)”為背景了。(《神秘的日本與我的文學歷程》,收入《用耳朵閱讀》,作家出版社,2012年)
訪日期間,莫言還參觀了川端康成創(chuàng)作《伊豆的舞女》時住過的名為“湯本館”的小旅館,據(jù)當年與莫言同行的旅日作家毛丹青回憶,莫言的那次日本之旅可謂“神神叨叨”,他甚至相信在“湯本館”遇見了“川端康成顯靈”。假如迷信一點,這件事情和莫言13年后摘得諾貝爾文學獎,沒準有著神秘的關聯(lián)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