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xué)批評》:文學(xué)批評的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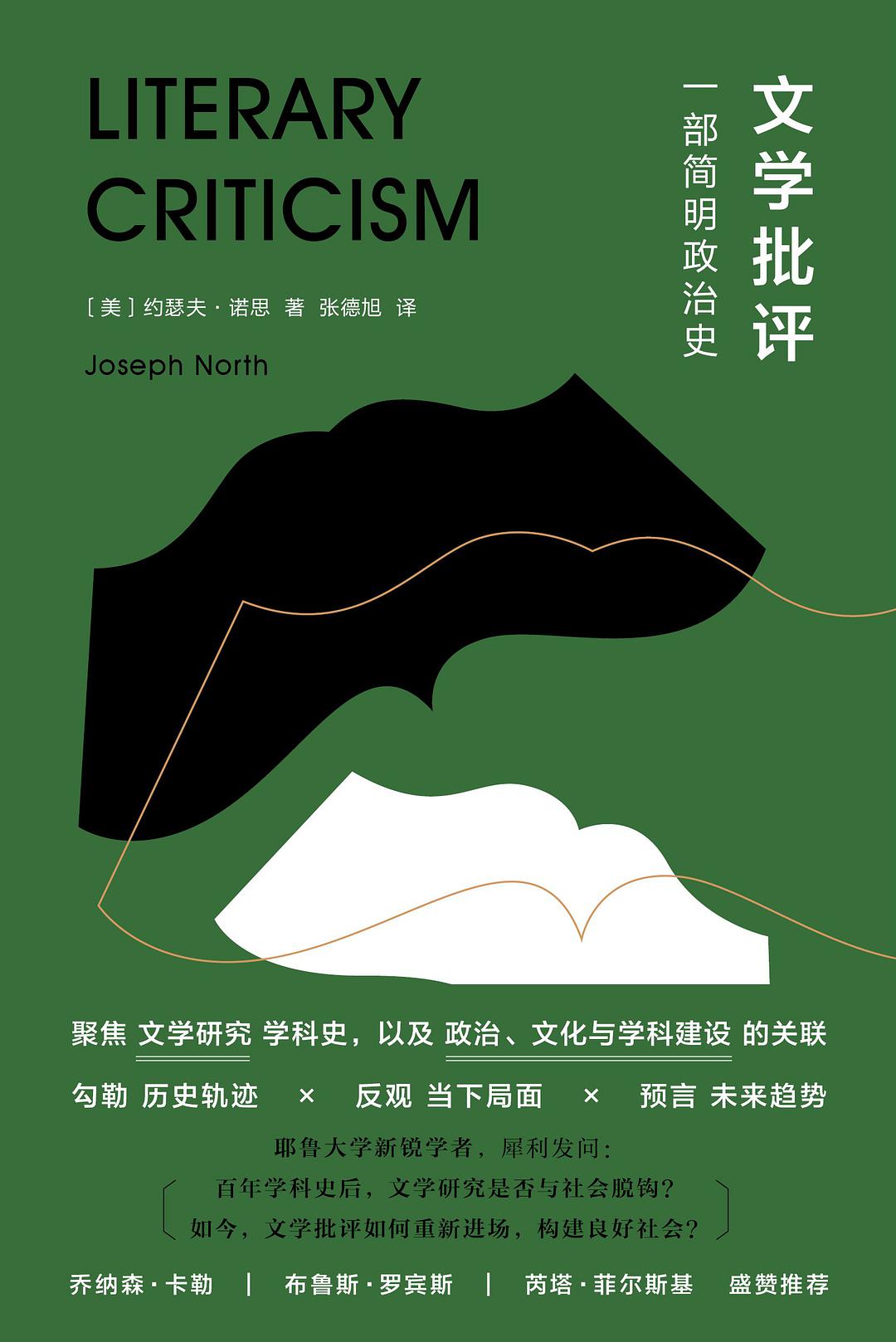
2018年1月4日,美國現(xiàn)代語言協(xié)會(huì)(MLA)舉辦的年會(huì)在紐約六十年不遇的暴雪中如期舉行。當(dāng)我準(zhǔn)時(shí)來到容納百人的最大分會(huì)場,里面已經(jīng)座無虛席了。研討對象是耶魯大學(xué)助理教授約瑟夫·諾思的《文學(xué)批評:一部簡明政治史》(2017年哈佛大學(xué)出版社)。現(xiàn)場討論異常熱烈,大家似乎全然忘記了窗外正在撲簌下落的大暴雪。
除了爆滿的會(huì)場,我隨后在其他幾個(gè)機(jī)構(gòu)場所也見識(shí)了該書獲得的廣泛關(guān)注:各大期刊雜志的書評、美國高校的博士生讀書會(huì)、研究生課程大綱上的必讀書目。這部著作勾勒了一百年來文學(xué)研究的主要范式,指出了這門學(xué)科在當(dāng)下存在的問題,并且對學(xué)科的未來做出規(guī)劃。可想而知,本書的話題性自然能引起學(xué)界的廣泛興趣。從更深層次上看,該書所激發(fā)的巨大關(guān)注,折射了文學(xué)研究在當(dāng)下面臨的學(xué)科危機(jī):它變得過分專業(yè)化,以致失去了原有的生命力和現(xiàn)實(shí)感,與普通人的關(guān)切漸行漸遠(yuǎn)。或許正是對這門學(xué)科在當(dāng)下缺乏合法性的焦慮,人們捧起諾思的書、走進(jìn)他的討論會(huì)場,以求弄清文學(xué)研究到底經(jīng)歷了怎樣的發(fā)展軌跡,以及如何走出當(dāng)前的困局,為文學(xué)研究在經(jīng)費(fèi)短缺的新自由主義高校體系中的合理存在尋覓理據(jù)。
在諾思看來,文學(xué)研究這門學(xué)科的價(jià)值,主要體現(xiàn)在它培養(yǎng)感受力和介入社會(huì)方面的實(shí)際效用,然而目前該學(xué)科很大程度上已淪落為空泛的文化分析,變得無實(shí)際用處。學(xué)科失效的主要原因是,它拋棄了1920年代其成立之初的文學(xué)“批評”模式——即用審美教育來培養(yǎng)人的感受力,進(jìn)而引發(fā)大規(guī)模的社會(huì)改良這一學(xué)科初心。《文學(xué)批評》旨在重啟失落的文學(xué)批評,從而激活文學(xué)研究的政治潛能,讓這門關(guān)于人的學(xué)科再次與人的生活息息相關(guān)。重建文學(xué)與人生的真正關(guān)聯(lián),這也正是標(biāo)題中“政治”一詞的終極所指。透過“政治”視角,諾思重寫的文學(xué)批評史,不僅揭示了錯(cuò)綜復(fù)雜的學(xué)科百年發(fā)展脈絡(luò),也讓我們得以反思當(dāng)前的文學(xué)研究與教學(xué)實(shí)踐,藉此構(gòu)想一個(gè)有助于實(shí)現(xiàn)良好生活的學(xué)科未來。
兩種范式:文學(xué)批評與文學(xué)學(xué)術(shù)
諾思重寫文學(xué)批評史的動(dòng)力,源于他對當(dāng)下研究范式的去政治性的不滿。在他看來,英美兩國幾十年來的文學(xué)研究,主要基于知識(shí)生產(chǎn)這一學(xué)術(shù)目的,從特定的歷史語境入手分析作品在怎樣的文化形態(tài)里被書寫和閱讀。自1970年代末以來的文學(xué)研究,譬如后殖民主義、新歷史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女權(quán)主義、酷兒理論等,無不出于這種以文化分析為己任的文學(xué)學(xué)術(shù)范式,或“歷史主義/語境主義”范式。此主導(dǎo)范式的代表人物多為左翼自由主義者,其政治主張聽來頗具激進(jìn)色彩,且取代的是利維斯主義和新批評等重視形式和審美的保守批評模式,故而讓人覺得它在政治上必然是進(jìn)步的、可取的。然而諾思認(rèn)為,此范式恰恰是去政治的。一方面,這一范式下開展的研究不再抱有培育主體性、介入現(xiàn)實(shí)的雄心,而是退守至“做出更好的文化分析”這樣的保守目標(biāo),呈現(xiàn)出鮮明的“右翼屬性”(17頁)。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從1980年代以來“毫無爭議地確立了自己的全球霸權(quán)地位,在每個(gè)領(lǐng)域都把左派打得潰不成軍”,文學(xué)研究自然不能獨(dú)善其身,必然受到歷史潮流的影響(13頁)。所以,在內(nèi)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現(xiàn)行范式雖然不乏對歷史語境和物質(zhì)性的投入,以及對普世主義和本質(zhì)主義的批判,卻因缺失“系統(tǒng)性地改造世界”的政治實(shí)踐而走不遠(yuǎn)(27頁)。
這門學(xué)科要想走得遠(yuǎn)、變得有用,需要學(xué)科人士的積極規(guī)劃,使之與人們當(dāng)下的日常生活相關(guān),釋放其政治潛能。諾思把目光轉(zhuǎn)向瑞恰慈等人在二十世紀(jì)初開創(chuàng)的文學(xué)“批評”,從中汲取思想資源。他指出,文學(xué)研究自1920年代在英國成立至今的一百年間,這門學(xué)科大體出現(xiàn)兩種范式:一種是由劍橋大學(xué)的瑞恰慈等人創(chuàng)建的“批評”(critical)范式:作為“審美教育的一種制度體系”,文學(xué)批評“把文學(xué)作品當(dāng)做手段,借以直觀地培養(yǎng)新的感受力、新的主體性和新的體驗(yàn)?zāi)芰Γ瑥亩鴮?shí)現(xiàn)豐富文化的教育宗旨”(第9頁);另一種是上文提及的學(xué)術(shù)(scholarly)范式,這種可被量化的文化知識(shí)生產(chǎn)范式頗能適應(yīng)當(dāng)下新自由主義高校的考核要求。基于這兩種范式,諾思修正了兩段論的學(xué)科史(通常以“1945年”“1968年”或“后現(xiàn)代主義”為界將二十世紀(jì)分為前后兩段),將其重新劃分為三個(gè)階段:第一階段從1920年代至1950年代,以傳統(tǒng)的“批評”范式為主導(dǎo);第二階段從1960年代至1970年代,“批評”范式與“學(xué)術(shù)”范式共存;第三階段從1970年代末至今,以“學(xué)術(shù)”范式為主導(dǎo)。諾思這里提出一個(gè)重要論斷:文學(xué)研究史與西方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史大致保持疊合,前者的三個(gè)階段分別對應(yīng)后者的自由主義階段、福利國家階段、新自由主義階段。于是,文學(xué)研究史的褶皺被抻開,其與政治的動(dòng)態(tài)關(guān)系被推至前景。在政治視域下觀照,當(dāng)今“學(xué)術(shù)”范式一家獨(dú)大的現(xiàn)象,與新自由主義制度對人文學(xué)科的規(guī)約密切相關(guān)。的確,我們?nèi)缃窈茈y讀到那種與人的日常經(jīng)驗(yàn)和個(gè)人情感相呼應(yīng)的文本細(xì)讀了,更常見的是符合學(xué)術(shù)規(guī)范的歷史化研究,文本細(xì)讀反倒成了點(diǎn)綴其間、為了佐證學(xué)術(shù)論點(diǎn)的裝飾物。
在諾思看來,這一轉(zhuǎn)變固然與新自由主義式高校的就業(yè)市場的要求有關(guān),但也源于人們對文學(xué)“批評”觀念的誤解,誤以為它就是利維斯的“偉大的傳統(tǒng)”所指向的文化保守主義觀念,或是新批評的文本自洽、審美自律觀念。諾思把文學(xué)批評的源頭追溯至瑞恰慈,后者在《實(shí)用批評》和《文學(xué)批評原理》中闡發(fā)的唯物主義美學(xué),為文學(xué)研究這門現(xiàn)代學(xué)科的創(chuàng)建奠定了哲學(xué)美學(xué)基礎(chǔ)。然而,經(jīng)由利維斯的發(fā)揮,文學(xué)批評在英國逐漸演變?yōu)閷?jīng)典文學(xué)作品的等級(jí)排序;漂洋過海到了北美,文學(xué)批評則被蘭瑟姆和他來自美國南方的學(xué)生加以改造,成為我們現(xiàn)在熟知的新批評。無論是利維斯,還是新批評,都是對瑞恰慈的文學(xué)批評觀念的誤讀,他們無一例外地忽視了瑞恰慈的美學(xué)觀念中的唯物主義元素,退回到康德的唯心主義美學(xué)觀,從而導(dǎo)致了文本與世界的相剝離。對瑞恰慈來說,文學(xué)作品的“審美潛能”是文學(xué)批評的關(guān)鍵。換言之,美育對我們實(shí)用能力的培養(yǎng)應(yīng)是文學(xué)批評的重心。提到“審美潛能”,后來的唯心主義美學(xué)家往往理解為作品本身的形式之美,而忘記了瑞恰慈的唯物主義美學(xué)觀,即文學(xué)作品能被用來培養(yǎng)我們的實(shí)際技能、改善我們的思維。瑞恰慈的學(xué)說致力于打通文本與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聯(lián),增進(jìn)人類的有效交際,最大程度地發(fā)揮了文學(xué)的公共性,因此有助于抵抗新自由主義對文學(xué)研究,乃至對整個(gè)人文學(xué)科的鉗制。經(jīng)過一番深刻的調(diào)整和動(dòng)員,這門學(xué)科在資本當(dāng)?shù)赖慕裉欤踔辆邆涓纳迫藗兩罘绞降臐撃堋?/p>
展望學(xué)科未來:“批評無意識(shí)”
在全書篇幅最長的第四章,諾思對這門學(xué)科的未來進(jìn)行了展望和動(dòng)員。從本章的標(biāo)題《批評無意識(shí)》中可以看出,他顯然是在影射弗雷德里克·詹姆遜的“政治無意識(shí)”。如果說詹姆遜作為歷史主義/語境主義范式的代表人物,他的“政治無意識(shí)”觀念致力于一種深度的闡釋實(shí)踐,旨在從文本的罅隙中挖掘隱蔽的政治意涵,那么諾思的“批評無意識(shí)”則正好相反:他要借鑒瑞恰慈等人開創(chuàng)的文學(xué)批評及其唯物主義美學(xué)根基,發(fā)展出一個(gè)能產(chǎn)生政治效果的文學(xué)研究范式,借此取代當(dāng)下主導(dǎo)該學(xué)科的懷疑闡釋學(xué)。
諾思把二十一世紀(jì)以來涌現(xiàn)的對現(xiàn)行學(xué)術(shù)范式不滿的新趨勢,歸結(jié)為“鐘擺”(Pendulums)、“暗示”(Intimations)和“擴(kuò)張”(Expansions)三大類。“鐘擺”趨勢呼吁審美和形式的回歸,其代表是英國女權(quán)主義學(xué)者阿姆斯特朗·伊莎貝爾的新審美主義;“暗示”所包含的新趨勢表達(dá)了文學(xué)體驗(yàn)中的私人情感對文學(xué)研究的重要性,代表人物是美國酷兒理論和情感理論的研究者伊芙·塞奇威克、D. A. 米勒和勞倫·貝蘭特;“擴(kuò)張”趨勢要求大幅度延展文學(xué)研究的時(shí)空框架,代表人物是美國學(xué)者大衛(wèi)·達(dá)姆羅什、宋惠慈和帕特麗夏·耶格爾。這些大大小小的創(chuàng)新,閃爍著瑞恰慈的批評之光,整體上構(gòu)成了抵抗學(xué)術(shù)范式的逆勢。當(dāng)時(shí)機(jī)成熟,它們有望“凝聚成一個(gè)全新的范式”(269頁)。諾思所暢想的新范式具體有如下特征:
它密切地關(guān)注審美和形式;對感覺和情感體察入微,將其視為認(rèn)知的方式,并把兩者看作是個(gè)體和集體的變化乃至歷史變遷的重要決定因素;這一方法的牽涉面較廣,橫跨不同的時(shí)期、地域和文化;它愿意將文學(xué)用作倫理教育的工具;它不單純地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的診斷作用,也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的治療作用;它還以一種深刻、嚴(yán)謹(jǐn),卻仍十分直接的方式發(fā)揮公共職能。(271頁)
此處,諾思是在進(jìn)行學(xué)科動(dòng)員。他呼吁學(xué)科中人有意識(shí)地對這些“批評無意識(shí)”加以整合。趁當(dāng)下新自由主義再次陷入危機(jī)之時(shí),文學(xué)研究者需要審時(shí)度勢,開啟一種面對普羅大眾的、能影響現(xiàn)實(shí)世界的新型批評范式,使這門學(xué)科重新煥發(fā)生機(jī)。說到底,諾思倡導(dǎo)的文學(xué)批評貫注于文學(xué)作品自身的形式和審美,并敏于捕捉閱讀中牽涉的情感、認(rèn)知、時(shí)空、歷史、倫理等多重維度,力圖培育一種具有物質(zhì)根基的新型感受力,從而介入現(xiàn)實(shí)。在這方面,諾思的《文學(xué)批評》與塞奇威克的《動(dòng)人的感覺:情動(dòng)、教育法和操演性》(2003)、阿特里奇的《文學(xué)的獨(dú)特性》(2004)、菲爾斯基的《文學(xué)之用》(2008)和《批判與后批判》(2015)等作品一道,構(gòu)成了二十一世紀(jì)以來學(xué)院派人士對學(xué)科范式改革的集體呼吁。
風(fēng)格印象
就西方學(xué)術(shù)的風(fēng)格而言,粗線條的歷史性論述方式,似乎更容易被國內(nèi)讀者辨識(shí)和理解,這類著作中遍布的警句往往能引起普遍共鳴。與之相比,《文學(xué)批評》雖然也算是一部史作,但為了細(xì)致入微地揭示問題的復(fù)雜性,該書充滿各種轉(zhuǎn)折和限制條件,因果關(guān)系一波三折,于是有些地方的論證邏輯顯得不夠一目了然。另外,作者的論述語言并非客觀中立,而是夾雜著諷刺、戲仿、操演,如賓大的一位教授在我們私下聊天時(shí)所說的那樣,這本書里的語氣常常是有態(tài)度的,有感情色彩的。這種風(fēng)格無疑增加了理解和翻譯的難度。諾思在書中倡導(dǎo)的是由瑞恰慈開創(chuàng)的、當(dāng)下幾近消失了的文學(xué)批評模式,批駁的是如今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的學(xué)術(shù)范式或歷史主義/語境主義范式,因此他在論述的時(shí)候,也盡量避免全盤歷史化、語境化,而是采取一種探索啟發(fā)式(heuristic)的論述風(fēng)格,力求在風(fēng)格上靠近其所呼吁的文學(xué)批評。這樣的論述風(fēng)格,在評價(jià)前輩學(xué)人的學(xué)術(shù)成果時(shí),體現(xiàn)在他頻繁采用的語意解析上:從最具影響力的學(xué)術(shù)作品中摘引關(guān)鍵段落,對其中的論點(diǎn)、措辭、情感、態(tài)度、風(fēng)格等方面進(jìn)行闡釋,指出其中明顯的語意含混,以及上下文的邏輯矛盾,最后利用后見之明評判作品的利弊得失。讀及此處,我們雖然會(huì)對他不留情面地駁斥的資深教授心生同情,但也隱隱感受到一種復(fù)仇的快樂。確實(shí),做外國文學(xué)研究的人,無論初學(xué)者還是熟練工,都要直面這門學(xué)科的不精確性和(有時(shí)不必要的)繁復(fù)性,這也是“消極能力”(濟(jì)慈語)對學(xué)科中人尤為重要的原因。概因缺少客觀的評價(jià)標(biāo)準(zhǔn),文學(xué)研究時(shí)常將讀者卷入語意的漩渦——?jiǎng)e人講得天花亂墜,我們讀得云里霧里。所以,當(dāng)本書作者這樣的學(xué)術(shù)新人出現(xiàn),他不惜得罪權(quán)威人物,對經(jīng)典學(xué)術(shù)作品中的核心段落進(jìn)行文本細(xì)讀,并抽絲剝繭地解構(gòu)原作觀點(diǎn),讀者宛如在嘈嘈切切的話語喧囂中獲得了大珠小珠落玉盤的心安之感。即便書中不乏輕率之論,此書也能在讀者中喚起一種快意恩仇的認(rèn)同感。這種不惜冒犯學(xué)術(shù)大佬的論辯風(fēng)格,不僅需要可與之媲美的智識(shí)水平,更需要舍身求法的勇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