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的歧路——“童話詩人”之殤與八十年代的“童話”話語
摘要:詩人顧城之死使人們產(chǎn)生了對“童話詩人”之“童話”的質(zhì)疑,“顧城現(xiàn)象”由此引出關(guān)于啟蒙的許諾與失落、童話的純真與危險的寓言。回到“童話詩人”一詞形成的歷史現(xiàn)場,彼時的詩人及批評家群體在“童話”之上寄予的啟蒙期待與顧城對童話釋義的差異便顯現(xiàn)出來。前者希望借由其自然與天真的特質(zhì)來治愈創(chuàng)傷并重新開始一個“新時期”,后者則賦予童話無始無終的時間觀并塑造“無為無不為”的兒童形象,在解釋歷史暴力的同時成為了暴力的同謀。以告別過去的意識為共同起點(diǎn)的啟蒙探索終究分道而行,童話話語內(nèi)部的復(fù)雜與矛盾暴露出八十年代的歷史癥候,并成為啟蒙歧路的起點(diǎn)。
關(guān)鍵詞:顧城、童話、啟蒙、八十年代
引言
1993年10月8日,著名詩人顧城在新西蘭的威赫克島(激流島)上殺妻,隨后自縊。這則令人震驚的消息在海內(nèi)外迅速發(fā)酵升溫,真假難辨的報道伴隨著倫理與文學(xué)的爭論一時沸騰。在當(dāng)時朦朧詩的熱潮已過,甚至文學(xué)也已經(jīng)邊緣化的情況下,顧城之死卻帶著光怪陸離的魅影激起巨浪,成為了所謂的“顧城現(xiàn)象”[1]。于是這位成名于八十年代的詩人在其死后又一次被濃墨重彩地“畫像”。除了出版社競相推出他的四部作品——《英兒》《墓床》《顧城新詩自選集——海籃》《顧城散文選集》之外,他的生前好友也紛紛寫下懷念文章,更有諸多批評家對此事件進(jìn)行反思。
“詩人”與“童話”,“暴力”與“死亡”,成為這些討論中的兩組關(guān)鍵詞。正如顧城在其成名作《一代人》中所寫:“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兩組看似分屬于“光明”與“黑暗”范疇的詞語在此時如讖言般被溝聯(lián)起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顧城之死被上升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正是出于對這些語詞的困惑。構(gòu)建這兩組詞之間繁絮的邏輯關(guān)系困難重重,遠(yuǎn)遠(yuǎn)超過了破解一起個人偶然死亡事件的難度,它牽涉到八十年代啟蒙的許諾與失落、童話的純真與危險的寓言。
一個“童話詩人”為何以如此暴力的方式結(jié)束他人與自己的生命?這個問題在顧城死后便被立即提出,本文也以此作為思考的起點(diǎn)。只是時隔多年,當(dāng)我們以歷史的“后見之明”去重新審視這個問題,我們再無十足的信心去直白地將此歸因于個人成長中的某些創(chuàng)痛。而且,當(dāng)這起事件消退了它離奇的新聞性,我們也會發(fā)現(xiàn)這個問題依舊夢魘般揮之不去,究其根源正在于“童話”二字。當(dāng)時的批評家直言,這種巨大的震驚源于殺人行為與“童話詩人”形象的不可調(diào)和[2],顧城的“童話王國”只是他“精心卻又無意識中營構(gòu)的迷魂陣”[3]。
可以說,“童話詩人”這頂桂冠對于顧城來說既是生前空洞的指涉,又是身后不可承受之重。于是我們由此尋找到繼續(xù)拆解這個問題的路徑——去一點(diǎn)點(diǎn)剝離附著于“童話”之上的意涵與期待(“童話”一詞在本文中不指涉文體范疇,只是作為“童話詩人”中“詩人”的形容詞)。這種“附著”絕不只是由顧城獨(dú)自完成的。他的作品以及文論只是構(gòu)建“童話”意義的一部分,而同代詩人與批評家,乃至“顧城現(xiàn)象”的所有締造者都分享或書寫了這個夢境/夢魘。

顧城
本文嘗試以顧城為線索來重新檢視八十年代的“童話”話語,梳理這種話語內(nèi)部盤繞而生的枝蔓,三個小節(jié)分別針對以下核心問題展開討論:
其一,“童話詩人”的名稱從何而來?八十年代的詩人與批評家(“一代人”)如何在朦朧詩論爭中詮釋這個名稱?他們借由童話的修辭表達(dá)了何種啟蒙理想?這種啟蒙理想中隱含著何種歷史觀與時間觀?
其二,顧城如何理解“童話詩人”?他在詩中建構(gòu)的童話性的自我有何特點(diǎn)?和同代人相比,顧城的啟蒙理想、歷史觀與時間觀有何特別之處?
其三,顧城在激流島上將童話理想變?yōu)楝F(xiàn)實(shí),他構(gòu)筑自己的“童話王國”依據(jù)的是何種理念?“童話王國”的最終損毀與他的“自然哲學(xué)觀”和童話觀之間有何聯(lián)系?
顧城的個例包含著多重聲部的對話。他的思索與當(dāng)時批評家對他的解讀/誤讀之間所形成的張力讓我們得以窺見八十年代關(guān)于童話與啟蒙話語的歷史癥候。而另一層深意則在于,顧城個人的悲劇雖然不能直接指向所謂八十年代啟蒙的結(jié)果,但卻提醒著我們?nèi)プ⒁馔捲捳Z內(nèi)部的危險性——童話的天真中是否已經(jīng)暗含了某種顛覆性的因素,或者說,它的矛盾與陰影如何被遮蔽?
一、光明與黑暗的悖論:“童話詩人”與“一代人”
1980年舒婷為顧城寫下了一首題為《童話詩人——給G·C》的詩。這便是“童話詩人”的稱呼最初的來源。[4]我們并無法確知這首詩對八十年代開始形成的顧城的“童話”印象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但它至少可以作為一個耐人尋味的引子。因?yàn)檫@其中既包含了一個親密的友人對顧城和童話的基本讀解,又悄悄埋下了一些關(guān)于這個稱呼的意味深長的謎題。
這首詩中寫到的事物,像“星星、紫云英和蟈蟈”“雨后的塔松”“桑椹”“風(fēng)箏”同屬于“自然”的類別。與之形成對立的則是“病樹、頹墻”和“銹崩的鐵柵”。細(xì)究起來,這些詞語都曾在顧城的詩中出現(xiàn),對自然的大量書寫的確是顧城詩歌的一個重要特征。顧城在自述中也會反復(fù)談及自然對童年和詩歌創(chuàng)作的影響。比如他熱愛閱讀法布爾的《昆蟲記》,繼而收集許多蝴蝶標(biāo)本,他說那是“大自然給我的詩的語言” [5]。這首詩用這些意象標(biāo)記出了顧城。但從并置的兩組事物來看,舒婷卻只是以當(dāng)時朦朧詩人較為普遍的對自然與童話的書寫和理解方式來表達(dá)了一種對抗的意圖。
正如奚密針對朦朧詩群體的研究所發(fā)現(xiàn)的,與“后朦朧詩”所寫的身處現(xiàn)實(shí)的童年相比,朦朧詩更多地將自然與兒童相聯(lián)系,并與社會系統(tǒng)相對立,以此表達(dá)未被污染的天真的涵義。她將此稱為“自然的兒童”,指出詩人們以三種互相關(guān)聯(lián)的形式來展現(xiàn)它。其一是假以兒童的視角來觀察這個世界;其二是直接在詩中描繪兒童;其三是追憶自己的童年。詩人們借由“孩子”來表達(dá)對充滿壓迫感的現(xiàn)實(shí)世界的疏離,同時也以兒童的邊緣化的社會身份來強(qiáng)調(diào)自己人格的獨(dú)立和完整。
所以在這些詩中,兒童所代表的天真、敏感、富有想象力的世界對抗著成人社會的冷漠、虛偽和無情,而童年則是詩人們在現(xiàn)實(shí)中遺失又寄望于詩歌的樂園。[6]奚密總結(jié)出了朦朧詩人在應(yīng)用童話話語時所表達(dá)的反叛意圖,然而自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未免是對這種反叛過于籠統(tǒng)的描述。如何看待童話話語在八十年代所具有的特殊涵義勢必需要我們回到當(dāng)時的啟蒙語境之中,追溯時人對“童話詩人”更多的討論。
因?yàn)槠浯碜鳌兑淮恕罚櫝菫樵u論者與公眾所熟知。這首詩在當(dāng)時激烈的朦朧詩論爭中被反復(fù)稱引,出其意料的是,它得到了論辯雙方的認(rèn)可。對朦朧詩持反對態(tài)度的批評家認(rèn)為,這首詩“反映了社會現(xiàn)實(shí),能引起大家的共鳴”[7],而且也“讀得懂”[8]。持贊成意見者,更稱贊其與北島的《回答》一道,堪稱“充滿了肩負(fù)民族興亡重任的大無畏精神的詩聲”[9]之雙壁。
這種一致性的達(dá)成主要是由于《一代人》中所寫的“黑夜”與“光明”有著兩方公認(rèn)的歷史指向。它的辯證性既符合時人對文革的反思需要,也不失為對現(xiàn)實(shí)和未來的樂觀期待。這正如徐敬亞在《崛起的詩群——評我國詩歌的現(xiàn)代傾向》中所寫,“無論是對黑暗的揭示和對未來的希望,新一代詩人顯然都更深刻、更明確——有一種徹底拋棄幾千年的因襲,全面走向現(xiàn)代社會的現(xiàn)代感”[10]。不過,這首詩也暴露出一個在八十年代難以回避的問題:即當(dāng)人們在有著清晰的“黑夜”意識的情況下,又該如何走向“光明”的路途?
顧城的這首《一代人》表面上與童話沒有任何關(guān)系,也因此在關(guān)于顧城詩歌童話性的研究中不被注意。[11]然而在八十年代,這首詩其實(shí)與“童話詩人”的稱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guān)系。而且正是這種關(guān)系為“黑夜”如何連接“光明”的問題提供了一個答案。顧城的第一本個人詩集名為《黑眼睛》,這顯然取自這首詩。結(jié)合詩歌的標(biāo)題來看,“黑色的眼睛”無疑是對“一代人”的描摹。在北島意味相似的詩歌《回答》中也有類似的表述——“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來人們凝視的眼睛”[12]。

《黑眼睛》 顧城著
但是,相較于北島語稱“人們”這樣明確的集體性表述方式,顧城的這首詩其實(shí)存在著一種含混(這種明確和含混不只是詩人創(chuàng)作的語調(diào)和用詞問題,也是在讀者接收時發(fā)生于文學(xué)場域的一種現(xiàn)象)。“黑眼睛”不僅是對一代人的想象,同時也加入了許多對顧城個人形象的理解。更確切地說,這是被作為他“童話詩人”的一種形容詞,進(jìn)而衍生出更多與孩子的單純懵懂相關(guān)的涵義。
當(dāng)時不乏這樣的評論,“在被人目為朦朧的這一代新詩人中,如果說舒婷的朦朧詩‘心較比干多一竅’式的精巧,北島的朦朧是一個角斗士出場拉下面罩的警覺,那么顧城的朦朧,則是象孩子般睜著一雙黑眼睛來看待那充滿機(jī)巧與世故的人生,反而使長期在畸形文化氛圍中失卻了心態(tài)平衡的人們瞠目”[13]。提取這些描述中互為詮釋的關(guān)鍵詞,那便是“兒童”“童話”“單純”。這些詞語被視為可以穿透“機(jī)巧與世故”的力量,可以使人瞠目。所以,“兒童”其實(shí)是一個隱藏在這首詩的文本后非常關(guān)鍵的要素,只有孩子的黑眼睛才具有凈化“黑夜”的能力,才可以提供一條通向光明的路途。
另外,當(dāng)這些八十年代的評論者以顧城的青年形象來談兒童時,暗含了更為復(fù)雜的“啟蒙”或者“拯救”意義。正如謝曉虹在對《狂人日記》的研究中所發(fā)現(xiàn)的,魯迅并不是將社會批判力寄托在現(xiàn)實(shí)中天真的兒童身上,而是借助于“狂人”所具有的兒童與成人的雙重視點(diǎn)。[14]顧城的例子也是如此。評論者們使用“童話詩人”的修辭來寄托將成人群體包含在可被拯救的范圍之內(nèi)的希望。同時,這種修辭還能以成人的能動性來解決誰來拯救的問題。啟蒙者與被啟蒙者之間的矛盾便在這樣一個懷有童心的成人形象上得到了疏解。
有趣的是,顧城自己對這首詩里的“光明”與“黑暗”有著截然不同的解讀。他寫道:
如果光明不愿到人間來,便不應(yīng)強(qiáng)求。強(qiáng)求來的光明未必不仍然是黑暗。但是有時候強(qiáng)求是必然的。而別人看是強(qiáng)求,對于你自身來說卻是命里注定,就像“尋找”是你的命里注定一樣。[15]
顧城所講的不僅是一種歷史意識,更是關(guān)于個人存在的問題。只是他提前到來的宿命的絕望感在當(dāng)時并未粉碎人們從他的詩中獲得未來可期的夢想。這是一個在中國二十世紀(jì)文學(xué)史上似曾相識的場景,是八十年代頻頻回望的“五四”也曾聚焦的問題——關(guān)于悲劇必然性與發(fā)展能動性的爭論。當(dāng)人們把社會拯救的期許放在孩子的天真之上的時候,魯迅卻寫下《狂人日記》和《孤獨(dú)者》,懷疑著同樣流淌在孩子血液里的“病”是否有痊愈的可能。
文革之于晚清,八十年代之于“五四”,任何具體的歷史情境都相差甚遠(yuǎn),但顧城的例子向我們呈現(xiàn)的卻是另一種與“五四”的呼應(yīng)——他在不經(jīng)意間開啟的不是對啟蒙合法性的確認(rèn),而是借由兒童和童話來表達(dá)了重新開始的意圖后,仍然存在著對“發(fā)展”的童話的深刻質(zhì)疑。而他與評論者之間對“光明”與“黑暗”關(guān)系理解的錯位,更讓人察覺到其與魯迅的“反抗絕望”之間奇妙的隱喻式聯(lián)接。
二、時間的童話:布林的出生與死亡
顧城雖然曾在訪談中說過“童話詩人”只是一種“外在的印跡”[16],但他自己其實(shí)為這個名稱也增加了許多筆墨。最為評論家所注意的是他在《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與《簡歷》這兩首詩中對自我的表述。“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我想涂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畫滿窗子/讓所有習(xí)慣黑暗的眼睛/都習(xí)慣光明”[17]。“我是一個悲哀的孩子/始終沒有長大”[18]。在天真之外,他又被認(rèn)為具有了困守于童年、“拒絕成年”和“無法成年”的悲劇特征。[19]
也有學(xué)者根據(jù)顧城自己的文論來分析他的自我,將這兩首詩列在他的第二個階段“文化的自我”之中,認(rèn)為顧城此時竭力融入八十年代的啟蒙思潮,在詩中進(jìn)行社會批判。而在此之前與之后的階段則分別是“自然的自我”“反文化的自我”和“無目的的自我”。[20]這種分期的意義其實(shí)并不在于時間上的界分,因?yàn)轭櫝堑乃枷朐谶壿嬌舷喈?dāng)連貫,詩學(xué)表現(xiàn)形式的一些改變并不能割裂這種內(nèi)在的連續(xù)性。這些標(biāo)簽更多的意義在于提示出一個“童話詩人”關(guān)于自我的多重面向,而且這些面向互相重疊又彼此補(bǔ)充。不過,這些概念化的表述不足以使我們更深入地理解顧城的童話性的自我,經(jīng)由他的詩歌則可能使這幅畫面更為明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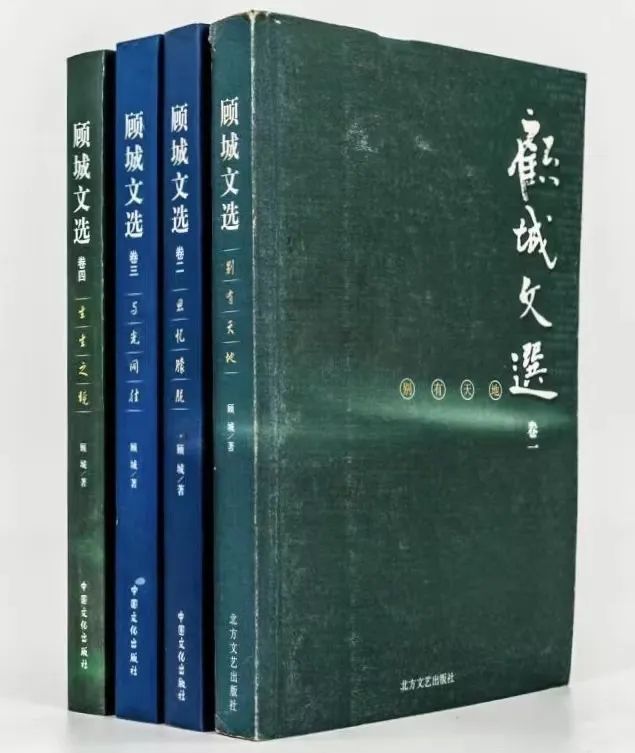
《顧城文選》 顧城著
顧城曾在1981到1987年創(chuàng)作了組詩《布林的檔案》,并親自為這組詩畫了插圖。這個叫布林的孩子被顧城視為“另一個我”。在給編輯的投稿信里,顧城寫道:
布林是一個孫悟空、唐·吉訶德式的人物,很小的時候就在我心里搗亂。他不規(guī)范、喜歡逃學(xué)的天性,使我覺得很有趣。我常常想他,給他編故事,用紙片記下這些故事,我甚至還用古文寫下這些故事,并且配上插圖。[21]
《布林的檔案》由十八首詩組成,風(fēng)格相當(dāng)荒誕。盡管其中不難找到一些與現(xiàn)實(shí)政治相關(guān)的隱喻或戲仿,但很快就會轉(zhuǎn)換到超現(xiàn)實(shí)的場景。整體看來,詩人希望描述的是一個可以隨意穿行在現(xiàn)實(shí)與夢幻之間的無所拘束甚至是變化無端的兒童形象。組詩所配的插畫也是如此,雜亂的線條并不著意于描摹出一個現(xiàn)實(shí)中孩子的樣子,而僅是一種將“任性”趨于極致。顧城進(jìn)一步解釋這種“任性”:
實(shí)際上是說他可以什么都不做,也可以什么都做,獨(dú)來獨(dú)往,“立乎不測”;他在一個高遠(yuǎn)的地方影響著文化的潮汐。從魏晉之風(fēng)到潑墨畫到孫悟空大鬧天宮號為“齊天大圣”,都含有這種游戲的痕跡。[22]
這段話不僅是對布林這個詩歌中的主人公形象的描述,它更是闡明了詩人這種布林想象的思想源頭和心理癥結(jié)之所在。顧城借用道家的“無為無不為”來指示一種立于法外的對規(guī)則的破壞。他真正想談?wù)摰钠鋵?shí)是在八十年代最為重要的問題之一:如何看待這段歷史?如上一節(jié)所論述,顧城的同代人更傾向于把這個問題表述為:如何從“黑暗”歷史中開啟一個“光明”的“新時期”?如何從“被污染”的童年中孵化出天真的童話?顧城從不諱言自己的童年是在混亂中度過的。他談到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和一切外國的影響,“都在一個白熱的爆炸中間消失了”[23]。
然而,他對這種混亂的態(tài)度卻是相當(dāng)曖昧的。換言之,他并沒有與同代人完全共享對“黑暗/光明”的隱喻預(yù)設(shè)。這段話里他談到的“游戲”和“無不為”顯然不是負(fù)面的詞語,反而指向了兒童的自由與天真。問題在于,當(dāng)他以這種很“輕”的說法來承載歷史之“重”,是否就使個人具備了在混亂大歷史中的超越性?他所想象的超越又指向何方?
這種超越性很容易被理解為知識分子對品格的堅守,然而在顧城自洽的邏輯中,他所指的卻更是一種審美性視角的獲得。顧城對此有一個形象的比喻。他說文革就如同一只老虎,你如果在地上看它,就會被它追逐;但你如果在樹上,或者老虎在鐵欄里,在畫中,你就欣賞它的斑紋,它的美麗。[24] 他繼續(xù)借助一個道家的概念來完成這個闡釋,叫做“以道觀”。
簡言之,就是通過改換成“非人間”的視點(diǎn)來達(dá)成“物無貴賤”的純粹審美。這套話語可以看作是詩人對創(chuàng)傷的應(yīng)對,也可以在其中看到他堅強(qiáng)的自我意志——“人可生如蟻而美如神”——這也是他在《一代人》中所展現(xiàn)出的無論如何都要去“尋找光明”的決心。然而,這種敘述是否也在某種程度上遮蔽了具體的歷史暴力?暗藏在這些詩意比喻之下的是一種對暴力存在的決絕否認(rèn),以審美跨越的是道德的邊界,衍生出了吊詭的殘酷美學(xué)。
顧城的這種美學(xué)觀/歷史觀繼而發(fā)展出了一種關(guān)于“光明”和歷史時間的奇特敘述。他在詩里寫道:
在一片柔順的夢想之上
光是一片溪水
它已小心地行走了千年之久[25]
詩人所要表達(dá)的是光明貫穿了整個歷史,而我們不能看見只是由于沒有具備某種類似“以道觀”的視角。他解釋道,“白天、黑夜、生命、死亡是我們的事,但是對于太陽來說,沒有黑夜也沒有死亡……只有我忽然想起這個光明的時候,我才存在”[26]。在這樣的邏輯里,光明被絕對化,黑暗變成了一種主觀的事物。相應(yīng)的,黑暗所隱喻的文革也隨之消弭在這樣的敘述之中。由此重讀他的《一代人》,則會發(fā)現(xiàn)“尋找光明”也未必具有朝向未來的時間概念,而更可能是詩人所說的“忽然想起這個光明的時候”。這是一種無始無終的歷史時間觀,與當(dāng)時將文革與八十年代劃分為時間兩端的“新時期”意識無疑大相徑庭。兩種歷史意識之間的唯一共同點(diǎn)是它們都生發(fā)于急切擺脫文革創(chuàng)傷的訴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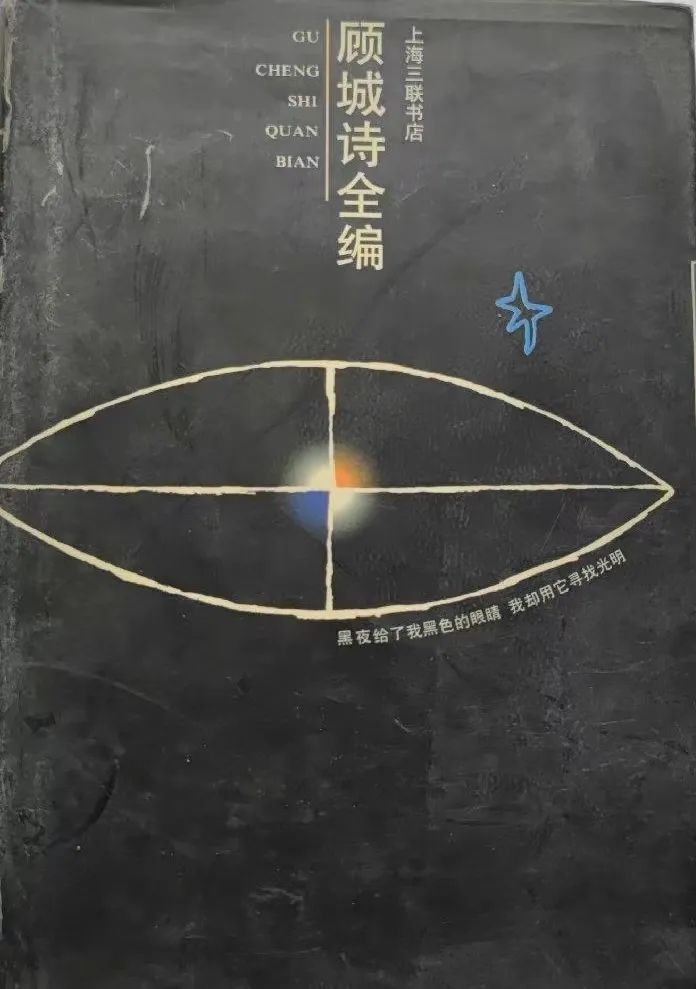
《顧城詩全編》 顧城著
顧城對歷史的時間意識與他對個體生命的理解糾纏在一處。他以光來比喻歷史的無始無終,又以相似的句式來形容人的生命歷程。“死亡是沒有的,我已在生命中行走千次。現(xiàn)在,我走的是小男孩最卑微的道路”[27]。這句話本身是要通過取消自我存在形式的唯一性來否認(rèn)死亡。也就是說,在當(dāng)下的時間中,我以小男孩的生命形式存在,而在這個生命開始之前與停止之后,我仍然以其他形式繼續(xù)存在于宇宙之中。在布林組詩中,顧城就這樣同時建構(gòu)又解構(gòu)著這個小男孩的存在。其中兩首叫做《布林進(jìn)行曲》與《布林不進(jìn)行曲》,一首寫著“拿餐刀上前線去/背著水瓶找你”,一首則是“路口擺著車/永遠(yuǎn)出不去”[28]。
兩首詩動作相反,詞語間全是悖論。用顧城的話說,就是“既不能存在,又不能不存在”[29]。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很難說顧城執(zhí)著于童年或者想維持于一個孩子的狀態(tài)。布林可以長大,可以衰老,甚至可以死亡。但哪怕是這樣的變化也并不遵循著線性時間的順序。如果說組詩從第一首《布林的出生及出國》到第十三首《布林好像死了》還能給人以發(fā)展的錯覺,那么在布林死后的幾首詩里,才出現(xiàn)了“布林決定要衰老”。但是,詩里的死亡和衰老都更像是角色扮演的游戲。“呵,呵,哦/布林死了,死了,死了/那么熟練地死了,好像真的/他在熱氣管道里眨下眼睛/后悔/安眠藥/沒有帶夠”[30]。
布林和時間的游戲構(gòu)成了對進(jìn)化論時間觀所允諾的成長的質(zhì)疑。在八十年代的“成長小說”中,作家也不再書寫成長的必然完成。他們筆下的兒童無法抵達(dá)成熟的境地,因?yàn)樵谖母飼r期度過的童年已經(jīng)伴隨著夭折或墮落的創(chuàng)痛。這種兒童成長的中斷也被看作是國家發(fā)展困境的隱喻。[31]這些作品直接迎擊了樂觀的發(fā)展觀,提出的是在病態(tài)的社會環(huán)境下是否有可能培養(yǎng)健康的兒童的問題,它們的社會批判意圖因此而表達(dá)得更為透徹。
然而,顧城雖然一直說布林是個“壞孩子”,卻并沒有評判他的成長方向,甚至不將死亡作為毀滅與終結(jié)。在這組詩中充斥著對文革政治的戲仿,比如“布林生下來時/蜘蛛正在開會……布林哭了/哭出的全是口號/糟糕!”[32]如果說這是對政治進(jìn)行了批判,那么也并不是指出了它的丑惡與錯誤,而是將它解構(gòu)成一個荒謬滑稽的外殼。布林這樣的小孩可以隨意走進(jìn)又走出,篡改時間,瞬間長大,并在這個虛無的形式下信筆涂鴉。
我們可以將布林組詩中的時間看作一種純粹的文學(xué)想象與虛構(gòu),一種超脫于現(xiàn)實(shí)的個人紓解形式。然而,顧城在那封給編輯的信的最后一句,卻格外強(qiáng)調(diào)了“它展現(xiàn)的是人間,不是在愿望中浮動的理想天國”[33]。這組詩指向的是真實(shí)的歷史劫毀與人的死亡,而它的危險性也正在于此。當(dāng)顧城用這種仿佛超越人世的觀念來敘述世事,他已經(jīng)涉及了語言與倫理的界限。對死亡具有超越性的認(rèn)知如若限于對自身生命的處置,也許便沒有了后世的許多爭論。所以,與其說是所謂童話/幻想與現(xiàn)實(shí)邊界的混淆導(dǎo)致了顧城最后的悲劇,毋寧說是他過于“任性”的視角轉(zhuǎn)換已然帶著所謂“天道”對人世的傲慢,為悲劇深埋了伏筆。
三、自然與野蠻的辯證:激流島上的“童話王國”
“他們中有些人重新歸于文化,有的人卻徜徉于文化之外”[34]。這是1987年顧城在英國漢學(xué)會上的發(fā)言。他說的有些人是指其他朦朧詩人,而有的人則是說的自己。這一年他和妻子遠(yuǎn)走他鄉(xiāng),抵達(dá)了南太平洋上的一座小島。在給父親的信里,他寫道,“我在這里找到了我的夢——在渤海灣、在濰河畔,在泥巴捏的村落里,做的許許多多夢,現(xiàn)在再次呈現(xiàn);不過,要比當(dāng)年的夢更美妙、更綺麗……”[35]在這里他將童年的詩與夢變?yōu)榱爽F(xiàn)實(shí),希望筑起一個童話般美好的烏托邦。然而也是這里,他的童話夢最終破碎,徒留給后世諸多謎題。
對顧城在島上生活的關(guān)注和想象,主要來源于他唯一的一部長篇小說《英兒》。這本書的副標(biāo)題為“一部刺入生命靈髓的情愛懺悔錄”。小說講述了顧城(化名林城)和他的妻子(化名雷) 以及情人(化名英兒)在島上度過的令人匪夷所思的三人生活。并且,顧城還在其中預(yù)告和預(yù)演了自己的死亡。這個關(guān)于愛與死的傳奇自述將人們的想象引向了“女兒國”和《紅樓夢》里的大觀園。[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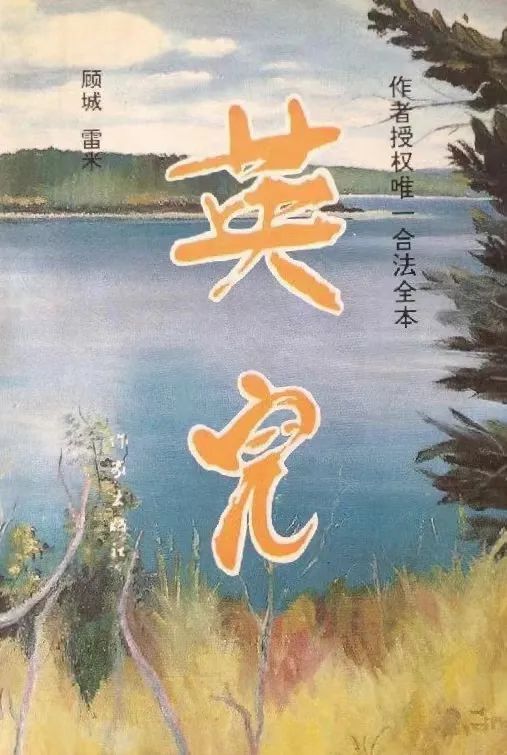
《英兒》 顧城 雷米著
不過,這些情愛糾葛以及它背后可能貫穿的顧城關(guān)于“女兒性”的想法,并不是他來到這個小島的原因,也不是他搭建這座城的起點(diǎn)。“到達(dá)那個小島的第一天,我對我的妻子說:我花了二十多年時間,準(zhǔn)備過這樣的生活,現(xiàn)在我終于跨過了這個倒霉的世界,到了我要到的地方,我的生活開始了。那時我對自然有一種信仰,我對我的自性也有一種信仰。我覺得到了自然界之中我就不再會又許多妄想,我的生命的自然美就會顯現(xiàn)出來”[37]。所以,我們要更仔細(xì)地去審視顧城所要建立的童話王國更為基礎(chǔ)的磚石——“自然”。
顧城所說的“自然”的第一個層次被廣泛地理解和接受,那是在本文的第一節(jié)提及的朦朧詩人們普遍使用的“自然的孩子”的修辭。它的反面是頹敗黑暗的社會,也意指文革高度“政治化”對詩歌的束縛。在顧城的自敘中,自然教會了他最初的詩歌。他在1969年跟隨父親離開北京,到山東的一片荒地上放豬。他在那時感覺自己完全融入了自然,聽到自然界鳥獸蟲魚的聲音,并學(xué)會了與它們說話。這就是顧城早期的代表作《生命幻想曲》中寫的:“蟋蟀歡迎我/抖動著琴弦。/我把希望溶進(jìn)花香。……我把我的足跡/像圖章印遍大地/世界也就溶進(jìn)了/我的生命”[38]。
后來顧城在17歲回到了北京,他無法適應(yīng)與人交談的語言,他寫下“我從北方的草灘上走出,走進(jìn)布滿齒輪的城市。……在一片淡漠的煙中,我繼續(xù)講綠色的故事”[39]。在混亂中,顧城讀到西班牙詩人洛爾迦的詩句,“啞孩子在尋找他的聲音,偷他聲音的是蟋蟀王”[40]。于是他明白了要找到自己的聲音。
顧城在這段關(guān)于詩歌創(chuàng)作的經(jīng)歷里提及的最關(guān)鍵的一點(diǎn)是自然與語言的關(guān)系問題。如果說朦朧詩人群體是以“自然的孩子”的修辭來達(dá)成反抗意圖,那么顧城則認(rèn)為自己從自然獲得的是語言的更新,詩人也斯稱此為“天真的革命”。他說“這種單純是對浮夸和裝飾的反叛,是對競用艱深文字,陳言套語,進(jìn)而對這種方法背后那種炫夸空洞的詩觀和人生觀的反駁”[41]。
有趣的是,當(dāng)顧城在八十年代后期開始海外漂泊,他并沒有像有類似經(jīng)歷的詩人(如北島、楊煉)那樣產(chǎn)生失去母語的焦慮,也并不熱衷于當(dāng)時在國內(nèi)興起的“尋根”創(chuàng)作。他相信“有根不用尋,無根無處尋。其實(shí)傳統(tǒng)也罷、藝術(shù)也罷,它活生生地就在你的血液里,在你的所有的言行舉止中間,只不過你不認(rèn)它、回避它罷了”[42]。顧城的這種態(tài)度倒未必說明他與“尋根派”有著截然不同的問題意識,抑或已經(jīng)解決了八十年代的中國在西方的參照下如何確認(rèn)自身的困惑。他基于血緣的敘述反而讓我們看到更深層次的“情迷中國”,對這種迷戀的紓解則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他所堅信的“語言來自自然”。
顧城所說的自己對“自然”的信仰并不僅僅指涉著自然界,它更與道家思想密切相關(guān)。在法蘭克福大學(xué)舉行的“人與自然”世界各文化哲學(xué)研討會上,顧城對他所謂的“自然哲學(xué)”做了詳盡的解釋。他說自然是中國哲學(xué)的最高境界,“自”是本源、天生的狀態(tài),“然”則是認(rèn)可。他從莊子的《齊物論》生發(fā)出“人世是無生命的秩序,而自然則是有生命的無秩序”的解讀,談到抵達(dá)自然之境的人便是“真人”,而真人不受人間秩序的褒貶,“換一個角度也可被視作魔鬼”。[43]
在會后的問答環(huán)節(jié)便有教授提出顧城所說的自然觀不能給倫理學(xué)提供一個基礎(chǔ),“報告里講的絕對的自發(fā)的那種自然,人和動物之間沒有區(qū)別”[44]。但顧城卻回答這是一個精神需要和生存需要的問題,完全可以分開。他再次講到關(guān)于文革的“樹上觀虎”的比喻,重申兩者之間并不存在矛盾。這種倫理的危險性是否可以被顧城分隔精神與生活的解釋消除實(shí)為可疑。后世的評論者便批評他以“六經(jīng)注我”的方式有意誤讀文本,為殺妻自殺尋找借口。[45]我們不能判別顧城是否有意如此,但他確實(shí)在詮釋“自然”時將赤子之心的比喻看作是與人世禮法無涉的狀態(tài),對兒童與野獸,甚至是魔鬼都不做更多界分。這一點(diǎn)也顯現(xiàn)于顧城在《英兒》這本書中所做的自我剖析和懺悔:
我們可以在壁爐里看火,在鍍著薄金的玻璃里,看窗外的暴風(fēng)雨。我們做到了這一切,可是我們沒有辦法真正地滿足我們內(nèi)心的期待。它是一個嬰兒,也是一個野獸,它渾然無覺地要離開這一切,到那充滿精靈的野蠻的世界中去。那有它真正活的同伴、它的愛、生和死、它真正的時間。[46]
王德威分析“英兒”這個標(biāo)題便恰巧是“嬰兒”的諧音,這對一個書寫自己不愿長大的作家而言,無異于一種自我指稱。[47]不過,除了拒絕成長這層意思以外,這段敘述中最奇異的部分正是顧城對嬰兒與野獸等同的修辭以及他對野蠻世界的向往之情。這使我們必須再次回返對“童話”的理解。童話自五四時期被中國知識分子引入之時便是進(jìn)化論的主要承載形式,它被看作是“小說的童年”,是進(jìn)化史的源頭,與天真、野蠻、獸性等等相聯(lián)系。周作人因?yàn)閷@種文學(xué)形式的興趣而繼續(xù)追索人與文化的起源,借鑒人類學(xué)對“野蠻人”的研究得出兒童是“小野蠻”,也就是文明的野蠻人的結(jié)論。
“小野蠻”這個詞轉(zhuǎn)借自十九世紀(jì)晚期英國文學(xué)批評家戈斯(Gosse),而它更遙遠(yuǎn)的源頭則是盧梭(Jean-Jacque Rousseau)。在盧梭看來,所謂文明狀態(tài)才是墮落的,因?yàn)樗谷似x了與生俱來的自然狀態(tài)。[48]周作人等五四作家的兒童觀倒并非被這種浪漫主義文學(xué)和美學(xué)形塑而成,他們所關(guān)心的仍然是如何以童話對兒童進(jìn)行教化,使他們脫離野獸進(jìn)步為人類。八十年代關(guān)于啟蒙的主流思想也與此分享同樣的邏輯。當(dāng)彼時的詩評家將“童話詩人”的桂冠賦予顧城時,他們并未意識到童話之中還暗藏著野蠻的危險。
在《英兒》這篇小說的最后,顧城所寫的主人公也走到了生命的盡頭。他所不能忘懷的是兩本遺留在山頂小屋中的書。一本是法布爾的《昆蟲的故事》,另一本則正是盧梭的《一個孤獨(dú)者的散步》。這個結(jié)局似乎提示著:當(dāng)顧城與他的同代人共同使用著兒童與童話的修辭時,這位“童話詩人”卻已然選擇了不同的啟蒙之路。
余論
“童話詩人”顧城的自戕帶來了個人主體與民族國家的啟蒙承諾的雙重幻滅。不過,承載一個時代或一個國家的啟蒙寓言對顧城的個例來說或許過于沉重,他被同代人共同推舉的“真善美”的童話精神本就包含著許多誤讀,無論是希望還是幻滅的情感其實(shí)都是寄托在這種誤讀之上。所以本文更傾向于將顧城的人生與創(chuàng)作視為對啟蒙的一種探索,哪怕是一條歧路。站在八十年代初對“光明”的熱切向往和之后對“黑暗”的困惑與痛苦的情感之外,所謂的啟蒙的歧路也和“童話詩人”一樣,最終成為了印刻著這段歷史的標(biāo)簽。
注釋:
[1] 王德威:《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臺北:麥田出版社,2004年,第213頁。
[2] 陳子善等:《編者與友人的對話(代前言)》,《詩人顧城之死》,陳子善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頁。
[3] 同上,第4頁。
[4] 洪子誠:《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史》,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9年,第316頁。
[5] 顧城:《剪接的自傳》,《青春》1983年第7期。
[6] Yeh, Michelle “Nature's Child and the Frustrated Urbanite: Expressions of the Self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World Literature Today, 3 (Summer, 1991), pp. 405-409.
[7] 方冰:《我對于“朦朧詩”的看法》,《光明日報》1980年1月28日。
[8] 周良沛:《說“朦朧”》,《文藝報》1981年第2期。
[9] 鐘文:《三年來新詩論爭的省思——兼論辯〈價值·變革·表現(xiàn)手法〉一文》,《成都大學(xué)學(xué)報》1982年第2期。
[10] 徐敬亞:《崛起的詩群——評我國詩歌的現(xiàn)代傾向》, 《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史·史料選(下)1945-1999》,洪子誠主編,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715頁。
[11] 張捷鴻:《童話的天真——論顧城的詩歌創(chuàng)作》,《當(dāng)代作家評論》1999年第1期。
[12] 北島:《回答》,《詩刊》1979年第3期。
[13] 張宜雷:《尋找光明的眼睛——評顧城詩集〈黑眼睛〉》,《書林》1986年第11期。
[14] 謝曉虹:《五四的童話觀念與讀者對象——以魯迅的童話譯介為例》,《兒童的發(fā)現(xiàn):現(xiàn)代中國文學(xué)及文化中的兒童問題》,徐蘭君、安德魯·瓊斯主編,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第148頁。
[15] 顧城:《那么“死”也該有克有死——1987年12月香港答問》,《顧城文選卷四·生生之境》,香港:中國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132頁。
[16] 顧城:《“別有天地非人間”——1992年7月9日發(fā)言于德學(xué)生座談會(節(jié)選)》,《顧城文選卷一·別有天地》,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05年,第71頁。
[17] 顧城:《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顧城詩全編》,顧工編,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5年,第310頁。
[18] 顧城:《簡歷》,《顧城詩全編》,第230頁。
[19] 張清華:《朦朧詩:重新認(rèn)知的必要和理由》,《當(dāng)代文壇》2008年第5期。
[20] 張捷鴻:《童話的天真——論顧城的詩歌創(chuàng)作》,《當(dāng)代作家評論》1999年第1期。
[21] 顧城:《關(guān)于布林》,《顧城詩全編》,第757-758頁。
[22] 顧城:《金色的鳥落在我面前——同伊凡、高爾登、閔福德問答》,《顧城文選卷一·別有天地》, 第193-194頁。
[23] 顧城:《“恢復(fù)生命”》,《顧城文選卷一·別有天地》,第40頁。
[24] 顧城:《“人可生如蟻而美如神”——德國之聲亞語部采訪》,《顧城文選卷一·別有天地》,第84頁。
[25] 顧城:《許多時間,像煙》,《顧城詩全編》,第524頁。
[26] 顧城:《“恢復(fù)生命”》,《顧城文選卷一·別有天地》,第42頁。
[27] 顧城:《詩·生命》,《顧城詩全編》,第914頁。
[28] 顧城:《布林進(jìn)行曲》《布林不進(jìn)行曲》,《顧城詩全編》,第751-752頁。
[29] 顧城:《金色的鳥落在我面前——同伊凡、高爾登、閔福德問答》,《顧城文選卷一·別有天地》,第194頁。
[30] 顧城:《布林好像死了》,《顧城詩全編》,第754-755頁。
[31] Li Hua,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by Su Tong and Yu Hua: Coming of Age in Troubled Times, Brill, 2011.
[32] 顧城:《布林的出生及出國》,《顧城詩全編》,第742-743頁。
[33] 顧城:《關(guān)于布林》,《顧城詩全編》,第757-758頁。
[34] 顧城:《大游戲·小人間——于英國漢學(xué)會上的發(fā)言提要》,《顧城文選卷一·別有天地》, 第282頁。
[35] 顧工:《顧城和詩》,《詩人顧城之死》, 第154頁。
[36] 王德威:《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第214-215頁。
[37] 顧城:《從自我到自然》,《顧城文選卷一·別有天地》,第107頁。
[38] 顧城:《生命幻想曲》,《顧城詩全編》,第43頁。
[39] 顧城:《簡歷》,《顧城詩全編》,第230頁。
[40] 顧城:《從自我到自然》,《顧城文選卷一·別有天地》,第101頁。
[41] 梁秉鈞:《童話詩人顧城》,《大拇指》1986年第1期。
[42] 顧城:《與光同往者永駐》,《顧城文選卷一·別有天地》,第208頁。
[43] 顧城:《沒有目的的“我”——自然哲學(xué)綱要(德法蘭克福大學(xué)“人與自然”世界各文化哲學(xué)研討會上的報告)》,《顧城文選卷四·生生之境》,第154-168頁。
[44] 顧城:《宣讀〈自然哲學(xué)綱要〉答問——1993年7月10日法蘭克福大學(xué)》,《顧城文選卷四·生生之境》,第172頁。
[45] 劉文元:《從〈自然哲學(xué)綱〉要看顧城對老莊哲學(xué)的誤讀》,《安徽文學(xué)》2012年第9期。
[46] 顧城、雷米:《英兒》,北京:華藝出版社,1993年,第254頁。
[47] 王德威:《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第216頁。
[48] 劉皓明:《從“小野蠻”到“神人合一”:1920年前后周作人的浪漫主義沖動》,李春譯,《新詩評論》2008年第1期。
(轉(zhuǎn)載時刪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