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要文學”本身并不獨立地構(gòu)建記憶,但它們有自己的聲望
德勒茲和瓜塔里所撰卡夫卡論著的副標題為“Pour une littérature mineure”,即“為了(或朝向)一種次要文學”。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卡夫卡的作品只是德勒茲和瓜塔里發(fā)展“次要文學”這一寬泛概念的契機,次要文學雖由卡夫卡提出并在其作品中得到示范,但它同樣成為其他具有各種寫作習慣和傾向的作家的共同特征。次要文學概念的核心要義在于語言的某種特殊使用,在于通過強化已然內(nèi)在于語言之中的特質(zhì)來對語言進行解域化。這種語言的次要使用通過陳述的集體裝置來實行,并作為一種政治行動而發(fā)揮作用。次要文學的諸要素究竟如何相互關聯(lián),它們以何種方式呈現(xiàn)在語言自身之中,這些都是需要詳加說明的問題。德勒茲和瓜塔里在《卡夫卡》中詳細列舉了次要文學的諸要素,并在《千高原》中對這一概念進行了精心闡發(fā),這兩部著作不時以卡夫卡之外的作家為例來說明語言的次要使用。1979年,在《減法宣言》(SP)這篇論意大利劇作家卡爾梅洛·貝內(nèi)的文章中,德勒茲將這一概念拓展至戲劇領域。這些文本都表明,次要文學首先乃是語言的行動,戲劇由于在某種實用語境中將臺詞融入姿勢而成為這種行動的典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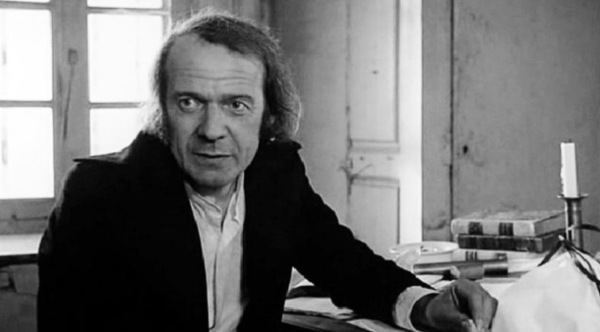
德勒茲
小眾文學
德勒茲和瓜塔里提出次要文學理論的靈感來源于卡夫卡寫于1911年12月25日的長篇日記。1911年初,卡夫卡開始參加一個來自倫堡([Lemberg]即奧匈帝國東北部靠近俄羅斯邊界的加利西亞[Galicia]省首府)的意第續(xù)語戲劇團體的演出,并與其中一位波蘭猶太裔演員伊茲霍克·勒維過從甚密。從勒維對華沙猶太文學的敘述和自己對捷克文學的接觸中,卡夫卡開始反思次要文學(字面義為“小文學”,“kleine Literaturen”)的活力。里奇·羅伯遜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卡夫卡在這篇厚重細密但時顯晦澀的日記中撰寫了“一篇純正的文學社會學論文”。
卡夫卡首先列舉了文學可能帶給民族或人民的諸多益處,即便此文學并不屬于某個特別龐大的群體。文學激發(fā)心靈和精神,提供公共生活中屢屢匱乏的某種統(tǒng)一的民族意識,并使民族在面臨敵對環(huán)境時擁有自豪感。它能帶來“對不滿意要素的吸納[die Bindung unzufriedener Elemente]”(Diary I, 191),并且通過文學雜志的持續(xù)活動而產(chǎn)生“單個人與其民族整體的持久結(jié)合”(Diary I, 192)。它使討論“父子之間的對立[des Gegensatzes]”成為可能,并且使以“暢所欲言和值得寬宥”的方式呈現(xiàn)民族缺陷成為可能。在這種文化環(huán)境中,人們會發(fā)現(xiàn)“文學從業(yè)者開始受到尊重”,此外,“一個欣欣向榮并因此自愛自重的圖書行業(yè)和對書籍的渴求勃然而興”(Diary I, 192)。文學成為一種直接的和生機勃勃的力量,它絕非某種僅供人們作壁上觀而品評鑒賞的事物,而是“一個民族的日記[Tagebuchführen einer Nation],這種日記與歷史編纂截然不同,并因此發(fā)展得更加迅速(但總是被仔細審察)”(Diary I, 191)。
在一個小民族中,并非“盡管有”(in spite of)而是“由于”(because of)文化規(guī)模的限制,次要文學才得以獲得乃至強化這些“文學益處”。一般而言,次要文學中沒有支配此領域的卓犖超倫之人,例如英國文學中的莎士比亞或德國文壇的歌德,這類人物的闕如產(chǎn)生了積極后果。沒有偉大的藝術家讓其他人黯然失色,并且“最大限度的真誠競爭具有真正的合理性”(Diary I, 192)。由于沒有任何出類拔萃的支配性作家,參與競爭的作家得以保持其相互的獨立性,并且由于沒有任何獨領風騷的偉大典范以供效顰,資質(zhì)平庸者的寫作也將難以為繼。當一個小民族開始書寫其文學史時,支配性作家的闕如會使不因品味而變動的穩(wěn)定經(jīng)典得以形成。這是因為作家們不可否認的影響“已經(jīng)如此確鑿無疑,乃至可以取代其作品”(Diary I,193)。甚至當讀者閱讀一部經(jīng)典名著時,他們所遭遇的并非作品自身,而是作品在民族傳統(tǒng)中聲望與地位的光環(huán)。在主要文學中有不勝枚舉的名著,其中一些隨著品味的改變而被遺忘,另一些隨著新生代讀者體驗到見棄于人的名著的感染力而再獲新寵。而在次要文學中,核心作品的影響力不會被遺忘,并且“作品本身并不獨立地對記憶產(chǎn)生影響”,這是由于它們有自己的聲望。因此,“再無遺忘,亦無憶起,文學史提供了一個不可變更和值得信賴的整體,幾乎不受時代品味的影響”(Diary I, 193)。不僅如此,由于納入文學史的作品數(shù)量相對較少,小民族“能更徹底地消化現(xiàn)存的資料”。不僅作品會得到更充分的吸收,而且民族自豪感將確保這些作品得到堅定的支持和保護,因為對于一個小民族而言,“文學關乎人民更甚于關乎文學史,所以,即便不是得到完全保存,也至少能得到可靠保存”(Diary I, 193)。
最后,在小民族那里,文學和政治學之間存在著密切關系。對此,卡夫卡的文字變得格外晦澀難解,這種關系背后的邏輯亦不全然明朗。卡夫卡寫道,由于缺少“相互關聯(lián)的人”,因此“相互關聯(lián)的文學行動”也付之闕如,他似乎想借此表明,在小民族那里,文人們并未組成一個以文學鑒賞為主的自足而相互關聯(lián)的團體。甚至當一部作品被人們冷靜地考察時,它的“邊界”也不是由它與其“相似物”(即其他文學作品)的關聯(lián)所規(guī)定,而是由它與政治的關聯(lián)所規(guī)定。事實上,政治關系“隨處”可見,并且常常是“人們甚至在它存在于此之前就力圖看到它”。但卡夫卡并不擔心文學會就此淪為純粹的政治宣傳,因為“文學的內(nèi)在獨立性使它與政治的外在關聯(lián)無傷大雅”(Diary I,194)。由此,小民族的文學緊緊黏附在政治標語中,但它們因此傳播到全國各地[die Litteratur sich dadurch im Lande verbreitet]。卡夫卡還指出,個人與政治在次要文學中互相滲透,因為“冒犯,作為文學的本意”,是作家和讀者之間論爭的公開而關鍵的部分。“偉大文學中發(fā)生在地底并構(gòu)成建筑物無關緊要的地窖的東西,于此處卻發(fā)生在昭昭白日之下,在彼處僅屬少數(shù)人心血來潮的問題,于此處卻吸引了每個人,堪稱生死攸關之事。”(Diary I, 194)
卡夫卡在日記結(jié)尾概括了“次要文學的特征列表”[Schema zur Charakteristik kleiner Litteraturen]:“1.生機勃勃:①沖突;②學派;③雜志。2.約束較少:①無法則;②小主題;③象征的建立輕松自如;④摒棄天資平庸者。3.普及性:①與政治相關;②文學史;③信仰文學,能為自身立法。”(Diary I, 195)由此,他總結(jié)道,次要文學因激烈的沖突而生機勃勃,不受大師的約束并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卡夫卡考察了小民族之所以產(chǎn)生這些特征的獨特條件,但他的興趣顯然超出了經(jīng)驗觀察和社會學闡釋的范疇。卡夫卡描述了捷克和華沙猶太文學,但也構(gòu)想了一個他希望參與其中的理想文學共同體的圖景,正如在日記結(jié)尾所說:“當一個人在其全部存在中已經(jīng)感受到這種有益的幸福生活時便難以再調(diào)整了。”(Diaries Ⅰ, 195)這一理想的共同體可能在小民族中培養(yǎng)出來,但它的實現(xiàn)并不必然地取決于這種佹得佹失的環(huán)境。最后,對于卡夫卡而言,次要文學應當在世界中發(fā)生作用,這也正是德勒茲和瓜塔里取用此概念的醉翁之意。他們從卡夫卡的文字中強調(diào)次要文學完全是政治性的,“關乎人民更甚于關乎文學史”;強調(diào)次要文學將個人納入政治之中,使個體沖突成為一件公共的“生死攸關之事”,讓父子之間的家庭爭論也成為公共議題;還強調(diào)次要文學不是以少數(shù)卓犖超倫的大作家為中心,而是集中在投身于欣欣向榮的集體事業(yè)的眾多作家身上。
解域化的語言
德勒茲和瓜塔里在描述少數(shù)文學時補充了卡夫卡未曾提及的兩個特征:在少數(shù)文學中,作家以“陳述的集體裝置”進行操作(K33; 18),使語言“受高度解域化的系數(shù)所感發(fā)”(K 29; 16)。他們在卡夫卡以布拉格猶太人身份用德語寫作的實踐中發(fā)現(xiàn)了語言解域化的例證。正如克勞斯·瓦根巴赫(Klaus Wagenbach)在研究早期卡夫卡時所詳細論述的,世紀之交的布拉格猶太人身處一個異乎尋常的語言環(huán)境中。大部分猶太人說德語并上德語學校。像卡夫卡一樣,許多猶太人的父母已經(jīng)背井離鄉(xiāng),融入都市生活,并棄用捷克母語,轉(zhuǎn)習布拉格的貴族用語。(據(jù)瓦根巴赫估計,布拉格市民中有百分之八十說捷克語,家境殷實的德裔居民占百分之五,其余則是說德語的猶太人[Wagenbach 28, 65, 181]。)卡夫卡成長于一個說德語的家庭,但不同尋常的是,他是當時猶太人中精通捷克語的人(Wagenbach 181)。由于還存在著“德語和捷克語的混合語”和Mauscheldeutsch(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猶太人語調(diào)的德語化的意第緒語),卡夫卡所處的布拉格的語言氛圍變得更加錯綜復雜。卡夫卡的父親偶爾會使用通行的Mauscheldeutsch的表達方式,瓦根巴赫還指出,卡夫卡父親的德語“與正確用法相距甚遠”(Wagenbach 80)。
瓦根巴赫認為,布拉格德語是一種貧乏的語言,是“一種由國家扶持的儀式語言”,它只是一具“異域的身體,如紙一般干枯無色”(Wagenbach 87)。正如《波希米亞》(Bohemia)雜志編輯海因里希·特韋勒斯(Heinrich Teweles)所感慨的,“在布拉格,我們沒有一個促使語言不斷更新的德裔族群;我們只是因受教育而成為德國人”(引自Wagenbach 77)。這種紙面語言不僅未能在業(yè)已組建的共同體中扎根立足,而且因與捷克語的持續(xù)接觸而在發(fā)音、句法和詞匯方面受到影響。許多說布拉格德語的人帶著濃重的捷克口音,并且其言談中典型的不標準的短語轉(zhuǎn)接常常泄露出捷克語語法結(jié)構(gòu)的影響。瓦根巴赫列出了這些特征的主要表現(xiàn),包括前置詞(darauf denken, daran vergessen)的誤用、代動詞(sich spielen)的濫用,以及冠詞(Wir gehen in Baumgarten,Eingang in Garten)的遺漏。普遍的詞匯貧乏同樣是布拉格德語的典型特征,這一情況的出現(xiàn)部分是因為捷克語使用者和德語使用者在交流時需要不斷對用語進行簡化處理,部分是由特殊的捷克語用法造成的。比如,布拉格的德語使用者經(jīng)常用簡單俗白的動詞geben(給予)來代替動詞legen、setzen、stellen和abnehmen(鋪陳、擺置、放置、移除),其用法對應于捷克語中的動詞dati(給予)。
用德勒茲和瓜塔里的話來表述,可以說卡夫卡的布拉格德語是一種解域化的德語。由于脫離了自然凝聚的德語民族共同體,布拉格德語通過親近捷克語而發(fā)生諸多變形,其貧乏性迫使有限的詞匯兼具多重功能,每個詞都承載著一種內(nèi)張的和變換的多音性(polyvocality)。瓦根巴赫注意到,許多布拉格作家為了彌補這種語言“漂浮”和“詞語貧乏”的狀況,采取了“豐富語匯”的應對方式,亦即大量運用明喻、暗喻、夢的象征、新詞、華麗辭藻、婉轉(zhuǎn)語等手法。與此相反,卡夫卡則借助瓦根巴赫所描述的“一種幾乎被褫奪所有本土影響的獨具個性的布拉格德語”(Wagenbach 80)來應對語言的漂浮和貧乏。這是一種“精確、冷靜、淡漠、質(zhì)樸,邏輯結(jié)構(gòu)至為縝密”(Wagenbach 76)的語言,滲透著“純化的傾向”和“‘取其字面義的遣詞’方法”(Wagenbach 86, 87)。從這種冷靜、淡漠、極簡風格中,德勒茲和瓜塔里發(fā)現(xiàn),卡夫卡接納了布拉格德語的貧乏,并通過苦行式的克制來強化其傾向,即有意增強業(yè)已存在于語言之中的解域化力量。
從這個方面來說,德勒茲和瓜塔里認為卡夫卡遵循了他本人于1912年1月18日在勒維劇團演出前發(fā)表的著名演講《意第續(xù)語導論》(“Introductory Talk on the Yiddish Language”)中所闡述的語言變形說。卡夫卡視意第續(xù)語為德語的分支,它的“習語簡短而急促”,是“一種奔流不息的口語”。詞語“并未深深地扎根其中,它們保持著被采納時的速度和活力。意第緒語充滿了從一端到另一端的大遷移”(Dearest Father 382)。它是“突發(fā)奇想和法則的語言混合物”,它“作為整體僅由方言組成,甚至書面語亦如此”。它和德語的親近保證了“每個德語使用者也能理解意第緒語”,盡管兩種語言之間的親密關系使得翻譯變得不可能:“事實上,意第緒語無法被翻譯成德語。意第緒語和德語之間的關聯(lián)是如此纖細脆弱和意味深遠,乃至一旦意第緒語被譯回德語,這種關聯(lián)就必定會被撕成碎片。”(Dearest Father 384-385)卡夫卡對他的聽眾說,使得現(xiàn)成的理解力成為可能的是,“除了你們所認知的,你們自身亦擁有主動力量并且能讓你們憑直覺領悟意第續(xù)語的力量進行聯(lián)合”(Dearest Father 385)。要言之,就像布拉格德語一樣,意第緒語也是(只是在更大程度上是)高度解域化(hyperdeterritorialized)的德語,奔流不息,簡短而急促,被大遷移橫穿而過,是突發(fā)奇想和法則的混合物,是無標準語調(diào)的方言混雜體,是一個不能被認識而只能憑直覺領悟的力量場域。
在德勒茲和瓜塔里看來,卡夫卡的意第緒語與其說是一種語言,不如說是棲居在語言中的一種方式,是小族群挪用大族群語言并破壞其固定結(jié)構(gòu)的一種途徑。意第緒語使用者和布拉格的猶太人一樣,對語言進行次要運用,對德語的標準要素進行去穩(wěn)定化的毀形(destabilizing deformation),這種毀形使它啟動,并向變形的力量開放。德勒茲和瓜塔里看到,這種語言的次要使用與卡夫卡對一個正常運轉(zhuǎn)的文學共同體的想象和諧一致,他們認為,卡夫卡在其作為作家的寫作實踐中,在其對意第緒語的理解和對“小文學”(small literatures)的分析中,至關重要的貢獻是將文學理解為語言實驗和政治行動的結(jié)合。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文學之為次要文學既非因它是屬于某個有限群體的文學(盡管文學的政治性常常鮮明地體現(xiàn)在“次要文學”中),亦非因它是屬于少數(shù)族群的文學(盡管語言毀形的效果經(jīng)常在少數(shù)族群的口語和書寫中昭然可見),而是因為它是次要使用的文學,是一種對語言中固有的支配性權力結(jié)構(gòu)進行“次要化”(minorization)處理的文學。現(xiàn)在,我們必須轉(zhuǎn)向德勒茲和瓜塔里在《千高原》中對語言的討論,去看看語言實驗在什么意義上具有直接的社會和政治效用。
語言和力量
對于德勒茲和瓜塔里而言,語言是行動的手段、行事的方式。正如言語行為理論家們所早已指出的,有一些特定的表達,如牧師宣布“我和你結(jié)婚”這句話,其陳述顯然就構(gòu)成一次行動。德勒茲和瓜塔里在這些施事表達中發(fā)現(xiàn)了所有語言的范例,并且認為語言學應被視為一種普通語用學或行動理論的分支。他們指出,語言的首要功能并非交流,而是施加命令——傳遞他們所說的mots d'ordre(“口號”“口令”,字面義即“命令詞”)(MP 96; 76)。每種語言都對世界進行編碼,對實體、行動和事態(tài)進行分類,確定它們的輪廓,指定它們的關系。語言介入產(chǎn)生的結(jié)果是現(xiàn)實按照某種支配性社會秩序被編排組織,并且任何地方只要出現(xiàn)言語行動,支配性社會秩序就被確認和強化。語言通過引發(fā)世界的“非身體轉(zhuǎn)變”(MP 102; 80)來運作,言語行為借助編碼改變事物、行動、事態(tài)等等,正如“現(xiàn)在我宣布你們結(jié)為夫妻”這個言語行為將新郎和新娘轉(zhuǎn)變?yōu)檎煞蚝推拮印_@一非身體轉(zhuǎn)變以常規(guī)的行動模式和實體的組織化的布局為先決條件,并且,正是借助被社會認可的慣例、制度和物質(zhì)實體的網(wǎng)絡,語言編碼才得以建立。這些復雜的網(wǎng)絡由“裝置”[agencements]組成,而裝置乃是以某種方式協(xié)同運作的諸異質(zhì)性行動和實體的集合。我們可以區(qū)分兩大類裝置,第一類為身體的非話語機器裝置,“施動和受動”的機器裝置,它們是“相互作用中的諸身體的融合”,第二類為話語的陳述的集體裝置,“行動和所述”的集體裝置,它們是“歸屬于身體的非身體轉(zhuǎn)變”(MP112; 88)。機器裝置是世界上諸實體賴以形成的諸實踐和要素的各種模式,陳述的集體裝置則是使得語言所述成為可能的諸行動、制度和慣例的程式。例如,當法官宣判被告“有罪”時,法典、司法機構(gòu)、立法機構(gòu)和執(zhí)法機構(gòu)的規(guī)范性及法庭行為慣例等等,所有這些協(xié)同運轉(zhuǎn)并共同組成一部陳述的集體裝置的東西都成為保證其判決有效性的先決條件。這種裝置的實體同樣通過非話語的實踐而得以成形,例如法院大樓、法槌、法官長袍等等,它們是由各式各樣作為機器裝置而發(fā)揮作用的行動網(wǎng)所產(chǎn)生出來的。盡管兩種裝置相互融合,但它們的進程相互獨立,陳述的集體裝置發(fā)揮著表達層面的作用,機器裝置發(fā)揮著內(nèi)容層面的作用。然而,表達和內(nèi)容之間的相互關系并非如能指和所指之間那般,而是體現(xiàn)為行動和實體的不同模式相互干預,相互介入彼此的運轉(zhuǎn):“在表達非身體的屬性并將此屬性賦予身體時,我們既不是在表征,也不是在指涉,而是以某種方式介入,而這就是一次語言的行為。”(MP 110; 86)
語言學家一般都從常量和衡量的角度來分析語言,然而德勒茲和瓜塔里認為標準的、固定的語言形式只是行動的常規(guī)模式產(chǎn)生出的次級效用。對于德勒茲和瓜塔里而言,首要的乃是變量,它們存在于一個由眾多“持續(xù)變動之線”組成的潛在維度中并由諸裝置在明確具體的情形中實現(xiàn)出來。試舉“我發(fā)誓!”(“I swear!”)這句話為例。從音位角度看,我們可能會將“發(fā)誓”發(fā)音時的變動視為對某個標準音位單位的無關緊要的偏離,德勒茲和瓜塔里卻認為“發(fā)誓”的所有可能發(fā)音構(gòu)成了一個聲音連續(xù)體,一條持續(xù)變動之線,它擁有潛在的實存,是真實的東西但并未成為現(xiàn)實。每個說話者都將此連續(xù)體的一個獨特份額實現(xiàn)出來,并且一種支配性社會秩序的調(diào)節(jié)性行動模式規(guī)定了連續(xù)體上哪些點是“正確的”發(fā)音,哪些點是“不正確的”“不標準的”“不正常的”發(fā)音。一種類似的連續(xù)體便構(gòu)成“我發(fā)誓”的句法基礎,這條持續(xù)變動之線包括“I do swear”“Me swear”“So do I swear”“Swear I”等等,標準和偏離再次通過行動的常規(guī)模式得到強化。最終,一條持續(xù)變動的語義之線貫穿“我發(fā)誓!”這句話。通常,一個陳述的語義內(nèi)容被視為穩(wěn)定的意指核心,在各種語境中呈現(xiàn)出各種具有細微差別的意義。但是德勒茲和瓜塔里將每個言語行為看作某個語義變量連續(xù)體的特定點的實現(xiàn)。兒子在父親面前發(fā)誓,未婚妻在未婚夫前面發(fā)誓或被告在法官面前發(fā)誓,每個情形中的“我發(fā)誓”都是蘊含著不同語義內(nèi)容的彼此相異的言語行為。每次語言運用都是某個潛在的“我發(fā)誓”的連續(xù)體的一次實現(xiàn),按照社會秩序的支配性慣例,各種具有細微差別的意義被裁定為是正常抑或偏離、字面抑或比喻、嚴肅抑或怪誕。
一種語言的所有持續(xù)變動之線是“抽象機器”的組成部分,而塑造世間實體的非話語行動模式的變化軌跡則是與其互補的另一個組成部分。陳述的集體裝置和非話語的機器裝置將抽象機器實現(xiàn)出來,而抽象機器則使兩種裝置彼此關聯(lián)。特定社會秩序的常規(guī)慣例對變量加以控制和約束,但持續(xù)變動之線依然內(nèi)在于裝置之中,它們使能夠動搖標準和規(guī)則的非標準的實現(xiàn)成為可能。因此,布拉格德語的各種“謬誤”和意第緒語中產(chǎn)生的德語變形都是持續(xù)變動之線上諸多點的實現(xiàn),這些變量從根基處破壞了標準德語的規(guī)則性并由此動搖了構(gòu)成語言規(guī)范性之前提條件的慣例、制度、實體和事態(tài)的所有裝置。因此,我們能夠理解為什么德勒茲和瓜塔里要將語言的解域化視為政治行動,這是因為語言自身就是權力結(jié)構(gòu)所塑造的行動,而語言的次要使用,例如布拉格猶太人對德語的次要使用,必然會挑戰(zhàn)權力關系,因為它抵抗標準用法的約束性控制并使非標準變量在語言之中運作。
[本文摘選自《德勒茲論文學》([美]羅納德·博格 著,石繪 譯,南京大學出版社·守望者,2022年1月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