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的返場》:細(xì)語眾聲和文學(xué)的可能性
在第六屆郁達(dá)夫小說獎審讀會議上,王堯教授提出小說再次發(fā)生革命的必要,而且以為新的“小說革命”已經(jīng)在悄悄進(jìn)行中。文學(xué)不論革命已久矣。王堯教授的發(fā)言自然引起文學(xué)界和大眾傳媒的興趣。《文學(xué)報》傅小平邀約近二十位作家和批評家做了對談,《江南》雜志開展了更大規(guī)模的筆談,張莉教授也正在組織相關(guān)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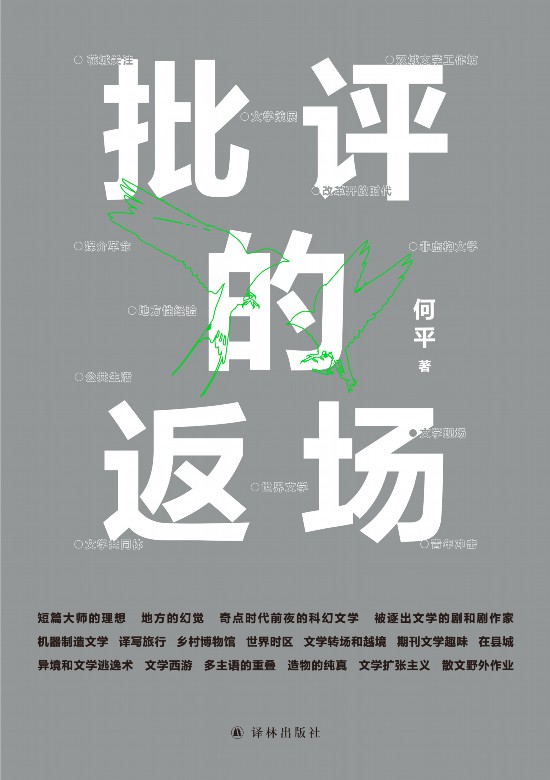
《批評的返場》
我同意王堯教授的“再次革命”說,也認(rèn)同他對“悄悄”的判斷。這五年給《花城》雜志主持《花城關(guān)注》欄目,以拓殖文學(xué)邊界,發(fā)微審美可能性作任務(wù),不可能不對可能策動的“文學(xué)革命”心向往之。但是,如果對標(biāo)百年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的文學(xué)革命范式,我又認(rèn)為,我們正處在一個“文學(xué)不革命”的時代——“文學(xué)不革命”,意味著類似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發(fā)生之初斷裂式的文學(xué)革命在當(dāng)下之不可能。“不革命”就是今天,甚至未來文學(xué)的常態(tài)。
首先,現(xiàn)代中國的“文學(xué)革命”,無論是五四前后,還是改革開放時代,都是新文化運動以及思想啟蒙的合體,是彼此聲援的自然結(jié)果。此間的邏輯,比如胡適的《建設(shè)的文學(xué)革命論》、陳獨秀的《文學(xué)革命論》、 周作人的《思想革命》都說得很清楚。周作人的結(jié)論是:“文學(xué)革命上,細(xì)語眾聲和文學(xué)的可能性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卻比第一步更為重要。我們不可對于文字一方面過于樂觀了,閑卻了這一面的重大問題。”以此觀乎改革開放初起的1980年代,文學(xué)革命同樣是和思想解放、文化啟蒙相互激蕩,彼此成就的。
文學(xué)沒有單獨的命運,哪怕是和文學(xué)相關(guān)的其他藝術(shù)門類,同樣也存在著彼此聲援相互激蕩的問題。我們可以有許多指標(biāo)去衡量二十世紀(jì)八十年代這個所謂的先鋒的文學(xué)革命時代。我說的先鋒的嘩變,不只是先鋒文學(xué)時代,更不只是先鋒小說時代。先鋒美術(shù)從“星星美展”到“85新潮美術(shù)”再到1989年的“首屆中國現(xiàn)代藝術(shù)展”,亦是二十世紀(jì)八十年代中國先鋒藝術(shù)最有力量和成果的部分。同樣,先鋒音樂和戲劇,其世界性的影響可能遠(yuǎn)遠(yuǎn)超過同時代的先鋒文學(xué)。
其次,雖然從梁啟超等人開始就已經(jīng)在現(xiàn)代意義上使用“革命”,但從“革命”更早的中國語源以及現(xiàn)代實踐來看,革命從來就是激烈的、斷裂的、替代的。在這一點上,現(xiàn)代的文學(xué)革命自然也不例外,斗爭思維和暴力手段也一直灌注在文學(xué)革命中。即便今天的文學(xué)革命取最平和的棄舊圖新的變革意義,依然涉及兩個問題:誰能領(lǐng)導(dǎo)這場文學(xué)革命?文學(xué)革誰的命?對于第一個問題,魯迅在《文藝和革命》一文中說:“先有軍,才能革命,凡已經(jīng)革命的地方,都是軍隊先到的:這是先驅(qū)。”“外國是革命軍興以前,就有被迫出國的盧梭,流放極邊的珂羅連珂……”那么,當(dāng)今中國文學(xué)誰能成為我們文學(xué)革命的盧梭和珂羅連珂?如果我們深究下去,我們之所以迷信文學(xué)革命,一定程度是預(yù)先相信了現(xiàn)代時間,也相信了文學(xué)進(jìn)化論。在現(xiàn)代時間上,人類文明存在著等級和級差。在傳統(tǒng)/現(xiàn)代、落后/先進(jìn)等等的文明譜系中,我們經(jīng)受了巨大的震驚時刻,也承擔(dān)著巨大的心理焦慮。不說更小的文學(xué)革命,五四前后和改革開放初起時的兩次大的文學(xué)革命都發(fā)生在從禁錮走向開放的歷史轉(zhuǎn)折點上。
青年在進(jìn)化的鏈條上是新的、未來的、進(jìn)步的,這是我們往往把文學(xué)革命托付給青年的前提。觀察中國現(xiàn)代歷次文學(xué)革命,青年們也都做了革命的先驅(qū),但是生命展開在承平時代的青年們,如《時鐘突然撥快——生于70年代》的主編之一蘇七七所說:“貧乏是我們共同的底色。童年的我們站在一個風(fēng)暴剛剛席卷而過的廢墟上,物質(zhì)貧乏,精神也一樣貧乏。”類似的感受也同樣地被收入本書的作者梁鴻體認(rèn)著,她說得更具體:“也許并不只是我。70后,在當(dāng)代的文化空間(或文學(xué)空間)中,似乎是沉默的、面目模糊的一群,你幾乎找不出可以作為代表來分析的人物。沒有形成過現(xiàn)象,沒有創(chuàng)造過新鮮大膽的文本,沒有獨特先鋒的思想,當(dāng)然,也沒有特別夸張、出格的行動,幾乎都是一副心事重重、懷疑迷茫、未老先衰的神情。”(梁鴻:《 歷史與“我”的幾個瞬間》)如果70后算“貧乏”的話,緊隨其后的80后和90后則更可能是。世界被抹平,落差被縮短,其結(jié)果則是,不要說召喚他們成為先驅(qū),可能像韓東、魯羊、朱文他們那樣搞“斷裂”的冒犯者和挑釁者都很難尋找。
退一步講,即便有所謂的青年先驅(qū),革命依然需要可動員的基本文學(xué)群眾,其中最大份額應(yīng)該是文藝青年。按照《深圳青年報》和安徽《詩歌報》的《中國詩壇1986’現(xiàn)代詩群體大展》的統(tǒng)計:“1986年——在這個被稱為‘無法拒絕的年代’,全國2000多家詩社和十倍于此數(shù)字的自謂詩人,以成千上萬的詩集、詩報、詩刊與傳統(tǒng)實行著斷裂。”不是所有的文藝青年都能成為先鋒作家和藝術(shù)家,他們也可能只“文藝”但不“先鋒”,也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放棄文藝,但挑戰(zhàn)既成慣例和體制的前衛(wèi)、反叛、反抗、創(chuàng)造卻是文藝青年成為文藝青年最有價值的部分。如果確實存在過先鋒文藝的黃金時代,也應(yīng)該是文藝青年的黃金時代。我曾經(jīng)在多個場合說過,如果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4.7億讀者的數(shù)據(jù)可靠,那么在證明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繁榮的同時,也說明國民整體文學(xué)審美堪憂,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這部分讀者很難成為我們想象中的文學(xué)革命的同路人。與此恰成對照的是,文學(xué)不革命以后,文藝青年也成為一種“群嘲”。
而且,文學(xué)革命落實在實踐層面,亟須有見地的編輯、出版人和批評家。今天幾乎所有的文學(xué)史都寫到,1980年代中國的先鋒文學(xué)是由殘雪、馬原、余華、蘇童、格非、孫甘露、洪峰等人組成的“想象的共同體”。我一直想的一個問題是,這些有著各自寫作出發(fā)點的人是如何被召喚到一起的?1986年,吳亮和程德培主編出版了《新小說在1985年》和《探索小說集》兩個小說選本,正是這兩個選本使得星散在各家文學(xué)期刊的先鋒作家得以聚合。而且聚合是以“新”和“探索”的名義,其刻意“編輯”和“設(shè)計”的意圖相當(dāng)明顯。吳亮和程德培明確指出:“一九八五年,既是前幾年小說觀念變化醞釀的結(jié)果和總結(jié),又是進(jìn)一步向未來發(fā)展的開端。”在《新小說在1985年》這個帶有“傾向性的選本”前言中吳亮則進(jìn)一步強調(diào)“1985年”這個時間節(jié)點的意義:“一九八五年的小說創(chuàng)作以它的非凡實績中斷了我的理論夢想,它向我預(yù)告了一種文學(xué)的現(xiàn)代運動正悄悄地到來,而所有關(guān)在屋子里的理論玄想都將經(jīng)受它的沖擊。”1986年除了這個富有意味的小說選本,在詩歌界還有《詩歌報》和《深圳青年報》的《現(xiàn)代主義詩群體大展》。1988年4月余華在給《收獲》編輯程永新的信中談到“極端主義的小說集”:“我一直希望有這樣一本小說集,一本極端主義的小說集。中國現(xiàn)在所有有質(zhì)量的小說集似乎都照顧到各方面,連題材也照顧。我覺得你編的這部將會不一樣,你這部不會去考慮所謂客觀全面地展示當(dāng)代小說的創(chuàng)作,而顯示出一種力量,異端的力量。就像你編去年《收獲》第5期一樣。”這封信里談到的應(yīng)該是程永新編輯的《中國新潮小說》。
在1980年代的文學(xué)革命中,巴金做主編的《收獲》是最不講究這種穩(wěn)妥平和的,其面目是反常的、革命的和摧毀式的,像余華信里提到的1987年第5期,還有1988年第6期,兩個專號的陣容幾乎全部由馬原、余華、格非、蘇童、孫甘露這些代表著當(dāng)時最為激進(jìn)的創(chuàng)作的作家組成。當(dāng)時的年輕編輯程永新多年以后回憶:“在《收獲》新掌門人李小林的支持下,我像挑選潛力股一樣,把一些青年作家匯集在一起亮相,一而再, 再而三,那些年輕人后來終于成為影響中國的實力派作家,余華、蘇童、馬原、格非、王朔、北村、孫甘露、皮皮等,他們被稱為中國先鋒小說的代表人物。”《收獲》這種充滿了強烈預(yù)先設(shè)計的先鋒姿態(tài),讓身在其中的作家也產(chǎn)生錯覺,以為是一個新的文學(xué)時代的降臨。1987年10月7日蘇童在給程永新的信中寫道:“《收獲》已讀過,除了洪峰、余華,孫甘露跟色波也都不錯。這一期有一種‘改朝換代’的感覺,這感覺對否?”說到“改朝換代”,如果我們今天諸事俱備,自然面臨文學(xué)革命“革誰的命”的問題:我們宣判誰,哪些是舊人、舊文學(xué)?事實上,五四新文學(xué)宣判過舊文學(xué);改革開放時代文學(xué)“pass過北島”,也宣告過新的文學(xué)原則崛起。因而,在今天,如果我們既不能坦誠地宣判哪些文學(xué)、文學(xué)的哪些部分是舊的、陳腐的,也不能明示哪些文學(xué)、文學(xué)的哪些部分是正在崛起的、新的,文學(xué)革命立足何處?尤可深思的,究竟是審美判斷匱乏,還是勇力不逮?
有意味的是,韓東、魯羊、朱文他們挑動“斷裂”的1998年恰恰是70后出場之后不久。這恰恰是一個歷史分界線,此后至今似乎再無文學(xué)革命。和韓東、魯羊、朱文這些兄長輩主動“斷裂”不同的是,70后最初的叛逆面目是大眾傳媒調(diào)教和制造出來的,而此后的80后也迅速復(fù)制了這種出場方式。文學(xué)新青年不是自我文學(xué)滌新的結(jié)果,我們將會在今天的文學(xué)看到,越到后來,青年作家的成長和成名越來越依賴其掌握和操縱的媒體資源。不只如此,在配合媒體的同時,青年作家也配合可資獲益的文學(xué)制度,以至于文學(xué)交際、文學(xué)活動、文學(xué)宣傳在一個作家成長生涯中所占份額越來越大。整個文學(xué)制度和文學(xué)譜系,青年寫作者的寄生性,導(dǎo)致的直接結(jié)果是他們不可能宣判代際意義上的中老年作家是舊文學(xué)。所以,我對今天文學(xué)革命之不可能的悲觀,正是基于我們有如此多的基礎(chǔ)工作沒有完成,或者干脆無法完成。如此,遑論文學(xué)革命。韓東曾經(jīng)說過,他們的“斷裂”是空間意義上的。“在同一時間內(nèi)存在著兩種水火不容的寫作。”(韓東:《備忘:有關(guān)“斷裂”行為的問題回答》)以我對“斷裂”至今二十余年中國文學(xué)的觀察,這種空間意義水火不容的寫 作秩序關(guān)系依然存在。去年“界面文化”出版過一本《野生作家訪談錄》,副標(biāo)題是“我們在寫作現(xiàn)場”。這些以“野生作家”為名的作家包括:趙松、朱岳、劉天昭、于是、獨眼、袁凌、盛文強、常青、楊典、史杰鵬、康赫、胡凌云和顧前。名之“野生”,大致等于韓東所說的“極少數(shù)的、邊緣的、非主流的、民間的、被排斥和被忽略的”。按照我對中國當(dāng)代作家構(gòu)成的了解,或者我們直接去翻翻這幾年后浪的原創(chuàng)出版書目,這個名單還可以開得更長,更年輕。再把這份大名單和引發(fā)王堯教授“再次革命”說的第六屆郁達(dá)夫小說獎終評備選篇目作者對讀(不僅僅是這個備選篇目,可以擴大到期刊、大學(xué)和文學(xué)組織機構(gòu)票選的榜單和評獎),就能發(fā)現(xiàn)他們幾無重合。我沒有和王堯教授交流,這些“野生作家”的異質(zhì)性屬于不屬于他所說的“悄悄”?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他們雖然和韓東他們的“斷裂”在時間中的空間站位相同,但從接受的訪談來看,他們并不想策動又一場空間意義“在野”和“在朝”的“斷裂”,從而成為文學(xué)革命的發(fā)起人。不僅不想,他們無視、不自覺另外的空間的存在,寫作成為自洽的、自適的,很隱微、很私人的事。即便我們能夠辨識他們提供的文本是異質(zhì)的,他們已然喪失成為類似1980年代先鋒文學(xué)實踐者的極端主義姿態(tài),自然也不會選擇需要充沛激情的先鋒姿態(tài)。
事實上,對當(dāng)下文學(xué)版圖的想象已經(jīng)從線性的、垂直的等級關(guān)系變成平行的對等關(guān)系,比如這些作者:今何在、貓膩、江南、天下霸唱、血紅、滄月、無罪、當(dāng)年明月、玄雨、桐華、辛夷塢、唐家三少、南派三叔、蝴蝶藍(lán)、夢入神機、流瀲紫、烽火戲諸侯、我吃西紅柿……他們從事的是資本定義的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即便傳統(tǒng)的所謂純文學(xué)(精英文學(xué)或者雅文學(xué))認(rèn)定他們的通俗文學(xué)身份,也并不能以垂直的等級關(guān)系將其清除出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版圖。這種垂直的審美高下的等級關(guān)系在今天只能是假想層面的,而從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這面,他們認(rèn)為他們和純文學(xué)版圖是同樣的文學(xué)部落,對等,但并不謀求對話。類似情況,還有劉慈欣、江波、糖匪、寶樹、陳楸帆、遲卉、郝景芳、夏笳、王侃瑜、飛氘等這些科幻作家。科幻文學(xué)有自己的刊物、圈子、傳播路徑和評價機制等。但最近幾年,以劉慈欣和郝景芳獲獎為標(biāo)志,這個專業(yè)而狹隘的圈子被打破,科幻文學(xué)的地理版圖越來越大。
如果細(xì)細(xì)梳理下去,比傳統(tǒng)期刊文學(xué)、野生文學(xué)、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和科幻文學(xué)更小的文學(xué)部落還有很多,甚至單個的人都可以成為一個文學(xué)部落。他們以期刊、圖書等紙媒,也以網(wǎng)絡(luò)社區(qū)、公眾號、圈(群)等勘定邊界和疆域,部落與部落、部落和個人之間不再是對抗的、征服的、收編的,而是綏靖的、相安無事的,這種綏靖和相安無事可能是對外的,也可能是內(nèi)部的。緣此,我們儼然進(jìn)入一個細(xì)語的眾聲文學(xué)時代,這就是我所說的“文學(xué)不革命”時代。在這個“文學(xué)不革命”時代寫作,神圣的文學(xué)事業(yè)降格為全民寫作的日常文學(xué)生活。文學(xué)可以和內(nèi)心相關(guān)、和體制相關(guān)、和生意相關(guān),當(dāng)我們真的想要文學(xué)革命,已經(jīng)組不了團,成不了軍,布不了陣。如此,說穿了,我們還心念的文學(xué)革命不過是宏大歷史敘事癖作祟。那么,我們一起假想一下文學(xué)革命的可能性,寫作者自己已經(jīng)不可依靠了,就依靠期刊策劃?還是研究者和批評家想象的建構(gòu)?那該需要怎樣的洞悉和統(tǒng)攝時空的能力,才可以將一塊塊收集的文學(xué)碎片拼貼出富有歷史感而又通向未來的文學(xué)地圖。或者,在今天“文學(xué)不革命”的時代,任何的參與者至多只是一個文學(xué)碎片的收集人和占有者。
本文選自何平所著《批評的返場》中“思潮”一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