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jīng)典作家在海外—— 汪曾祺:“人間送小溫”
汪曾祺被譽(yù)為短篇巧匠、文體名家、多面圣手,從上世紀(jì)40年代以詩歌、小說、散文走上文壇,中經(jīng)上世紀(jì)50年代的沉寂與厚積,再到晚年憑借短篇小說《受戒》《大淖記事》等異軍突起,他成為20世紀(jì)中國文壇為數(shù)不多的融匯古典文章與現(xiàn)代技巧、延續(xù)“五四”文脈而藝術(shù)常青的作家。汪曾祺作品中既有民族性,又有豐富的世界性因素,隨著中外交流的深入開展,他的作品以獨(dú)異的風(fēng)格引起世界文壇關(guān)注,為海外讀者所喜愛。

法譯本小說選《歲寒三友》,安妮·居里安譯
先聞其名,后識(shí)其作
早在上世紀(jì)70年代,海外讀書界就對汪曾祺有所知曉。1973年,旅居美國的華裔中國文學(xué)學(xué)者許芥昱出版了英文著作《中國的文藝界》,如實(shí)記錄了他回中國拜訪27位作家、音樂家、演員的經(jīng)過。其中一篇《舞臺(tái)上不再是帝王將相》,訪談對象是京劇現(xiàn)代戲《沙家浜》劇組的兩位主創(chuàng)人員——汪曾祺和李慕良。這本書成為海外了解中國文藝界動(dòng)態(tài)的難得資料,也讓外界了解到汪曾祺的編劇工作。
1986年11月,50多位外國漢學(xué)家和40多位中國作家、評論家在上海金山賓館參加“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國際討論會(huì)”,史稱“金山會(huì)議”。這是一次影響深遠(yuǎn)的當(dāng)代文學(xué)會(huì)議。汪曾祺在會(huì)上與葛浩文、金介甫、李歐梵、陳幼石、顧彬、易德波、秦碧達(dá)等國際中國文學(xué)研究者愉快交流,擴(kuò)大了其人其作的海外影響。
1987年的美國之行,堪稱汪曾祺國際交往中的“高光時(shí)刻”。行前,美國《紐約時(shí)報(bào)》發(fā)表了中國作家專訪稿,稱汪曾祺為“尋根文學(xué)之父”。當(dāng)期愛荷華大學(xué)國際寫作計(jì)劃邀請了27個(gè)國家的33名作家,3個(gè)月里,汪曾祺除了與寫作計(jì)劃主持人聶華苓及其丈夫保羅·安格爾成為朋友,還與各國作家共同寫作、交流、聯(lián)誼、參訪,廣泛接觸美國僑界、報(bào)界、漢學(xué)界。汪曾祺精湛的廚藝、幽默的談吐、敏捷的才思、率性靈動(dòng)的書畫小品、隨和而善解人意的交際藝術(shù),使他成為同儕中耀眼的明星。他在愛荷華、芝加哥、耶魯、哈佛、賓夕法尼亞等各大學(xué)發(fā)表了《我是一個(gè)中國人》《談作家的社會(huì)責(zé)任感》《中國文學(xué)的語言問題》《我是如何寫作的》等演講,反響強(qiáng)烈。他在寫作計(jì)劃期間著手的寫作項(xiàng)目是“聊齋新義”系列,部分篇章首先在美國《華僑日報(bào)》《中報(bào)》等發(fā)表。《華僑日報(bào)》還轉(zhuǎn)載了汪曾祺與林斤瀾的一次有關(guān)文學(xué)社會(huì)性與小說技巧的對談。這次美國之行加深了美國乃至海外學(xué)界對汪曾祺和他的文學(xué)觀的認(rèn)識(sh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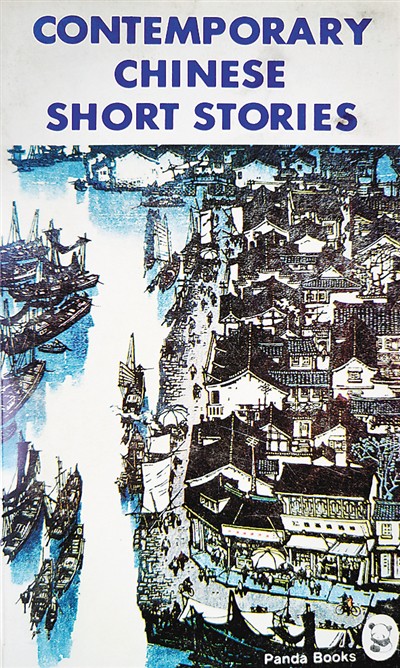
“熊貓叢書”《當(dāng)代優(yōu)秀小說選》英文版
向世界講述高郵故事
汪曾祺作品譯介到海外,起始于入選面向海外發(fā)行的《中國文學(xué)》及其“熊貓叢書”。1981年,《大淖記事》甫一問世,就被《中國文學(xué)》選中翻譯至海外,1984年又入選英文版《當(dāng)代優(yōu)秀小說選》。1989年和1990年,“熊貓叢書”先后推出法文版、英文版的汪曾祺小說選,作者特意撰寫了前言,即自傳散文《自報(bào)家門》。其中英文版題名《晚飯后的故事》,收入《雞鴨名家》《異秉》《受戒》《歲寒三友》《大淖記事》等13個(gè)短篇小說,有10篇以上是以故鄉(xiāng)高郵的舊時(shí)生活為題材。
上世紀(jì)80年代后期,海外譯者開始不斷譯介汪曾祺的短篇小說,尤其是他的高郵題材與一些小小說珍品。在英語世界,1988年,葛浩文翻譯的《陳小手》《尾巴》在美國發(fā)表,后收入《哥倫比亞現(xiàn)代中國文學(xué)作品選》《麻雀高聲叫:中國當(dāng)代小小說選集》等多種重要選集。1991年冬季號《青山評論》(GMR)為“中國寫作”專號,也選登了《陳小手》。1995年,《二十世紀(jì)中國短篇小說》由老牌出版社勞特里奇出版,方志華翻譯。該書選入魯迅以降小說家十余人,包括汪曾祺的《受戒》,提供了汪曾祺經(jīng)典代表作的另一個(gè)英譯本。
在法語世界,1988年法國出版的《重回白晝:中國小說選(1978-1988)》,收入了《晚飯花》,有學(xué)者認(rèn)為該書篇目是“精心選擇的,并且具有無可爭辯的代表性價(jià)值”。安妮·居里安翻譯的小說集《歲寒三友》(包括《歲寒三友》《大淖記事》《受戒》),是汪曾祺代表作最重要的法譯本。安妮·居里安是汪曾祺最熟悉的、通常也被認(rèn)為是對汪曾祺理解最深的法國漢學(xué)家。作家布里吉特·杜贊晚近創(chuàng)辦的“當(dāng)代華文中短篇小說”專題網(wǎng)站,在汪曾祺條目下列有資料豐富的評傳,同時(shí)附有中法對照的《羊舍一夕》《尾巴》。
在俄羅斯,汪曾祺作品譯介始于1996年格里高利·卡舒巴翻譯的《八月驕陽》。其后則有瑪麗娜·切列夫科、葉卡捷琳娜·扎維多夫斯卡婭、林雅靜等翻譯的《受戒》《大淖記事》《陳小手》《李三》等作品,有的還不止一個(gè)譯本。在捷克,1993年漢學(xué)家包婕譯介了《黃油烙餅》《受戒》等。在日本,汪曾祺有很多知音,除了上述主要作品,還有《鑒賞家》《李三》《橋邊小說三題》等被譯成日文。汪曾祺小說《小芳》還被編入日本放送大學(xué)振興會(huì)出版的漢語教材中,無意中感動(dòng)過不少學(xué)習(xí)中文的日本讀者。
汪曾祺的小說代表作,通過高郵故事表現(xiàn)傳統(tǒng)的中國文化觀念、寄寓溫暖的人間情懷,引發(fā)了國際文壇的濃厚興趣,使它們相當(dāng)程度上成為“世界性文本”。安妮·居里安的法譯本《歲寒三友》問世后,有書評盛贊小說所表現(xiàn)的中國式情感、氣氛,工筆描繪,敘述的簡潔與節(jié)制,想象的豐富以及對中國古典散文傳統(tǒng)的繼承等,較為典型地反映了西方讀者喜愛汪曾祺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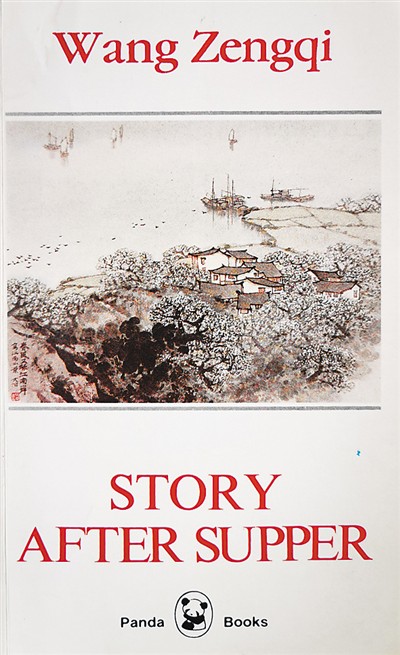
“熊貓叢書”小說選《晚飯后的故事》英文版
漸成海外研究熱點(diǎn)
1988年,在美國、中國召開的兩次討論會(huì),開啟了海外學(xué)者對汪曾祺的專題研究。當(dāng)年春,在舊金山一次重要的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會(huì)議上,加拿大漢學(xué)家杜邁可在討論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小說的沖突時(shí),以汪曾祺作品為例,指出傳統(tǒng)在現(xiàn)代浪潮之下找到宣泄口這一現(xiàn)象。杜邁可在后來的研究中持續(xù)關(guān)注汪曾祺,認(rèn)為“其作品的推動(dòng)力,在于對民族命運(yùn)的憂心”。當(dāng)年9月,《北京文學(xué)》在京召開“汪曾祺作品研討會(huì)”,法國的安妮·居里安、瑞典的秦碧達(dá)、美國的林培瑞等漢學(xué)家參會(huì)。該刊稍后辟出“汪曾祺作品研討會(huì)專輯”,收錄了安妮·居里安的《筆下浸透了詩意——沈從文的〈邊城〉和汪曾祺的〈大淖記事〉》,標(biāo)題準(zhǔn)確概括了作者對汪曾祺作品的閱讀體驗(yàn)與判斷,也深得汪本人認(rèn)同。
1992年,赫爾穆特·馬丁與金介甫合作編輯了《現(xiàn)代中國作家自畫像》一書,收錄44位作家?guī)в小白援嬒瘛毙再|(zhì)的創(chuàng)作談文章,“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洞察了作家的思想”。有書評指出,汪曾祺的《自報(bào)家門》是“精心制作的、有啟發(fā)性的”篇章之一。1993年,在英國任教的趙毅衡編了《迷舟:中國前衛(wèi)小說》一書,介紹上世紀(jì)80年代后期以來的新潮小說,菲利普·威廉姆斯在一篇書評中指出,趙毅衡在背景介紹中忽視了上世紀(jì)40年代的汪曾祺。這說明,早在1993年,一些西方學(xué)者對青年汪曾祺的創(chuàng)作已有相當(dāng)認(rèn)識(shí)。而在中國,汪曾祺的早期創(chuàng)作還要晚幾年才稍稍引起關(guān)注,其早期作品的發(fā)掘、編入全集,更遲至汪曾祺逝世20年后。
中國批評家的論述在海外發(fā)表,也影響了世界范圍內(nèi)的汪曾祺研究。1993年,李陀的《現(xiàn)代漢語的新活力》被收入奧爾胡斯大學(xué)出版社的《中國文學(xué)文化中的現(xiàn)代主義與后現(xiàn)代主義》一書。李陀指出,汪曾祺等作家開啟了對漢語美感與特質(zhì)的探索,汪有意識(shí)地重建與古典和白話傳統(tǒng)之間的聯(lián)系,是抵制過度西化的范例。1995年,錢理群的《1940年代以來中國的小說理論概觀》譯文在美國《現(xiàn)代中國文學(xué)》雜志發(fā)表,高度評價(jià)了汪曾祺寫于1947年的論文《短篇小說的本質(zhì)》。
汪曾祺有句流傳很廣的玩笑話,是對自己的晚輩說的:“你們都對我好點(diǎn)啊,我以后可是要進(jìn)文學(xué)史的!”他不僅進(jìn)入了中國的各類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史,還是海外中國文學(xué)史中的“常客”。2001年,梅維恒主編的《哥倫比亞中國文學(xué)史》出版,認(rèn)為“沈從文和其弟子汪曾祺可以被稱為現(xiàn)代漢語的文體大師。吊詭的是,雖然二人并沒有回避外來的借詞或者句法結(jié)構(gòu),但是它們在現(xiàn)代散文中成功地傳遞了一種古典的審美感受性”。這與汪曾祺本人對自己“文體家”的定位相一致。2005年,德國顧彬的《二十世紀(jì)中國文學(xué)史》出版,談到民族歷史記憶的文學(xué)表現(xiàn)時(shí),舉“富有天分的小說家”汪曾祺為例:“他最有名的短篇小說是《受戒》(1980),反映了他對美和天然的審美觀點(diǎn)。這里不是一位知識(shí)分子在對國家和人民作一個(gè)(道德)評判,這里是某個(gè)人,某個(gè)覺得和江蘇的故鄉(xiāng)民間文化緊緊相聯(lián)的人,在描繪像你和我一樣的普通人……”顧彬認(rèn)為,汪曾祺“描述了一個(gè)永恒的、如樂園般的世界”,這在上世紀(jì)80年代的中國文壇是不多見的。2010年出版的美國《劍橋中國文學(xué)史》(孫康宜、宇文所安主編)里,在奚密撰稿的“1937-1949年的中國文學(xué)”一章中,把研究的觸角伸向了汪曾祺上世紀(jì)40年代的作品《復(fù)仇》:“《復(fù)仇》的文字既口語又抒情,既意象化又簡潔……這個(gè)關(guān)于化解和超越的故事充滿了佛道哲思。”
汪曾祺自述詩中有一句“寫作頗勤快,人間送小溫”。他的文學(xué)情懷,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滋養(yǎng)的結(jié)果,也是世界讀者都能感知的一種普遍情懷。2003年,日本學(xué)者德間佳信在致汪曾祺研究會(huì)的信中談及,是汪曾祺的作品使他走上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之路,“我認(rèn)為汪先生是中國本世紀(jì)屈指可數(shù)的偉大作家,他的作品能使所在的國家為之感動(dòng)。他的作品不靠什么支配性的文藝?yán)碚摚奶频那楣?jié)等,而是文學(xué)本身的力量創(chuàng)造出充滿了象征、美麗的世界,所以,我很尊重汪先生。”這代表了海外學(xué)者與讀者的共同心聲。
(作者系東北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