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弢:我自書生甘白袷
巴金先生生前倡議建立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館,有人擔(dān)心藏品難以征集,巴老頗有信心地說:有唐弢的藏書,文學(xué)館就有了半邊江山。如此可見唐弢的分量。唐弢曾有詩云:“我自書生甘白袷,人生不盡滄桑感。”如此書生般作家,文壇還會有幾何?
一、郵局里的進(jìn)步“文青”
唐弢(1913年3月—1992年1月)原名唐端毅,字越臣,生于浙江省鎮(zhèn)海縣古唐村的一個農(nóng)戶家。雙親目不識丁,但父親堅持借債讓他讀書,又讓他跟同村的人到上海去開闊眼界、增長見識,十三歲考入華童公學(xué),勉強(qiáng)讀到初中二年級,因父親患病,他被迫輟學(xué),早早挑起養(yǎng)家重?fù)?dān)。正巧得悉上海郵局招人,他應(yīng)考被錄取為投遞組揀信生。十六歲的他,在上海開始了人生新篇章。

唐弢先生
他做信件分揀工作,一般作業(yè)時間是在傍晚至第二天凌晨一點左右,這個工作特別適合他,完工后去宿舍睡一覺,第二天白天,他就去四川路橋郵局附近的圖書館待一整天,如東方圖書館、申報量才流通圖書館、市商會圖書館,去得最多的還是自己的郵務(wù)工會圖書館。可見他年少志堅,求知欲之強(qiáng)。
抗戰(zhàn)中,在上海職業(yè)界救亡協(xié)會郵政分會里,地下黨辦了一份進(jìn)步刊物《驛火》,報頭是一排綠色大雁,唐弢受命以筆名“馬前卒”寫了一首《獻(xiàn)詩》作為發(fā)刊辭,以鼓舞郵工們,最后兩句寫道:“在激蕩的風(fēng)雨中宵/驛站上的火把又亮起來了!”他的詩文很受郵局員工喜愛。此時,他在郵局內(nèi)已小有名氣,是積極要求上進(jìn)的有為青年,也是名副其實的“文青”了。
在投遞組工作了十多年,唐弢工作出色,被調(diào)到郵政公眾服務(wù)組,專職從事對外聯(lián)絡(luò)與公關(guān)工作,這發(fā)揮了他的秀才作用。唐弢就在《文匯報》《大公報》上,先后開辟了“郵政問答”“郵政常識”等專欄,撰寫“星期論文”,夾帶宣傳要和平、反內(nèi)戰(zhàn)的道理。
二、第一部雜文集
唐弢是著名雜文家,他的寫作成就,主要體現(xiàn)在雜文上。1936年3月,上海天馬書店出版了他的第一本雜文專著《推背集》。魯迅先生曾兩次在信中談及此書如何出版,并幫他聯(lián)系出版界朋友。最后,在魯迅、陳望道的幫助下,該書得以順利出版。
在郵局工作的業(yè)余時間,唐弢最喜歡閱讀的是《申報》黎烈文主編的《自由談》副刊,他最早投稿的也是這個副刊,寫的多是雜文。所以,在《推背集》的《前記》中,他第一句話就是:“這里是我的七十幾篇雜文。我開始想寫文章,是一九三三年的春天,那時候我掙扎在生活的重?fù)?dān)下,常常想找一個排遣的方法,孤身寄寓,可與閑談的人少,所以就翻翻《申報》,也看看里面的《自由談》。這樣就有了投稿的念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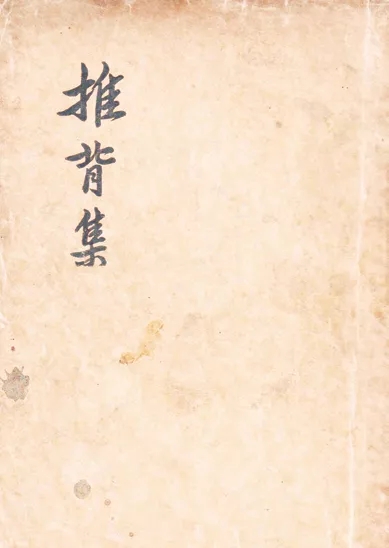
《推背集》
那時,年小的唐弢獨自在上海打工,寂寞可想而知。父親因病早歿,留下了四百元債務(wù)。加上母親心急如焚,右眼也病瞎了。親人疏遠(yuǎn),債主威逼,家里的每次來信,都讓他感到有“一萬支箭一齊射向我這顆年青的心”。他無法擺脫孤寂,寄寓在遠(yuǎn)房親戚開設(shè)的三陽南貨店擱樓里,看著窗外,雨水滴滴,千愁萬緒襲上心頭,在不停的雨聲中,想著家里的往事,他不由自主地提起筆,寫下了《故鄉(xiāng)的雨》,署名唐弢,投寄《申報》,過了沒幾天,文章居然在《自由談》登出來了。這是他用“唐弢”第一次正式發(fā)表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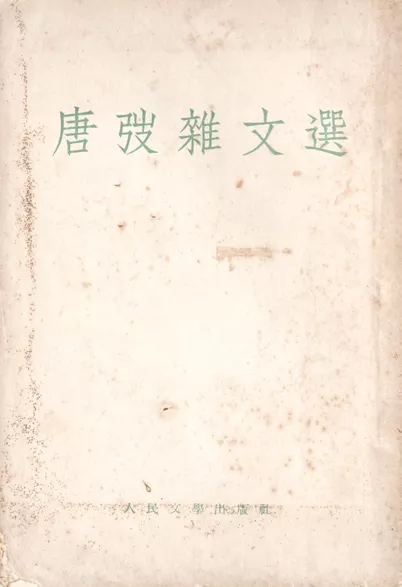
《唐弢雜文選》
《推背集》共分五輯,“老話”六十一篇,“說實話”七篇,“物喻”六篇,“鄉(xiāng)音”十篇,“讀書記”一篇,總計應(yīng)該八十五篇。其實這應(yīng)該是一部雜文和散文的合集,“鄉(xiāng)音”一輯,均是散文。此書甫出,文學(xué)評論家孔羅蓀就寫了《讀〈推背集〉》一文,刊在《北平新報》副刊上,文中說:“它不但為某些人物畫了像,某些事件作了記錄,而且也為某一個時代畫了一個輪廓,指出了里面的鬼祟、丑惡、腐敗,黑暗和光明”。《立報》副刊發(fā)表了周楞伽(苗埒)的評論:“如若說小品文是投槍而不是小擺設(shè),則這個集子就是充分發(fā)揮了投槍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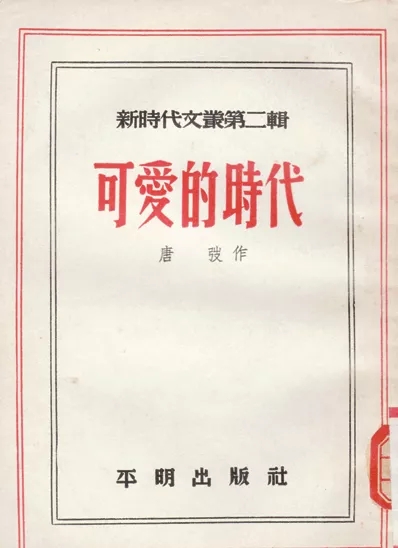
《可愛的時代》
《推背集》之后,唐弢陸續(xù)出版了《海天集》《投影集》《短長書》《勞薪集》《識小錄》等雜文集,及至新中國成立,他依然執(zhí)著于雜文的創(chuàng)作,先后出版《上海新語》《可愛的時代》等,在讀者中贏得了雜文家的稱譽(yù)。
三、與魯迅先生的交往
說到雜文,不能不說的是唐弢與魯迅先生的交往。有人稱他是“魯門弟子”,他回答說:“自己從來沒有聽過魯迅先生講課,沒有資格充當(dāng)他的學(xué)生,雖然曾經(jīng)向他請教,他也的確指導(dǎo)過我。”如此看來,應(yīng)該稱唐弢為魯迅的“私淑弟子”較為合適。
早年,唐弢在《申報》副刊《自由談》上讀到魯迅先生的雜文,就很喜歡,買來魯迅的《二心集》,看多了,自己也躍躍欲試,1933年開始向《自由談》投稿。半年后的1934年1月,《自由談》編輯黎烈文在三馬路(今漢口路)“古益軒菜館”,請作者們吃飯,其中有魯迅、郁達(dá)夫、林語堂、胡風(fēng)等,也請了唐弢,這是他與魯迅第一次見面。一番互通姓名后,魯迅笑著對他說:“唐先生做文章,我替你挨罵!”當(dāng)年雜文的風(fēng)格像魯迅的,除了唐弢,還有一個徐懋庸。因魯迅用過“唐俟”的筆名,所以唐弢的不少文章被誤認(rèn)為是魯迅的,似乎“嗅到了一點異端氣,大排哈兒陣,表面上是圍剿我的,骨子里卻暗暗地指著魯迅先生”(唐弢語)。這也讓唐弢爆得大名,以后的投稿命中率也大大提高了。那晚與魯迅的初次見面,“先生的親切笑容,簡短有力的語氣,時時在我的耳邊浮動,不易于忘卻”。

唐弢主編《麗芒湖上》創(chuàng)刊號
魯迅一生,總計給唐弢寫過九封信。第一次是在1934年7月,唐弢有次路過內(nèi)山書店,見有不少日文版馬克思主義的書,想學(xué)日語便于閱讀,就寫信給魯迅,魯迅逐條回答來信所問:“社會科學(xué)書,我是不看中國譯本的。但日文的學(xué)習(xí)書,過幾天可以往內(nèi)山書店去問來,再通知,這幾天因為傷風(fēng)發(fā)熱,躺在家里。除德國外,肯介紹別國作品的,恐怕要算日本了。倘要研究蘇俄文學(xué),總要懂俄文才好。自修的方法,很容易隨便放下,不如進(jìn)夜校之類的穩(wěn)當(dāng)”。回信的那幾天,魯迅因午睡受涼,頭痛發(fā)燒,到日本醫(yī)生須滕診所去看了病,還給一個青年看了四篇稿子,三篇轉(zhuǎn)給《申報》,一篇轉(zhuǎn)給《中華日報》,都附了給副刊編輯的推薦信。如此勞累,他自己得到的報酬是“肋痛頗烈”。魯迅信上說的事,他都一一照辦,信中提到的學(xué)習(xí)書目,身體稍愈后,他就去內(nèi)山書店取來,書目上有魯迅請內(nèi)山先生推薦的書,都加了紅色箭頭,共有九種,魯迅又在四種加了圈,即《漢譯日本口語文法教科書》《改訂日本語教科書》《中日對譯速修日語讀本》《現(xiàn)代日語》(上卷),其他五種,魯迅認(rèn)為可以“緩買”或“不買”。魯迅沒有具體說明為什么,但唐弢心里明白呀,這是魯迅體諒年輕人的經(jīng)濟(jì)實際,一下子買不起這么多書哪!
之后,唐弢參與了《魯迅全集》(1938年版)的校勘工作,發(fā)現(xiàn)還有不少魯迅的文章沒有編入全集,就把更多時間花在尋找集外遺文上,先后編輯出版了《魯迅全集補(bǔ)遺》及續(xù)編,于1946年和1952年出版,共集得魯迅逸文162篇,總字?jǐn)?shù)達(dá)七、八十萬之多,可謂功德無量。
唐弢先后撰寫了許多學(xué)習(xí)魯迅、研究魯迅的文章,結(jié)集的有《向魯迅學(xué)習(xí)》《魯迅在文學(xué)戰(zhàn)線上》《魯迅——文化新軍的旗手》《魯迅的美學(xué)思想》等,不愧為魯迅研究領(lǐng)域里的專家。他在1959年調(diào)任中國社科院文學(xué)研究所研究員后,主要精力放在現(xiàn)代文學(xué)和魯迅文學(xué)研究上。他有兩大心愿,一是編寫一部完整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三卷),此于1979年由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陸續(xù)出版。為此,他足足準(zhǔn)備了大半生,搜羅的現(xiàn)代文學(xué)史料及相關(guān)書籍可稱包羅齊全,是我國新文學(xué)版本收藏最為豐富的個人,堪稱“現(xiàn)代文學(xué)藏書第一人”。他從1945年在《萬象》發(fā)表關(guān)于書的隨筆,這種書話體形式的寫作,他雖不是第一個,但卻是以此命名欄目和出版書名為《書話》的第一人。二是撰寫一部較為完整的《魯迅傳》,為此,他也做了熱身,先在上世紀(jì)50年代和80年代,為少兒出版了兩部《魯迅先生的故事》。在唐弢心目中,他要寫的《魯迅傳》:“希望不是寫一部中國現(xiàn)代史,中間嵌入一個魯迅,而是寫魯迅的一生,通過魯迅的道路反映出中國革命的歷史進(jìn)程。”可是,終因事務(wù)冗雜,創(chuàng)作超負(fù),晚年更是心力交瘁,無法完成自己的宿愿,留下一部殘稿及一大堆史料。十卷本《唐弢文集》中的《魯迅研究卷》(上下冊),《魯迅傳——一個偉大的悲劇的靈魂》只登了殘稿,是前面的十一個章節(jié),才寫到辛亥革命時期魯迅在日學(xué)醫(yī)。一代學(xué)者,壯志末酬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