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只“棲息著的鷹”開(kāi)始 ——特德·休斯文集《冬日花粉》讀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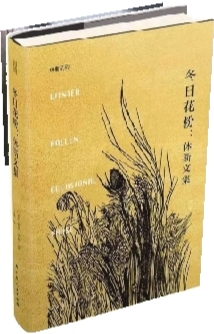
一
第一次接觸英國(guó)桂冠詩(shī)人特德·休斯的作品還是1994年秋天。那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印數(shù)寥寥的《英美桂冠詩(shī)人詩(shī)選》。英國(guó)部分以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的詩(shī)人劇作家本·瓊森為起點(diǎn),以當(dāng)時(shí)尚在世的休斯為壓軸。我沒(méi)去考證,該書(shū)選收的11首休斯詩(shī)歌是不是第一批休斯?jié)h譯,我只記得當(dāng)時(shí)撲面而來(lái)的閱讀震動(dòng),尤其那首《棲息著的鷹》,令人看到休斯與眾不同的敘述角度。而且不難看出,休斯繼承了維多利亞時(shí)代以勃朗寧為代表的獨(dú)白體詩(shī)歌傳統(tǒng)。但繼承傳統(tǒng),不等于被傳統(tǒng)遮蔽,從整部世界詩(shī)歌史來(lái)看,強(qiáng)有力的詩(shī)人往往在繼承中破繭成蝶。在休斯那里,將獨(dú)白轉(zhuǎn)換到動(dòng)物身上,形成別具一格的“動(dòng)物詩(shī)”,就已顯示了詩(shī)人對(duì)新領(lǐng)域的開(kāi)拓能量。
獨(dú)白往往直白,休斯在極為堅(jiān)決的語(yǔ)調(diào)中體現(xiàn)了直白的力度。讀過(guò)這首詩(shī)的讀者不可能忘記它既充滿(mǎn)寓意,又充滿(mǎn)自信和打擊力的結(jié)尾:“太陽(yáng)就在我背后。/我開(kāi)始以來(lái),什么也不曾改變。/我的眼睛不允許改變。/我打算讓世界就這樣子下去。”這是鷹的獨(dú)白,也是極其冷酷和有力的本質(zhì)獨(dú)白——生活的本質(zhì)、世界的本質(zhì),同時(shí)是詩(shī)歌和詩(shī)人的本質(zhì)。沒(méi)有非凡的力量,不可能要求“讓世界就這樣子下去”。所以,這首詩(shī)能成為休斯的名篇,也成為現(xiàn)代主義的詩(shī)歌名篇。
這11首短詩(shī)為我打開(kāi)了休斯的詩(shī)歌大門(mén),乃至后來(lái)在坊間每見(jiàn)一部翻譯詩(shī)選,我都會(huì)首先瀏覽目錄,看書(shū)內(nèi)是否有休斯的詩(shī)歌,一旦發(fā)現(xiàn),就立刻翻到他的作品細(xì)讀。當(dāng)然,這種情況只偶然發(fā)生。英國(guó)桂冠詩(shī)人的頭銜終究不如獲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的詩(shī)人更引人注目。必須強(qiáng)調(diào)一句,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是對(duì)一個(gè)詩(shī)人的作品衡量不假,但絕不是唯一的標(biāo)準(zhǔn),更不是至高無(wú)上的標(biāo)準(zhǔn)。在里爾克面前、奧登面前、博爾赫斯面前、弗羅斯特面前、曼德?tīng)柺┧访媲埃簧佾@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的詩(shī)人水準(zhǔn)就很難說(shuō)比肩甚至超過(guò)了他們。
令我感到驚喜的一次購(gòu)書(shū)經(jīng)歷發(fā)生在2001年年初,逛書(shū)店時(shí)陡然看到一部署名特德·休斯的詩(shī)集《生日信札》。我當(dāng)即買(mǎi)下,盡管詩(shī)集名已經(jīng)告訴我,它不是休斯名震詩(shī)壇的“動(dòng)物詩(shī)”集結(jié),但它畢竟是休斯的詩(shī)集,自然不能錯(cuò)過(guò)。果然,這部詩(shī)集不是“動(dòng)物詩(shī)”,而是紀(jì)念他妻子西爾維婭·普拉斯的一部詩(shī)集。從封面上原版“暢銷(xiāo)數(shù)十萬(wàn)冊(cè)”的推薦語(yǔ)和譯者張子清先生的序言來(lái)看,英文詩(shī)集“暢銷(xiāo)”的最大理由是引起了讀者的好奇和獵奇心理。畢竟,生前默默無(wú)聞的普拉斯已成自白派詩(shī)人代表,被公認(rèn)為是繼艾米莉·狄金森和伊麗莎白·畢肖普之后最重要的美國(guó)女詩(shī)人。她的自殺與休斯的情變有直接關(guān)系,飽受長(zhǎng)達(dá)35年指責(zé)的休斯以這部詩(shī)集的出版進(jìn)行了回應(yīng)。他與亡妻的點(diǎn)點(diǎn)滴滴都濃縮為他筆下的一首首詩(shī)歌。這些詩(shī)歌與獨(dú)白無(wú)關(guān),而是一首首或長(zhǎng)或短的敘事詩(shī)歌。從獨(dú)白到敘事,是詩(shī)人的變化,也是表現(xiàn)題材的變化,關(guān)鍵是,從自己駕輕就熟的手法進(jìn)入另外一種敘述,考驗(yàn)的不只是詩(shī)人的才力,還有詩(shī)人對(duì)文體的深入理解。
理解詩(shī)歌文體也就是理解詩(shī)歌本身。讀完那部《生日信札》,我在暫且撇開(kāi)詩(shī)集主題后想到,對(duì)休斯這樣的詩(shī)人來(lái)說(shuō),如果缺失對(duì)詩(shī)歌的深度理解,就不可能游刃有余地展開(kāi)多種寫(xiě)作技藝,更不可能開(kāi)辟屬于自己的詩(shī)歌道路。進(jìn)入現(xiàn)代以來(lái),越是出類(lèi)拔萃的詩(shī)人,對(duì)詩(shī)歌的建設(shè)就越不僅僅只停留在單純的詩(shī)歌寫(xiě)作上面。對(duì)一個(gè)詩(shī)人來(lái)說(shuō),寫(xiě)出了什么詩(shī)歌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他為什么能寫(xiě)出這樣的詩(shī)歌。就西方詩(shī)歌來(lái)看,從數(shù)千年前的荷馬到揭開(kāi)文藝復(fù)興序幕的但丁,再到俯瞰全球的莎士比亞,有條清晰的發(fā)展線路呈現(xiàn)在讀者和詩(shī)歌史面前。在那些源頭性詩(shī)人那里,作品意味著一切。當(dāng)詩(shī)歌來(lái)到20世紀(jì),詩(shī)歌對(duì)詩(shī)人的要求已不僅僅是寫(xiě)出作品。伴隨人類(lèi)的思想和社會(huì)發(fā)展,詩(shī)歌變得日益多元,最明顯的特征是,詩(shī)歌已從垂直的線性抒情中完成了擺脫。不是說(shuō)詩(shī)歌不再是抒情的載體,而是作為載體本身,詩(shī)歌的復(fù)雜性和多面性在現(xiàn)代主義的多元手法中有了醒目的凸顯。這時(shí)詩(shī)人該走什么路,該展開(kāi)何種探索,該如何界定時(shí)代對(duì)詩(shī)歌提出的新的要求,無(wú)不使詩(shī)歌的發(fā)展變得錯(cuò)綜復(fù)雜——浪漫與現(xiàn)代、現(xiàn)代與象征、象征與后現(xiàn)代等等,都成為詩(shī)人能驅(qū)趕詩(shī)歌進(jìn)行橫沖直撞的領(lǐng)域。
二
這部《冬日花粉》是休斯畢生的思想結(jié)晶,它匯集了休斯各個(gè)時(shí)期的著名文論。這部沒(méi)有分輯的書(shū)其實(shí)可分為兩個(gè)部分,第一部分是全書(shū)的后半部,它顯示了休斯對(duì)傳統(tǒng)的關(guān)注——不論詩(shī)人如何現(xiàn)代,沒(méi)有誰(shuí)可以擺脫傳統(tǒng)。艾略特的文論精華不就包含了他對(duì)莎士比亞和伊麗莎白時(shí)代的核心解讀?休斯同樣如此,眼光從來(lái)沒(méi)有從莎士比亞身上離開(kāi)過(guò)。在休斯筆下,他對(duì)莎士比亞的理解也完全不同于艾略特的理解。最起碼,當(dāng)艾略特將目光集中在莎士比亞和塞內(nèi)加斯多葛派哲學(xué)的糾纏中時(shí),休斯已將關(guān)注點(diǎn)位移到莎士比亞所代表的文學(xué)世界與意大利新柏拉圖主義所代表的社交世界的編織中。構(gòu)建理論的前提是視野。休斯在這里展現(xiàn)了自己的視野。沒(méi)有這一視野,休斯就不會(huì)在另一篇《偉大的主題》中體會(huì)到莎士比亞“一詞一句都具備如此微妙的準(zhǔn)確性”。龐德不也異常決絕地說(shuō)過(guò)“準(zhǔn)確的陳述是寫(xiě)作的第一要素”?當(dāng)然,休斯說(shuō)的莎士比亞“準(zhǔn)確”與龐德的“準(zhǔn)確”沒(méi)什么必然關(guān)系。作為詩(shī)人,休斯緊扣的是自己對(duì)莎士比亞的語(yǔ)言理解,“當(dāng)我們的目光透過(guò)這些文字,注入我們內(nèi)心深處的黑暗時(shí),種種新的事物、新的可能便層出不窮,盡顯于詞句之中。”
視野的重要性就體現(xiàn)在這里——經(jīng)典能成為經(jīng)典的理由再多,語(yǔ)言始終是不可繞過(guò)的核心環(huán)節(jié)。休斯對(duì)語(yǔ)言“準(zhǔn)確”的理解導(dǎo)致他對(duì)“內(nèi)心深處的黑暗”觸及。不是說(shuō)“黑暗”是詩(shī)歌的核心,對(duì)一個(gè)不斷挖掘生活的詩(shī)人來(lái)說(shuō),深處的事物無(wú)不具有“黑暗”的質(zhì)地,在莎士比亞身上,休斯發(fā)現(xiàn)了其“惡魔”與“神圣”的統(tǒng)一,才讓后世讀者最終面對(duì)“一位完整的詩(shī)人”。并且,通過(guò)對(duì)莎士比亞的作品選編,休斯還體會(huì)到“莎士比亞的語(yǔ)言依然比之后存世的任何文字都更貼近英語(yǔ)本身的生命內(nèi)核”。這就是閱讀帶來(lái)的認(rèn)知。我既感意外又覺(jué)正常的是,休斯不像一般編選者那樣,將筆墨集中在對(duì)作者的生平介紹和對(duì)入選作品的闡釋之上,而是極為深入地展開(kāi)個(gè)人與經(jīng)典的相互糾纏,乃至提煉出自己對(duì)詩(shī)歌的理解,所以他才能堅(jiān)定地以為“一首長(zhǎng)詩(shī)的片段并不構(gòu)成一首短詩(shī)”,甚至不含糊地指出,“即便是莎士比亞,也終究無(wú)法擺脫自我。”這是令人意外和驚訝的判斷,研究者公認(rèn)的,恰恰是莎士比亞在作品中過(guò)于缺失自我,才導(dǎo)致后人對(duì)其生平的研究十分欠缺。在休斯那里,結(jié)論完全不同,這決非休斯的標(biāo)新立異,它反而證明了,一個(gè)真正理解創(chuàng)作的詩(shī)人會(huì)有一種什么樣的視角,不論通過(guò)該視角形成的結(jié)論是否在更寬廣的范圍內(nèi)被承認(rèn)和接受,它畢竟體現(xiàn)了休斯充滿(mǎn)個(gè)性的理解。
三
而我所理解的第二部分集中在“更趨尖銳,更顯嚴(yán)肅”的表述。休斯離開(kāi)人物,將全部身心集中在對(duì)詩(shī)歌本身的理論探索當(dāng)中。這部分的篇章包括《奇聞異事和血淋淋的冒險(xiǎn)》《火狐》《詩(shī)的鍛造》《略談中小學(xué)寫(xiě)作》《隱匿的能量》《人性之歌》《國(guó)家的幽靈》等等。這是休斯面對(duì)詩(shī)歌的直接言說(shuō),哪怕《奇聞異事和血淋淋的冒險(xiǎn)》和《火狐》不無(wú)詩(shī)人的自傳元素。早在11歲時(shí),休斯就對(duì)韻律發(fā)生興趣而大量閱讀詩(shī)歌。這是成為詩(shī)人的最初和必要準(zhǔn)備,但休斯又決非要寫(xiě)一篇或數(shù)篇自傳,通過(guò)自述,休斯剖析了韻律和節(jié)奏的重要,也回顧了自己對(duì)惠特曼從失望到崇敬的接近。初時(shí)的失望是自己在后者詩(shī)歌中沒(méi)找到韻律,后來(lái)的崇敬是因?yàn)樽约航K究理解了什么是詩(shī)歌。
在這部書(shū)里,休斯至少用兩種方式定義了他以為的現(xiàn)代詩(shī)歌。在《詩(shī)的鍛造》中,休斯現(xiàn)身說(shuō)法,敘述了自己如何寫(xiě)下第一首“動(dòng)物詩(shī)”《思想之狐》的過(guò)程。令人意外的是,休斯明確告訴讀者,詩(shī)名雖有“思想”二字,但“從這首詩(shī)里,很難找得出堪稱(chēng)‘意義’的成分”。這是休斯包括“動(dòng)物詩(shī)”在內(nèi)的全部詩(shī)歌的核心標(biāo)志,也是現(xiàn)代詩(shī)的核心標(biāo)志——詩(shī)歌從來(lái)不是對(duì)“意義”的尋找,而是如何準(zhǔn)確呈現(xiàn)出客觀風(fēng)貌。這首被詩(shī)歌史重視的詩(shī)歌也被休斯自己重視。他的重視方式不是淺薄的自鳴得意,而是為讀者打開(kāi)專(zhuān)屬于詩(shī)歌的隱秘通道,“每當(dāng)我讀起它來(lái),那只狐貍都會(huì)從黑暗中現(xiàn)身,然后鉆進(jìn)我的腦袋。我想,在未來(lái),即便我離世已久,只要有人讀它一回,那只狐貍就會(huì)再次現(xiàn)身——從黑暗中的某個(gè)地方現(xiàn)身,然后一步一步向他走來(lái)。”這種表述是作者對(duì)自己詩(shī)歌的回望,也讓讀者在這些話中體會(huì)到一首現(xiàn)代詩(shī)的本質(zhì)——它與思想無(wú)關(guān),只是不折不扣的存在。休斯在另外的篇章中說(shuō)得更加明白,“我所謂‘思考’——說(shuō)是花招也好技巧也罷——能使我們有能力抓住那些難以捉摸或者幽暗不明的想法,將它們聚斂一處,放平擺穩(wěn),供我們真真切切地看上一看。”
用自己的寫(xiě)作方式來(lái)闡述自己的詩(shī)歌定義,沒(méi)幾個(gè)人這樣做到過(guò),而且,在讀者跟隨休斯的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不僅能體會(huì)詩(shī)歌的含義,還能體會(huì)一首現(xiàn)代詩(shī)的魅力形成。休斯的詩(shī)歌的確充滿(mǎn)魅力,很少有讀者能抵擋從他詩(shī)歌中散發(fā)出的魅力。休斯一方面承認(rèn)“所有從事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人都不可避免地置身于模仿或者替換的維度”,一方面又異常堅(jiān)定地對(duì)詩(shī)歌下出了和龐德等先行者有所區(qū)別的直接定義,“當(dāng)文字足以在短暫的一瞬間里掌控‘某某’,從中辨識(shí)并透視出所有最具生命也最為關(guān)鍵的信號(hào)——不是原子,也不是幾何圖形,更不是一堆晶體,而是人的信號(hào)時(shí),我們便稱(chēng)之為詩(shī)。”
在這句話里,他特意在“人”字下劃了一杠,提醒讀者重視,因?yàn)椤叭祟?lèi)存活的證據(jù)無(wú)聲地合唱,匯成一曲普遍的吟詠,倘若作者置身事外,對(duì)這歌聲充耳不聞,便會(huì)立即被拒之門(mén)外”。休斯自己的實(shí)踐也無(wú)不如此,在他至今擁有全球讀者的“動(dòng)物詩(shī)”里,沒(méi)有哪首詩(shī)不是看似在寫(xiě)動(dòng)物,實(shí)則在寫(xiě)人,仍以那首堪為代表作的《棲息著的鷹》為例,不論評(píng)論家們的解讀如何有異,共同的一點(diǎn)是,那只“鷹”不僅僅是“鷹”,而是“人”的化身,這就像休斯自己說(shuō)過(guò)的那樣,其寫(xiě)作目的,是“企圖通過(guò)我與世界真實(shí)關(guān)系的建立來(lái)證明世界的真實(shí)性和我在這個(gè)世界上的真實(shí)性”。所以無(wú)論他寫(xiě)下什么、暗示什么、隱喻什么,表面上看,與他宣稱(chēng)“可教”和“可訓(xùn)練與強(qiáng)化”的想象力有關(guān),往深處看,則與他在《退世》一文中展現(xiàn)的思想核心有關(guān),“讓人類(lèi)的靈魂完整,幸福地回歸社會(hu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w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