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力量 | 趙天成:想象力的大時代
想象力從來都是文學(xué)的“誕生地”。縱觀近兩年的青年文學(xué)創(chuàng)作,有不少寫作者,用幻想、想象以及寓言的方式將社會歷史、日常經(jīng)驗與私人歷史記憶雜糅,以或詭譎熱烈、或?qū)拸V平靜的想象力將日常時間與空間推拉變形,重構(gòu)生活的另一些真實。想象力如同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顯示著它勾連現(xiàn)實卻又全然不同于現(xiàn)實的潔凈、深刻、輕盈的審美創(chuàng)造力,成為重新擦亮漢語寫作的“法器”,小說借此重獲上天遁地的超能力,擁有飛翔與呼吸的自在空間。誠然,虛構(gòu)與現(xiàn)實并非二元對立的關(guān)系,想象力的虛構(gòu)與社會現(xiàn)實生活應(yīng)當(dāng)是怎樣一種關(guān)系?想象力是否可以嵌入其中去反映內(nèi)在性、碎片化、高景觀的現(xiàn)實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想象力是否是通往現(xiàn)實之路的多棱鏡?本期“新力量”分別邀請到華語文學(xué)圖書編輯黃盼盼,以及青年學(xué)者趙天成、范思平對談與此相關(guān)的諸多話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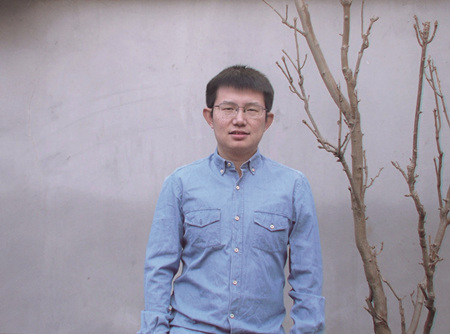
趙天成,現(xiàn)供職于中央民族大學(xué)中國少數(shù)民族語言文學(xué)學(xué)院。主要研究領(lǐng)域為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史、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批評。
想象力的大時代
趙天成
如果承認文學(xué)是歷史性的,那么作為文學(xué)關(guān)鍵性元素的想象力也是歷史性的。具體地說,想象力的位置、功能和社會性意義,在不同的時空語境下并非完全等價。中國新文學(xué)百年的歷史進程中,素有重摹仿而輕表現(xiàn)、重經(jīng)驗而輕想象的隱性傳統(tǒng)。倚重想象力的寫作,往往被視為現(xiàn)實性的缺乏,甚或是歷史的虛無。而作為現(xiàn)代主義的代表人物,普魯斯特的生活圈子并不開闊;卡夫卡更是聲稱,他最理想的生活,就是終日在地洞中思考和寫作。他們都是與外部生活關(guān)系緊張的內(nèi)省式作家,但又恰恰因此,他們?nèi)缤 ⑸勘葋喤c歌德一樣,與其所處時代形成了深刻的同構(gòu)關(guān)系。復(fù)雜混亂的時代,正是想象力以廣義的文學(xué)為載體、重建并提供意義的歷史時刻。
后疫情時代與百年前的世界一樣,也是滄海橫流的大時代。一成不變、日復(fù)一日的生活,無論我們是否喜歡,似乎都已成為難以企及的奢望。這是全球保守主義抬頭的時代,完整的共同體想象漸次破碎,處處布滿有形無形的“柏林墻”和“次元壁”,人們的悲歡并不相通。在普遍意義的共識和真相不易獲得的情況下,我們已經(jīng)無法通過體驗,而必須經(jīng)由想象,才可能穿透話語的層疊泡沫,接近歷史和現(xiàn)實的內(nèi)在性。這就像中國古典文論中的言意之辨,盡管言不盡意、得意忘象,也即“言”只是通向“意”的一個并不完善的中介,但是“意”也只能經(jīng)由“言”才可能通往。此時此刻,想象就是達“意”之“言”,是我們實現(xiàn)破壁、靠近真意的唯一方式。我在今年年初的一篇筆談中說:“如果從未來的眼光回望,我們當(dāng)下可能正處于《三體》中大低谷時期的開端,或者用阿甘本的術(shù)語說,我們將長期處于一種世界性的‘例外狀態(tài)’。在這個歷史的‘?dāng)帱c’上,我們無法再按照某種目的論從未來解釋過去,甚至無法通過過去理解當(dāng)下。”也就是說,事到如今,想象力已經(jīng)不僅是科幻文學(xué)的必需要素,因為無論是遠未來(far future),還是近未來(near future)乃至“明天”(immediate future),都需要想象才能撬動。
在這樣的因緣際會中,一批青年作家開始走入人們——兼括文學(xué)圈內(nèi)和圈外、職業(yè)讀者和普通讀者——的視野,并以異質(zhì)化的想象獲得其風(fēng)格的新穎性。與前輩作家相比,他們較少中國現(xiàn)實主義的痕跡(obsession with China Realism),而是自始就帶有一種我稱之為“新世界主義”的視野。這種視野降臨在小說中,就如卡夫卡《中國長城建造時》或博爾赫斯《小徑分岔的花園》中的“中國”元素,是符號的、象形的、言近旨遠的“世界”。青年小說家陳春成在《音樂家》《夜晚的潛水艇》,以及新作《雪山大士》中,都嘗試挑戰(zhàn)不限于中國,而是更具抽象意義的人物、故事、主題。識者自可由此生發(fā),探討認知層面的微言大義,關(guān)于如何理解自我、國家與世界,如何理解過去、現(xiàn)實與未來的關(guān)系,這些作品都提供了不同的契機和可能性。
但更為重要的是,“想象”自身的邊界和秩序,在陳春成等小說家的作品中打破,又在新的層級得到重新結(jié)構(gòu)。誠如王夫之《姜齋詩話》中所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作者用一致之思,讀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例如,在對小說集《夜晚的潛水艇》的接受層面,我注意到不同群體間的微妙差異。出版者青睞其中更“文藝”的篇什(如“同名主打”《夜晚的潛水艇》),而批評家則重視更具“厚度”的《竹峰寺》《音樂家》和《紅樓夢彌撒》。在我看來,在后面的這幾篇小說中,作者的文學(xué)想象力、歷史想象力與社會學(xué)想象力,達到了更高程度的綜合和平衡。歷史和現(xiàn)實在其中以高度抽象化、但絕非抽空化的方式存在。《竹峰寺》對于歷史暴力、《音樂家》對于極權(quán)政治、《紅樓夢彌撒》對于意識形態(tài),都有個人化的獨立看法,但這些看法,又不能簡單劃歸于某種立場、態(tài)度、理論或觀念形式。這正是想象力柔軟、豐富而又極具綿延性的潛能所在。不只是陳春成,周愷的歷史小說《苔》及其新作《少年、胭脂與靈怪》,李唐的奇幻小說《身外之海》及新小說集《菜市場里的老虎》等作品,或以今鑒古,或以實證虛,都從不同方面開掘并延展著想象的綜合性潛力。他們引起的廣泛影響,也讓我們從另一角度重新思考1980年代以后的先鋒寫作。無論捍衛(wèi)者還是抨擊者,大抵都將“非歷史”或“去歷史”的藝術(shù)特征,視為先鋒小說的觀念核心。但事實上,其時或后來獲得較高聲譽的代表性作品,如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余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殘雪的《山上的小屋》、馬原的《岡底斯的誘惑》、格非的《迷舟》,其實都是想象力、形式感和歷史性的綜合。它們都從特殊的路徑觸及歷史,以及處在歷史連續(xù)性中的某種現(xiàn)實。
除此之外,青年作家的想象,還呈現(xiàn)出內(nèi)、外兩個向度的辯證互動,也即自我想象與社會想象的關(guān)聯(lián)方式問題。在公共空間阻隔、失序的時間節(jié)點,需要想象力進行理解和建構(gòu)的,不只是個體存在與公共生活兩端,還包括“我”與這個世界、個人與其實際生存之間的想象性關(guān)系。加繆名句“重要的不是活得更好,而是活得更多”言猶在耳,但又如前所述,今天我們已經(jīng)(或仍然)很難通過“親歷”的方式活得更多,而只能通過反向運動,以想象的神游“占有”更多的生活。一些青年小說家的小說癡迷于密閉空間的營造——比如潛水艇、水甕等各式“洞穴”,并由此生發(fā)出一整套“藏”的方法論。在內(nèi)外交互的維度,我認為“藏”的詩學(xué)在兩個線索上提供了耐人尋味的啟發(fā)。其一,窮則獨善其身,個體首先通過“我思”確認“我在”(有趣的是,傳說笛卡爾早年在巴伐利亞的寒冷冬日,就是鉆進一個火爐子整日沉思的),繼而“照我思索,可理解人”,密閉成為領(lǐng)悟的前提條件;其二,所謂用舍行藏,可以說舍是一種特殊的用(介入),藏是一種特殊的行(實踐)。由此,以舍為用,以藏為行,就成為特殊年代里個人與集體之間特殊的聯(lián)動方式,一種雖然被動卻不消極的生命形式。或如陳培浩所言,《音樂家》中藍鯨體內(nèi)、花苞內(nèi)部、月球背面、雪花玻璃球,都在“內(nèi)面”的世界里成為主人公古廖夫的音樂廳,想象由此具有了生命救贖的意義。
在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在無所希望中得救。無論如何悖謬,我愿與青年作家們抱持相同的信念:人類想象能力破壁、綜合與聯(lián)動的潛在能量,將在業(yè)已展開的大時代中承擔(dān)重要的使命,甚至從未如此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