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之間說《神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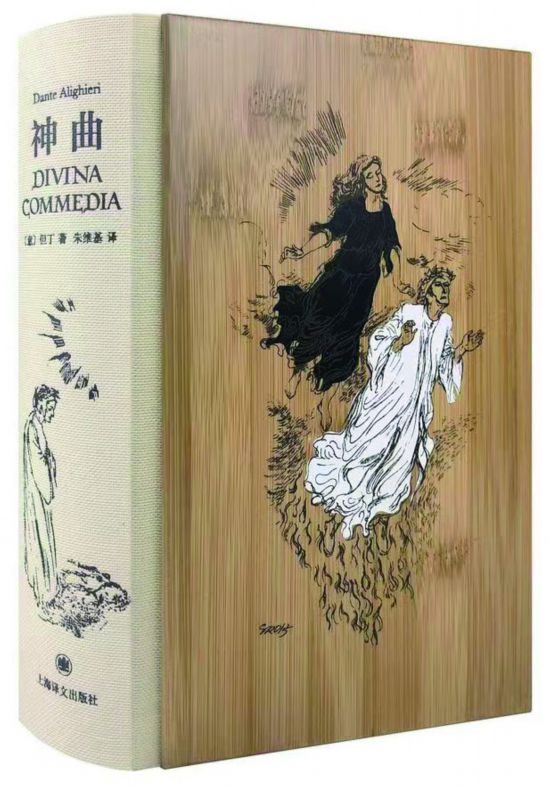
700年前,但丁以自己“神圣的詩篇”《喜劇》(Commedia)總結(jié)了歐洲中世紀(jì)。詩人曾在寫給斯卡拉大親王的書信中對“喜劇”進(jìn)行過解釋,按照他的說法,自己詩歌的主題有別于古羅馬詩人維吉爾的典雅史詩《埃涅阿斯紀(jì)》,后者在他看來是一部“悲劇”:
它(喜劇)在主題上區(qū)別于悲劇,悲劇的開端令人羨慕而寧靜,但結(jié)尾則邪惡而可怖……而喜劇則開始于種種相反的處境,但其結(jié)局卻是幸福的。(《致斯卡拉大親王書》)
但丁指出,《神曲》之所以是喜劇,是因為其開端《地獄篇》邪惡而可怖,而其結(jié)局《天國篇》則幸福快樂,令人向往。與主題相應(yīng)的是詩歌的寫作風(fēng)格:這部被后世稱為《神曲》(La Divina Commedia)的詩篇以俗語寫成,按照詩人自己的解釋,“自然而平實”的俗語與“喜劇”的風(fēng)格一致,而與之相對的,“悲劇”的語言則“夸張而崇高”:
就語言風(fēng)格而論,(這部詩歌)的風(fēng)格自然而平實,就像婦女們也能使用的方言一般,顯然這就是它被稱作“喜劇”的緣由。(《致斯卡拉大親王書》)
雖然但丁強調(diào)《神曲》內(nèi)容與形式的相符,但這部一萬多行的長詩崇高的主題、詩歌中恢弘的宇宙以及三界(地獄、煉獄、天國)中出現(xiàn)的英杰靈魂卻無法不讓讀者將其與“典雅”聯(lián)系在一起,而關(guān)于《神曲》的雅俗之辨也貫穿著但丁的接受史。
20世紀(jì)初,但丁進(jìn)入中國人的視野,同樣的問題也困擾著《神曲》的譯介者,這主要體現(xiàn)為將《神曲》翻譯為何種文體、或用什么樣的體裁講述《神曲》的故事。作為《神曲》的第一位譯者,錢稻孫于1921年9月發(fā)表于《小說月報》的《神曲》節(jié)譯《神曲一臠》選擇了楚辭體。在中國傳統(tǒng)文學(xué)體系中,楚辭被看做僅次于《詩經(jīng)》的“高雅”文學(xué)代表,所謂“《國風(fēng)》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而“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文心雕龍·辨騷》)也多少可以代表古人對《楚辭》文化經(jīng)典地位的肯定。與錢稻孫形成對照的是梁啟超,他創(chuàng)作的《新羅馬傳奇·楔子一出》以戲曲的形式改編了《神曲》的故事,他還特別在喜劇開篇的念白中讓但丁自述,自己的詩歌“庶幾市衢傳誦,婦孺知聞”,這意味著,在梁啟超心中,《神曲》應(yīng)像中國戲曲一樣作為通俗文學(xué)為世人傳唱。在新文化運動中,作為文壇領(lǐng)袖的魯迅等為了高揚白話文學(xué),同樣強調(diào)但丁在俗語創(chuàng)作上的貢獻(xiàn)。
事實上,無論《神曲》在西方的接受史中激起的爭論、還是《神曲》進(jìn)入中國初期所體現(xiàn)的多面性,都緣起于詩歌本身的多面性。在漢語語境中,固然很難從語言學(xué)層面對《神曲》的“雅”與“俗”進(jìn)行一番評判,但從《神曲》的內(nèi)容及譬喻入手,仍不難對這一問題進(jìn)行一番體味。
《神曲》之“俗”,首先體現(xiàn)為《地獄篇》書寫內(nèi)容相對于古典史詩的突破,在《神曲》開篇,但丁向《埃涅阿斯紀(jì)》的作者、詩人維吉爾致意:“你是我的老師,我的權(quán)威作家,只是從你那里我才學(xué)來了使我成名的優(yōu)美風(fēng)格”(《地獄篇》)。《神曲》的寫作也無往而不是《埃涅阿斯紀(jì)》的印記,然而在對地獄景象的書寫中,但丁卻大大突破了《埃涅阿斯紀(jì)》“冥府之行”的界限。
《埃涅阿斯紀(jì)》第6卷記述的“冥府之行”中,羅馬之父埃涅阿斯來到塔爾塔路斯(Tartarus)——冥府最黑暗的地方,在入口的大門上有堅硬的花崗石柱子,“休說人力,就是天上的神大興干戈也休想推倒它們”,從其中傳出罪大惡極的靈魂受罰時發(fā)出的令人恐怖的喧囂,復(fù)仇女神之一提希豐涅“腰里掛著鞭子,跳將出來,抽打那些罪人。”她還手舉著兇惡的蛇,呼喚著其他兩位復(fù)仇女神。當(dāng)埃涅阿斯驚駭?shù)貑柹磉叺南驅(qū)А戎鞅葼枺镞吺窃鯓拥撵`魂在受罰時,西比爾在回答前告誡說:“特洛亞人的聲名遠(yuǎn)揚的領(lǐng)袖,任何心底純潔的人都是不準(zhǔn)邁進(jìn)這罪孽的門檻的”,而作為以“虔敬”著稱的民族領(lǐng)袖,埃涅阿斯聽從了勸告,自絕于地府最幽深的秘密,取道冥王居住的狄斯城前走到了“樂土”,聽到了亡父安奇賽斯對羅馬未來輝煌成就的預(yù)言。
《地獄篇》中沒有出現(xiàn)“塔爾塔路斯”的名稱,淺層地獄和深層地獄的分界線是狄斯城,然而這里卻充滿著“塔爾塔路斯”式的意象——地獄深處的靈魂顯然更為罪惡多端,而復(fù)仇女神三姐妹也在城頭現(xiàn)身:“左邊這個是梅蓋拉;右邊哭的那個是阿列克托;中間的是提希豐涅”,她們還呼喚蛇發(fā)女妖美杜莎,想讓她把但丁變成石頭。當(dāng)?shù)∨c維吉爾受到阻攔與恐嚇踟躕不前時,一位天使穿過地獄的迷霧,“他來到城門前,用一根小杖開了城門,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就這樣,在維吉爾本人的見證下,古羅馬詩人筆下天神也無法打開的黑暗的大門打開了,作為蕓蕓眾生的代表、亞當(dāng)有罪子孫之一的但丁走進(jìn)地府深處,看到了埃涅阿斯不曾看到的景象。在這里,從地獄走向天國沒有第二條路徑,兼具狄斯與塔爾塔路斯特征的大門也正是從黑暗走向光明的必經(jīng)之途。對比《埃涅阿斯紀(jì)》第六卷和《地獄篇》第9歌,不難看到但丁富有戲劇意味的情節(jié)下掩蓋的“喜劇宣言”,那就是:通過描述更為卑俗的故事,實現(xiàn)“喜劇”對人心靈的教化。
與此相應(yīng)的,是“地獄深處”的故事里隨處可見的并不雅觀、乃至令人發(fā)笑的場景或譬喻:在地獄第八層懲罰淫媒罪和誘奸罪的惡囊中,惡靈們赤身露體,他們排著貌似朝圣的隊列,卻遭到長著角的鬼卒的抽打,“一鞭子就打得他們抬起腳跟就跑,確實沒有一個人等著挨第二下或第三下的”;在懲罰貪官污吏的惡囊里,污濁滾燙的瀝青湖中煮著一群生前的貪污犯,誰敢露頭,就會被鬼卒用叉子叉住,其做法“和廚師們讓他們的下手們用肉鉤子把肉浸入鍋正中,不讓它浮起來,沒有什么兩樣”;特別著名的還有在16世紀(jì)引起俗語人文主義者本博(Pietro Bembo)反感的片段:
我看見兩個互相靠著坐在那里,好像兩個平鍋在火上互相支著似的,他們從頭到腳痂痕斑斑;由于別無辦法解除奇癢,他們個個都不住地用指甲在自己身上狠命地抓,我從來沒有看見過被主人等著的馬僮或者不愿意熬夜的馬夫用馬梳子這樣迅猛地刷馬;他們的指甲搔落身上的創(chuàng)痂,好像廚刀刮下鯉魚或者其他鱗更大的魚身上的鱗一樣。
在這個段落中,“兩個平鍋在火上互相支著”、馬梳子刷馬、廚刀刮下魚鱗絕非典雅的意象,本博甚至依此表達(dá)了對但丁的惋惜與批評:“他的《喜劇》就好比一片美麗寬闊的麥田,上面卻灑滿了燕麥、稗子和毫無生氣的有害的雜草”。
誠然,在“看”地獄深處之“丑”、并不知不覺迷戀其中的過程中,但丁也受到了維吉爾的警告——這種想要旁觀的欲念本身就是“一種卑鄙的愿望”。然而《地獄篇》洋洋灑灑的千百詩行卻無聲地告訴讀者,只有看過、參透地府深處的種種惡,才能實現(xiàn)“喜劇”真正的教化。
《神曲》之“雅”則首先體現(xiàn)在其主題之崇高。《地獄篇》第2歌中詩人對維吉爾所說的話預(yù)設(shè)了旅程所依據(jù)的兩個崇高先例:
“引導(dǎo)我的詩人哪,你在讓我冒險去做這次艱難的旅行之前,先考慮一下我的能力夠不夠吧……我不是埃涅阿斯,我不是保羅;不論我自己還是別人都不相信我配去那里……”
這里提到的兩個旅程,一個是《埃涅阿斯紀(jì)》中的“冥府之行”,另一個則是《哥林多后書》中講到的保羅神游第三重天的故事:
我認(rèn)得一個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層天上去……他被提到樂園里,聽見隱秘的言語,是人不可說的。(《哥林多后書》)
但丁的自我懷疑在《天國篇》中得到的卻是明確而肯定的回答,在火星天上,但丁遇到了在圣戰(zhàn)中殉難的高祖卡恰圭達(dá)的靈魂,詩人這樣描述祖孫的重逢:
如果我們最偉大的詩人的話可信,安奇塞斯的幽魂在樂土中看見自己的兒子時,就懷著同樣的感情向他探身迎上前去“啊,我的骨血呀,啊,上帝給予你的深厚的恩澤呀,天國的門對誰,像對你那樣,開兩次呢?”
安奇塞斯是埃涅阿斯之父,在《埃涅阿斯紀(jì)》“冥府之行”的末尾,正是他指引埃涅阿斯看到了自己未來子孫的靈魂和他們的命運。天國之門“開兩次”,所指的正是保羅生游天國,而死后也得進(jìn)天國。在火星天的語境下,但丁經(jīng)歷了地獄和煉獄的洗禮,同時成為埃涅阿斯和保羅,而在《天國篇》結(jié)束時,但丁也將上帝的花園描述為樂土一般的“天上的羅馬”:
如果那些來自每天都被她和她心愛的兒子一起運轉(zhuǎn)的艾麗綺的光照射的地帶的野蠻人,在拉泰蘭宮凌駕一切人間的事物的年代,看到羅馬及其高大的建筑時,不禁目瞪口呆;何況我,從人間來到天國,從時間來到永恒,從佛羅倫薩來到正直的健全的人民中間,心中該充滿何等驚奇呀!
在《天國篇》長達(dá)33篇的詩歌里,但丁描繪了九重天中享天福靈魂的種種樂境,從太陽天里基督教圣哲圍成光環(huán)舞蹈的“群星之舞”到火星天上殉難者組成的十字架、從水星天上查士丁尼大帝激情的演說到木星天上由正義的君主組成的雄鷹……但丁將種種難以言表的異象展現(xiàn)在讀者眼前,就這樣將保羅口中“不可說的”“隱秘”的言語用鏗鏘的詩行描述了出來。土星天上的兩個場景體現(xiàn)了這種“大雅”的崇高之詩對凡人理解力的考驗,那是在進(jìn)入天國的第七重天土星天后,但丁看到神圣的愛人貝雅特麗齊收斂了令自己心馳神往的微笑,圣女解釋說,一旦詩人凡俗的視力看到貝雅特麗齊在新一重天的光芒照耀下的真容,他就會像古代神話中因見到尤庇特真容而焚毀的塞墨勒一樣毀滅,因為:
“……順著這永恒的宮殿的臺階拾級而上,上得越高,我的美就點燃得越旺,如果它不被減弱,它就會發(fā)出那樣強烈的光芒,你們凡人的視力被它一照,會像被雷擊斷的樹枝似的。”
在同一歌中,當(dāng)朝圣者問起為何在土星天中沒有像下邊各層天體中聽到的天國樂曲時,一個靈魂回答說:“你的聽覺如同你的視覺一樣是凡人的,所以這里不唱歌和貝雅特麗齊沒有微笑原因相同。”
然而詩人沒有成為塞墨勒,在貝雅特麗齊的引領(lǐng)下,他最終突破了凡人理智的極限,看到了圣人們在天國之光覆蓋下的形象、看到了像“人間的太陽照亮我們看到的天空的星辰”一樣照亮諸圣人的耶穌基督、最后看到了上帝本身。
《神曲》之“雅”,還特別體現(xiàn)在其對世俗愛情主題的升華。整部詩篇的精神救贖中,但丁少年時代愛慕的貝雅特麗齊起著精神向?qū)У淖饔茫鳛樯系鄣氖ヅ诘∠萑胛ky時,秉承上天旨意來到地獄上層的靈泊(Limbo),請求維吉爾引導(dǎo)但丁,而她自己則作為旅程第二階段的向?qū)ВH自引領(lǐng)但丁游歷了天國。
在但丁時代意大利的抒情詩創(chuàng)作中,“理想女郎”是寄托詩人們塵世愛欲的對象,由于徘徊在世俗情感與信仰之間,這一時代詩人們的作品充滿了纏綿悱惻的痛苦,但丁早年創(chuàng)作的《新生》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這一詩歌傳統(tǒng),而貝雅特麗齊就是但丁的“理想女郎”。但在《神曲》中,貝雅特麗齊的形象脫胎換骨,由塵世之愛的美麗偶像變成了上帝神圣的表記,這表記甚至引領(lǐng)但丁超越了古典詩歌的愛情理想——《煉獄篇》末尾戀人重逢的場景見證了這種超越,其時,“蒙著白面紗,披著綠斗篷,里面穿著烈火般的紅色的長袍”的貝雅特麗齊從天而降,但丁看到這景象時:
我就像小孩害怕或者感到為難時,懷著焦急期待的心情向媽媽跑去似的,轉(zhuǎn)身向左,對維吉爾說:“我渾身沒有一滴血不顫抖: 我知道這是舊時的火焰的征象”。
貝雅特麗齊裝束中的白綠紅三種顏色無疑意味著“信望愛”三德;而“我知道這是舊時的火焰的征象”出自《埃涅阿斯紀(jì)》第4卷,愛上埃涅阿斯的迦太基女王狄多一往情深地說:“……自從我可憐的丈夫希凱斯遭難,自從我的哥哥血濺了我的家園,只有他一個人(埃涅阿斯)觸動了我的心思,使我神魂游移,我認(rèn)出了舊日火焰的痕跡(Agnosco veteris vestigia flammae)……”
在《埃涅阿斯紀(jì)》第4卷的語境中,背叛亡夫的狄多對埃涅阿斯的愛被看做一場錯誤:“她說這就是結(jié)婚,她用這名義來掩蓋她的罪愆。”埃涅阿斯最終也服從命運的安排拋棄了狄多,導(dǎo)致女王在羞憤中自殺。而在《神曲》中,貝雅特麗齊變成了圣愛的象征,但丁還在她的斥責(zé)下懺悔了過去沉溺其中的錯誤愛情(《煉獄篇》)——詩人就用這樣的方式宣告了對維吉爾古典史詩中愛情故事的修正與超越。
以“雅”“俗”論《神曲》,不難理解,無論《神曲》之“俗”還是“雅”,都取決于這部“天與地都一同參與其中”(《天國篇》)的詩歌的理想:詩人想要通過一場精神之旅,寫盡宇宙間的存在秩序,那就是“人,通過運用自由意志去行善或作惡,而理應(yīng)受到正義的懲罰或報償”(《致斯卡拉大親王書》)。他以地獄的“幽深”實現(xiàn)了“喜劇”的“俗”,又以天國的“崇高”突破了古典史詩的“雅”和《圣經(jīng)》的戒律,最終成就了自己“神圣的喜劇”(La Divina Commed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