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瓦那眾聲飛舞 ——讀因凡特《三只憂傷的老虎》

吉列爾莫·卡夫雷拉·因凡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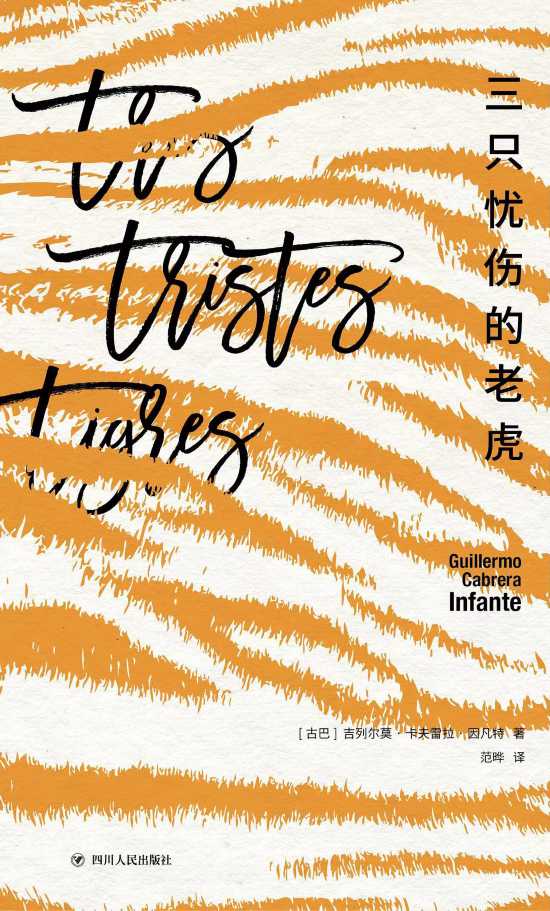
“本書用古巴語寫作、也就是說,用古巴的各種西班牙語方言來寫,而寫作不過是捕捉人生飛舞的嘗試。”吉列爾莫·卡夫雷拉·因凡特(Guillermo Cabrera Infante)在《三只憂傷的老虎》的第一頁,寫下了提示說明,“書中有些部分比起閱讀更適合聆聽,念出聲來是個不壞的主意。”
有經(jīng)驗的讀者可以很快領(lǐng)悟到,《三只憂傷的老虎》是一本難以翻譯的書。口語,方言,多重聲音,任何一位致力于此的作家或詩人,都會讓遠在異國的翻譯者陷入困境。僅僅是這個看起來很普通的標(biāo)題,tres tristes tigres(三只憂傷的老虎),就已經(jīng)讓譯者煩惱不已,不得不放棄了繞口令的俏皮意味,更何況此后眾聲喧嘩的哈瓦那夜場大戲。
這又是一個譯者的不可能之任務(wù),翻譯必然會損耗此類文學(xué)作品的能量。然而,因凡特的能量足以支撐起這種消耗,只要譯者敲打出合適的洞口,這股能量便會穿墻透壁呼嘯而來,正如書中開篇“序幕”中主持人的開場詞一樣:“不需要翻譯……不需要言語只要你們的呼喊……不需要聲響,只要你們熱情的掌聲……不要言語只要音樂和歡樂和激情……”因凡特在此書中構(gòu)建的,是一個無限環(huán)繞的回音壁。
巴赫金借自古典樂的“復(fù)調(diào)”概念,在這里要升級成千禧年的電子混音。因凡特穿行在哈瓦那的夜晚,采集了各種各樣的人聲,然后設(shè)計結(jié)構(gòu)、調(diào)配音質(zhì),制作出了一場專屬于哈瓦那夜晚的俱樂部大秀。譯者范曄在這里做的工作,可以理解成一種細致的轉(zhuǎn)碼,在充分動用漢語音形義組合變化的基礎(chǔ)上,讓因凡特的電子樂在中國音響中播放出來。這是一種再創(chuàng)造,而漢語的彈性得以充分體現(xiàn)。比如,用“資道”代替有口音的“知道”;比如,將漢字的部首拆開,以展現(xiàn)原文的綿延;比如,用“劉別謙”替代“莫索爾斯基”,因為后者在西文中與“謙虛”諧音, 而這種諧音在漢語中只能換一種方式呈現(xiàn)。如此種種,都是細致的轉(zhuǎn)碼,一步不到位,就是失卻音樂的細節(jié)。
有人說閱讀《三只憂傷的老虎》是困難的。最大困難或許不在于缺乏情節(jié),也不在于突破常規(guī)的語言,而是因為因凡特并不是講述故事,而是搭建聲音的舞臺,這是一種可以追溯到福克納的演出形式,而因凡特在此基礎(chǔ)上,帶著古巴人的無所畏懼,玩起了喬伊斯的語義游戲。走進因凡特的俱樂部,你先是會被一陣陣的轟鳴震破耳膜,然后會艱難地在光影與人影、音樂與人聲中穿行,試圖去找尋一個屬于你的位置。最后你會發(fā)現(xiàn),在因凡特的俱樂部里,你不能坐下,只能走走停停,當(dāng)一個潛行的竊聽者,因為只有這樣,你才能捕捉到隱藏于暗處的人聲,聽到屬于哈瓦那的秘密。
哈瓦那到處都是秘密。兩個小女孩躲在卡車底下,透過窗戶發(fā)現(xiàn)了閨房秘密。在電話、書信乃至街頭巷尾的八卦中,處處都是秘密。在夜店的低聲交談中,在汽車駕駛室里的暢談中,在人行道上的搭訕中,處處都是秘密。這些秘密不是什么重要的機密,它們瑣碎得一如理發(fā)店地板上的碎頭發(fā),僅僅只是某個人身上微不足道的殘余而已。然而,在原始時期,最神圣的秘密就是八卦。否則,在古巴神話里,女子喜坎便不會因為多舌(用椰殼碗捕捉了神圣的埃庫埃)而被處死,被做成鼓面以警示世人。在古巴,一個秘密可能無關(guān)緊要,也可能會引爆一顆子彈。在因凡特的俱樂部里,轟鳴的電子樂伴隨著嘈雜的八卦聲,其中還不時響起一兩聲槍響。有人狂歡,有人死去,有人玩著愛情或者語言的游戲。這就是古巴的夜晚。
在秘密的中心,都有哪些主要演員呢?當(dāng)然是一群“新潮”知識分子,沉浸在哲學(xué)、文學(xué)和電影,還有酒精和年輕女孩之中的青年人。他們是攝影師、記者、作家或詩人,還是語言的煉金術(shù)師。他們在經(jīng)歷生活,他們在講述自己。“生活是一種向心的混沌?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生活是一種夜間混沌,只有一個中心就是‘拉斯維加斯’,在中心的中心是一杯朗姆酒加水或朗姆酒加冰或朗姆酒加蘇打,然后從十二點起待在那兒……”在這本書里,每個講述者(如果我們能確證他們的身份的話)都有屬于自己的聲音和語調(diào),我們能沿著聲線摸索到他們的內(nèi)心。這些年輕的知識分子用知識武裝自己,用酒精麻醉自己,用年輕女子的美貌轉(zhuǎn)移注意力。他們有著一個共同的朋友,這個人還未登場就已經(jīng)因為腦部腫瘤死去,但他的聲音卻彌散在朋友們的思緒里。他唯一的樂趣就是重新創(chuàng)造語言,他的名字是牾斯忒羅斐冬(Bustrofedon牛耕式轉(zhuǎn)行書寫法,一種古代錯行書寫法)。
誰是牾斯忒羅斐冬?“想象他就仿佛想象下金蛋的母雞,想象沒有答案的謎題,想象螺旋線。他是所有人的牾斯忒羅斐冬,牾斯忒羅斐冬的所有都是他。”他帶領(lǐng)這群古巴青年知識分子玩起了語言的游戲。倒錯,回文,故意的誤讀,沒有意義的玩笑。牾斯忒羅斐冬是因凡特的另一個分身。從莎士比亞到何塞·馬蒂,所有以語言而聞名的人,都遭到了因凡特的調(diào)侃;從哲學(xué)、文學(xué)、音樂到電影,所有人們引以為傲的精神食糧,都被一一拆解,成為游戲的一部分。在全書的中間部分,因凡特以七位古巴作家的口吻講述了托洛茨基之死。這一部分或許是最理想的文學(xué)史書寫方式——用屬于前輩大師的語言,來重寫一個故事。還有什么樣的文學(xué)史,能夠比這樣的文學(xué)史更精彩呢?因凡特在書中肆意使用英語、法語、德語等語言,信手拈來莎士比亞、普魯斯特乃至希區(qū)柯克,他不否認(rèn)世界文學(xué)是古巴文學(xué)的底色,卻依然將全書的中間位置留給了古巴作家。因為,這本書歸根結(jié)底,還是屬于哈瓦那。
在這本書里,有知識的青年們掌握了話語權(quán)。他們富有,聰慧,自由,并擁有揮灑不盡的精力。然而哈瓦那真正的魔力,則在于那些沒有受過什么良好教育的女性。在古巴這樣的國家,女性就如傳說中的喜坎一樣,受到諸多不可明說的限制。因此,她們可能會粗俗,虛榮,怯懦,好管閑事,多嘴多舌。然而,她們的身體里又蘊藏著最可怕也最神圣的自然之力。哈瓦那的女神是“星星雷亞”,一個龐大固埃式的形象,“一種宇宙奇觀”。她言行粗俗,極度自戀,滿嘴謊言,有點神經(jīng)質(zhì),但有一副好嗓子和一個好靈魂。當(dāng)她唱起波麗露,自詡文藝、喜好美女的知識青年也只能在對她外表的厭棄中,屈服于她的神秘魔力。書中的其他女子,“古巴”、薇薇安、麥卡雷娜、蓓巴、勞拉,或多或少都帶有點她的影子,只是更漂亮一些而已。但美貌以及對美貌的追求,反倒造就了她們的庸俗,讓他們成為了被追逐的獵物。
除了當(dāng)?shù)鼐用瘢绹慰鸵彩枪吣堑囊环葑印C绹藷釔酃吣牵葠酃虐透唷_@里是他們的殖民風(fēng)光游樂場。于是,在哈瓦那的喧嘩中,混入了一對美國夫婦的聲音。他們滿懷自信來到哈瓦那觀光,因為一根手杖,以及自己對“土著”的畏懼,經(jīng)歷了一次不大不小的“驚魂記”。因凡特用兩人的視角和口吻記錄了這個小故事,而所有聽說過“猴爪”(The monkey's paw)故事的讀者,或許都能在這個故事里找到一點分量恰好的幽默。閱讀這本書最快樂的地方在于,不僅每頁都有令人拍案叫絕的妙句,隨著閱讀的深入,還能不斷獲得解謎的快樂。這對莫名其妙的美國游客,其實早在“序幕”一章中被主持人點過名字。在一片嘈雜中,線索早已埋好,只等著讀者一點點探尋。
這場大秀開始于熱鬧的俱樂部主持發(fā)言,結(jié)束于一個瘋女人的囈語。瘋女人宣告著一個時代的結(jié)束。正如麥克白所言:“這是篇荒唐故事,是白癡講的,充滿了喧囂的吵鬧,沒有一點兒意義。”這種莫名其妙的安排,正如那對美國夫婦的“亂入”一般,是因凡特的精心設(shè)計。這個瘋女人是誰?是坐在路邊的那個女子?是那個在書中做了十多次心理咨詢的不幸女人?不論是誰,她都如同傳說中的喜坎一樣,是因為無意觸碰了真相而瘋狂。而只有瘋狂的女人,才將哈瓦那的夜幕拉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