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樹的時間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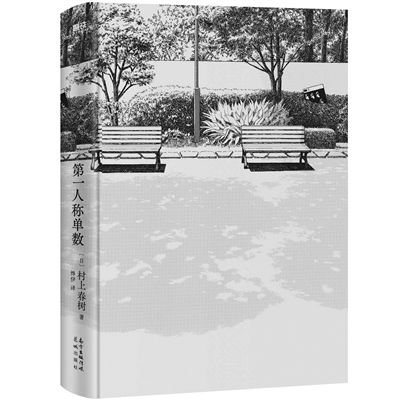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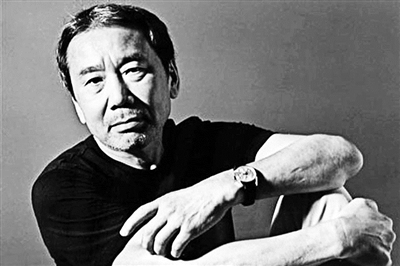
村上春樹已經(jīng)年過七十了,雖然早就知道他生于1949年,卻無法把他跟“衰老”這個詞聯(lián)系在一起。他的小說世界里自然有時間的刻度,可是又像是不存在時間似的,無論他寫于哪個時代的作品,無論他的讀者更新?lián)Q代過多少,閱讀的感覺始終是恒定的,寫作的內(nèi)容也是恒定的,就像是身處一個調(diào)控得剛剛好的房間,待在里面涼爽、舒適,時間絲滑得讓人感受不到重量。
那么他的這一本最新短篇小說集《第一人稱單數(shù)》,與他過去的作品相比會怎樣呢?
1
先說相同之處,一如既往恒定的閱讀愉悅感(只要是在旅途中一定會想帶上一本看看),一如既往地反復(fù)寫著他那些熟悉的人物和故事,一如既往地把人物安排在“人生的中間地帶”……總之,哪怕不看作者名,我們都能一眼看出這還是村上熟悉的配方。再說變化之處,文章一開始我提到村上已經(jīng)七十歲了,這其實是不容忽視的,無論他如何要保持自己的狀態(tài),時間的重量感還是在作品中體現(xiàn)了出來。
全書一共八個短篇小說,前面七篇都發(fā)表在日本文學(xué)雜志《文學(xué)界》,時間集中于2018年和2019年,最后一篇同名小說《第一人稱單數(shù)》是新寫的,基本上都是村上七十歲左右寫的。人走到了這個年齡段,該經(jīng)歷的事情基本上都經(jīng)歷過了,該探索的路也基本上走過了,就會忍不住回望過去,“時間怎么說都是同樣的時間,一分鐘就是一分鐘,一小時就是一小時。無論如何,都是我們必須珍視的。與時間好好和解,盡可能留下寶貴的記憶——這比什么都重要。”(《養(yǎng)樂多燕子隊詩集》)可以說,“記憶”是這本小說集一個關(guān)鍵詞,“無法在現(xiàn)實世界中圓滿地得到這份悸動的時候,我便讓過往對它的記憶從自己的身體內(nèi)部悄悄復(fù)蘇。就這樣,記憶有時成了我最珍貴的情感資產(chǎn)之一,也成了我活下去的寄托,就像躲在外套大口袋里熟睡的、暖乎乎的小貓。”(《和披頭士一起》)
小說中的“我”自然不等同于現(xiàn)實中的村上春樹。不過寫作的曖昧之處也在這里,我們會忍不住把小說中的“我”代入到作者身上。這里要提一筆的是書名“第一人稱單數(shù)”,它不僅僅是此書的同名小說,也是全書的寫作特點:每一篇都是以“我”的第一人稱來講述的。“我本來以第一人稱‘我’開始寫小說,這種寫法持續(xù)了二十年左右。”村上春樹曾經(jīng)在《身為職業(yè)小說家》里專門談過這個問題,“每一本不同的小說,‘我’的人物就會改變,雖然如此,但在繼續(xù)以第一人稱寫作時,有時現(xiàn)實上的我和小說中的主角‘我’的界限,對寫的人或讀的人而言——某種程度也難免會變得混淆不清。”當(dāng)然我們作為讀者也知道這些故事不是發(fā)生在作者身上的,但那種敘事的心態(tài)卻是屬于村上這個人的。
2
那是怎樣一種敘事心態(tài)呢?書中有一篇小說《奶油》,其中的一段可以很好地回答,“我們的人生中,有時是會發(fā)生這樣的事,無法解釋,也不合邏輯,卻唯獨深深地攪亂了我們的心。這樣的時候,大概只有什么也不想、什么都不考慮,只有閉上眼睛,讓一切過去,就像從巨大的浪濤之下鉆出去一樣。”《在石枕上》里那個做愛時喜歡叫前男友名字的女人,《和披頭士一起》里那個會喪失片段記憶的女友哥哥,《品川猴的告白》那個偷了七個心愛女人名字的猴子……哪一個是可以解釋而且合乎邏輯的呢?哪一個不是“攪亂了我們的心”的呢?站在現(xiàn)在回望過去,常常就是這樣的事情回旋在記憶中。
不過頗有意思的是,既然是記憶,有記得的,也有記不得的,“想不起來”“記不太清”在全書里頻繁出現(xiàn):“我對她的了解幾乎可以說是一點也沒有,就連她的名字和長相也想不起來。”(《在石枕上》)“一個我已經(jīng)想不起來的、極為普通的陌生男人的名字。”(《在石枕上》)“為什么會和他講這個,我已經(jīng)記不太清了。”(《奶油》)“可還是連一個小節(jié)都想不起來。”(《和查理·帕克演奏波薩諾瓦》)“除此之外,我對她一無所知。”(《和披頭士一起》)……
如果熟悉村上過去作品的讀者,會發(fā)現(xiàn)這是他常用的敘事策略。他筆下的人物經(jīng)常是面目模糊的,哪怕他會給出一些交代背景的筆墨,也不能增加人物的厚度。通讀完小說,基本上沒有人物會在我腦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除開那只品川猴,但它不是人),他們又輕又薄。如果說在很多作家那里需要濃墨重要刻畫的人物是油畫,那在村上這里的人物就是用鉛筆幾筆勾勒的素描,只有線條,沒有色彩,沒有背景,只有空白。但在村上的文學(xué)世界,這不是缺點。畢竟寫活一個人物,不是村上要達(dá)成的目標(biāo),他志不在此。
3
再回到“記得”這部分上來說。同名小說《第一人稱單數(shù)》里寫道:“這可能和我早先就感受到的那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違和感有關(guān)。我能意識到一種微妙的偏差,好像此刻我的靈魂和它的載體不相契合,或是它們原有的契合在某個時間點被打破了一樣。這樣的事時有發(fā)生。”我認(rèn)為村上的短篇小說非常迷人的部分就是這種“微妙的偏差”。
在日常生活中,大家都戴著面罩,都在正常地扮演著各自社會賦予的角色,有各種道德法律紀(jì)律約束著你在正常的按照規(guī)定生活。你發(fā)現(xiàn)每個人的生活都差不多,上課學(xué)習(xí),上班工作,都是平淡乏味的。你不可能一下子對一個陌生人知根知底的了解。因為大家太正常了。但在這日常生活中總覺得有隱隱的不安。這不安像是一條細(xì)細(xì)的裂縫,在生活光滑的質(zhì)地上分外觸目。好比是端上一碗熱騰騰的米飯放在你面前,你卻總覺得吃得不踏實,要么是這米飯散發(fā)出來的不是米香,卻是肉香,或者是端飯的人那一抹輕俏的微笑,讓你惴惴不安。總要發(fā)生點什么吧?在看小說的時候,我們不常懷有這種期待嗎?這種細(xì)軟如絲般的不安就是村上經(jīng)常寫到的“微妙的偏差”。
舉一個例子,同名小說《第一人稱單數(shù)》里的“我”,平日都不會穿西裝,因為他覺得一旦穿了西裝,就會有異樣的感覺,有一天他穿上西裝后,“可不知道為什么,那一天站在鏡子前,我的情緒卻有些異樣,其中似乎暗含著一絲負(fù)疚。負(fù)疚?該怎么形容好呢……也許和那些慣于給自己的履歷添油加醋的人的罪惡感差不多。即使不和法律相悖,也是倫理道德上的欺詐。明知不該做這樣的事,也清楚這么做不會有什么好結(jié)果,卻還是忍不住做了——那種不好受的滋味正是如此而來的。容我擅自想象,瞞著大伙男扮女裝的男人們,心里的感受也大抵如此。”結(jié)果,穿著西裝的“我”到一家咖啡館看書,卻惹怒了一個素不相識的女人,莫名地給自己“正常的人生”惹來了無來由的麻煩。
村上的小說里,常見這種的情節(jié)設(shè)置,人在“正常”的人生軌道上滑行,忽然莫名地略微出軌(注意,不是完全出軌),產(chǎn)生了摩擦,由此激發(fā)了異樣的心理體驗,然后又一次回到了正軌。《奶油》里“我”忽然無法正常呼吸時,遇到一個老人跟他談起不同尋常的圓,之后這個老人消失不見了;《品川猴的告白》“我”在蕭索的旅館碰到跟其聊天的猴子,說起了種種奇妙的事情,然而第二天卻發(fā)現(xiàn)無人知道這只猴子;《狂歡節(jié)》里“我”碰到一位同樣喜歡一樣音樂的丑女,而這個女人之后就消失了,再見她是在電視中……種種“偏差”出現(xiàn),而后都一一消失,唯有在心頭留存“微妙”的漣漪。
4
最后必須要提到的是在這本書里能鮮明地感覺到村上的確“老”了,因為每一篇小說的中間和結(jié)尾“感嘆”的部分比之前過去多了很多。村上的短篇小說向來輕盈、散淡、微妙,這在此書中也有部分體現(xiàn),但很多大段落的“感嘆”,讓全書有了人生累積下來的重要感(我統(tǒng)計了一下,全書出現(xiàn)了22次“人生”)。
當(dāng)然,我特別喜歡這些感嘆,其中有我認(rèn)為是全書最動人的段落,“迄今為止,我的人生有幾個重要的分水嶺——恐怕大部分人的人生都是如此。向左或向右,往哪邊都可以走。面對這樣的時刻,我有時選左,有時選右……然后才有了如今的我。就這樣,第一人稱單數(shù)的我實實在在地出現(xiàn)在這里。要是我在其中任何一處選擇了不同的方向,也許就沒有今天的我了。”遙想當(dāng)年,村上春樹在29歲時走上了寫作這條路,一晃就是四十余載了,他可能也沒想到這樣一個選擇把他導(dǎo)向了現(xiàn)在。我知道,他依舊會繼續(xù)走下去的。
作為讀者,我繼續(xù)等待他的下一本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