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歲村上春樹寫《第一人稱單數(shù)》,仿佛他“永遠不老”
當我在朋友圈分享已經(jīng)七十歲的村上春樹新書《第一人稱單數(shù)》的閱讀感受時,許多朋友都表達了對村上年輕的恍惚感,原來不知不覺中,曾經(jīng)那個讓我們迷戀不已的《挪威的森林》作者已經(jīng)進入老年。
在我們的印象里,村上似乎永遠是不老的,而導(dǎo)致這一印象的最大原因或許就是他的小說。在某種程度上,村上就像是日本那些一輩子專精于某個特定工藝的手藝人一般,在其小說創(chuàng)作中,少男少女們的情愛糾葛與由此而來的苦惱、少年的成長與苦澀以及關(guān)于充滿人生中的那些偶然、恍惚和遺憾等主題層出不窮……恰恰是這些似乎永遠“年輕”的氣質(zhì)以及其小說所特有的品味,讓我們對村上春樹產(chǎn)生一種似乎“永遠也不老”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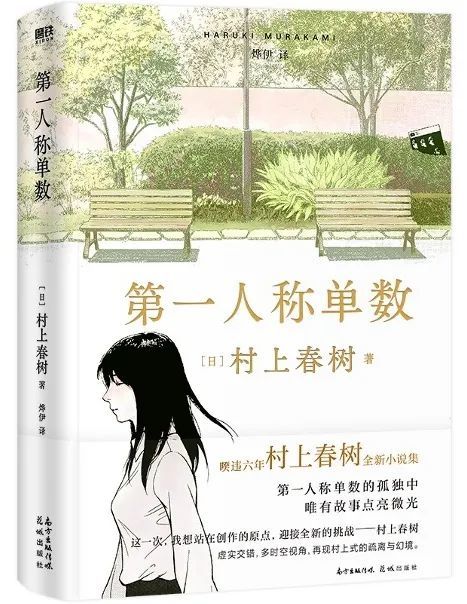
《第一人稱單數(shù)》[日]村上春樹 / 著 燁伊 / 譯
而七十之年的這部小說集,更是如其所言的“再一次站在最初的位置上,迎接全新的挑戰(zhàn)”。其中一個最典型的特征便是再次使用其在《挪威的森林》、《且聽風吟》與《尋羊歷險記》中出色的“第一人稱敘事”,以今日自我作為所有故事的開始與故事的結(jié)局,來展現(xiàn)已經(jīng)在時光中消逝的過去種種。“第一人稱”再次成為回憶的主體,通過講述重現(xiàn)那些充滿了奇異、偶然和精彩的瞬間。而作為讀者的我們,在作者第一人稱的帶領(lǐng)下被重新帶回故事發(fā)生的現(xiàn)場,觀察著看似日常和充滿必然性的生活里的驚異,以及由此所塑造的未來,即我們的現(xiàn)在。
《第一人稱單數(shù)》共收入8篇小說,有意思的是它們在某種程度上都分享著相似的敘事結(jié)構(gòu),即以第一人稱“我”的視角出發(fā),回憶往事;而這些往事如今大都被遺忘了,因為某些意外才又重新想起。就如村上在第一篇《在石枕上》開頭所寫的:“我要寫的,是一個女人的故事。不過,我對她的了解幾乎可以說是一點也沒有,就連她的名字和長相也想不起來”。恰恰是因為記憶的模糊才導(dǎo)致這些回憶充滿了曖昧和某些不可見的部分,于是驚詫的瞬間便頻繁出現(xiàn)。這些奇異之事或相關(guān)的經(jīng)歷在當時或許看來無足輕重,因此并未在記憶里留下過深的痕跡,但在回憶這一空間中,它們卻重新顯示出新的面向,而讓作為回憶者的“我”感到生活表層下的波瀾以及充滿我們?nèi)松械姆N種意外與偶然。
在《奶油》中,“我”被一個不是很熟的女生邀請去聽她的演奏會,但按照邀請函上的地址尋找最終卻是一處深山而一無所獲。“我”覺得自己是被惡作劇了,但也恰恰是在下山途中遇到的一個陌生老人,以及和他的一席對話,讓整個看似無趣且毫無意義的故事出現(xiàn)轉(zhuǎn)折。并且更重要的是,讓“我”突然在這個原本糟糕的午后靈光乍現(xiàn)般地意識到關(guān)于人生和生活的某些真諦。正是這些“靈光”時刻,讓這些原本看似稀松平常且樸實的故事中顯露出深藏其中的美玉寶藏。
而區(qū)別于村上之前的“第一人稱”故事,《第一人稱單數(shù)》里的作品大都采取倒敘的回憶模式,從而使得整個故事事先充滿了一股被結(jié)局早已注定的宿命感。而這恰恰是我們回憶的特定運作方式,而村上這些故事企圖對抗的也恰恰是這一看似無法扭轉(zhuǎn)的既定性,從而對那些在我們生活和人生中匆匆而過或是驚鴻一瞥的時刻注入更多的目光,并由此發(fā)現(xiàn)在線性時間之流中我們曾經(jīng)被賦予的另一種可能和選擇的機會。
在《和披頭士一起》中,有兩個女孩在“我”的生命里留下了或許連主人公自己都無法意識到的印痕。一個是在走廊抱著披頭士唱片的長裙女孩,另一個則是后來戀愛的女孩。這兩個女孩在“我”之后的人生中變成舊日記憶儲藏中的一部分,無足輕重,但當偶然回想起時,以后見之明看到的東西卻遠遠超出了曾經(jīng)所以為的,并且始終潛移默化地塑造著“我”之后的人生,從過去到現(xiàn)在然后通向未來。
當多年后“我”偶然在東京街頭遇到曾經(jīng)只有一面之緣的戀愛女孩哥哥時,后者告訴了主人公女孩之后的自殺悲劇。而恰恰是這一偶然仿佛是人生之神所希望由此向他透露些什么,但對其的參透最終也始終都是模糊不清且模棱兩可的。就如村上在小說中所寫的:“那不是普通的閑談,其中含有某種暗示——某種類似于人生活于世的意義之類的暗示。但追根究底,這暗示不過是在偶然之間湊巧發(fā)生的”。這一切都并不會因為回憶的回溯性溯源而整合出某種必然性或人生規(guī)律,村上在這些小說中所企圖展現(xiàn)的似乎恰恰是他在自己這個年紀所感受到的人生之謎:沒有什么是可以事先知曉的,無論是其給個體帶來的影響,還是在關(guān)于人生和生活的某種真理上,我們都迷茫且一無所知。普遍性的迷思,我們難以勘破,而偶然性或許更加撲朔迷離,但似乎正是因為這一未知所引起的恐慌、焦慮和憧憬,才構(gòu)成了人生豐富多彩和值得過的理由。
在《<養(yǎng)樂多燕子隊詩集>》中,那個叫“村上春樹”的作者親自出場,回憶著自己一直以來對棒球的喜愛,以及在看棒球途中所寫的一部詩集。在這篇小說中,我們似乎無法也不必企圖去分清哪些情節(jié)所謂“真”,而哪些情節(jié)是“假”,因為無論如何它們都是無數(shù)可能人生中的一束支流。對于他人來說,無論是對爵士樂的愛好,還是對棒球的癡迷都可能只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但恰恰是這些小事讓原本并無意義的生活充滿樂趣。
因為就如村上在《狂歡節(jié)》這個故事的末尾所說的,這些或許只是“走了點彎路的插曲,就算它們不曾發(fā)生,我的人生大概還是和現(xiàn)在一樣,幾乎不會有什么變化”,然而真正讓這些“插曲”充滿生機和對人生有了新的意義的,恰恰是對“它們的回憶”。是回憶令那些早已被遺忘的“彎路插曲”產(chǎn)生了光芒,而之所以回憶能具有如此大的力量也正是因為我們意識到自己“老之將至”。
回憶在村上的小說里幾乎成了一種對抗成長、世故、衰老和死亡的武器,即使是那些處在人生最繁華時期的少男少女們似乎也在回憶的耽溺中品味著愛情的飄忽、人生的無常以及個體存在的虛無。
或許正是這一點讓村上春樹的“苦咖啡”文學(xué)被無數(shù)的青年追捧和喜愛,因為相比于那些過分宏大的家國天下,愛恨情仇和遺憾失落對每一個個體都有著足以致命的誘惑與傷害。而在《第一人稱單數(shù)》中,已經(jīng)老去的村上如二十三歲寫作《且聽風吟》的作者一樣,再次捕捉這些無常與失落,而相比于曾經(jīng),此時的故事早已經(jīng)簡潔清明到令人難以沉湎,也不會再無法自拔,而是在作者舉重若輕的筆觸和敘述中漸漸釋然與接受。
因為這樣的遺憾就是組成我們生命跳動的重要部分,就如《品川猴的告白》中那只無法向自己所迷戀的人類女人表達愛意,而只能偷走她們名字的品川猴。人生的空虛需要愛來填滿,但愛似乎卻又總是轉(zhuǎn)瞬即逝且無法持存的,因此漸漸變得越來越像人的品川猴才會意識到孤獨和寂寞的不可避免以及愿而不得的痛苦。
《品川猴的告白》和《狂歡節(jié)》都構(gòu)成了這本小說集中最熱烈的部分,在欲言又止和節(jié)制之間,我們看到那些自始至終貫穿于村上小說中的主題,以及他對于個體存在于世所必然遭遇的危機的體認與理解。
但即使如此,村上卻似乎變得更加豁達,從8個短篇中我們都能感覺到一股舉重若輕的氣質(zhì)以及他小說里迷人的浪漫。就如那只來自《東京奇譚集》里的品川猴,雖然老了但卻如村上一樣依舊春心永存。而在其他幾篇的回憶故事里,似乎也恰恰是那些遺憾、錯過和求不得讓它們在苦澀的時光流逝中變得浪漫,變得像一首悲傷卻不會令人絕望的情詩。這是村上那些看似輕輕的故事里的迷人之處,哀而不傷,怒而不怨。
這或許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始終會覺得村上依舊年輕的原因,他仿佛“永遠也不老”,但卻不像白先勇筆下那個如幽靈般的尹雪艷,淡漠地旁觀著塵世中貪嗔癡者的沉溺與無法自拔,而是始終都積極且真摯地“愛這個世界”(漢娜·阿倫特語)——在《第一人稱單數(shù)》里,村上盡情地展現(xiàn)著自己對爵士樂、搖滾樂和古典樂的喜愛,以及對棒球的著迷——以一種青春的、具有體認且理解的方式,書寫著個體在人生、情感和生活里的碰撞與無奈。在他七十歲時寫的《第一人稱單數(shù)》里,我們再次見到那個寫《挪威的森林》時的年輕作家,通過其干凈利落的故事療愈著現(xiàn)代都市中迷惘和虛無的個體心靈。
也許“關(guān)于它們的回憶有時會走過漫漫長路,來到我身邊,然后以令人難以置信的力量,撼動我的心。就像晚秋的夜風一般,卷起森林中的樹葉,吹倒芒草叢生的荒原,有力地叩響家家戶戶的大門”。村上春樹的小說就是這陣風,吹在我們?nèi)諠u荒漠化的心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