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做學問要“會搭架子” ——王力先生對建構(gòu)中國語言學系統(tǒng)的不懈追求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廣西博白人。語言學家、教育家、翻譯家、散文家。早年考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后留學法國,獲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回國后,先后在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廣西大學、西南聯(lián)大、嶺南大學任教,曾任中山大學及嶺南大學文學院院長。1954年后任北京大學教授。著有《漢語史稿》《漢語語音史》《漢語語法史》《漢語詞匯史》《中國語言學史》《漢語音韻學》《同源字典》《龍蟲并雕齋文集》等,主編有《古代漢語》。圖片由作者提供
王力先生是中國語言學的一代宗師。人們經(jīng)常評論王力先生“會搭架子”,從一個側(cè)面道出了他研究中國語言學極為重視系統(tǒng)建構(gòu)的鮮明特色。說王力先生“會搭架子”,一方面是指他在對漢語進行精細的微觀研究基礎(chǔ)上成功構(gòu)建了多種宏觀性系統(tǒng),另一方面是指他對于理論創(chuàng)新有自覺追求,通過成功構(gòu)建研究漢語的多種宏觀性系統(tǒng),率先揭示了大大小小的中國語言學規(guī)律,照亮了語言學星空。
“語言是一個系統(tǒng)”:這個原理一生受用
系統(tǒng)是一個具有某種特定功能的有機總體,由相互獨立又相互依存、聯(lián)系、作用的不同部分構(gòu)成。語言符號是由不同層級構(gòu)成的復雜社會系統(tǒng),語言研究中,給一門學科“搭架子”和對其中個別字詞句的微觀考察都可以是系統(tǒng)研究。郭錫良先生在《王力先生的學術(shù)道路》中比較詳細地總結(jié)了王力先生所創(chuàng)建的中國語言學多種學術(shù)體系:“(王力先生)在漢語音韻學、漢語語法學、漢語史、漢語詞匯學、中國語言學史、漢語詩律學等許多方面都作出了創(chuàng)立學科體系的貢獻。”王力先生創(chuàng)建這么多學術(shù)體系,在世界語言學史上都是罕見的,其中有的是原創(chuàng)性的,有的是集大成性質(zhì)的,都能做到血肉豐滿,體系完備,沾溉后人于無窮。
王力先生反復強調(diào)系統(tǒng)研究的重要性,總結(jié)系統(tǒng)研究給他治學帶來的深刻影響。他的《漢語史稿》說“每一門科學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和其他科學部門有聯(lián)系的”,強調(diào)不能孤立、片面地研究漢語史,將研究視野局限在漢語史內(nèi)部;談到漢語史的研究方法,他指出要“重視語言各方面的聯(lián)系”,“在語言的構(gòu)成部分中,語音、詞匯和語法是有機地互相聯(lián)系著的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平常我們把這三方面分開來研究或分開來敘述,那只是程序問題,并不意味著這三方面是截然分開的”。在《漢語史稿》的《緒論》部分,王力先生舉“詞”這種語言現(xiàn)象為例,指出“詞”是意義、聲音、形態(tài)結(jié)構(gòu)組成的一個整體,“語音的關(guān)聯(lián)往往意味著詞義的關(guān)聯(lián)(例如‘小’和‘少’)”,“詞尾的產(chǎn)生往往引起語音的輕化(例如‘子’‘們’‘了’‘著’)”,“我們?nèi)绻蝗娴匮芯窟@三方面的因素,我們就不能發(fā)現(xiàn)一個詞的特征”;漢語語音史部分,第一節(jié)就是“語音和語法、詞匯的關(guān)系”,舉出聯(lián)綿詞和駢詞等證據(jù);漢語語法史部分,特地在開頭舉出漢語音變構(gòu)詞等證據(jù);漢語詞匯史部分,專門舉出漢語同源詞等證據(jù)探討語音、詞匯、語法相結(jié)合的研究,都貫徹了這種研究理念。后來出版的《同源字典》更是集中探討漢語史上的同源詞。這種研究理念,在今天仍然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意義和針砭作用。
《先秦古韻擬測問題》談到古音擬測的意義:“所謂擬測或重建,仍舊只能建立一個語音系統(tǒng),而不是重建古代的具體音值。如果擬測得比較合理,我們就能看清楚古今語音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以及上古語音和中古語音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同時又能更好地了解古音的系統(tǒng)性。”王力先生在《我的治學經(jīng)驗》中說:“‘語言是一個系統(tǒng)’這個原理我一生受用不盡。我用這個原理指導我的語言研究,相信是有成效的。”
他認為,哪怕是一個詞的微觀研究,也必須注意系統(tǒng)性。他對上古音韻母“脂微分部”的研究可以算作微觀研究,受到了章炳麟《文始》分出隊部的啟發(fā),不僅根據(jù)《詩經(jīng)》至南北朝的押韻,還充分運用“語言是一個系統(tǒng)”的原理,做到系統(tǒng)和材料的完美結(jié)合。王力先生仔細抽繹以《詩經(jīng)》為主的先秦韻文,明確清儒所分脂部應(yīng)該分為脂微兩部。傳統(tǒng)音韻學有陰聲韻、陽聲韻、入聲韻的說法,按現(xiàn)代語言學理論,陰聲韻指韻尾是元音或沒有韻尾的韻母,陽聲韻指韻尾是鼻音m、n、ng的韻母,入聲韻指韻尾是p、t、k的韻母。王力先生自覺接受清儒所創(chuàng)陰陽入對轉(zhuǎn)的科學理論,看出清儒的分部,質(zhì)(韻尾為t)、真(韻尾為n)二韻部的主要元音相同,形成陽入搭配,物(韻尾為t)、文(韻尾為n)二韻部也是主要元音相同,形成陽入搭配,唯獨陰聲韻只有一個脂部,不能形成一陰、一陽、一入的相配格局。如果將清儒所分脂部分為脂、微兩部,那么就能形成“脂、質(zhì)、真”“微、物、文”這種整齊的搭配,陰、陽、入對轉(zhuǎn)的系統(tǒng)性觀念在他進行脂微分部時幫了大忙。由于論證極周密,因此脂微分部很快獲得舉世公認。再如中古的祭、泰、夬、廢四韻,上古常常互相押韻,有人據(jù)此給上古音單立一個陰聲韻的祭部,這個祭部放到陰陽入相配的格局中顯得孤零零的,破壞了上古韻部的系統(tǒng)性格局。王力先生敏銳地發(fā)現(xiàn),這個祭部上古韻文中常常跟月部相押,其他各部也多有中古陰聲韻的去聲在上古跟入聲韻相通的證據(jù),于是他將中古陰聲韻的部分去聲字歸到上古入聲,稱為“長入”,祭部不獨立成部,而是歸入月部長入。這樣,既解決了祭部的上古歸屬,又維護了上古韻部的系統(tǒng)性。由此可見,王力先生不為創(chuàng)建理論而歪曲分析具體材料,不生搬硬套,力爭觀察正確,達到十分精審的地步。《中國現(xiàn)代語法·自序》談到他在研究中國語法“疑的時期”發(fā)表了《中國文法學初探》,“當時我的破壞力雖大,建設(shè)力卻不足;批評人家的地方雖大致不錯,而自己創(chuàng)立的理論卻往往陷于觀察不確”;到“悟的時期”,覺悟到“空談無補于實際,語法的規(guī)律必須是從客觀的語言歸納出來的”,要做到“能觀其全”,強調(diào)觀察語言事實必須正確、全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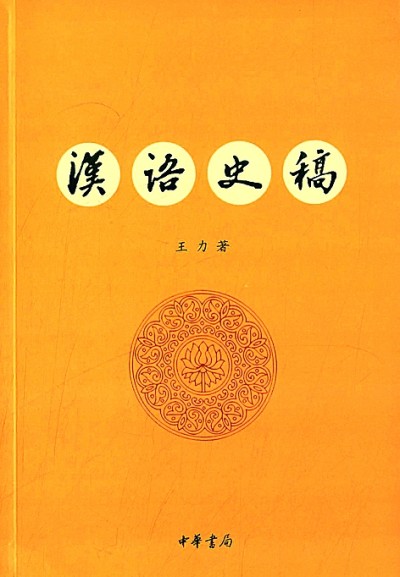
王力著《漢語史稿》 圖片由作者提供
創(chuàng)立系統(tǒng)與占有材料、重視例外
《我的治學經(jīng)驗》說:“科學研究并不神秘,第一是要有時間,第二是要有科學頭腦。有時間才能充分占有材料,有科學頭腦才能對所占有的材料進行科學的分析。古今中外有成就的科學家都是具備這兩個條件的。”這兩條經(jīng)驗是王力先生學習和研究實踐的總結(jié),樸素表達了他所認定的從事中國語言學系統(tǒng)研究的基本條件。
從事系統(tǒng)研究,必須高度重視構(gòu)建系統(tǒng)的各種材料,全面搜集、整理,尋求邏輯的自洽,這需要花費大量時間。王力先生28歲時出版《老子研究》,附記寫道:“今人喜言歸納,實則恒用演繹。凡利于己說者,則搜羅務(wù)盡;不利己說者,則絕口不提。舍其不利己說者而觀之,誠確乎其不可拔矣;然自欺欺人,莫此為甚。余為是篇,于《老子》全書,幾無一語未經(jīng)道及,宜無片面觀察之嫌。顧彼此相較,則吾術(shù)為拙;往往一語齟齬,全章改作。非不知棄全取偏之易為力,羞而不屑為也。”
《我的治學經(jīng)驗》:“從事科學研究要有科學頭腦。對語言研究來說,科學頭腦也就是邏輯頭腦。”任何一門學科的知識系統(tǒng)都由概念組成,系統(tǒng)化的概念是獲得新知的必要前提。王力先生1934年出版《論理學》,“論理學”即后來的“邏輯學”,說明他對形式邏輯下過大功夫。他重視邏輯和語言,邏輯和學術(shù)研究的關(guān)系,他的《邏輯與學術(shù)研究、語言、寫作的關(guān)系》指出,“沒有思維就沒有語言”,“思維,或者說思想,只有在語言材料的基礎(chǔ)上才能產(chǎn)生”;“我們搞學術(shù)研究”,“只有在綜合分析材料之后,才能引出結(jié)論”,“在學術(shù)研究上,我們對邏輯的應(yīng)用非常重要”,要求運用概念有同一性,推理要嚴密等,重視它們在創(chuàng)建系統(tǒng)中的基礎(chǔ)作用。
王力先生博覽古今中外相關(guān)書籍,特別是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親炙中外名士,早有負弩先驅(qū)之志。他治學高度清醒,自覺儲備多方面系統(tǒng)知識,包括西方語言學理論以及哲學、邏輯學等。《中國現(xiàn)代語法·自序》:“中國語法學者須有兩種修養(yǎng):第一是中國語史學;第二是普通語言學。缺一不可。”他以超常毅力,擠出點滴時間,占有極其豐富的第一手材料,充分運用邏輯思維,既有很多精細的微觀考察,又精心研究建立學科體系的各種系統(tǒng)和非系統(tǒng)材料,抽絲剝筍,去偽存真,取精用宏,揭示了很多規(guī)律,搭起了漢語研究的多種學科框架,創(chuàng)建多學科體系。
研究語言系統(tǒng),必然面臨對非系統(tǒng)部分的例子的分析,也就是對例外的處理。語言是一種高度復雜的社會系統(tǒng),非常便于人們觀察系統(tǒng)中夾雜的非系統(tǒng)部分。這些例外,絕大部分直接關(guān)涉語言演化,有些跟語言演化無關(guān)。治漢語史學科,時空矛盾更加突出,面對的例外更多,必須鉆研歷代古書才能解決。古書是用古代漢語、古代漢字來記錄的,異質(zhì)成分多,諸如訛脫誤衍,還有后人改動的情況。這些例外大多都跟寫書時的語言演化無關(guān),治漢語史,必須剔除它們。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中都會存在文字錯訛和后人改動的情況,如果沒有校勘的功夫,以為凡是例外都是反映漢語演變的材料,就會導致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囫圇吞棗的治學方式,在漢語語音史研究中特別多,我們應(yīng)引以為戒。
王力先生一直注重材料中的例外,提出利用“系統(tǒng)”的方法來克服“非系統(tǒng)”帶來的干擾。《中國文法中的系詞》說:“我們研究中國文法,與校勘學發(fā)生很大的關(guān)系。古書的傳寫……另有一種訛誤的來源:有些依上古文法寫下來的文章,后代的人看去不順眼,就在傳寫的時候有意地或無意地添改了一兩個字,使它適合于抄書人的時代的文法……我們研究文法史的人,對于這類事實卻絕對不該輕易放過”;提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嚴守著‘例不十,法不立’的原則,凡遇單文孤證,都把它歸于存疑之列,以待將來再加深考”,“如果我們在某一時代的史料中,只在一個地方發(fā)現(xiàn)了一種特別的語句構(gòu)造方式,那么就不能認為通例,同時也就不能成為那時代的文法。縱使不是傳寫上的錯誤,也只能認為偶然的事實罷了”。對于“單文孤證”的語言現(xiàn)象,他提出存在兩種可能性,一是傳寫的訛誤,二是偶然的事實。所謂“偶然的事實”,指的是還沒有形成一條規(guī)律,是“非系統(tǒng)”的現(xiàn)象。
王力先生的研究實踐有大量用系統(tǒng)方法處理“非系統(tǒng)”的經(jīng)典案例。古音研究方面,對例外諧聲的處理是一個典型個案。瑞典學者高本漢常常據(jù)例外諧聲反映出來的聲母相通現(xiàn)象,給上古音構(gòu)擬一類聲母,這就是復輔音聲母。王力先生《漢語史稿》根據(jù)系統(tǒng)觀批評高氏的這種“形式主義”做法:“他不知道諧聲偏旁在聲母方面變化多端,這樣去發(fā)現(xiàn),復輔音就太多了。”這個批評很深刻,因為變化“多端”,所以存在多種可能的解釋,復輔音的處理方案就顯得草率。在語法史研究方面,王力先生對系詞“是”產(chǎn)生時代的例證分析也是一個典型個案。他注意到上古有《史記·刺客列傳》“此必是豫讓也”一類極個別“是”作系詞的例子,屬于“非系統(tǒng)”,因此他不將這種例子作為系詞“是”產(chǎn)生時代的例證。后來人們從馬王堆出土的文獻中發(fā)現(xiàn)有5例“是”作系詞的例子,這些例子的“是”作系詞不可能是“傳寫的訛誤”,但沒有排除他所謂“偶然的事實”這種可能,也就是還沒有成為一條規(guī)律,所以他仍然持保留意見。后來人們找到先秦兩漢更多古書有“是”作系詞的例子,遠在10例以上,才可以說徹底論證了戰(zhàn)國以后系詞“是”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在詞匯史研究方面,《“江、河”釋義的通信》《說“江、河”》二文是利用系統(tǒng)方法克服“非系統(tǒng)”因素干擾而正確分析詞義的典型案例。王力先生通過對大量材料的分析,明確上古“江”專指長江和長江支流,“河”專指黃河和黃河支流,針對一些糊涂認識,指出《荀子·勸學》“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的“江河”只能理解為長江、黃河。
語言的發(fā)展,常常帶來對舊系統(tǒng)的破壞,這種破壞作用“其來有漸”,表現(xiàn)出某種臨界狀態(tài),不一定反映新的語言現(xiàn)象的達成。對于例外中涉及語言系統(tǒng)演化的部分,要特別注意這些材料是否真正反映了跟系統(tǒng)的質(zhì)的區(qū)別。王力先生重視例外材料的細致辨析,哪怕是一個不起眼的用例,他都放到成熟的理論系統(tǒng)中加以審視,徹底弄清其真諦。在他的著述中,這種微觀的精細辨析比比皆是,往往鑿破鴻蒙,令人大開眼界,至今都是處理例外現(xiàn)象的最佳方案。碰到模棱兩可的情況,他提出要根據(jù)一個時代的整體語言系統(tǒng)來加以決斷,也就是建立歷史和系統(tǒng)的觀點。如果這些“例外”只有一例,那么,即使它們真正跟共時系統(tǒng)反映的事實有質(zhì)的區(qū)別,但由于是個別用例,因此他就作為孤證對待,“孤證就是缺乏社會性的偶爾出現(xiàn)過一次的例證”,要考慮傳世文獻具有后人改動的可能,希望找到確鑿不移的證據(jù)加以取舍,但這不能作為語言演變的確證。如果不屬于“孤證”,就確認它屬萌芽或殘存狀態(tài)。這樣精微的研究,是使王力先生創(chuàng)建的系統(tǒng)血肉豐滿的根本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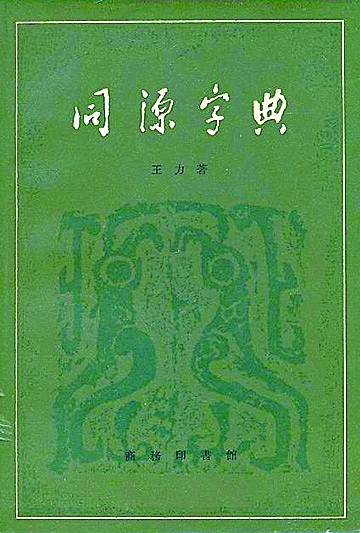
王力著《同源字典》 圖片由作者提供
系統(tǒng)地吸收,才能系統(tǒng)地構(gòu)建
王力先生能在中國語言學研究方面搭起多種學科框架,跟他充分吸取古今中外學術(shù)精華有極大關(guān)系。人們說王力先生“學貫中西”,這只是一個通俗說法。嚴格說來,科學研究不分古今中外,古今中外都有科學成果,也都有非科學成果。過去,不少人用“學貫中西”來判別一個學人成就的高下,至今還有一定影響,但這不準確。科學的認識應(yīng)該是:充分吸收古今中外的已知知識或?qū)W術(shù)精華。
王力先生搭建不同學科的框架,都有中外比較的視野,框架總體和研究思路主要接受了西方的影響,具體內(nèi)容采納我國學術(shù)精華甚多。這樣安排學科框架的研究理路符合清末新式學堂創(chuàng)辦以來的學術(shù)取向,將學科內(nèi)容分為若干部分,有條理地分篇、分章、分節(jié)加以敘述,理論色彩遠超古代。中國古代語言學重實用,古代語言學家對相關(guān)學科做了很多微觀和宏觀研究,成果累累,足資后人吸收;但他們大多不注重搭建各門學科的理論框架,理論創(chuàng)新常常湮沒在材料分析之中。《中國語言學史》說,“中國社會發(fā)展的歷史,規(guī)定了中國古代語言學是為了實用的目的”。王力先生吸收西方語言學理論,主張理論不能脫離實際,要吸取西方科學有用的理論、方法和研究視角,棄其糟粕;物物而不物于物,反對亦步亦趨。清華研究院研究生畢業(yè)論文《中國古文法》(1927年)對此已有明確闡述,《中國現(xiàn)代語法·自序》回顧他研究中國語法“蔽的時期”的毛病:“只知從英語語法里頭找中國語法的根據(jù),不知從世界各族語里頭找語法的真詮。當時我盡管批評別人削足適履,‘以英文法為楦’,其實我自己也只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他創(chuàng)立不同學科框架,根據(jù)不同研究條件和需要靈活吸收,不同學科體系吸收學術(shù)精華的側(cè)重點不完全一樣,漢語詩律學、中國語言學史研究吸收我國古代相關(guān)成果尤多。中國語言學史對我國歷代語言學的分析、評價都建立在細讀原注的穩(wěn)固基礎(chǔ)之上,往往要言不煩,恰如其分。
王力先生很早就從演變的角度思考漢語史的問題,《中國古文法》已有這方面內(nèi)容,提出“文法之為物,但賴習慣以成,例不十則法不立;所謂合法非法,當以合習慣非習慣為標準,不當以見于名人之文為標準”,竭力祛除崇古抑今之病,分“古文法”和“今文法”,探討語言習慣的變遷。《中國文法學初探》(1936年)明確提出“至少該按時代分為若干期,成為文法史的研究”。漢語史學科框架的建立深受歐美語言學,特別是蘇聯(lián)的影響。19世紀后半葉以來,歐洲人就寫出了英語史、德語史、法語史、俄語史等著作。王力先生仿照歐洲一些單一語言演變史,主要是蘇聯(lián)多部俄語史著作建立漢語史框架,《漢語史教學一年的經(jīng)驗和教訓》一文詳細闡述了《漢語史稿》的借鑒之處。《漢語史稿》《漢語語音史》《漢語詞匯史》《漢語語法史》采取語音、詞匯、語法史的敘述框架,借鑒了歐美著作,法國語言學家房德里耶斯《語言》就是采用這種框架敘述語言學的,《漢語史教學一年的經(jīng)驗和教訓》講按照語音、語法、詞匯三部門敘述漢語史,“這樣做,是蘇聯(lián)俄語史的做法”。王力先生漢語史研究的一些視角、內(nèi)容也對西方語言學多所吸收,《漢語史稿》和《漢語詞匯史》都有“詞是怎樣變了意義的”和“概念是怎樣變了名稱的”,吸收了房德里耶斯《語言》的觀察視角和部分內(nèi)容。
王力先生看出,中國古代語言學在漢語材料分析和組成系統(tǒng)的各部分及其關(guān)系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成功,對創(chuàng)建學科體系作用巨大,一反舊時部分學者棄慎思而任情,執(zhí)偏見為入流,毀萬古以趨時的“逢古必反”的研究趨向,客觀冷靜地將這些優(yōu)秀成果納入各種學科框架,這是他開創(chuàng)多種學科的制勝法寶之一。《漢語詩律學》將“漢語詩律的一般常識”和“前人研究”得出的“比較高深的知識”,加上王力先生“自己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句式和語法”,以及韻律方面的意見整合在一起,構(gòu)建漢語詩律學系統(tǒng)。《漢語史稿》敘述“中國歷代學者對漢語史的貢獻”,指出:“中國歷代學者對漢語史的貢獻是很大的。我們必須利用古人語言研究的成果,在原有的基礎(chǔ)上提高”。《同源字論》總結(jié)既往漢語同源詞研究得失,提出“將要謹慎從事,把同源字的范圍縮小些,寧缺毋濫,主要以古代訓詁為根據(jù),避免臆測”。
王力先生的《中國古文法》已體現(xiàn)出致力于立足漢語材料,構(gòu)建古代語法系統(tǒng)的追求。他區(qū)分“世界文法”和“中國文法”,主張治世界文法要“觀其會通,不當限于西文也”,治中國文法“當自其本身求之,不必以西文律之也”;明確指出語法研究要揭示客觀存在的語言結(jié)構(gòu)規(guī)律,“夫文法者,敘述之事也,非創(chuàng)作之事也;習慣之事也,非論理之事也;客觀之事也,非主觀之事也”。王力先生畢生創(chuàng)建中國語言學多種學科體系,都謹守探尋“客觀之事”這個治學的根本原則。無論對既往研究成果的取舍,還是自己得出的新結(jié)論,都以是否揭示客觀規(guī)律為準繩。
科研不等于寫文章,只有系統(tǒng)反映自然、社會、思維等客觀規(guī)律的分科的知識體系才是科研。有些感悟式、碎片化的治學成品,可以歸到科研成果一類,但常常缺乏全局觀、系統(tǒng)觀,難以達到深廣的境界。追溯王力先生為什么善于構(gòu)建中國語言學的學科系統(tǒng),是饒有興味的話題。
我們可從他的求學歷程和學術(shù)抱負方面去探討,但學術(shù)抱負又根源于他的求學。王力先生的系統(tǒng)構(gòu)建,一個重要的來源就是,他很早就系統(tǒng)閱讀中西語言學及相關(guān)學科那些建立系統(tǒng)框架的著作。據(jù)《我是怎樣走上語言學的道路的》,他20歲時就開始閱讀語言學方面的著作。倘若王力先生沒有仔細閱讀這些建構(gòu)系統(tǒng)的著作,他畢生致力于創(chuàng)建中國語言學不同學科體系的事就無從做起。
中國古代不乏建構(gòu)學術(shù)框架的語言學著作,音韻學方面尤其顯著。例如上古音研究,顧炎武《音學五書》、江永《古韻標準》、段玉裁《六書音均表》、孔廣森《詩聲類》等等,都建構(gòu)了各自的上古韻部框架。王力先生之前,章炳麟《文始》《國故論衡》、黃侃《音略》等,都建立了他們的上古聲韻系統(tǒng)框架,這得益于他們閱讀清代這些上古音著作。王力先生也是深受這些著作的啟發(fā),建立自己的上古音系統(tǒng)的。據(jù)《漢語音韻學》(原名《中國音韻學》)和《清代古音學》等著作,王力先生對顧炎武以迄章、黃的著作都做過非常細致的系統(tǒng)閱讀。清末,中國人仿照西方模式,寫出一些建立中國語言學分科框架的著作,例如《馬氏文通》,王力先生26歲時就詳細地閱讀了此書,他《談?wù)勗鯓幼x書》中說:“昨天我看從前我念過的那本《馬氏文通》,看到上邊都寫有眉批。那時我才二十六歲,也是在清華當研究生。”他的導師梁啟超、趙元任等,都是善于建構(gòu)系統(tǒng)的學者。
《我的治學經(jīng)驗》:“我到二十四歲才學英語。二十七歲我開始學法語……五十歲學俄語……我還憑這點外語知識讀了一些外國出版的語言學書籍和雜志。”留學法國以后,他閱讀了大量西方學者的語言學著作。西方學者比較擅長系統(tǒng)建構(gòu),閱讀這些書籍,無疑有助于他構(gòu)建中國語言學的學科系統(tǒng)。他的博士論文《博白方音實驗錄》,征引了魯斯洛《法語發(fā)音概要》、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后來的《漢語音韻學》,附錄部分《漢語音韻學參考書》更征引了多部英法文寫的關(guān)涉系統(tǒng)框架的著作。方光燾《王力〈中國語法理論·造句法〉導讀》談到“王力的書所依據(jù)的理論”,明確指出,王力的漢語語法研究“受到房德里耶斯《語言論》一書的理論的影響。同時,他又采納了美國語言學家布龍菲爾德的某些學說。他所受到的最大的影響是丹麥語言學家奧托·葉斯伯森的‘三品說’”,此說有根據(jù)。《我的治學經(jīng)驗》寫道:“有人說我做了許多開創(chuàng)性的漢語研究工作,其實并不是什么開創(chuàng)性,只是普通語言學原理在漢語研究中的應(yīng)用。”
唯有真正系統(tǒng)地吸收,才有可能真正系統(tǒng)地構(gòu)建。為了將中國語言學研究導向深入,我們必須系統(tǒng)地構(gòu)建,零敲碎打的閱讀是不可取的,必須真正系統(tǒng)地閱讀中外有用的語言學著作。
繼承先賢遺產(chǎn),不斷逼近中國語言學真詮
學術(shù)史告訴我們,學科的整合和分支是學術(shù)發(fā)展的兩條主線,貫穿整個學術(shù)史。王力先生創(chuàng)立各種學科體系的實踐,深深地體現(xiàn)了這樣的主線。他以構(gòu)建多種學科體系為己任,珍惜光陰,筆耕不輟,不斷提出真知灼見,死而后已,留下近千萬字的學術(shù)著作,光照學林。
中國語言學的真詮遠遠沒有窮盡,我們需要在王力先生等先賢研究的基礎(chǔ)上,不斷整合中國語言學的不同學科,分支、裂化原有學科,扎實推進,不斷逼近中國語言學的真詮,這是我們的時代使命。從這個角度說,王力先生構(gòu)建中國語言學不同學科體系的實踐會帶給我們多方面的啟示。
(作者:孫玉文 劉翔宇,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