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頑強的,多彩的,迷人的 伊朗四千年的起承轉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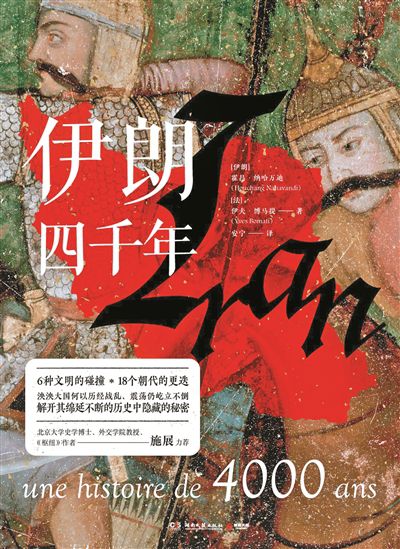
你可能也經常在媒體上看到“帝國”一詞,它有時用來形容某些超級大國,有時則隱喻那些財大氣粗的跨國企業(yè),但若問“哪個是世界上第一個帝國”,就未必那么廣為人知了。有人說是埃及,有人認為是羅馬,還有人相信是秦帝國,但事實上,埃及不能算是那種多民族復合的“帝國”,羅馬太遲了,秦帝國則不僅遲,還有很多學者堅持它并非西方意義上的那種“帝國”。這個頭銜最無可爭議的歸屬,其實是公元前550年建立的波斯帝國。
迷人的根源
短短數十年內,這個大帝國席卷了“肥沃新月”的諸多國家和城邦,征服了埃及,近東各地在歷史上首次被統(tǒng)一在一個國家政體內,盡管在希波戰(zhàn)爭中稍稍受挫,但它仍然成功存續(xù)了兩個半世紀之久。部分或許也因此,當時希臘雖然是戰(zhàn)勝方,但卻從未停止對波斯帝國的迷戀,史學家阿米爾·馬德希·巴迪說:“這一迷戀的根源只能解釋為一種文明的非凡生命力和持續(xù)影響力,在二十五個世紀中憑借其德行、生活方式、風尚令所有人傾倒,無論敵友都試著去了解它。”
然而,像這樣一個看起來盛極一時、幾乎所向無敵的大帝國,到后來卻被孤軍深入的亞歷山大大帝在短短一兩年內征服——這還不是第一次,數百年后,作為“羅馬帝國在東方永恒的敵人”,薩珊波斯帝國又被不及自身一半兵力的阿拉伯人迅速擊潰;到蒙古崛起時,它又被輕易納入蒙古人囊中。極少有哪個國家像伊朗這樣,在漫長的歷史上經歷這么多的盛衰起落,即便看慣了興亡的中華五千年,恐怕都比不上伊朗四千年有這么多苦難。
不夸張地說,伊朗的歷史提供了一個極端的個案,可以讓我們看到,一個國家雖然早就形成了早熟的政體,但由于其內在的結構性缺陷,卻難以抵擋接踵而來的內外部的挑戰(zhàn),以至于不得不一次次推倒重來,直到近代仍然步履蹣跚。
現在的首都德黑蘭,在卡扎王朝1786年進占之前原本只是一個卑微的小鎮(zhèn),點綴著狩獵行宮和花園,但這個由土庫曼人建立的異族王朝決定拋開國內那么多名城,從頭建立一個新首都,它才由此成為伊朗第32座都城。
然而,這也意味著,不管遭遇什么樣的危機,伊朗內部總能涌現出一股新力量,從頭收拾舊山河。因而又正是這樣一個多災多難的國家,一次次扛過了毀滅性的打擊,即便屢次被希臘人、阿拉伯人、蒙古人、阿富汗人等外族亡國,更多次瀕臨覆滅,但它卻作為一種獨特的文明仍然頑強地存活了下來。若論這兩方面經歷之復雜,伊朗可能都是世界之最。
破碎的心臟
為什么伊朗四千年如此多彩又充滿血淚和波折?這可能首先得歸結于它特殊的地緣政治位置:伊朗高原處于歐亞大陸東西方諸大文明的要沖,西方的希臘/羅馬、近東的兩河/埃及、南部鄰近阿拉伯半島、北方是草原諸文明,而往東則是中國和印度。在近代地理大發(fā)現之前,沒有哪個國家能像伊朗這樣,同時與舊世界的幾乎所有主要文明接壤并密切互動。這是東西方之間的心臟地帶,但卻屬于地理上的“破碎帶”,難以實現自身的整合。
這既成就了絲綢之路沿線“波斯胡商”的名聲,使他們開放地采納不同文化的因素,并能在強盛時向四方擴張,但也使它變得格外脆弱,因為這個十字路口幾乎吸引著各種紛至沓來的外部勢力,乃是強敵環(huán)伺的“四戰(zhàn)之地”,而再強盛的國家也總有出錯牌的時候。
盡管伊朗國家在歷史上不止一次表現脆弱,似乎輕易地就被外族征服了,但如果對比其他文明的表現來看,就會發(fā)現它其實是極其堅韌頑強的。四大文明古國中,中國和印度因其相對孤立和安全的地理位置、龐大的人口和深厚的文明基底,幸存了下來,但兩河和埃及文明,則在阿拉伯大征服之后,就都早已被同化得蹤影全無。連小亞細亞的希臘-羅馬文明,在經歷了奧斯曼帝國的漫長統(tǒng)治后,現在也變成土耳其了。然而,伊朗哪怕迭遭入侵,被異族統(tǒng)治超過一千年之久,但它仍是伊朗人的伊朗。
說來吊詭,它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根本原因很可能在于其國家政體的結構性缺陷。波斯帝國的統(tǒng)治者一直是“萬王之王”,內部包容著多元異質的獨立半獨立王國——這就是為什么亞歷山大大帝這樣的入侵者能一擊得手,因為帝國一旦戰(zhàn)敗,喪失威望之后,就再也沒有什么粘合劑能維系這個龐雜的組織不分崩離析了。與此同時,每個相對自治的單元卻又能頑強地抵御外部的滲透和統(tǒng)治,而只對新的統(tǒng)治者表示象征性的順從。這是一個“易于征服,但難以平定”的國家。
因此,伊朗歷史上那些王朝的覆滅,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社會有機體在內外部力量沖擊下解體的結果,但正因為這一崩潰往往十分迅速,因而社會的基本組織反倒是相對完整地保留了下來——用中國人容易理解的話說,就像是“換了個皇帝,別的都沒變”。亞歷山大大帝無疑是個偉大的征服者,但他身后沒能留下什么,促進民族融合的想法也以失敗告終;阿拉伯人崛起時,波斯各地又望風披靡,甚至接受了伊斯蘭教,但它的內核卻依然故我,對阿拉伯帝國內部的異端來說,人人都清楚,伊朗是唯一一個天然的反對派活動基地,可以讓他們安身立命并獲得源源不斷的支持。
最大挑戰(zhàn)是擺脫孤立
這是在伊朗歷史上反復出現的篇章:這個國家即便一時低頭,但內在卻頑強地堅持著自身的獨特認同。在當今的所有伊斯蘭國家中,伊朗是唯一的什葉派大國,這不是偶然的,事實上,最初將什葉派確立為國教的薩非王朝(1501-1736),原本也是信奉遜尼派的,但它的統(tǒng)治者隨后意識到,秉持一種有別于對手的特殊認同,將能更好地為這個國家提供凝聚力,反對所有外部敵人。
現代伊朗的幾乎所有方面,都可以直接追溯到薩非王朝:這是近九百年來,第一個完全統(tǒng)一伊朗東西部的政體,并努力嘗試將多元混雜的族群加以統(tǒng)合,在此基礎上逐漸打造成了后來為世人所了解的伊朗國家。雖然它起初是以一個不具有政治色彩的教派起家,但一旦它攫取了國家之后,教權就逐漸讓位給世俗政治權力或與之結合,宗教戒律在積聚的財富面前不斷退卻,王朝的疆域和邊界日趨清晰,并壟斷了在境內征稅的權力。在此基礎上,它第一次對葡萄牙、英國等西方國家打開國門,在積極采納現代技術的同時,學習如何在一個全新的國際體系內與列強打交道。
從這些歷史經歷來看,伊朗可能比土耳其之外的任何中東國家都更早做好了國家制度現代化的準備,而它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又再一次必須歸功于其強大的國家傳統(tǒng)。作為世界上第一個大帝國,伊朗的國家即便一再被打碎,但它最終都能重新打造起一個制度框架,拯救并守護自身的文化傳統(tǒng)。
在這漫長的歷史上,伊朗成功地讓它的文明和文化得以存續(xù),但到了現代社會,它還得不可避免地面臨一個全新的挑戰(zhàn):如何在保持自身認同的同時,向外界開放,進而讓人接受自己的特殊性,擺脫受孤立的處境。對伊朗人來說,這可能尤為困難,因為在過去的四千年里,外部世界對它來說有時是威脅,常常是挑戰(zhàn),卻很少只是單純的機會。不過,只要這個文明對自己的生命力抱有信心,它應該遲早會意識到,世界固然不能沒有伊朗,但伊朗更不能沒有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