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對青年的關(guān)愛與寬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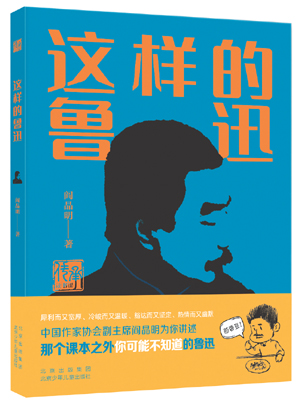
閻晶明新著《這樣的魯迅》,北京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向青少年朋友講魯迅故事,通過講故事的方式介紹魯迅的人生歷程,感受他的思想和精神,欣賞他的各類作品,是我一直以來的一個心愿。網(wǎng)絡(luò)發(fā)達的今天,魯迅不但沒有被淡化,反而有成為網(wǎng)絡(luò)熱點的趨勢。講魯迅的趣事,談魯迅的逸聞,推魯迅的“金句”,是年輕人在網(wǎng)絡(luò)上喜歡做的事之一。每當(dāng)在生活里遇到、看到、聽聞到某件事,總有人會問,如果魯迅還在,他會怎么說、怎么看。關(guān)于魯迅的種種討論、爭論總是不斷。從這一個側(cè)面足以見出,作為一百年來最具經(jīng)典性的文學(xué)家,魯迅的魅力和影響力何等巨大和持久。在這些紛紛揚揚的說法和議論中,魯迅形象在日益生動、豐富的同時,也有被誤讀甚至曲解的時候,有各種解讀與事實明顯不符的地方。我以為,魯迅研究界有必要為普及魯迅做必要的工作,有必要對一些基本的事實做匡正和說明,有必要以自己的研究和理解,讓更多的人走近魯迅,走進魯迅的內(nèi)心世界。
我對魯迅的閱讀理解遠遠不夠,但愿意以一己之力做一些帶有普及性的事情。今年以來,在熱心的編輯朋友鼓勵下,我寫成了一本小書:《這樣的魯迅》。這本面向青少年讀者的小書在紀(jì)念魯迅誕辰140周年之際出版,具有格外特殊的意義。這本書的努力方向,是以講故事的方式呈現(xiàn)魯迅的人生歷程,聚焦他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的崇高境界。
繼承和弘揚魯迅精神,包含非常豐富的內(nèi)涵。其中,魯迅對待青年的態(tài)度、魯迅的青年觀也是我想向青少年朋友們介紹的。
魯迅對青年總是充滿了熱愛、關(guān)心、幫助和支持。有數(shù)不清的青年,特別是在工作上得到魯迅支持、創(chuàng)作上受到魯迅鼓勵、生活上得到魯迅扶助的青年,用文字懷念魯迅給予他們的愛心與教誨。魯迅與各色青年的交往,有許多故事可以講述,而且?guī)Ыo我們諸多有益的啟示。以極大的熱誠、耐心和寬宥之情對待青年,是魯迅身上難得的品質(zhì)。
1927年9月底,魯迅離開廣州到上海,送行者中有一位青年學(xué)生,叫廖立峨,他曾經(jīng)是廈門大學(xué)的學(xué)生,追隨魯迅從廈門轉(zhuǎn)學(xué)到廣州的中山大學(xué)。魯迅到上海后,拿到新出版的散文詩集《野草》,第一本就寄贈給了廖立峨,可見對其看重之情。廖立峨仿佛有情有義,魯迅剛在上海立足兩三個月,這位青年就帶著女友跑到上海投奔魯迅。他自稱,自己因為魯迅離開廣州而無心繼續(xù)上課,所以拋棄一切來到上海,甘心“伺候”魯迅。這位學(xué)生于是就擠進了魯迅在景云里很小的住宅里。吃穿住加零用錢,一律由魯迅負(fù)擔(dān)。
這位廖立峨也真不見外,他甚至要求魯迅出錢供自己的女友上學(xué),又要求魯迅為自己在上海謀個賺錢的職業(yè)。無奈之下,魯迅只好找到自己的朋友——著名作家郁達夫幫忙。他甚至對郁達夫提出,只要能為廖立峨找到個干事的地方,學(xué)習(xí)一點本領(lǐng),每月的薪水可以由自己支付,而不給雇用者添負(fù)擔(dān)。郁達夫很快為其找到一個到書店幫工的工作,每月工資由書店和魯迅各付一半。魯迅那一半交郁達夫轉(zhuǎn)給書店,書店則以薪水名義發(fā)放給廖立峨,并不告訴對方是由魯迅出資。然而,廖立峨在出工當(dāng)天就“炒”了老板,拒絕了這番好意。理由是要做的事太瑣碎,薪水也不足以養(yǎng)活自己和女友。
這位學(xué)生和他的女友,在魯迅家里白吃白住達半年之久,看到魯迅可利用的價值漸小,于是索要了兩個人的盤纏,離開上海回老家去了。更讓人大跌眼鏡的是,從鄰居的問話中,魯迅才知道,廖立峨的女友竟然向周圍的鄰居說,他們是魯迅的兒子兒媳婦,是為了“伺候”魯迅才住在這里的。
魯迅自己講起這位奇葩人物的故事,總是帶著詼諧的微笑,并沒有表示特別的鄙夷和憤怒。面對青年,他總是盡可能以禮相待,不讓對方難堪。
1928年3月的一天,魯迅收到一位并不認(rèn)識的姓馬的女子來信,說與魯迅自1月10日在杭州孤山分別后,很久沒見面了,希望魯迅能答應(yīng)與她保持通信并接受拜訪。這讓魯迅一頭霧水,趕緊回信說,自己一直住在上海,已經(jīng)有十年沒有到過杭州了,你所見到的一定是另一人。那女子于是邀請了兩個熟人去訪問魯迅,才知道果然與之前見到的并非同一人。但她拿出了一首詩,說是在杭州蘇曼殊墓旁看見的一首魯迅題詩。詩曰:“我來君寂居,喚醒誰氏魂?飄萍山林跡,待到它年隨公去。魯迅游杭吊老友曼殊句。”魯迅于是請青年友人許欽文和川島去調(diào)查事情的究竟。二人很快就獲知,這個自稱魯迅的人,在一個鄉(xiāng)村小學(xué)教書,于是他們就跑到這個鄉(xiāng)村里的小學(xué)校,見到了這位假魯迅。那人一聽是兩位慕名而來的青年,于是很得意地說:“我是周作人,就是魯迅。”許欽文和川島心里說,連周樹人和周作人都分不清楚,還敢自稱是魯迅。而那位假魯迅卻完全進入角色,用很高的聲音說:“我寫的《彷徨》已經(jīng)印了8萬本,一出版就賣完了,但是我自己不滿意,要另外寫來。”
許欽文和川島把觀察到的情形寫信告訴了魯迅,他們很想知道,魯迅會怎樣揭批這個冒充自己名字行騙的人。結(jié)果,魯迅只是希望管理那個小學(xué)校的機關(guān),讓那位假魯迅以后不要再這樣做就可以了,并沒有懲罰的要求。當(dāng)然,為了澄清一些基本事實,魯迅還是發(fā)表了一篇聲明文章,標(biāo)題叫作《在上海的魯迅啟示》。文章對這位假魯迅并沒有大加痛斥,而是不失幽默,也略帶一點同情地寫道:“我之外,今年至少另外還有一個叫‘魯迅’的在,但那些個‘魯迅’的言動,和我也曾印過一本《彷徨》而沒有銷到八萬本的魯迅無干。”
都說魯迅對待論敵是“一個都不寬恕”,為什么對這么一位沒品位的冒名者卻手下留情呢?應(yīng)該說,魯迅一定也猜到了,這位雖是冒名者,倒也并無惡意,大半是生活所迫才至于如此。對這樣的人,魯迅難免要起惻隱之心,得饒人處且饒人。魯迅的寬厚胸懷可見一斑。
魯迅本來出生在一個比較富有的大家庭里,因為祖父下獄的原因家道中落,所以少年時就跌入生活艱辛甚至寄人籬下的境地。他說過,“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也許是從小就經(jīng)歷了很多磨難,面對過太多世俗的眼光,成為中國最著名的作家后,他對世俗的眼光及其態(tài)度,反而并不在意,還不無寬宥之情。
更看重青年認(rèn)真做事的態(tài)度而不是給自己的回報有多少,這也是魯迅青年觀里重要的一點。魯迅的許多作品,如小說集《吶喊》《彷徨》、散文詩集《野草》以及多部雜文集等,都是由一家叫北新書局的出版社負(fù)責(zé)出版印行的。北新書局的老板叫李小峰,可以說,他完全是魯迅扶持、培養(yǎng),并進入出版界不斷取得事業(yè)發(fā)展的。北新書局創(chuàng)辦是在北京,1927年遷到上海。依靠魯迅的資助和魯迅作品的發(fā)行,北新書局的經(jīng)營保持了很好的勢頭。然而,到了上海后,李小峰對商業(yè)利潤更加追求與渴望,甚至有了去投資辦紗廠的想法。于是,開始拖欠魯迅應(yīng)得的版稅。此時魯迅并無固定職業(yè),主要靠版稅和稿費生活。盡管魯迅多次催促詢問,李小峰要么避而不見,要么找各種理由拖欠。
這一過程中,魯迅認(rèn)識了一位叫張友松的青年,張友松自己辦了一個春潮書局,創(chuàng)辦了一份《春潮》雜志,很希望得到魯迅支持。交往中,張友松知道北新書局拖欠魯迅版稅一事,就托朋友找到一位律師幫助魯迅打官司。經(jīng)過一場訴訟,魯迅討回了公道,維護了權(quán)益。
事情得到解決后,有一次,李小峰邀請魯迅和許廣平吃飯,同席參加的還有著名作家郁達夫夫婦以及林語堂夫婦。席間,李小峰因為官司一事對張友松頗有怨恨之言,認(rèn)為張友松是想從他這里把魯迅作品的出版權(quán)搶走。林語堂可能因為并不知事情真正的原委,附和李小峰表達了對張友松的不滿。這時也是酒過三巡之際,大家都有點微醺的意思,話題又如此敏感,情緒都比較激動。魯迅認(rèn)為林語堂隨意責(zé)備一個不在場的人,而且話中還含有諷刺自己的味道,于是臉色鐵青,從座位上突然站起來,大聲說道:“我要聲明!我要聲明!”林語堂當(dāng)然也要聲辯自己并無惡意,兩人針鋒相對地爭辯起來,場面十分緊張。幸虧還有二人都很信任的共同朋友郁達夫在場,郁達夫趕緊起身調(diào)停,一面按住魯迅,一面拉著林語堂離席,事情才算結(jié)束。
其實,魯迅從內(nèi)心對李小峰始終保持著基本信任,即使面對拖欠版稅的情形,依然繼續(xù)把自己的作品交給北新書局出版。魯迅凡事都有自己的判斷。“我到上海后,看看各出版店,大抵是營利第一。小峰卻還有點傻氣。前兩三年,別家不肯出版的書,我一紹介,他便付印,這事我至今記得的。雖然我所紹介的作者,現(xiàn)在往往翻臉在罵我,但我仍不能不感激小峰的情面。”(1927年12月26日致章廷謙)不以自己的得失判斷一個人,不以一時一事選擇好惡,這是一種難得的信任,更是一種做人的品格。
在魯迅的心目中,青年就應(yīng)當(dāng)是敢于說出真話、敢于挑戰(zhàn)傳統(tǒng)和權(quán)威、敢于拋棄誘人光環(huán)的人。“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fā)表出來。”(《無聲的中國》)為了這樣的“真”,魯迅從不計較他們因此做出的選擇是否周全,是否“合乎情理”。只要是敢于前行的青年,即使他們身上有初出茅廬的幼稚,但仍然讓人看到未來的希望,所以他對這幼稚不但可以原諒,甚至認(rèn)為是青年區(qū)別于老年的標(biāo)志。
在魯迅看來,青年應(yīng)當(dāng)走自己的路。只有那些敢于照著自己確定的目標(biāo)勇往直前的青年,才能在血氣方剛中見出真性情。正是從這一角度出發(fā),魯迅眼里的青年和年齡無關(guān),并不是年紀(jì)輕的人都可以統(tǒng)稱為“青年”。“近來很通行說青年;開口青年,閉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論?有醒著的,有睡著的,有昏著的,有躺著的,有玩著的,此外還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進的。”在這些類別里,魯迅只欣賞那些勇于前進的青年。
魯迅對青年的關(guān)心支持,體現(xiàn)在鼓勵他們勇敢地前行,同時又反對青年無謂地犧牲。他當(dāng)然看重文學(xué)青年的才華,但更欣賞那些擁有誠實、踏實品質(zhì),默默耕耘與付出的青年。在著名的《為了忘卻的記念》一文中,他指出了柔石身上最難得的,是“無論從舊道德,從新道德,只要是損己利人的,他就挑選上,自己背起來”。而對同是“左聯(lián)”五烈士之一的柔石的女友馮鏗,卻“疑心她有點羅曼諦克,急于事功”。聯(lián)想到在獄中受難的青年,他在嚴(yán)冬的深夜里遙想:“天氣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們是有的。”聽到這些青春的生命被無情屠殺,內(nèi)心充滿了難以抑制的悲憤。“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是的,他注重青年身上金子般閃光的品格,同時又把他們看作是有血有肉的常人,特別關(guān)心他們生前身后的親情。年輕時的朋友范愛農(nóng)死了,魯迅仍然記得,“他死后一無所有,遺下一個幼女和他的夫人”。并且在14年之后仍然掛念著,“現(xiàn)在不知他唯一的女兒景況如何?倘在上學(xué),中學(xué)已該畢業(yè)了罷”。面對病痛中的韋素園,悲哀的緣由就包括“想到他的愛人,已由他同意之后,和別人訂了婚”。這是何等的凄涼。想到柔石還有一位深愛他的雙目失明的母親,魯迅更是難掩悲傷之情,“我知道這失明的母親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為了紀(jì)念柔石,也為了能撫慰一位一直不知道愛子已經(jīng)被殺害的雙目失明的母親,魯迅選擇了一幅珂勒惠支的木刻作品,發(fā)表在《北斗》創(chuàng)刊號上。這幅木刻名為《犧牲》,內(nèi)容是“一個母親悲哀地獻出了她的兒子”。魯迅說,這是“只有我一個人心里知道”的一種對亡友的紀(jì)念。
這就是魯迅,他傳遞著的哀傷、悲憤、友愛和溫暖,他表達出的坦直、率真以及對死者的懷念、對生者的牽掛,怎能是一個“忘卻”可以了得?直到1936年,魯迅為已經(jīng)就義5年的白莽(殷夫)詩集《孩兒塔》作序,說“他的年青的相貌就又在我的眼前出現(xiàn),像活著一樣”。更確切地說,感受過魯迅對亡者的那樣一種深重、親切、無私、博大的愛意,那“忘卻”二字,又含著怎樣的復(fù)雜、深厚的內(nèi)涵!一種無奈之后的奢望?一種無力感的表達?可以說,在不同的讀者那里,會激起不同的心靈感應(yīng)。
魯迅對青年有教誨,但他時常提醒青年,切不可將自己作為榜樣甚至偶像對待。魯迅有自我解剖的自覺,他非常擔(dān)心自己看穿一切后的沉穩(wěn)太過感染有為的青年。“所以,我終于不想勸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們的年齡,境遇,都不相同,思想的歸宿大概總不能一致的罷。”(《北京通信》)他真心希望青年們對人生有一個更加明確、長遠的目標(biāo)。“但倘若一定要問我青年應(yīng)當(dāng)向怎樣的目標(biāo),那么,我只可以說出我為別人設(shè)計的話,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fā)展。”(《北京通信》)
魯迅對青年的態(tài)度因此有時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看到青年充滿熱血和激情、不顧個人安危的勇猛;另一方面,又非常害怕青年因為這份勇猛而犧牲;同時,他懷著美好的愿望,愿有為的、正直的青年,能夠保證“生存”、越過“溫飽”、求得“發(fā)展”。這也就是魯迅為什么時常要對青年發(fā)出自己的意見和看法,同時又擔(dān)心自己的言論、心情影響了青年進取的步伐。
在青年心目中,魯迅是長者,是導(dǎo)師,但魯迅自己從不以這樣的身份和姿態(tài)自許。他總是以滿懷熱誠關(guān)心青年成長,真心為他們的每一點進步高興,對想做事又有實際困難的青年,總是給予無私的幫助和切實的扶助,他希望他們勇猛,又不主張他們冒進甚至無謂地犧牲,為了青年能做成事,他可以寬宥他們在過程中的失誤、錯誤,包括對自己的不義之舉。這是一種寬廣的胸懷,是一種博大的境界。當(dāng)代青年,可以從魯迅身上感受到前進的力量。而更多的人應(yīng)該從魯迅身上讀懂關(guān)愛、奉獻、大度的風(fēng)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