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卷本《嚴(yán)家炎全集》新近出版—— 嚴(yán)家炎先生的“嚴(yán)加嚴(yán)” ——學(xué)科領(lǐng)軍 堅(jiān)守求實(shí)
嚴(yán)家炎先生,歷任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主任、國務(wù)院學(xué)位委員會語言文學(xué)學(xué)科評議組成員、北京市文聯(lián)副主席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學(xué)會會長等職務(wù),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領(lǐng)域的學(xué)術(shù)泰斗、第二代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學(xué)者的代表人物。嚴(yán)先生1933年出生于上海寶山,1950年考入華東人民革命大學(xué),1956年進(jìn)入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為副博士研究生,1958年肄業(yè),留校任教,從此開始了超過一個(gè)甲子的學(xué)術(shù)與教育生涯。在中國現(xiàn)代小說研究、“五四”文學(xué)思想研究、魯迅研究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編纂等方面,嚴(yán)先生都做出了突出貢獻(xiàn),推進(jìn)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學(xué)科的成熟。
日前,收錄了嚴(yán)家炎先生畢生學(xué)術(shù)精華的《嚴(yán)家炎全集》(十卷本)由新星出版社出版。這是嚴(yán)先生首次系統(tǒng)整理自己的學(xué)術(shù)著作,也是他對于自己一生學(xué)術(shù)思想的鄭重總結(jié)。本版特約錢理群、陳平原與李今三位學(xué)者撰文,評述嚴(yán)家炎先生的學(xué)術(shù)思想與學(xué)術(shù)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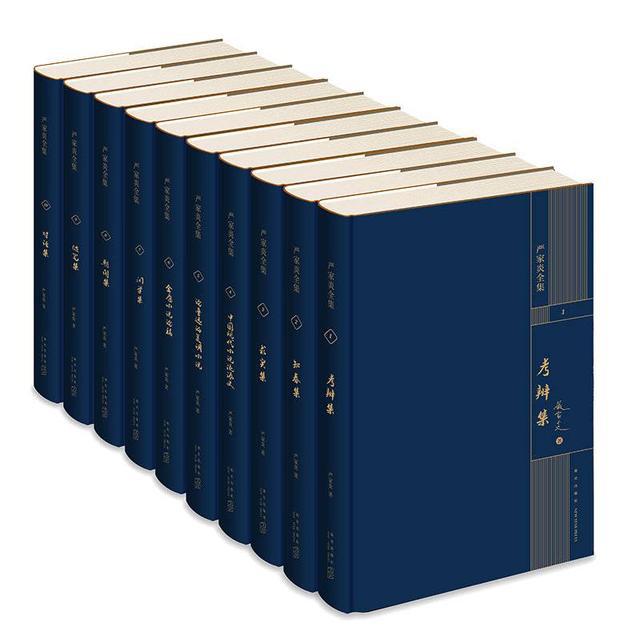
十卷本《嚴(yán)家炎全集》
嚴(yán)家炎先生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學(xué)科
◎錢理群(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教授)
我想談?wù)剣?yán)家炎先生的學(xué)術(shù)思想,在我們學(xué)科建設(shè)上所起到的作用。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三篇文章,對現(xiàn)代研究界影響也最大。
我在《我們所走過的道路》一文里,談到上世紀(jì)八十年代初學(xué)科重建時(shí)有幾篇指導(dǎo)性的文章,一篇是王瑤先生的《關(guān)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工作的隨想》,確立了學(xué)科“既是文藝科學(xué),又是歷史科學(xué)”的“質(zhì)的規(guī)定性”;樂黛云先生的《了解世界文學(xué)研究發(fā)展?fàn)顩r,提高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水平》,打開了學(xué)科發(fā)展與世界聯(lián)系的通道;而嚴(yán)家炎先生的《從歷史實(shí)際出發(fā),還事物本來面目》,則完成了學(xué)科“歷史品格”的重建。嚴(yán)先生在文章里,用大量的事實(shí),說明“隨意修改歷史,隱瞞事實(shí)真相的不科學(xué)、反科學(xué)的做法”,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歷史科學(xué)本身的信用危機(jī)。因此,大聲疾呼要“敢于說真話,敢于如實(shí)反映歷史”,強(qiáng)調(diào)“只有真正實(shí)事求是,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也才有可能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xué)”,“只有從歷史實(shí)際出發(fā),弄清基本史實(shí),尊重基本史實(shí),把認(rèn)識統(tǒng)一到作品和史料的基礎(chǔ)上,這樣總結(jié)出來的經(jīng)驗(yàn)和規(guī)律,才比較牢靠,比較扎實(shí),也才有助于我們較好地轉(zhuǎn)變學(xué)風(fēng)”。這里所說的“以接觸原始材料作為研究起點(diǎn),強(qiáng)調(diào)從史實(shí)出發(fā),堅(jiān)持實(shí)事求是的原則和學(xué)風(fēng)”,不僅是嚴(yán)家炎先生此后幾十年一以貫之的基本學(xué)術(shù)思想、作風(fēng),而且也是許多學(xué)術(shù)前輩共同倡導(dǎo)與身體力行的,深刻地影響了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界,形成了一個(gè)傳統(tǒng)。嚴(yán)家炎先生正是這一傳統(tǒng)最有力的開創(chuàng)者和堅(jiān)守者之一。
嚴(yán)家炎先生第二篇影響深遠(yuǎn)的文章是《走出百慕大三角區(qū)——談二十世紀(jì)文藝批評的一點(diǎn)教訓(xùn)》,此文寫于1988年12月。嚴(yán)先生認(rèn)為,“五四”以來,中國的文藝批評、學(xué)術(shù)研究,也有這樣的危險(xiǎn)區(qū),他稱為“異元批評”,又稱“跨元批評”,“在不同質(zhì)、不同‘元’的文學(xué)作品之間,硬要用某‘元’做固定不變的標(biāo)準(zhǔn)去評判,從而否定一批可能相當(dāng)出色的作品的存在價(jià)值”。比如用現(xiàn)實(shí)主義標(biāo)準(zhǔn)衡量現(xiàn)代主義、浪漫主義的作品,反過來用現(xiàn)代主義標(biāo)準(zhǔn)衡量現(xiàn)實(shí)主義、浪漫主義作品,等等。嚴(yán)先生針對這樣的認(rèn)識誤區(qū),做出了一個(gè)重要判斷:“二十世紀(jì)文學(xué)的一個(gè)根本特征,就是多元并存”。話雖一句,卻確立了嚴(yán)家炎先生的基本學(xué)術(shù)觀點(diǎn)、學(xué)術(shù)立場、態(tài)度和方法,即以揭示現(xiàn)代文學(xué)“多元并存”的歷史復(fù)雜性和豐富性為己任,以開闊的視野,寬容的態(tài)度,看待現(xiàn)代文學(xué)的不同追求的作家與流派,并以多元的、變動(dòng)發(fā)展的標(biāo)準(zhǔn)去衡量不同質(zhì)、不同“元”的文學(xué)作品。嚴(yán)家炎先生的這一“多元并存”的文學(xué)史觀念和方法論,對學(xué)科的發(fā)展起了很大的推動(dòng)作用,成為文學(xué)流派研究和通俗文學(xué)研究的理論依據(jù)和基礎(chǔ)。他自己也是這兩個(gè)領(lǐng)域重要的開拓者。他對茅盾、吳組緗、沙汀等的“社會剖析的現(xiàn)實(shí)主義”,路翎等的“體驗(yàn)的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概括、命名,被廣泛接受,幾成定論。他對新感覺派和金庸的研究,都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意義。而他對魯迅創(chuàng)作方法多元性的揭示,“復(fù)調(diào)小說”的概括,也都是魯迅研究的重要收獲。這里所說的小說流派研究、金庸研究、魯迅研究,再加上對丁玲的研究,就構(gòu)成了嚴(yán)家炎先生在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的具體領(lǐng)域的四大貢獻(xiàn)。當(dāng)然,嚴(yán)家炎先生的主要貢獻(xiàn),還是他五十年一貫的對現(xiàn)代文學(xué)史的研究與寫作,以及對整個(gè)學(xué)科的推動(dòng)。
還要特別指出的,嚴(yán)家炎先生的這些研究,在學(xué)術(shù)界也有過不同意見,曾經(jīng)引發(fā)過一些爭論,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關(guān)于金庸的論爭,關(guān)于七月派小說的論爭。在論爭中,嚴(yán)家炎先生都堅(jiān)持用事實(shí)說話,據(jù)理力爭,其基本立場就是要維護(hù)文學(xué)的多元并存和文學(xué)研究、批評的多元性。在這樣的原則問題上,嚴(yán)先生是態(tài)度鮮明、堅(jiān)定,絕不含糊的,這和他在學(xué)術(shù)上的寬容是相輔相成的,在學(xué)術(shù)界也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
在關(guān)于“五四”新文學(xué)的評價(jià)的論爭中,嚴(yán)家炎先生發(fā)表了《不怕顛覆,只怕誤讀》一文(載《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叢刊》1997年1 期),文章不長,卻有重要的意義。嚴(yán)先生認(rèn)為,“反對‘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和文學(xué)革命的意見,自來就有。新儒學(xué)、后現(xiàn)代之類的顛覆,也不必多慮。值得注意的,我以為倒是對‘五四’的誤讀。把‘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說成是‘歐洲中心論的產(chǎn)物’;責(zé)備‘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全盤反傳統(tǒng)’,造成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斷裂,都是不符合史實(shí)的誤讀。對‘五四’反對派的意見,也要防止和警惕誤讀,并非一講‘五四’毛病就是‘顛覆’”。他的態(tài)度是:“我們贊美‘五四’,繼承‘五四’,又超越‘五四’”。“不怕顛覆”,表現(xiàn)了嚴(yán)先生的開闊心態(tài),在他看來,歷史與現(xiàn)實(shí)的一切,當(dāng)然也包括“五四”,都是可以批評的;“只怕誤讀”,是他一貫的從事實(shí)出發(fā)的態(tài)度,對建立在誤讀基礎(chǔ)上的批評,是要論爭、辯駁的,其所依據(jù)的,依然是事實(shí)。因此,嚴(yán)先生近年研究工作的一個(gè)重要方面,是對“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一些引起爭議的重大問題的重新考釋,寫了一些很有分量的文章。
而“繼承‘五四’,超越‘五四’”,則為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者在面臨新的挑戰(zhàn)時(shí)所應(yīng)有的態(tài)度提出了一個(gè)原則:一方面,要堅(jiān)守學(xué)科的基本立場,維護(hù)和繼承“五四”新文化傳統(tǒng);另一方面,又不要將其凝固化,不回避所存在的問題,要有新的發(fā)展和超越,這樣就可以使學(xué)科的發(fā)展,保持一種開放的態(tài)勢。在我看來,嚴(yán)家炎先生所提出的這一“既堅(jiān)守,又開放”的原則,對現(xiàn)代文學(xué)學(xué)科的健康發(fā)展,是具有長遠(yuǎn)的指導(dǎo)意義的。
應(yīng)該說,嚴(yán)家炎先生有三大學(xué)術(shù)思想:堅(jiān)持從史料出發(fā)的實(shí)事求是的原則與學(xué)風(fēng);多元共生的文學(xué)史觀和方法論;繼承、堅(jiān)守“五四”,又超越“五四”的基本立場。嚴(yán)家炎先生有一個(gè)評價(jià),他說,我們現(xiàn)代文學(xué)這門學(xué)科,發(fā)展路子比較正,學(xué)風(fēng)也比較正。這大概是包括我在內(nèi)的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者,對這學(xué)科、學(xué)界總有一種依戀心態(tài)的原因所在吧。這樣的學(xué)術(shù)正氣,是由學(xué)科開創(chuàng)者的第一代學(xué)人,王瑤、唐弢、李何林、賈植芳、田仲濟(jì)、陳瘦竹、錢谷融……諸位先生奠定的,又經(jīng)過以嚴(yán)家炎、樊駿先生為代表的第二代學(xué)人的培植與堅(jiān)守,已經(jīng)形成一個(gè)傳統(tǒng)。

嚴(yán)家炎與《嚴(yán)家炎全集》 供圖/盧曉蓉
引領(lǐng)風(fēng)騷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流派史》
◎陳平原(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教授)
最能體現(xiàn)嚴(yán)家炎作為文學(xué)史家的功力及見識的,無疑是《中國現(xiàn)代小說流派史》。學(xué)界普遍將其視為嚴(yán)家炎先生的代表作。
關(guān)于思潮流派研究,北大中文系教授們可謂引領(lǐng)風(fēng)騷。除了嚴(yán)家炎1989年推出《中國現(xiàn)代小說流派史》(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還有孫玉石的《中國初期象征派詩歌研究》(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83)、《中國現(xiàn)代主義詩潮史論》(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3),以及孫慶升的《中國現(xiàn)代戲劇思潮史》(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4)。當(dāng)然,這幾部思潮流派史著述中,嚴(yán)書影響最大。
關(guān)于此書的寫作過程,嚴(yán)家炎在“后記”中有清晰的交代。1982和1983年曾在北大中文系講授專題課,聽講者包括高年級本科生、研究生以及進(jìn)修教師。每次開講,近十臺錄音機(jī)同時(shí)啟動(dòng),講課內(nèi)容傳播甚廣,部分觀點(diǎn)被他人的文學(xué)史、小說史著作所吸納,講者于是下決心整理成書。“這是根據(jù)我的講稿整理、補(bǔ)充、修訂而成的一部著作”,而成書的關(guān)鍵是1986—1987年出任斯坦福大學(xué)東亞研究中心訪問教授,這才使得“六十年代以來的一點(diǎn)愿望和追求即將實(shí)現(xiàn)”。除了長期研究的結(jié)晶,制約本書寫作的,主要是北大課堂聽眾以及美國校園文化。后者不僅提供了整理的時(shí)間與心境,也包括若干思路的調(diào)整。
在考察大量第一手資料的基礎(chǔ)上,鉤沉和總結(jié)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的小說家群落,開創(chuàng)新時(shí)期以來中國現(xiàn)代小說流派史研究的新格局,這一披荊斬棘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逸興遄飛的北大課堂與正式刊行的專門著作之間,還有選編《新感覺派小說選》(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5)、《中國現(xiàn)代各流派小說選》四冊(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86),以及出版《論現(xiàn)代小說與文藝思潮》(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1983年秋,嚴(yán)家炎應(yīng)上海《小說界》之邀,連續(xù)撰寫并刊出五篇“中國現(xiàn)代小說流派論”,從“五四”時(shí)期的“問題小說”一直說到上世紀(jì)三十年代的現(xiàn)代派小說。至于全書打頭的綜論性質(zhì)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流派史漫筆》《中國現(xiàn)代小說流派鳥瞰》,也都是北大課堂的產(chǎn)物。相對于日后一錘定音的專著,這些陸續(xù)刊出的論文,同樣認(rèn)準(zhǔn)“現(xiàn)實(shí)主義、浪漫主義、現(xiàn)代主義這三種思潮、三條線索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相互扭結(jié)、相互對抗,同時(shí)又相互滲透、相互組合,這就構(gòu)成了現(xiàn)代小說流派變遷的重要內(nèi)容”,只是在具體流派的確認(rèn)與劃分上不盡一致。
中國現(xiàn)代小說流派的研究,并不自嚴(yán)家炎始;但《中國現(xiàn)代小說流派史》首次發(fā)掘了新感覺派、社會剖析派、七月派、后期浪漫派等小說流派,引發(fā)后來相關(guān)流派的研究熱潮,有很大功績。其中,第七章“七月派小說”很有特點(diǎn),第八章“后期浪漫派小說”不太成立,最為人稱道的,還是第四、第五章。
第四章“新感覺派和心理分析小說”如此開門見山:“稍晚于太陽社、后期創(chuàng)造社的‘革命小說’,二十年代末期和三十年代初期,中國文壇上出現(xiàn)了一個(gè)以劉吶鷗、穆時(shí)英、施蟄存、葉靈鳳為代表的新的小說流派——新感覺派。這是中國第一個(gè)現(xiàn)代主義小說流派。”此前學(xué)界或因立場限制對其視而不見,或以為不過是日本新感覺派的拙劣模仿,基本持否定態(tài)度。嚴(yán)家炎借為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編《新感覺派小說選》之機(jī),認(rèn)真梳理了橫光利一、川端康成等的理論主張及其對中國作家的影響,還有劉吶鷗等上海作家如何借助《無軌電車》《新文藝》《現(xiàn)代》等雜志,嘗試將日本新感覺派初期主張的新感覺主義與后期提倡的新心理主義結(jié)合起來,最終闖出自己的道路,成為“中國現(xiàn)代都市文學(xué)開拓者中的重要一支”。第四章的內(nèi)容主要根據(jù)作者的《論新感覺派小說——<新感覺派小說選>前言》一文改寫,主要差別在于增加了第五節(jié)“心理分析小說的發(fā)展和張愛玲的出現(xiàn)”。從思潮流派轉(zhuǎn)到了創(chuàng)作手法,拉進(jìn)了那時(shí)在海外影響極大而大陸尚未認(rèn)真關(guān)注的張愛玲,看得出作者的“趨新”。好在作者最終還是守住了邊界,沒有更多離題的發(fā)揮,只是引證張愛玲《流言·寫什么》中談初學(xué)寫文章,借鑒各種資源及文體,其中包括新感覺派:“可見,說張愛玲曾得益于新感覺派,大概是可以的。但自然,不能據(jù)此簡單地把她當(dāng)作新感覺派作家。”
相對來說,第五章“社會剖析派小說”最能顯示史家嚴(yán)家炎的立場、趣味與功力。第一節(jié)“《子夜》的出現(xiàn)和社會剖析派的形成”、第二節(jié)“小說家的藝術(shù),社會科學(xué)家的氣質(zhì)”、第三節(jié)“橫斷面的結(jié)構(gòu),客觀化的描述”、第四節(jié)“復(fù)雜化的性格,悲劇性的命運(yùn)”,單看各節(jié)標(biāo)題,就能大致把握此章要義。其中第二節(jié)最有創(chuàng)意,日后左翼文化研究崛起,社會科學(xué)在三十年代中國的流播與影響日益凸顯,此類小說的研究得以深入展開。可惜受制于體制及篇幅,當(dāng)初嚴(yán)家炎只是點(diǎn)到為止。
“幾乎是在新感覺派的都市文學(xué)和心理分析小說獲得發(fā)展的同時(shí),以《子夜》為代表的另一種路子的都市文學(xué)也應(yīng)運(yùn)而生了。《子夜》的出現(xiàn)還帶來了社會剖析派小說的崛起。這樣,在三十年代,新感覺派的都市文學(xué)與左翼作家的都市文學(xué),心理分析小說與社會剖析小說,這兩類作品就互相映襯,互相競爭,并在某種范圍內(nèi)互相影響,互相滲透。”這段話很能顯示嚴(yán)家炎的特點(diǎn)——站位較高,概括力強(qiáng),簡明扼要,用詞準(zhǔn)確,不慍不火。這是長期編寫教材鍛煉出來的本事,得益于作者閱讀量大,眼界開闊,有明顯的自家立場,但照顧到方方面面,說話不會太偏頗,聲音也不會太尖銳。
日后嚴(yán)家炎出版《中國現(xiàn)代小說流派史》(1989),李歐梵則撰寫名著《上海摩登:一種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英文版1999年由哈佛大學(xué)出版社推出,中譯本2001年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刊行)。單看書名,一談“小說流派”,一講“都市文化”,各自的側(cè)重點(diǎn)及理論資源明顯不同。更何況,教材必須面面俱到,專著不妨千里走單騎。嚴(yán)家炎長期撰寫教科書,養(yǎng)成準(zhǔn)確、清晰的表達(dá)習(xí)慣,全書風(fēng)格大致如此,每章四至五節(jié),每節(jié)若干要點(diǎn),單看精心提煉的章節(jié)標(biāo)題,就能大致了解該書的主要觀點(diǎn),讀者很容易記憶與把握。

1983年嚴(yán)家炎在課堂上講新感覺派小說
嚴(yán)家炎先生的“求實(shí)”精神
◎李今(中國人民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
嚴(yán)家炎先生做學(xué)問主張的是“求實(shí)”,他以《求實(shí)集》作為自己早期論文的集名,一錘定音地宣示了他所追求的學(xué)術(shù)道路。
我體會先生主張的“求實(shí)”起碼有三層意思。其一,言必有據(jù)。記得剛到北大報(bào)到不久,和嚴(yán)老師談起如何做博士論文的話題,他首先教我的就是,“要有證據(jù)”“用證據(jù)說話”。我覺得嚴(yán)老師一下子就把做學(xué)問這層窗戶紙捅破了,論文重在實(shí)證說理。從此也似乎給我戴上了緊箍咒,每當(dāng)我閱讀作品和材料有了感受、想法和觀點(diǎn)都會反過頭去再看,再想,再琢磨這些感受、想法和觀點(diǎn)因何而生,想明白,落實(shí)到支撐的證據(jù)后,論文的框架結(jié)構(gòu)基本就有了。
后來,我告訴嚴(yán)老師為研究海派,想去上海查資料。嚴(yán)老師也就一句話,“穆時(shí)英曾在上海《晨報(bào)》上發(fā)過文章,你可以去找一找”。如果沒有嚴(yán)老師的指點(diǎn),面對歷史文獻(xiàn)的汪洋大海,我很可能會無功而返。有了這個(gè)線索,盡管費(fèi)盡周折,終于還是在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看到了這份發(fā)黃的報(bào)紙,發(fā)現(xiàn)了一批穆時(shí)英及其新感覺派的軼文,并由此帶出其他報(bào)刊,雪球越滾越大,后來嚴(yán)老師和我一起匯編《穆時(shí)英全集》時(shí),統(tǒng)計(jì)有40余萬字。我博士論文《海派小說與現(xiàn)代都市文化》能出些新意,是和這些新發(fā)現(xiàn)的史料分不開的。
這就要說到先生“求實(shí)”的第二層含義,即他一再申明的“實(shí)事求是”精神。對于學(xué)術(shù)研究來說,所謂“實(shí)事”,即回到原始材料之中。這是進(jìn)入研究的第一步,不能將后來的概括及認(rèn)識與歷史事實(shí)相混淆;所謂“求是”,即嚴(yán)老師謹(jǐn)守的一條治學(xué)原則:“憑原始材料立論”,“讓材料本身說話;有一份材料,就說一分話;沒有材料就不說話”。也就是說,你的述史與評判要把握分寸,而不能為嘩眾取寵,過甚其詞,刻意拔高求深。
正因?yàn)橄壬回灡种皩?shí)事求是”“憑原始材料立論”的求實(shí)精神,其學(xué)問做的是實(shí)學(xué),其觀點(diǎn)才中肯可靠,往往成為不刊之論。如1981年老師在《文學(xué)評論》第5期上發(fā)表文章,對魯迅小說的歷史地位所作出的評價(jià):“中國現(xiàn)代小說在魯迅手中開始,在魯迅手中成熟。”這是多么簡潔而樸素的文字,又多么精準(zhǔn)而到位,真可謂評論中的絕頂。如今幾十年過去了,仍然不可改易,歷久彌新。
然而,這些樸素至簡的經(jīng)驗(yàn),都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先生的“求實(shí)”精神中同樣不可或缺的第三層意思,即他信守不怠,知行合一的踐行。我現(xiàn)在體會,嚴(yán)老師的“嚴(yán)加嚴(yán)”根本是對自己的“嚴(yán)加嚴(yán)”。
先生的學(xué)問與學(xué)識就建立在盡量“求全”閱讀的案頭準(zhǔn)備與深思熟慮上。對于我們這個(gè)產(chǎn)生自報(bào)刊時(shí)代的專業(yè)來說,雖說“求全”不可能做到,但先生堅(jiān)信“最終決定成果質(zhì)量的,是作者占有相關(guān)原始資料是否充分”。他的典范之作《中國現(xiàn)代小說流派史》用了八年的時(shí)間才問梓,如果再加上醞釀的時(shí)間,平均每年不過寫兩萬多字。通過廣泛的閱讀和琢磨,先生才能精準(zhǔn)地為初期鄉(xiāng)土派、“革命小說”派、社會剖析派、后期浪漫派命名,恰切地概括出各流派的特征,而成為定見,被廣泛襲用。其間所花費(fèi)的看不見的功夫,從先生說“有好幾章寫完時(shí)都讓我覺得仿佛脫了一層皮”的感嘆中,掂量出一二。
(本版由北京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講師李浴洋協(xié)助策劃,得到了盧曉蓉女士、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高遠(yuǎn)東教授的幫助,謹(jǐn)致謝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