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長的一天與倏忽的百年 | 從《尤利西斯》的譯介看文化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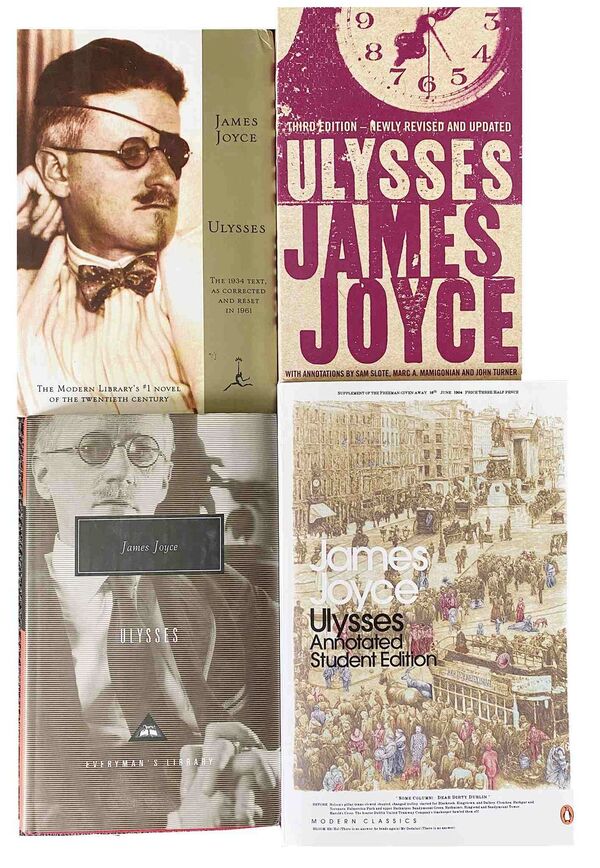
1922年,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的小說《尤利西斯》出版,講述了1904年6月16日早上8點到次日凌晨2點發(fā)生在都柏林的故事。6月16日也是詹姆斯·喬伊斯與妻子諾拉相識的日子。這部經典的意識流小說在當時就影響了我國作家的創(chuàng)作,在新時期更是形成了創(chuàng)作潮流。
在推出的《尤利西斯》中譯本中,有金隄的選譯本和全譯本、蕭乾和文潔若的多個修訂本、劉象愚的節(jié)選本和全譯本。人們從譯者對譯本的修訂和不同譯者譯本之間的比較中可以看到,隨著文化交流的深入,翻譯家根據(jù)不同的原則,對語言、寫作技巧等進行不同的處理,尤其是譯者對誤讀的消除。當然,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頻繁、深入的背景下,誤讀、誤譯等現(xiàn)象依然會存在,但通過各種修訂,人們會看到文化交流的障礙被進一步清除。
詹姆斯·喬伊斯的貢獻
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在1884年首先使用了“意識流”這個術語,后來柏格森、弗洛伊德等理論家的觀點對這一心理學術語進入文學領域產生重大影響。20世紀末,小說對世界摹寫殆盡,尤其是自然主義小說對世界的描寫已經細致入微,人們無法探知今后的路怎么走。這時,意識流小說出現(xiàn)了,改變了西方傳統(tǒng)小說注重敘寫事件、刻畫人物的寫作手法,實現(xiàn)了“向內轉”,在意識流小說中,作家不會把人物的行為和意識直接對讀者進行說明,而是改由人物自身來傳達感受。用詹姆斯·喬伊斯的話來說,就是:“一個藝術家,和創(chuàng)造萬物的上帝一樣,永遠停留在他的藝術作品之內或之后或之外,人們看不見他,他已使自己升華而失去了存在,毫不在意,在一旁修剪著自己的指甲。”這種新的審美模式淡化情節(jié)、注重心理分析,小說家杜夏丹的《月桂樹被砍掉了》被認為開了先河。
跟以往的文學作品相比,意識流小說展現(xiàn)了思緒的飄忽不定,更符合人們平時的真實狀況,學者羅伯特·漢弗萊認為:“意識流小說家同自然主義小說家一樣,都力圖準確地描寫生活;但他們又不同于自然主義小說家,他們所描寫的生活是個人的精神生活。”對讀者來說,則提高了進行閱讀理解的門檻,因為意識流的自由聯(lián)想絕不是胡思亂想,讀者不能憑主觀臆測來揣度作者的意圖,而是要基于小說中的情境、意象的類似、英語單詞的結構特點等來補充思維跳躍時的空白。當因果斷裂,流淌的就是想象,那么,意識流說的是誰的意識在流動?讀者的填補可能一次未必成功,而詹姆斯·喬伊斯有時還會有心地把答案放到幾百頁之后。意識流小說并未在思緒的跳躍中失控,哪怕《尤利西斯》第18章中莫莉的夢,前后文其實都是關聯(lián)的,體現(xiàn)了外部世界對意識的影響。其實后來出現(xiàn)的自動寫作作品也并不是一氣呵成的,哪怕是凱魯亞克的作品也進行了多次修改。
詹姆斯·喬伊斯的貢獻主要體現(xiàn)在兩方面,一是結構上與經典作品的對話。尤利西斯是荷馬史詩《奧德賽》主人公奧德修斯的拉丁語名字。《奧德賽》共24卷,主要寫的是聰明、勇敢的奧德修斯的歷險,可大致分為三部分:忒勒馬科斯外出打聽父親奧德修斯的消息;奧德修斯歷盡艱險回到家鄉(xiāng);奧德修斯跟妻子裴奈羅佩相認,殺死求婚者。《尤利西斯》18章分為三部分:斯蒂芬尋找精神上的父親;布魯姆在都柏林的游蕩;布魯姆帶斯蒂芬回家,在莫莉漫長的夢境中小說結束。作品的主題從回歸變成尋找,基調也從昂揚變成平庸,海上的歷險變成了街上的漫步。起初詹姆斯·喬伊斯用《奧德賽》中的人物、意象等為章節(jié)命名,后來刪掉了。例如《尤利西斯》第6章寫的是布魯姆在墓地對死亡的反思,可以跟《奧德賽》第11卷奧德修斯在冥府遇故人的描寫對照著讀。深層神話結構展現(xiàn)了作品深厚的文化底蘊,讓讀者在不同的時空穿梭,感受對經典作品的不同解讀維度。
其次是語言上的模仿與創(chuàng)造。詹姆斯·喬伊斯的作品給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語言的晦澀,尤其是對語言的創(chuàng)造,但仍基于英語本身,有時模仿以前的文體,有時把很多詞連成一個詞,有時對單詞進行簡單的修改。《尤利西斯》最復雜的一章是第14章,連詹姆斯·喬伊斯都說:“我認為這(第14章)是整個《奧德賽》中難度最大的一章,從闡釋和表現(xiàn)兩方面說都是如此。”第14章原題為《太陽神牛》,詹姆斯·喬伊斯在這章通過英語的發(fā)展演進來象征孩子的誕生過程。詹姆斯·喬伊斯自述,以薩盧斯特—塔西陀文體的引子為開端,然后用最古老的押頭韻的單音節(jié)英語及盎格魯—撒克遜語,然后是曼德維爾口吻,然后是馬洛扎的《亞瑟王之死》,然后是伊麗莎白編年史體,然后是彌爾頓、泰勒、胡克等人的一種莊嚴散文,隨后是一段白頓—布朗的支離破碎的拉丁雜談式文體,接著是班揚式文字,再接著是一些日記題材,佩皮斯—伊夫林式的等,然經過笛福—斯威夫特、斯梯爾—艾迪生—斯特恩,以及蘭多—佩特—紐曼,最后以一種亂七八糟的可怕混合體告終,其中有洋涇浜英語、黑人英語、倫敦土話、愛爾蘭語、紐約鮑厄里俚語以及支離破碎的打油詩。這一章金譯、蕭譯、劉譯都以文言文形式呈現(xiàn),讀者可能看不出行文的變化,但已經是比較用心的處理方式了。
意識流在中國
詹姆斯·喬伊斯改變了很多作家的創(chuàng)作理念和面對經典的態(tài)度。詹姆斯·喬伊斯、普魯斯特、伍爾夫、福克納等意識流作家風格不一,但作品影響深遠,之后在很多作家的小說中會看到意識流的影子,包括中國作家。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作家已經開始了意識流小說的創(chuàng)作,魯迅的《狂人日記》、郁達夫的《沉淪》、穆時英的《街景》等小說中都有意識流的影子。劉以鬯的長篇意識流小說《酒徒》出版于1962年,書中的對話不是用引號,而是遵循詹姆斯·喬伊斯的寫作習慣,用破折號。白先勇發(fā)表于1967年的小說《游園驚夢》,寫錢夫人參加宴會時在熟悉的唱段中追憶過去,白先勇提到:“起初我并沒有想到要用意識流手法,女主角回憶過去時的情緒非常強烈,也有音樂、戲劇背景,為了表達得更好,嘗試用了意識流手法。”白先勇在小說中將中國傳統(tǒng)審美與西方的意識流寫法融為一體,既恰切,又實現(xiàn)了突破。
進入新時期,意識流小說成為較早譯介到中國的西方現(xiàn)代主義小說流派,譯介成果蔚為壯觀,西方代表性作家的作品以及后來有意識流特色的小說都有譯介,我國作家也開始有意識地進行模仿。譯本帶來模仿潮流的原因是很多作家外文基礎薄弱甚至為零,無法閱讀原著,譯作推出后才能一窺原作風貌。茹志鵑的《剪輯錯了的故事》、王蒙的《布禮》、張承志的《綠夜》、莫言的《歡樂》等意識流色彩明顯的小說,要么基于社會對個人的影響、要么基于個人情緒的起落等,是對意識流在中國扎根的探索。
那么,只是套用意識流寫作技巧是不是就能稱之為意識流小說呢?學者瞿世鏡就提出:“中國人并不因為穿了西服就變成西方人。中國現(xiàn)代小說也絕不會因為借鑒了意識流小說的形式技巧而變成意識流小說。”意識流小說是對西方文化傳統(tǒng)、價值觀念的顛覆,在對心靈世界的探索中尋找真實。很多作家模仿詹姆斯·喬伊斯不加標點的寫法,寫了很多“文不加點”的意識流小說,那么我國的古籍都沒有標點符號,算不算意識流呢?用不加標點的行文呈現(xiàn)意識綿延不斷地流淌,形式只是內容的外衣,創(chuàng)新與傳承都需要文化根脈的支撐。

《尤利西斯》的幾個中文版本
1987年8月,學者金隄翻譯的《尤利西斯(選譯)》由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包括第2章、第6章、第10章3個整章和第15章、第18章的片段。金隄翻譯的《尤利西斯(上)》(共12章)于1993年底由臺北九歌出版社出版,又于1994年9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金隄翻譯的《尤利西斯(下)》(共6章)于1996年2月由臺北九歌出版社出版,又于同年3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98年,金隄獲得第一屆魯迅文學獎的全國優(yōu)秀文學翻譯彩虹獎榮譽獎。
金隄的選譯本跟全譯本比有很多變化,全譯本再版時也進行了很多修訂。例如,第2章中的“金斯敦碼頭”,改譯為“國王鎮(zhèn)棧橋”,因為前文提到了棧橋,地名也從音譯變成了意譯;第6章中的“有一個窗簾拉開了一點兒,露出一張老太太的臉”,改譯為“有一個窗簾拉開了一點兒:一位老太太在窺視”,不再突出兩句話的因果關系,呈現(xiàn)而非引導更符合作者的本意;第15章中的“莫推茲而她也真不推辭小姐”,改譯為“杜必達而她也真的肚皮大了小姐”,能從英文的諧音梗譯成中文的諧音梗,可見金隄文字功底之深厚;第15章中的“喊叫起來,但喊聲也聽不清”,改譯為“用聽不清的聲音喊叫起來”,文字更順暢。
1994年4月,學者蕭乾、文潔若翻譯的《尤利西斯(上)》(8章)、《尤利西斯(中)》(7章)由譯林出版社出版,《尤利西斯(下)》(3章)也于同年10月由譯林出版社出版。此后還出了修訂版、最新修訂版,2010年又有修訂。
蕭譯前后改動較多。例如,第1章“輕輕地把這消息透露給她吧”,改譯為“要委婉地向她透露這消息”,“委婉地”比“輕輕地”更準確;第13章把“把世界籠罩在神秘的擁抱中”改譯為“把世界攏在神秘的懷抱中”,“攏”比“籠罩”更有文學氣息,“懷抱”比“擁抱”更準確;第13章“那就是我們……的地方”改譯為“我們在哪兒”,是原文直譯,刪掉了譯者添加的文字;第14章“賜與”修訂為“賜予”,屬于用詞修改;第15章中,初版譯為“骹”在最新修訂版中變成了大黑點,在2010年版則變成了“膠骨”,比較費解。
2004年1月,學者劉象愚編選的《喬伊斯精選集》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其中包括劉象愚翻譯的《尤利西斯(節(jié)選)》10章(全書共18章),包括第1、2、3、4、9、10、11、14、15、18章。2021年6月,劉象愚翻譯的全本《尤利西斯》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
劉象愚的節(jié)選本跟全譯本比,有較多改動。例如,第2章中的“即便不完全像記憶的女兒們編的謊言,那也總有點譜吧”,改譯為“即便不是記憶編造的寓言,那也不是空穴來風吧”,“空穴來風”其實不是完全沒有原因,這里改變了原意;“時間給它們打上了烙印,它們被戴上鐐銬,關進被它們驅逐的無限可能性的空間里”,改譯為“時間給它們打上了烙印,給它們戴上鐐銬,把它們關進被它們逐出的無限可能性的空間里”,把主語統(tǒng)一成了時間;“微弱的眼睛”改譯為“衰弱的眼睛”,對錯誤用詞進行了修改。在第3章,“那幽靈般的女人”改譯為“那已是幽靈的女人”,狀態(tài)發(fā)生了改變;把“別在這兒擺你那副討厭的架子”改譯為“這兒可用不著你那套哩格楞的花架子”,“哩格楞”這種方言俚語確實容易讓人理解;“他看著他和我艱難地爬下階梯”,改譯為“看著他我艱難地爬下階梯(下去!)”,初譯人稱錯亂,比較費解;“你那些書都要送到世界上許多大圖書館,甚至包括亞歷山大嗎?數(shù)千年之后還會有人在那兒讀這些書,大梵天日”,改譯為“抄本都要送到世界上所有的大圖書館,甚至包括亞歷山大城的嗎?數(shù)千年乃至多少億萬年之后還會有人在那兒捧讀這些書”,初譯只稱“亞歷山大”不夠準確,“大梵天日”更難理解,只是要表達時間長而已。第15章中的“舉起癱瘓的左臂”,改譯為“舉起顫抖不止的左臂”,“癱瘓”是無法舉起的,改為“顫抖不止”更準確;“一個一文不名的人”改譯為“一個被剝奪者”,對原文的理解更準確。劉譯把“喝”改為“咂”更傳神,但劉譯“你當過大學生”的譯法本身有問題,蕭譯為“你曾經是個學生”,劉譯為“你那時是大學生”,畢竟學生是沒法“當”的。
譯本之間的比較
譯本修訂體現(xiàn)了認識的深化,不同譯者的譯本之間則可看出理念的不同。
下面以第3章為例,比較一下各位翻譯家的原則。
在第3章中,劉象愚把“白鬃海馬,大口咀嚼著,發(fā)出一片噪聲,駕著生氣勃勃的海風,曼納南的駿馬”,改譯為“白鬃海馬群,套著生機勃勃的風馭轡頭,大聲咀嚼著,曼納南的駿馬”,更加簡潔流暢。金譯為“大群大群抖著白色鬃毛的海馬,嚼著亮晶晶的風馭馬勒,曼納南的戰(zhàn)馬群”。蕭譯為“有如白鬃的海馬,磨著牙齒,被明亮的風套上籠頭,馬南南的駿馬們”。蕭譯為直譯,但駿馬后加“們”并不合適,金譯和劉譯都對原文語序作了調整,金譯還進行了整合,其實還應以傳達作者原意為上。
在第3章中,劉譯“一九○房舍的百葉窗關著,我拉了一下那吱啦作響的門鈴”,改譯為“房子的門窗關著,我拉了一下那喘著粗氣的門鈴”。蕭譯為“我拉了拉他們那座關上百葉窗的茅屋上氣不接下氣的門鈴”,金譯為“我在他們那門窗緊閉的小平房外,拉了一下好像生了哮喘病的門鈴”。劉譯的“一九○房舍”不知出處在哪,蕭譯的“茅屋”有中國特色,也容易給人誤導。
在第3章中,劉象愚把“這些連接以往一切的帶子,把所有的肉體纏結在一起的電纜線……喂,我是金切,請接伊甸園。A001”,改譯為“這些連接以往一代又一代的帶子,由眾生擰成的一條肉纜……喂,我是金切,請接天堂。阿萊夫、阿爾法、○、○、一”,把電話號碼從數(shù)字改成了直譯。蕭譯為:“蕓蕓眾生擰成一股肉纜……喂,喂。我是金赤。請接伊甸城。阿列夫,阿爾法,零,零,一。”金譯為:“人的臍帶全都是連著上代的,天下眾生一條肉纜……喂!我是啃奇。請接伊甸園。甲子零零一號。”蕭譯是直譯,金譯中加入了中國元素“甲子”,確實有想法,但容易讓人出戲。
中文元素的加入確實是個問題,以前很多翻譯家會給小說中的角色加一個中文的姓,如郝思嘉,作家喬治·伯納德·蕭也變成了國人熟知的蕭伯納。在《尤利西斯》中,劉象愚把第1章中的“威嚴的、渾身滾圓的巴克·莫里根從樓梯頂端下來”,改譯為“威嚴、壯碩的雄鹿莫里根從樓梯頂端出來”,從一開始的音譯改為用諢號稱呼莫里根,更能傳達原文的含義。在第5章中,蕭譯為“亨利·弗羅爾先生”,金譯為“亨利·弗臘爾先生”,劉譯為“花亨利先生”,花是布魯姆姓氏的英文意思,漢語里也有花姓,但如果不能讓人感受多重意思,還是保持直譯比較好。第16章中,金譯為“我從來就不是你們那種聰明學生”,蕭譯為“我從來也不是像你們這樣的秀才”,劉譯為“我從來就不是你們那種聰明人”。蕭譯本把“學生”譯成“秀才”,其實二者是不能類比的。
此外,在第1章中,金譯為“他媽媽挺了狗腿兒啦”,劉譯為“他老媽蹬了狗腿啦”,蕭譯則把“他母親死得好慘哪”改譯為“他母親死得叫人惡心”,說“死得好慘”是一種同情的態(tài)度,改譯則更好地傳達了原文的態(tài)度,金譯、劉譯沒有直接表明態(tài)度,而是通過用詞來體現(xiàn)。
在第2章中,金譯為“孩子的茫茫然的臉轉過去問白茫茫的窗戶”,蕭譯為“孩子把茫然的臉掉過去問那扇茫然的窗戶”,劉譯為“那孩子茫然的臉詢問茫然的窗戶”。金譯不帶有主觀色彩,蕭譯、劉譯則都是讓窗子擬人化。同樣是第2章,金譯為“皮洛士到頭來怎么樣”,蕭譯“皮勒斯的結尾怎么樣”,劉譯為“皮洛士到底怎么樣呢”。蕭譯是直譯,但沒能傳達原文的多重含義,金譯和劉譯則考慮到原文的語義雙關了。
在第14章中,劉譯用金文等古文模擬古愛爾蘭語等,并把“煌煌哉,輝輝哉,霍霍恩,賜余胎動邪,賜余子宮之邪”,改譯為“日神邪,光神邪,赫赫恩,賜民胎動邪,賜民子宮之實邪”。金譯為:“燦燦哉,明亮哉,霍霍恩,賜予胎動乎,賜予子宮果實乎。”蕭譯為:“光神啊,日神啊,霍霍恩啊,將那經過胎動期,孕育于子宮之果實賜予我等。”3個譯本都是用文言文翻譯的。
在第16章中,金譯“一種美的語言”,蕭譯和劉譯都是“美麗的語言”,但美麗跟語言搭配還是有問題。在第17章中,劉譯為“涂肥皂時要看報,看報時又涂肥皂,看看涂涂涂涂看,一驚一急有點亂漫不經心思緒飛,剃刀一快割破嘴,趕緊涂上創(chuàng)傷膏,也就只能這么著”,在傳達原文節(jié)奏、韻味方面確實高于蕭譯、金譯。
一日長于百年
當人們認為文學創(chuàng)新的路已經走到盡頭,如何走出新路?面對經典,該如何出新,實現(xiàn)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自1922年,詹姆斯·喬伊斯在《尤利西斯》中講述了1904年6月16日發(fā)生了什么,已過去一百年,這一天已成為愛爾蘭的重要節(jié)日——“布魯姆日”。這一百年里人們一直在思考、解讀那天的事情,還會繼續(xù)走下去。一百年倏忽而過,人們還在探索、消化這漫長的一天的價值所在,后來的作家在重寫經典時,也經常落入詹姆斯·喬伊斯思路的窠臼。或許這就是經典的意義,讓一日長于百年。
在影響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譯本出現(xiàn)、譯本修訂之后,人們還會回到原著。詹姆斯·喬伊斯在寫對話時,習慣用破折號代替引號,而金譯、蕭譯一開始都是用的中文標點,后來的版本中則改用破折號,尊重詹姆斯·喬伊斯的創(chuàng)作習慣,也是對讀者的信任。金隄認為:“‘信、達、神韻’標志譯文的精神實質、傳遞效果、藝術風格這三個方面。我認為我們在翻譯藝術上的追求,就是要爭取在三者兼顧的條件下和原文一致……譯文的流暢易懂也是一種韻味,不能脫離原文而獨立。”
詹姆斯·喬伊斯的偉大之處在于,一生只寫了4部小說,包括《都柏林人》《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尤利西斯》《芬尼根守靈夜》,卻實現(xiàn)了從現(xiàn)實主義到現(xiàn)代主義再到后現(xiàn)代主義的跨越,每部作品都是一個里程碑。《尤利西斯》的每個章節(jié)都運用了不同的寫作手法,例如,第7章的新聞體、第10章的蒙太奇手法、第11章的音樂結構、第17章的問答體、第18章只有兩個句號的長篇內心獨白等。一百年了,人們對《尤利西斯》的印象還停留在難懂的“天書”狀態(tài),再向前跨一步還需要隨時間而來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