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桑的《天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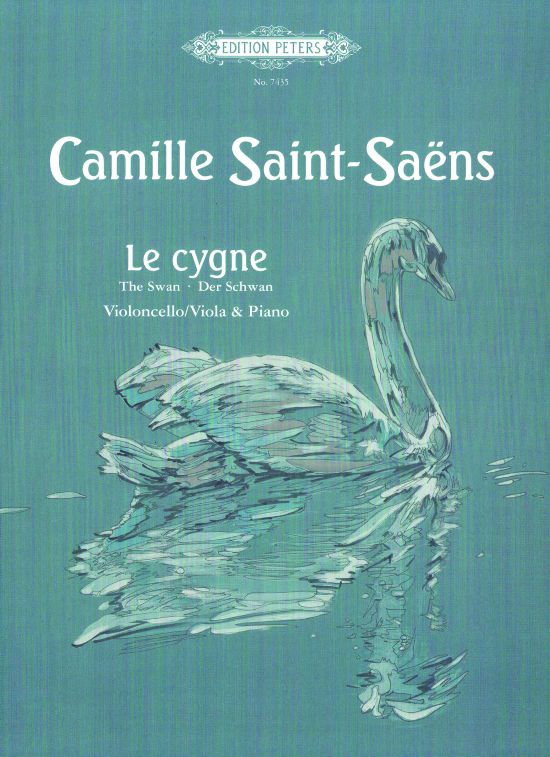
法國音樂界對新冠肺炎疫情下沒能舉行奧涅格和普蘭克等組成的“六人集團”百年祭十分惋惜。可是,巴黎《古典音樂》雜志2021年新年伊始就推出《圣桑百年專號》,開啟“圣桑年”。該刊特邀音樂評論家雅克·波諾赫撰文,全面追述這位音樂家的創(chuàng)作生涯。波諾赫引述圣桑對“音樂往昔、今朝和未來”的預(yù)言:“將會突然出現(xiàn)一種新藝術(shù),讓人難以預(yù)見,無法判斷,就像要讓中國人欣賞貝多芬的交響樂那樣。”(見《和諧與旋律》,卡勒曼-雷維出版社,1895)他見證道:“今天,中國人能聽懂貝多芬的交響樂了,人們自然能夠賞識圣桑和格哲納斯基。”評論者之所以提及格哲納斯基,是因為圣桑與這位希臘血統(tǒng)的法國音樂家一樣,越出了純音樂范圍,還涉獵哲學(xué)、數(shù)學(xué)和建筑學(xué)等多種學(xué)科,是一位藝苑里的博學(xué)家。在圣桑逝世百周年之際,法國國家圖書館和巴黎大歌劇院還分別舉辦展覽,追懷這位音樂家。
在中國,圣桑主要是以他的大提琴獨奏曲《天鵝》(le Cygne)為人所知,而且往往是獨立演播。其實,《天鵝》只是圣桑《動物狂歡節(jié)》(le festival des animaux,1886)里的一支曲子,但它卻是套曲中流行最廣的作品。該曲還被米哈伊爾·福金改編成芭蕾舞《天鵝之死》,由俄羅斯女舞蹈家安娜·巴甫洛娃在臺上獨舞,跳得出神入化,成為芭蕾舞劇目中的一朵艷葩。
《天鵝》曲調(diào)優(yōu)美,聞?wù)咚埔姲子痫h浮粼粼清波,一似銀河里的“天鵝座”在蒼穹曲頸歌吟,展示廣闊宇宙中的生死場。人們也會聯(lián)想到馬拉赫美的詩篇《牧神午后》:
一群天鵝驚飛。
不,那是水仙女們在逃逸,
一個個潛入深水……
德彪西為馬拉赫美譜寫《牧神午后序曲》,色粉畫家馬奈用彩筆幻化出牧神大潘夢醒吹奏蘆葦排簫,仿佛在宣泄自己的情愫:
我為自己的幻聲驕矜,
將長久地描述仙女的神韻。
法語里根據(jù)天鵝死前的哀鳴,得出“天鵝絕唱”(le chant du cygne)一詞,意大利人由此稱《牧歌》的作者,古羅馬拉丁大詩人維吉爾為“曼托瓦的天鵝”。現(xiàn)代“曼托瓦的天鵝”,無疑是《布呂赫的幽靈》一書作者,比利時小說家、詩人喬治·羅登巴克。他留有長篇哀怨抒情詩《天鵝》,描繪天鵝的絕唱:
途中,一聲長鳴
劃破了寂靜的脈絡(luò)。
一似人聲長吟,
聲聲飄向碧落。
那是一只最美麗的天鵝,
唱出了垂死的歌。
一念及此,筆者想到作為第一國際使者,曾參加1871年巴黎公社運動的俄羅斯女郎伊麗莎白·德米特里耶娃。她在當年五月“流血周”奮戰(zhàn)巴黎街壘,返回祖國后竟被處決,實令人悲其遭際:
天鵝!天鵝!
跌落在干巴巴的荒漠,
回望萊蒙湖清波,
你唱完了愛的悲歌。
筆者這一系列浮想,似緣于圣桑的《天鵝》和安娜·巴甫洛娃表演的《天鵝之死》。可見,一首旋律動人的樂曲,亦是一個自然意象,能給人深邃啟迪,衍化延展到更廣的文學(xué)藝術(shù)領(lǐng)域,滋潤受眾的思維和心靈。
回到圣桑本人,他并不是一位思想家,更無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企求。在詩歌與音樂領(lǐng)域里,圣桑主張維護古典傳統(tǒng),他重視固有的格律模式,反對用音樂表達情感,而強調(diào):“藝術(shù)可以問津到自然的淵藪,在心靈里深閉固拒,但它并不是一種必須承擔的義務(wù)。”他還堅稱:“我認為,藝術(shù)就是形式。不懂得形與色的系列和諧,就不是藝術(shù)家。”他尊崇先賢的倫理,在《通俗韻律》一詩中寫道:
切莫自負地相信勝利,
只憑淵博的學(xué)歷。
別那么驕矜,
以瞬息的癡想,
達到藝術(shù)的太極。
詩人呀,瞧瞧荷馬吧!
至于音樂家嘛,
倒也有莫扎特的先例。
圣桑1835年生于巴黎,自幼接受音樂熏陶,10歲上就舉行鋼琴演奏會,彈奏莫扎特的第六協(xié)奏曲和貝多芬的第三鋼琴協(xié)奏曲。1853年,1857-1877年間,他分別在圣麥里教堂和瑪?shù)氯R娜大教堂擔任管風(fēng)琴師,以擅長即興演奏出名,被李斯特譽為“世上最杰出的管風(fēng)琴家”。爾后,他到世界各地巡演,終于成為歐洲19世紀跟李斯特和魯賓斯坦齊名的鋼琴演奏家。在巴黎音樂學(xué)院,他師承雅克-弗洛芒達爾·阿勒維,同時受到古典派作曲家古諾指導(dǎo),作曲才華得以充分發(fā)揮。1853年,圣桑結(jié)識李斯特,在其支持下于1877年在德國魏瑪公演歌劇《參孫與達麗拉》。他還有抒情劇《銀色音質(zhì)》《始祖》,歌劇交響詩《赫拉克萊斯的青春》以及《奧姆法爾的紡車》《費頓》《阿爾及利亞組曲》,和以木琴奏出骸骨相碰聲響的《死神舞蹈》等多部交響樂。自然,人們不能忘記他的《動物狂歡曲》,以及更為大量的鋼琴、小提琴和大提琴協(xié)奏曲,還有100來首旋律樂曲,近三四十年來都一反昔日幾乎被埋進墓地的冷清,陸續(xù)進入音樂演奏會曲目,破天荒緊隨德彪西和弗雷之后一一錄制傳世。
圣桑曾于1871年跟弗蘭克、拉羅、馬斯奈、比才、杜怡克和弗雷一道創(chuàng)建“法國音樂學(xué)會”。在文藝觀和音樂風(fēng)格上,他更貼近福樓拜和高蹈派(亦稱巴納斯派),為巴納斯派詩人配曲,就是一種表象。他與德彪西和拉威爾格格不入,彼此雖然認識,但相形日遠。德彪西捍衛(wèi)法國音樂特性,反對當年巴黎樂壇對瓦格納的盲目崇拜,而圣桑起始非常珍視德國“音樂之王”的權(quán)威,盡管他后來轉(zhuǎn)變立場,也表示反對德意志在歐洲樂壇的霸權(quán),號召抵制所有德意志音樂家,維系法蘭西本民族的優(yōu)越音樂傳統(tǒng)。另一方面,他一直與德彪西不睦,反對德彪西的現(xiàn)代主義傾向,不喜歡那種過于浪漫的情緒宣泄,尤其厭惡德彪西的歌劇《佩里亞斯與梅麗桑德》和巨型音樂詩《大海》。
且看,圣桑1915年在寫給好友加勃里埃爾·弗雷的信中說:“我建議你瞧一下德彪西先生剛發(fā)表的‘黑與白’兩段鋼琴小品,他竟然能夠干得如此惡劣,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應(yīng)該盡全力讓法蘭西學(xué)院對這位先生關(guān)閉大門。”對德彪西如此公然排斥,應(yīng)是圣桑辨識自己在既立秩序下生活走向的一種方式。顯然,圣桑與德彪西在同一時代的感受是很不一樣的。德彪西的父親是1871年巴黎公社社員,他始終因此受到來自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社會政治壓力。圣桑維護既立秩序,1900年為巴黎世界博覽會譜寫康塔塔《天火》,五年后還前往波爾多去為共和派政客甘必大塑像落成典禮捧場致賀。
圣桑本名叫夏爾-卡米耶(Charles Camille Saint-Sa?ns),喜歡別人叫他“夏爾”。法國現(xiàn)今普遍以其姓“圣桑斯”(Saint-Sa?ns)稱呼他,字母“s”在此發(fā)音,中文將他的姓名譯成“圣桑”不很恰切。同樣,中文將女作家“George Sand”的姓氏譯成“喬治·桑”也有些不妥,準確譯名應(yīng)該是“喬治·桑德”。因為,女作家使用的這一筆名中,隱含跟她合作寫小說《羅絲與布朗什》的作家桑多(Sandeau)的身影,保留字母“d”發(fā)音,表明二人有過一段可追敘的情緣。
1875年,圣桑在創(chuàng)作《死神舞蹈》時,娶法國西北勒卡朵鎮(zhèn)鎮(zhèn)長之女瑪麗-洛爾·特魯弗為妻。其時,圣桑已到不惑之年,而女方年僅19歲。婚后,夫婦倆跟父母一起生活,婆媳不和導(dǎo)致夫妻不睦,橄欖樹下無和平。他們生育的兩個孩子都不幸先后夭折,給圣桑造成終身痛苦。1878年,二人住在多爾多涅省的布赫布爾鎮(zhèn)時,圣桑突然離家出走,不辭而別。其妻一連數(shù)日沒有他的音訊,以為他死了。實際上,圣桑遠走他鄉(xiāng),在摩洛哥隱姓埋名,再也不愿見妻室,只是沒有辦離婚手續(xù)而已。圣桑秉性悲觀,暮年變得更加孤僻,憤世嫉俗,于1921年12月16日在北非阿爾及爾患肺炎辭世,恰如他生時譜寫的《天鵝》那般凄愴,唱完了一首慘淡人世的悲歌。
圣桑的遺體被運回法國,安葬在巴黎的蒙巴納斯墓園,接受來自各地的音樂愛好者憑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