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第安人的斗爭(zhēng)與文學(xué)的表征 ——評(píng)2021年普利策文學(xué)獎(jiǎng)獲獎(jiǎng)小說(shuō)《守夜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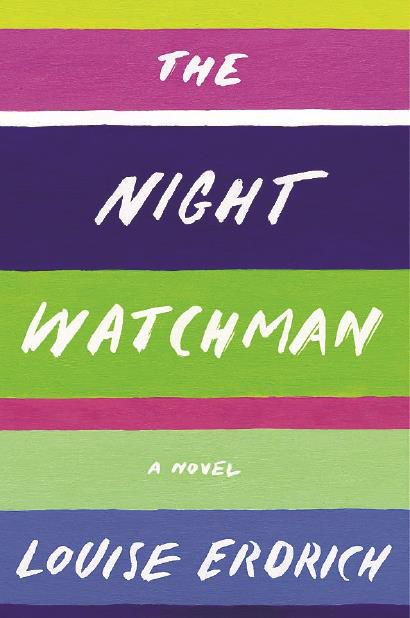
《守夜人》 [美]路易絲·厄德里克 著 哈珀出版社
獲得2021年普利策文學(xué)獎(jiǎng)的小說(shuō)《守夜人》,講述了一個(gè)印第安人部落為阻止美國(guó)政府的一項(xiàng)決策而付出艱辛努力的故事。小說(shuō)的獲獎(jiǎng)讓很多讀者再次回到了幾十年前。
1953年美國(guó)國(guó)會(huì)通過(guò)決議,要求在一些印第安領(lǐng)地終結(jié)自治狀態(tài)。決議的目的是要讓在這些地方的印第安人從此以后成為“美國(guó)公民”,享有公民權(quán),做“美國(guó)人”。很顯然,這是在對(duì)待印第安人的政策上, “同化”作用再次顯現(xiàn)其威力。從1940年代起,美國(guó)政府就實(shí)施了一系列同化印第安人的計(jì)劃,1953年通過(guò)的這項(xiàng)決議只是更加顯示了一種迫切性。這項(xiàng)決議給很多印第安人造成了困境以致毀滅,他們面對(duì)的是拋棄、壓抑、剝奪和絕望。離開(kāi)自己土地的印第安人變成了無(wú)家可歸者,所謂的成為“美國(guó)人”在他們這里猶如一粒干癟的葡萄。
也有一些印第安人團(tuán)結(jié)起來(lái)進(jìn)行抵制,用正當(dāng)?shù)姆绞奖磉_(dá)其不合作的態(tài)度和行為,在這過(guò)程中他們向美國(guó)社會(huì)呈現(xiàn)了其堅(jiān)強(qiáng)的性格,堅(jiān)韌的品性,與土地共生的決心,同時(shí),也展現(xiàn)了他們投身斗爭(zhēng)、維護(hù)權(quán)利的勇敢精神。具有印第安人血統(tǒng)的美國(guó)小說(shuō)家厄德里克在其新作《守夜人》里,講述的就是這樣一個(gè)故事。
厄德里克在小說(shuō)前言和后記中講述了她寫(xiě)作這部作品的緣由。她筆下的故事源自真實(shí)事件,在美國(guó)國(guó)會(huì)宣布實(shí)施“終結(jié)政策”后,厄德里克的外公、一位北德科他州切皮瓦印第安人龜山聯(lián)盟領(lǐng)袖就開(kāi)始組織當(dāng)?shù)厝藛T研究如何進(jìn)行抵抗,直至到華盛頓國(guó)會(huì)山參加聽(tīng)證會(huì),傳播他們自己的主張。厄德里克在讀到其外公寫(xiě)給相關(guān)人士的大量表明抗議和策劃抵抗行為的信件后,深為感動(dòng),遂萌發(fā)創(chuàng)作這部作品的意愿。從這個(gè)角度而言,這是一部政治立場(chǎng)鮮明,時(shí)代特征明顯的作品,作者試圖通過(guò)自己的寫(xiě)作留下一幅特殊時(shí)期的畫(huà)面,從中看出其祖輩是如何抗拒來(lái)自這個(gè)國(guó)家上層的種族歧視乃至種族消融政策的。
小說(shuō)中的人物都是普通人,即便是擔(dān)任當(dāng)?shù)赜〉诎踩寺?lián)盟領(lǐng)導(dǎo)人一職的托馬斯·瓦渣斯克(厄德里克外公的原型)也只是一個(gè)普通印第安領(lǐng)地里的農(nóng)民,同時(shí)在當(dāng)?shù)匾患夜S做守夜人的工作。但是這并不等于他們就沒(méi)有維護(hù)自己的權(quán)利并為之奮斗的意識(sh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小說(shuō)在講述印第安人團(tuán)結(jié)斗爭(zhēng)的同時(shí),也明確表述了他們自我意識(shí)覺(jué)醒,看到那些個(gè)以國(guó)家的名義頒發(fā)的政策背后的真正問(wèn)題所在。這是小說(shuō)政治立場(chǎng)明確的有力表現(xiàn)。這里的“政治”不僅是指批判的態(tài)度,更是指向批判得以成立的認(rèn)識(shí)深度。很顯然,以瓦渣斯克為首的一些印第安人成為了作者的代言人,在刻畫(huà)這些人物的同時(shí),作者也借他們之口對(duì)長(zhǎng)期以來(lái)美國(guó)政府的印第安人政策進(jìn)行了激烈抨擊,揭示了那些聽(tīng)上去冠冕堂皇但實(shí)際上充滿(mǎn)了種族歧視內(nèi)容的政策的虛偽的兩面性。
當(dāng)瓦渣斯克得悉國(guó)會(huì)通過(guò)的印第安領(lǐng)地“終結(jié)政策”動(dòng)議時(shí),這位部落領(lǐng)導(dǎo)人便敏銳地感到,這項(xiàng)政策背后的意圖是要消除印第安人的存在,似乎要表明,印第安人在這個(gè)國(guó)家從一開(kāi)始就沒(méi)有存在過(guò)。同時(shí),他也從閱讀政策文件中深深感受到了一股文字的力量,因?yàn)閺淖掷镄虚g中跳躍出來(lái)的是諸如“解放” “自由” “平等” “成功”這樣的“高尚”字眼。確實(shí)如此!如果查閱歷史的話(huà),可以發(fā)現(xiàn)這個(gè)動(dòng)議的主要制定者參議員瓦特金斯認(rèn)定經(jīng)他一手寫(xiě)下的那些政策文字被賦予了正義的內(nèi)涵,在美國(guó)政府看來(lái),印第安人長(zhǎng)期生活于領(lǐng)地之內(nèi),脫離于美國(guó)社會(huì),成為了被“守衛(wèi)”者——這也是瓦特金斯本人使用的一個(gè)詞匯,其結(jié)果是他們失去了自由,也無(wú)緣于平等,更遑論成功。這個(gè)邏輯看起來(lái)是那么順理成章,而邏輯推理的唯一結(jié)果是要讓他們成為“美國(guó)人”。但是,信仰這個(gè)邏輯的人似乎忘記了一個(gè)基本的事實(shí),印第安人本是這塊土地上的主人,所謂“美國(guó)人”是征服者,帶著征服者的高傲的姿態(tài)反過(guò)來(lái)用主人的口吻來(lái)要求被征服者。更重要的是,貌似包容性很強(qiáng)的成為“美國(guó)人”的過(guò)程,事實(shí)上并不如此,尤其是在對(duì)待一些處在邊緣地位上的少數(shù)裔而言,成為“美國(guó)人”不僅讓其失去自我身份,同時(shí)也消融了其文化傳統(tǒng)和種族根基,而這是那些強(qiáng)調(diào)“自由”和“解放”的人不屑和不愿考慮的,因?yàn)樵谄淇磥?lái),成功在于個(gè)人的努力,他們看到的是他們自己的努力的成果,他們看不到或不愿看到的是,印第安人在走向成功之路時(shí)一直陷在其中的不平等現(xiàn)實(shí)。在一個(gè)不平等的起跑線上,成功只是一種虛妄。
在小說(shuō)中,厄德里克設(shè)計(jì)了一個(gè)細(xì)節(jié),非常有意味地講述了上述“美國(guó)人”邏輯的展開(kāi),由此透視問(wèn)題所在。一個(gè)白人青年到瓦渣斯克家拜訪,在其看來(lái),這些印第安人成為“美國(guó)人”一點(diǎn)問(wèn)題也沒(méi)有,就像德國(guó)人、挪威人、愛(ài)爾蘭人、英國(guó)人來(lái)到美國(guó),最后都成為了“美國(guó)人”一樣。但是,瓦渣斯克的一句話(huà)就戳穿了這種話(huà)語(yǔ)的貌似蘊(yùn)含真理的邏輯。“我們是這里土生土長(zhǎng)的人。想想看吧,要是我們印第安人到了你們那里,殺了你們的人,占了你們的地,那會(huì)怎樣?”自然,白人小伙子無(wú)法面對(duì)瓦渣斯克的尖銳設(shè)問(wèn)。延伸開(kāi)來(lái)說(shuō),這正是美國(guó)政府要面對(duì)的事實(shí)。在歷史上,美國(guó)政府曾與印第安人簽下各種協(xié)議,也曾莊嚴(yán)承諾印第安人的自治權(quán)利,更曾留下過(guò)這樣的文字: “只要太陽(yáng)依舊照耀,青草依舊生長(zhǎng),河流依舊流淌”,協(xié)議就有效。但是,此時(shí)此刻,在以“解放”和“自由”的名義下,政府卻要廢除這些協(xié)議,不經(jīng)過(guò)對(duì)方的同意,以主人的身份來(lái)重新安排印第安人的命運(yùn),這不啻是極大的諷刺!
小說(shuō)的故事發(fā)展線索分成兩條路線敘述,一條是講述瓦渣斯克領(lǐng)導(dǎo)的抗?fàn)幎窢?zhēng),另一條圍繞年青女孩皮曦到城里尋找姐姐的過(guò)程,后者離開(kāi)鄉(xiāng)村到城市找尋夢(mèng)想中的好生活,卻落入虎口,不知音訊,實(shí)際上被人販賣(mài),最終淪為性工具,而皮曦自己也差點(diǎn)跌入類(lèi)似的陷阱。后一條故事線索從現(xiàn)實(shí)的角度說(shuō)明印第安人處于社會(huì)底層的事實(shí)。 “終結(jié)政策”試圖讓印第安人融入美國(guó)人社會(huì),并由此促使其生活的改變,這只是一種一廂情愿、脫離現(xiàn)實(shí)的想象而已。另一方面,小說(shuō)的兩條主線互相交叉,聚焦印第安人的家庭生活。在作者的筆下,既能看到一些印第安人的社會(huì)問(wèn)題如酗酒,不務(wù)正業(yè),也能看到家庭成員間的互敬互愛(ài)、互相幫助,在困苦中砥礪前行。作者的描述更是把筆觸伸向與印第安人朝夕相處的大地與自然的深處,時(shí)時(shí)用一種魔幻的語(yǔ)言烘托出他們與大地和自然共生同在的景象,象征性地表明洋溢在其身邊、包圍著他們的世代相傳、永生不滅的氤氳,而這是任何來(lái)自某些人的社會(huì)計(jì)劃所無(wú)法撲滅的,這是印第安人用以抵抗的有力武器,是他們賴(lài)以生存的精神食量。小說(shuō)結(jié)尾時(shí),與瓦渣斯克一同從華盛頓參加聽(tīng)證活動(dòng)回來(lái)的皮曦與母親一同喝下樺樹(shù)樹(shù)汁,作者這樣寫(xiě)道: “樹(shù)汁進(jìn)入他們的身體,就像在樹(shù)的身體中流淌,生出嫩芽,長(zhǎng)出枝干。”印第安人的抵抗如同自然一樣,生生不息,無(wú)法阻止。
厄德里克是美國(guó)有代表性的印第安人作家,著作等身的她一直沒(méi)有停止過(guò)與種族主義的斗爭(zhēng)。在其準(zhǔn)備歇筆之時(shí),來(lái)自歷史的靈感讓她再次拿起筆,寫(xiě)出了這部新作,而這同樣也是來(lái)自當(dāng)下的責(zé)任召喚所致。雖然故事中的印第安人最終贏得了勝利,但是現(xiàn)實(shí)中的美國(guó)離真正的種族平等還有很長(zhǎng)的路要走,厄德里克這部小說(shuō)的現(xiàn)實(shí)意義不言而喻。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xué)外語(yǔ)學(xué)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