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生的故事該如何講述? ——關于《T.S.艾略特傳:不完美的一生》一席談

T.S.艾略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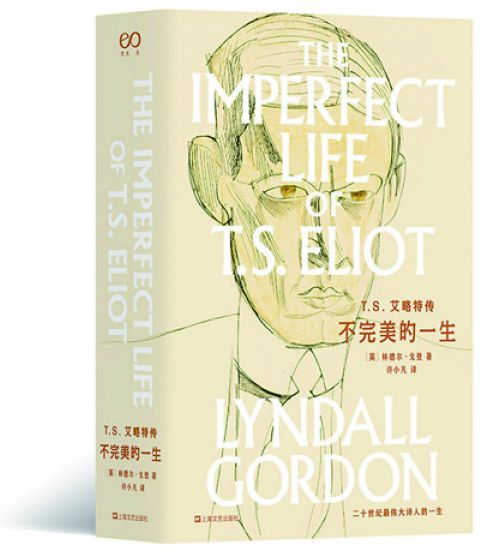

張新穎 許小凡 張定浩
主持人(本書編輯):很榮幸邀請到張新穎、張定浩、許小凡三位嘉賓,來一起談談《T.S.艾略特傳:不完美的一生》這本書。張新穎老師的傳記文學作品《沈從文的后半生》《沈從文的前半生》大家可能都讀過或者有所了解,張新穎老師也是極熟悉艾略特的讀者,他有一篇流傳非常廣的文章《T.S.艾略特和幾代中國人》,文章從徐志摩、葉公超、趙蘿蕤、卞之琳、穆旦到袁可嘉,一直綿延到如今自己這代人。張定浩可以說是這本書的起因,因為他讀艾略特,促使我想重新讀艾略特。張定浩是詩人,這幾年以寫批評文章出名。如果說在批評文章中他有什么師承的話,我想艾略特一定是最重要的人。我也很幸運地遇到譯者許小凡,如果沒有她,我肯定沒有這個勇氣在這里跟大家推薦這本書。許小凡用了兩年時間,一字一句地打磨它,像磨鏡子一樣,這樣才成就出這樣一部作品。
我想從一個簡單的話題開始:你們是怎么接觸到艾略特的,怎么開始讀他的,以前讀他和現在讀他有什么不同?
張新穎:在80年代中后期,我上大學的時候,中國的文學正好處于實驗、探索的階段,所以當時的人對于現代主義文學有非常強烈的興趣。我作為學生,正好趕上這樣一個時代,今天看起來很難讀的東西都是在那時候讀的。我最早讀到的是80年代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的《外國現代派作品選》,那本書的主編是袁可嘉,他選的是艾略特的《普魯弗洛克的情歌》,選了穆旦的譯文,《荒原》選的是趙蘿蕤的譯文。那時不覺得這些作品那么難讀,當然其實也不一定讀懂了,稀里糊涂就卷入到對這些作品的興奮中去了。對我們來說特別重要的是看到了和以前不一樣的文學,而那個時候我們正在尋求這種不一樣。我們對那些一樣的、熟悉的東西可能是厭倦了,所以那個時候它引起我們心智上的興奮。那個時候我很年輕,現在老了,一個年輕人和一個老人讀一個東西的時候,差距還是很明顯的,艾略特自己也發(fā)現了。艾略特曾說我年輕時候寫的東西比較受歡迎,年老后寫的不太受歡迎。年輕時寫的東西語氣明確,很決斷,當然也很率真,稍微老一點就變得復雜,變得猶疑,但是都充滿了智慧。所以我們對艾略特的了解也有這樣一個過程,一開始讓人很激動,慢慢地我們會理解除了激動之外更多、更復雜的東西,因為他的詩屬于那種不是一下就能理解的詩。今天讀和不讀其實已經不重要了。怕引起誤解,我要解釋一下:你讀過的東西會嵌入你的身體里,它會變成你的一部分,即使以后不讀它了,它也已經在你的身體里面,抹也抹不掉。
許小凡:艾略特在國內還是一個現象,但其實他在英美學界已經慢慢成為邊緣了。在我們國內的英語系,大家最開始接觸的都是艾略特。因為他的詩不管從音律層面還是從內容層面,確實都太美了。我一開始接觸到的是《普魯弗洛克》,后來在國內英語系讀到《小吉丁》。我上研究生時,在20世紀英美詩歌的課上跟著讀了這本傳記,還接觸了海倫·文德勒對艾略特的批評,當時選了一篇講《荒原》的。后來誤打誤撞,我走上了艾略特研究的道路。回過頭想,剛開始讀書的時候可能更多的是循章摘句地讀,我們會把艾略特視作一個警句式詩人。但是當我進入知識生產系統(tǒng)之后,我可能更多地關注艾略特作為一個詩人、一個知識分子以及其他的身份,比如出版商、編輯。我記得書中有一個很有趣的細節(jié):艾略特當時做了一本文學刊物,叫《標準》。創(chuàng)立《標準》就是為了打破既有的文學建制,打破那些將死的文學傳統(tǒng),想要引入一套新的傳統(tǒng)。他管自己和龐德這些同道中人、能夠帶來創(chuàng)新的人叫“囚徒”,意為從文學內部突圍。但這套新的傳統(tǒng)只能夠有策略地建立,他做《標準》時,有個策略是大規(guī)模地刊登已經出名了的作家和批評家的作品,但是在里面插入新人的作品,就好像從內部炸開一個保險箱。
張定浩:我很慚愧,因為我很晚才讀艾略特。像《荒原》,因為很有名,很多人以為自己讀過,但其實沒讀過。我就以為自己讀過,結果25歲后才接觸到它。最早看到的是艾略特的評論文章《傳統(tǒng)與個人才能》。他的詩歌我接觸得太晚,可能沒有對我的寫作產生太大的影響,這是很誠實的想法。我覺得他用的方法很簡單,就是比較和分析,喜歡用強硬的判斷和給人排列次序的等級制的區(qū)分,這些東西讓我印象很深。尤其在這樣的多元時代,大家不愿意做等級式的區(qū)分,只是強調不一樣。但是在艾略特心里好像有一個嚴厲的天使,讀他的文章像被這個嚴厲的天使帶領著,有一種俯瞰式的視角。
主持人: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讀一個詩人的傳記,讀一個作家的傳記,讀一個哲學家的傳記,有必要嗎?這種閱讀有意義嗎?
張定浩:這個問題其實是個偽命題。就好比,關鍵不是傳記好不好,關鍵是誰寫,寫得如何。今天這本書的作者不在場,我就不表揚了,譯者要好好贊美一下。這是我讀得特別舒服的一本書,從中文語感來講我特別喜歡,就好像用我喜歡的語言寫成的。其次,在現代中文世界里,關于現當代漢語詩人,幾乎沒有這樣有分量的書。我們的詩人傳記常常是做一些很無聊的瑣碎的史料研究,以至于大眾對于詩人的印象出現各種扭曲,這和這些傳記多少有些關聯。比如泛濫成災的林徽因的傳記、海子的傳記、穆旦的傳記,等等。
許小凡:關于這個問題,我覺得需要從兩個角度想。第一,為了生活讀。有人覺得傳記不值得讀,奧登也這么說過,沒有必要通過傳記解讀作品,因為傳記不可能全然真實,根據對一些傳記事實的懸想解讀作品的話,會有相當大的問題。但是為了解決你生活當中的一些問題,我覺得還是值得一讀。這本傳記給我印象最深的一點是,這絕非一本八卦式的傳記,里面有很多非常細膩的鋪陳與分析,關于感情,關于知識分子在重大歷史時刻的選擇。閱讀的時候,作為一個普通人對艾略特發(fā)生認同之后,我們會關注他在做重要選擇時是怎樣思考的。我覺得這是讀傳記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有認同感,且有介入點。要做詩歌研究的話,傳記是要謹慎看待的。目的不一樣,傳記對讀者的作用也不一樣。
張新穎:受庸俗社會學的影響,人們對從作家的人生經歷來解釋作品的方法特別厭煩,我上大學的時候,新批評的主張已經變成了文學理論最基本的觀念。那時奠定的觀念就是要把文本和作者區(qū)分開,要關起門來讀文本。當然,不存在可以被關起來的文本,一定要把這個文本和寫下這個文本的人割裂開來,聲稱沒有關系,這是自欺欺人。為什么是這個人寫下這個文本,而不是我?其中當然是有關系的,并且這個關系是無法被取代的。只不過是說,我們的研究有沒有能力在作者和文本之間建立起更可信賴的聯系,不是說要否定這個聯系。不少人反對所謂的外部研究,就是這個道理。當然很差的外部研究和很差的內部研究一樣糟糕,也有光讀文本讀得一塌糊涂的。我其實是持比較簡單的、開放的態(tài)度。如果我們相信文本的豐富性,相信它包含著很多信息,我們就不應該拒絕各式各樣的手段,只使用一種手段是不對的。當然,前提是傳記是個好傳記,傳記是需要的,而且是非常需要的。舉一個具體的例子。我們以前讀艾略特的詩時,很少考慮到他的宗教問題,即使考慮到也是模糊的。但是讀了這本傳記之后,很多以前想不明白的問題能夠弄明白了,這就是傳記可以告訴我們的。
主持人:請三位老師跟我們分享一下自己印象深刻的段落或者句子。
張定浩:讀了這本傳記之后,我有一種在炮火當中、在防空洞里與各種人一起聽《四個四重奏》的感覺。艾略特跟社會是有關系的,只是以他自己的方式產生關系,而不是直接迎合他的時代,是在慢慢塑造這個時代。我覺得這是我讀這本傳記后印象很深刻的一點。我以為《荒原》只是一個隱喻,讀過以后發(fā)現它里面潛藏著很多感情,那些生活中不堪的事情,那些難以面對的時刻。好的傳記是對一個人的內部研究,作為文本來講,傳記是外部研究,但是對于一個人本身來講,傳記又成了內部研究。好的傳記尤其是作家的傳記,應該觸及這個人如何面對生命中最艱難、最不堪的時刻。周圍人不會知道那么多,只知道一點點,那些都是碎片,只有他自己知道如何挨過生命中特別難挨的時刻,等待著未來某一刻一個人把所有信息拼在一起,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有一天這個人抵達了,這是特別動人的時刻。一個作家、一個藝術家跟普通人一樣,有各種各樣難堪的時刻,但是不同在于,他可以用藝術把它們轉化成一種不朽的時刻,把這種歷史時間轉化成一種永恒時間,把每個人都遇到過的時間轉化成會不斷重復的永恒的時間。這個人是如何做到的?這是好的傳記要面對的問題,我覺得戈登在這方面做得特別好。一般傳記都會圍繞傳主說話,寫傳記的人會是傳主的粉絲和研究者,對傳主周圍的人態(tài)度會比較輕蔑。而這本傳記的作者對艾略特周圍的女性都抱有同情的態(tài)度,但也不是要拔高她們。她特別理解她們,理解艾略特身邊每個人,盡力做到了一種平等,平等地對待一個偉人和在偉人光環(huán)照耀下沒有那么重要的人,這也是特別難得的。艾略特的第一個妻子去世之后,艾米莉以為他要和她結婚了,我們從書中能夠讀到,從一個愛著艾略特的女人的角度來看,這會是怎樣一個故事。這段很短,是作者的感慨,但這些話特別精彩。艾米莉是艾略特年輕時的初戀,他們后來又遇見了,等于有二三十年的情感糾葛,兩人互相寫了很多封信,據說這些書信今年10月份才能公開。
許小凡:這確實很讓人悵然。大家一直在等著這批書信解禁,我個人不太敢看這些信。艾米莉寫給艾略特的信,他讓朋友燒毀了,另外一部分今年解禁。剛才張定浩老師講的這些我都非常認同。艾略特作為一個詩人,作為一個重要的知識分子,如何與歷史、與當時發(fā)生的重大事件產生一種有效的聯系?比如很多人批評艾略特在二戰(zhàn)時沒有寫下明確反對德國納粹的作品,沒有寫過帶有政治性的東西,但同時,《小吉丁》算是一首愛國詩、戰(zhàn)爭詩,也是艾略特對于戰(zhàn)爭的反映,它是艾略特在戰(zhàn)爭中對英格蘭產生的一種新的認同,但是這種認同恰恰是通過返回種種歷史時刻來達到對當下有距離的理解。這兩天為了準備這場活動,我重新讀了艾略特有關詩歌批評的一些文章。艾略特很明顯地表達過:如果你是一個對世界漠不關心的詩人,你寫出來的批評也只能是漠不關心的批評。艾略特絕對不是一個對現實漠不關心的詩人,他對現實是有關切的,他的作品都是他走向大眾的一種形式。他的詩劇《大教堂兇殺案》看似與當時的英格蘭現實沒有關聯,但其中也有對現實的折射,二戰(zhàn)期間他的詩劇被各種劇團到處巡回演出。在這本傳記中,我讀到了他作為一個詩人,如何在世間行走,如何與現實發(fā)生關聯,我對這點印象很深。
簡短地說一下另外兩點,我也在譯后記里面寫到了。這本書幫助我們理解了艾略特的宗教情結,從他年輕時一直存在。這本書的前半部分,戈登一直用一個詞叫“寂靜”。表面上戈登把他的皈依寫成突然的事件,但實際上,戈登寫出了他內心中的自然連續(xù)性,比如他年輕時有禁欲情結,向往圣徒生活。但是戈登寫了一句話:這個時候他還沒有罪,尚且不需要宗教。所以在皈依那章,戈登從艾略特的婚姻開始寫,因為皈依使他對在婚姻中犯的罪有了反思。戈登寫到了艾略特的皈依與他生活中其他行為之間的聯系,把它們寫成一個有機的整體,這點我是非常佩服的。另外讓我感受很深的是書中對他晚年的描寫,寫艾略特晚年離群索居的孤獨,我覺得是這本傳記最成功的地方。因為艾略特的晚年在各種傳記中相當于空白,大部分傳記事實只能從檔案館里搜集。戈登只能靠各種材料的拼接以及對艾略特心靈的理解,寫他功成名就后如何用孤獨來保護自己的詩。這是我很佩服的一點。
張新穎:我看這本書的第一個印象是,翻譯得太好了。翻譯的不足足以扼殺我們的閱讀興趣,哪怕是一本很好的書,而這本書翻譯得這么好。單看中文呈現出來的版本,都能感受到這本書很難譯,因為要面對很復雜的問題。中文譯本的讀者其實是有福的。從頭到尾我都覺得挺好,所以我就不挑其中某段了。第二,《不完美的一生》這個書名其實還有一層意思,就是完美的力量。書從頭到尾就是在完美和不完美的張力中推進,所以書名很好,但要讀了以后才能知道這個書名的好處。
主持人:許小凡在后記里就說,艾略特比誰都渴望完美,但是他應該沒有達到。在書的最后一章最后一段,他說他自己沒有達到,但是他把這個“完美”交給后世的我們,也許我們可能享有這個完美的人生。接下來我想問問幾位,對于材料,傳記應該怎么做取舍?要不要講那些完全發(fā)生在內心的故事?
張新穎:這個問題很難回答。面對不一樣的傳主,寫作方法就不一樣。寫艾略特和寫穆旦肯定是不一樣的。還有寫作者不一樣,所以會面對不同的條件。我覺得不存在一個模板式的傳記的寫法,只能根據寫傳的人和傳主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寫法。這個回答聽上去很平庸,但確實是實話。關于寫傳的人和他擁有的材料之間的關系,打個比方,不同的木料適合做不同的家具。木料不夠,只能做小板凳,反過來,做大柜子的木料來做小板凳,那是浪費。要對得起那種材料,要做到合適。但是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更好的木匠。有一堆垃圾,所有木匠都認為是廢料,但是偏偏有一個木匠覺得這些東西不但有用,而且比好木料還要好,用這些做出了更好的東西。很多偉大的傳記用的材料在一般的作家眼里就是沒用的材料,但是好的傳記作家能夠煥發(fā)出它們的能量。
許小凡:作為譯者,我自己也沒有寫過傳記。但是我有兩個跟傳記寫作有關的問題,是我在讀沈從文傳記時考慮的。第一個問題是,我看到張老師寫的傳記里大量地引用了《從文自傳》,這些材料不知道您會不會做一些篩選?還有一個問題是,傳記與傳記小說之間的邊界究竟在哪里?
張定浩:相信對于張新穎老師,把沈從文那本書叫作傳記,他是勉為其難的,這是一部作品。從作品角度講,真正的客觀是不存在的,我們無法接近。你要理解一首詩,你要寫一首新的詩,你要理解一個杰出的人,你就要努力去讓自己成為杰出的人。如果做不到自己寫出一部杰出的作品,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能去努力理解。比如談論蘇東坡時,好像怎么談論都可以,但是這樣的態(tài)度就無法對自身有益。因為你面對一個比你更杰出的人,首先要做到準確地接近他。傳記也是這樣,你要做到準確地接近他,并不是要還原他,那是件虛妄的事情,你只是為了在準確地接近他之后,讓自己呈現出更好的面貌,通過自己面貌的好映照出他的好,其實是通過自身映照他,你自己成為鏡子一般的東西,這種時候就體現出了精髓。第二,艾略特有一篇談論丁尼生的文章。丁尼生對社會政治宗教沒有那么強烈的感覺,但是在對語音的感覺上,別人難以企及他。聲音的感覺是在表面,只有真正進入表面,才能深入內部。這本傳記也是,作者沒有偏見地面對艾略特,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能進入他的內部。艾略特談論丁尼生時,說到要進入這種內部,進入深淵般的悲傷里面去。艾略特覺得最好的批評是讓你看到了從未看到過的東西,但不是去解釋,而是讓你看到之后,自己在那個地方獨自待著,讓你自己去面對他。
張新穎:《沈從文的前半生》前面一定要用到《從文自傳》的材料,因為《從文自傳》這本書太有名了。要引用是因為沈從文本身已經寫了,再重復沒有什么意思。《從文自傳》只寫到20歲,20歲以后要我來寫。《從文自傳》是他30歲時寫了他20歲的事情,30歲正是意氣風發(fā)的時候,所以他在敘述他20歲以前的生活時,那意氣風發(fā)的狀態(tài)會被帶到他對以前生活的回憶中。所以他寫的以前的生活雖然很苦,但是整個基調非常明朗,甚至是歡快的,而他真實的生活可能不是這樣。他為了突出從邊緣地區(qū)來的野孩子的形象,他寫自己“逃學來讀社會這本大書”,但是沈從文小時候讀書讀得很好,他為什么逃學?因為他上學之前已經把很多東西都學會了,上學對他來說沒有意義,學校已經滿足不了他的智力需求,他有意地把這一面去掉了。沒讀過什么書,整天在野地里玩,這是他的自傳建構出來的形象。我只能借助不太多的資料,把他有意忽略的那部分補上,試著把明朗的調子換成也許不那么明朗的時刻。寫《沈從文的后半生》時,大量地引用了他書信的內容。有人問,你怎么敢這樣用?我還挺敢這樣用的。很少有人能連續(xù)地記錄自己幾十年的精神活動,好在沈從文把這些東西記下來了,他不是記下回憶,而是記下了當時的感受,所以這些材料我就直接拿來用了,當然我可以有我的分析。當你需要相信一個東西的時候,你要勇敢地去相信它,不要猶疑,在一個瞬間果決地獻身。這也需要勇氣,我有這樣的勇氣。
主持人:最后想請幾位談一談,詩人和時間之間的關系。我覺得艾略特一定是對時間領會最深的一個人,我不知道他有什么詩不是在寫時間的,像《四個四重奏》開始那段,包括剛才讀的那些詩。
張定浩:艾略特在《四個四重奏》的第二部分里有一句話,“老年人應該是探索者”。從過去到現在都是這樣,像尤利西斯也是,回到故鄉(xiāng)重新啟航,第二次遠航,這種氣象特別好。我覺得年輕的時候寫的衰老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因為一個年輕人特別缺乏能力,而一個年老的人擁有了很多心智,所以應該是探索者。我有時候也會說,詩人是克服時間的人,類似于張新穎老師說沈從文是一個時間勝利者。我覺得他克服了歷史時間,所有藝術家包括詩人面對的是復活,這也是詩人傳記難以表達的東西,簡單的生平八卦無法呈現復活的時刻。所謂永恒的時刻,好詩人就是能把時間挽回,把已經失去的東西召喚回來。因為他的存在,所有東西都依舊存在。似乎這也是古希臘哲人的話:愛讓所有元素聚集在一起,恨讓所有東西分離。對于好詩人來說,他使用的能力就是愛的能力,因為愛的能力讓不同時間、不同空間的最真實的東西重新聚集在一起。過去的空間和時間里他覺得最珍貴的東西,因為他的愛重新聚集在一起,而這種東西不是知識能帶給我們的。比方說艾略特最喜歡的但丁,但丁是一個導師,是比他更為淵博和寬闊的人。但丁可以帶他經歷現實,但如果要抵達一個更為崇高的層面,導師是沒有能力做到的,必須把他交付給一個愛的力量,讓他繼續(xù)向上攀登。可能某一刻這樣的人并不存在,但不能說因為這個人沒出現就不能寫出好作品,其實是反過來的:你自己擁有了愛的力量,杰出的人才會出現,或是出現在你的作品當中。
張新穎:把時間的問題變成空間的問題,我們可以講講中國人讀艾略特的歷史。我們這幾年翻譯了奧登,我前些年在芝加哥教書的時候,因為要講到穆旦,就讓學生去讀奧登,可是奧登在美國沒人讀。一樣東西換了空間之后,換了環(huán)境之后,它起的作用確實不一樣。我們從20年代開始讀艾略特,他對于我們的作用確實不像他在英語世界里的作用,卞之琳個人的經歷就能說明這一切。卞之琳當時是北大學生,有一門課叫英語詩歌,老師是徐志摩,講浪漫主義的東西,講得天花亂墜,學生也很高興。這門課上到一半,徐志摩的飛機出事了,換了一個老師,同樣一門課完全變樣,變成了葉公超講艾略特。對于學生來講,這個轉變非常大,所以很多年以后卞之琳回憶起來仍記憶猶新。對于中國新詩來說,從30年代到40年代的轉變起的作用還是比較大的,而且卞之琳說了一句話,當然這句話其實包含驕傲的成分:經得起檢驗的,今天還能夠讀的三四十年代的詩歌,就是現代主義。以艾略特為代表的現代主義起了很大的作用。卞之琳做學生的時候譯了一本,到了40年代,穆旦他們的時代,和卞之琳做學生的時期又不一樣了。穆旦整天讀艾略特的雜志《標準》,那就更不一樣了。到了今天,我給研究生上課,每年會讓他們讀一本艾略特,我會挑選艾略特的書中最容易讀的《批評批評家》讓他們讀,比較薄,很多都是演講,不是那么難讀。文學作品似乎變成另外一種東西,在另外一個時空中獲得生命,就是張定浩說的復活,艾略特可能沒有想到他在中文語境里會這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