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燕郊的“衰年變法”
從某種意義上,對(duì)于跨越傳統(tǒng)意義上現(xiàn)代、當(dāng)代的詩(shī)人群體來(lái)說(shuō),20世紀(jì)80年代的來(lái)臨既是機(jī)遇又是挑戰(zhàn):一方面,這批經(jīng)歷坎坷、已屆晚年的詩(shī)人終于重返詩(shī)壇,獲得了重新寫(xiě)作的權(quán)利,而另一方面,則是他們需要面對(duì)日新月異的時(shí)代,在不斷接受青年詩(shī)人沖擊的同時(shí),寫(xiě)出符合當(dāng)代美學(xué)風(fēng)格的作品。因此,所謂“衰年變法”超越以往的創(chuàng)作、抵達(dá)“成熟的晚年”,必然要以轉(zhuǎn)變、修正自己的創(chuàng)作為前提。令人遺憾的是,由于種種主客觀原因的制約,能夠突破“晚年”限制的詩(shī)人其實(shí)并不多見(jiàn)。是以,基于研究者的立場(chǎng),我們總期待能夠在回顧歷史的過(guò)程中有所發(fā)現(xiàn),以填補(bǔ)幾近蒼白的“詩(shī)歌想象”。
依照這樣的邏輯,將彭燕郊(1920—2008)20世紀(jì)80年代以后的創(chuàng)作作為獨(dú)立的個(gè)案加以解讀,相當(dāng)于一次時(shí)隔多年、適度歷史化之后的“再解讀”——在此過(guò)程中,我們不僅要反思“七月詩(shī)派”“歸來(lái)的詩(shī)群”等命名的階段性和局限性,還要以辯證綜合的方式將其和彭燕郊的創(chuàng)作史、心靈史以及已有的文獻(xiàn)有效地結(jié)合起來(lái),進(jìn)而在“重識(shí)一位詩(shī)人”的同時(shí)豐富和深化彭燕郊研究,觸及一些新的論題。

彭燕郊在書(shū)房
一、以重審詩(shī)歌史上的命名為起點(diǎn)
從曾經(jīng)歸入“七月詩(shī)派”,到如今終于可以回歸正常的寫(xiě)作軌道,以“歸來(lái)的詩(shī)群”(或曰“歸來(lái)者”“歸來(lái)的歌者”)概括彭燕郊重返詩(shī)壇自有其道理。1981年8月,綠原、牛漢主編的《白色花——二十人集》于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出版,選彭燕郊詩(shī)七首,更是強(qiáng)化了兩個(gè)命名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1]。然而,如果強(qiáng)調(diào)“歸來(lái)的詩(shī)群”意味著重返詩(shī)壇中心位置,那么始終身處“邊緣”甚至自我“邊緣”[2]的彭燕郊又從未經(jīng)歷過(guò)“歸來(lái)”。辨析彭燕郊與“歸來(lái)者”之間的關(guān)系并以此為講述的“起點(diǎn)”,對(duì)于認(rèn)知其20世紀(jì)80年代以后的詩(shī)歌道路有著重要的意義。它不僅有助于我們看到彭燕郊與“歸來(lái)的詩(shī)群”在創(chuàng)作上的不同,而且也有助于我們了解彭燕郊從未斷裂過(guò)自己創(chuàng)作的根脈。沒(méi)有藝術(shù)上的故步自封、日漸遲鈍,也沒(méi)有轉(zhuǎn)向舊體詩(shī)詞的創(chuàng)作或是直接停筆,彭燕郊只是在不斷思考?xì)v史、現(xiàn)實(shí)與詩(shī)歌之間互動(dòng)關(guān)系的過(guò)程中,實(shí)現(xiàn)了創(chuàng)作經(jīng)驗(yàn)的整合與發(fā)展,他在晚年抵達(dá)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許多方面為20世紀(jì)中國(guó)新詩(shī)做出的成就卓然的探索,都與此有關(guān)。
作為“前奏”,彭燕郊于1979年3月受聘于湘潭大學(xué)文學(xué)系,實(shí)現(xiàn)了人生的重大轉(zhuǎn)折。同年8月,他的《畫(huà)仙人掌》發(fā)表于《詩(shī)刊》上,標(biāo)志著多年的“潛在寫(xiě)作”終于結(jié)束,重獲創(chuàng)作的自由和發(fā)表的權(quán)利。有感于曾經(jīng)沉重的歷史,彭燕郊重返詩(shī)壇后的第一首公開(kāi)發(fā)表的詩(shī)在語(yǔ)意上略顯隱晦曲折:“我”本想以“光”和“色彩”還有“創(chuàng)作的愉快”畫(huà)出美麗的花、“畫(huà)出那真正的天國(guó)的愉快”,但結(jié)果畫(huà)出的卻是“向四面八方射出去的箭”的仙人掌,“一味的綠……/沒(méi)有深,沒(méi)有淺/沒(méi)有中間調(diào)子的柔和轉(zhuǎn)換”;“沒(méi)有枝,沒(méi)有葉/當(dāng)然也沒(méi)有花……的花!”在理想與現(xiàn)實(shí)的錯(cuò)位之間,讀者可以看到一個(gè)特殊的形象:“這些帶刺的簡(jiǎn)單的形體/它不需要描繪,不需要贊美”,同時(shí)也很容易感受到一種帶有自喻色彩的孤立、拒絕與純粹的精神。從形象到精神,既凝結(jié)著詩(shī)人藝術(shù)的轉(zhuǎn)換能力,同時(shí)也蘊(yùn)藏著樸實(shí)無(wú)華、堅(jiān)忍不屈的靈魂。
《畫(huà)仙人掌》曾被作家無(wú)名氏譽(yù)為自有《詩(shī)刊》以來(lái)“唯一的好詩(shī)”[3],這一判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為彭燕郊從重返詩(shī)壇那一刻起,就具有高超藝術(shù)水準(zhǔn)的佐證。但從當(dāng)時(shí)具體的寫(xiě)作情況來(lái)看,經(jīng)歷過(guò)風(fēng)云變幻的詩(shī)人在回歸初期并未立即擺脫濃重的歷史感,相反地,記憶的壓力往往使其在面向現(xiàn)實(shí)和未來(lái)時(shí)有些情不由己。在“滿懷希望之中有一絲憂慮”[4],渴望上升與迂回介入的狀態(tài)共存,使其敘述充斥著理性的思考:
上升,螺旋形沒(méi)有后,沒(méi)有前,取消前后。
上升,從六個(gè)角度拋棄前后。
上升,只有高和更高,取消低。
螺旋形的規(guī)律是:終點(diǎn)也不是結(jié)束。
攀登者把過(guò)程留給腳下的梯級(jí),
它們正殷勤地在轉(zhuǎn)折中進(jìn)行有節(jié)奏的退卻。
——《旋梯》
出于對(duì)邊緣身份的自我認(rèn)同,彭燕郊在書(shū)寫(xiě)“歸來(lái)的詩(shī)群”共同關(guān)注的主題時(shí)顯得從容、平和。沒(méi)有過(guò)多的直抒胸臆、浪漫抒情,也沒(méi)有一味地沉湎于記憶的傷痛、舔舐帶血的傷口,在更多時(shí)候,他只是像一位多年未見(jiàn)的老朋友一樣于重逢時(shí)即興獻(xiàn)詩(shī)。區(qū)別于當(dāng)代詩(shī)歌史對(duì)“歸來(lái)的詩(shī)群”特征的整體描述,彭燕郊在20世紀(jì)80年代初期詩(shī)歌的“與眾不同”集中體現(xiàn)在以下三個(gè)方面。其一,是重返詩(shī)壇后的憧憬。雖也講述過(guò)重返的坎坷與艱辛,但彭燕郊明顯有淡化苦難敘述的傾向。他只是將重返作為詩(shī)歌的必經(jīng)之旅,并在輔以象征手法的同時(shí),讓情感和體驗(yàn)穿過(guò)厚重的歷史,直至當(dāng)下、寄向未來(lái)。“啊,你/壯游歸來(lái)的天上的大眼睛/你看見(jiàn)了嗎,在我的眼睛里/跳動(dòng)的這許多夢(mèng)的影子”(《月夜》);“我需要的永遠(yuǎn)是腳下深厚、堅(jiān)韌的土地,/和這土地上由無(wú)數(shù)先行者的腳步踩出來(lái)的,/清清楚楚地朝向前方/無(wú)限地伸展出去的道路。”(《歸來(lái)——給遠(yuǎn)清》)應(yīng)當(dāng)說(shuō),對(duì)重返后的憧憬,使彭燕郊成為“歸來(lái)的詩(shī)群”中最早擺脫記憶夢(mèng)魘和主題限制的詩(shī)人,同時(shí)也有助于其“塑造”出一種個(gè)性化的風(fēng)格。其二,是勸勉、鼓勵(lì)與祝福。80年代初期的彭燕郊寫(xiě)有大量的贈(zèng)答詩(shī),這些詩(shī)或懷念前輩、獻(xiàn)給師長(zhǎng),或贈(zèng)給有著同樣經(jīng)歷的詩(shī)人、祝福有著同樣經(jīng)歷的友人。他的《黃昏之獻(xiàn)——呈半九兄》是寫(xiě)給黃昏時(shí)分海上航行者的贊歌、寄托著“晚年”的雄心壯志:“海上的黃昏是莊嚴(yán)的。晚潮正急,/遠(yuǎn)航的水手揚(yáng)帆啟碇。……覺(jué)得人渺小嗎?/正相反。我記得一句話:/‘終點(diǎn),又是一個(gè)起點(diǎn)。’/航程在信念的基點(diǎn)上持續(xù),/水手的話短促又響亮,/在海上,只能這樣地說(shuō)話。”他的《一朵火焰——呈孟克》是受難者的寫(xiě)照、散發(fā)著平凡而又偉大的光輝:“一朵火焰,平凡的圣跡/在它的每一個(gè)斜面和尖端上/在所有的金紅的霧靄和陰翳里/殉教者般地發(fā)光,但不耀眼,也不刺目”。還有因小說(shuō)家、詩(shī)人三耳的“新居了無(wú)陳設(shè),一如數(shù)十年前流寓浙、桂、渝、港時(shí)”而寫(xiě)的贈(zèng)詩(shī)《鷲巢》,里面有一只“一邊沉思,一邊奮進(jìn),/在天光云影中上下盤(pán)旋”的荒鷲,在翱翔覓食時(shí)“無(wú)遮無(wú)攔光禿禿的巢于它最為合適”。“勸勉、鼓勵(lì)與祝福”是彭燕郊從沉痛語(yǔ)境中突圍出來(lái)的見(jiàn)證,不僅給被勸勉者、祝福者以信心,而且也是其借此喚起久違的激情,在“晚年”續(xù)寫(xiě)絢爛生命篇章的源泉之一。其三,回歸鄉(xiāng)土田園。彭燕郊曾在這一階段寫(xiě)有總題為“南國(guó)淺春譜”的組詩(shī),該組詩(shī)就緣起來(lái)看自是與詩(shī)人當(dāng)時(shí)的生活環(huán)境有關(guān):“學(xué)校才建不久,宿舍前就是水田,與農(nóng)家錯(cuò)落而居。”但就相對(duì)于詩(shī)人創(chuàng)作道路的意義而言,卻并不僅停在“重溫童年村居歲月和50年代初參加土改的深刻記憶”[5]這樣簡(jiǎn)單的層次之上。首先,相對(duì)于“歸來(lái)”的詩(shī)人群,由于卸下精神的重負(fù)、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山水行吟題材創(chuàng)作是一個(gè)普遍的現(xiàn)象,但對(duì)于鄉(xiāng)土田園題材的書(shū)寫(xiě)卻十分少見(jiàn),這說(shuō)明彭燕郊的詩(shī)歌趣味、對(duì)詩(shī)歌題材的關(guān)注度與前者有很大的不同。不僅如此,詩(shī)人將其命名為“南國(guó)淺春譜”,其實(shí)暗示著他很享受這種自然的、歡暢的、無(wú)憂無(wú)慮的生活。其次,相對(duì)于彭燕郊自己,“南國(guó)淺春譜”的誕生意味著彭燕郊詩(shī)歌表現(xiàn)形式的增加和語(yǔ)言表現(xiàn)力的拓展。“當(dāng)時(shí)正參與整理土家族長(zhǎng)歌《擺手歌》《哭嫁歌》,很受影響”,“南國(guó)淺春譜”雖“極力避免了形式上的模仿”[6],但從《“呵叱,呵叱……”》《太陽(yáng)照著》《插田上岸》《田頭即景》等具體的寫(xiě)作情況來(lái)看,民間語(yǔ)言及民歌形式的融入還是讓讀者看到了“另一個(gè)彭燕郊”,他已在不經(jīng)意間走得很遠(yuǎn),他的詩(shī)也隨即出現(xiàn)了不易覺(jué)察的變化。
很早就有人注意到彭燕郊20世紀(jì)80年代的創(chuàng)作早已超越“七月派”且與“歸來(lái)的詩(shī)群”有很大的不同[7];很早就有人發(fā)現(xiàn)相對(duì)于彭燕郊,“歸來(lái)者”是一個(gè)“概念迷津”,而將彭燕郊稱之為“不是‘歸來(lái)者’的‘歸來(lái)者’可能更合適”[8]。歷史地看,上述觀點(diǎn)的出現(xiàn)絕非偶然。一則是諸如“七月詩(shī)派”“歸來(lái)的詩(shī)群”作為與現(xiàn)實(shí)聯(lián)系較為緊密的文學(xué)史命名,雖在誕生時(shí)具有合理性,但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和所指詩(shī)人仍在繼續(xù)進(jìn)行創(chuàng)作特別是在風(fēng)格發(fā)生變化、誕生名篇佳作的前提下,曾經(jīng)的命名就會(huì)自然而然地顯露出階段性的局限,何況作為一種整體性的命名,其關(guān)注的往往是“共性”而非“個(gè)性”,因此也很難做到精準(zhǔn)。二則是基于發(fā)展的眼光、當(dāng)下的視野,人們也會(huì)因?yàn)閷徝纼r(jià)值、藝術(shù)風(fēng)格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的變化甚至是批評(píng)的壓力而易于產(chǎn)生所謂的“再發(fā)現(xiàn)”。當(dāng)然,“再發(fā)現(xiàn)”的重要前提是找到新的證據(jù)并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由此比較彭燕郊80年代初期和同一時(shí)期“歸來(lái)的詩(shī)群”作品的差異性,自認(rèn)邊緣、積極樂(lè)觀和寬容的心態(tài),使其多了幾分自然與舒緩,少了幾分晦暗與緊張。像一位智者,彭燕郊沒(méi)有深陷沉重的往昔而難以自拔,他只是平靜地審視著過(guò)往和正在發(fā)生的一切,在不斷感悟中實(shí)現(xiàn)理性的超越:“體味著悲哀,體味著痛苦之中最痛苦的/生和死的隔絕帶來(lái)的憾恨/你,嘗到了嗎?生命的鹽里/卻有著甜味呢:甜的醒悟和甜的理解”(《鹽的甜味——懷一位前輩》);“洪水時(shí)代來(lái)了又去了/來(lái)來(lái)去去多少次/永存的是肥沃的大地/——大地在等待洪水的到來(lái)”(《四月的云》),而重審詩(shī)歌史上的相關(guān)命名乃至“重寫(xiě)詩(shī)歌史”的契機(jī)正蘊(yùn)含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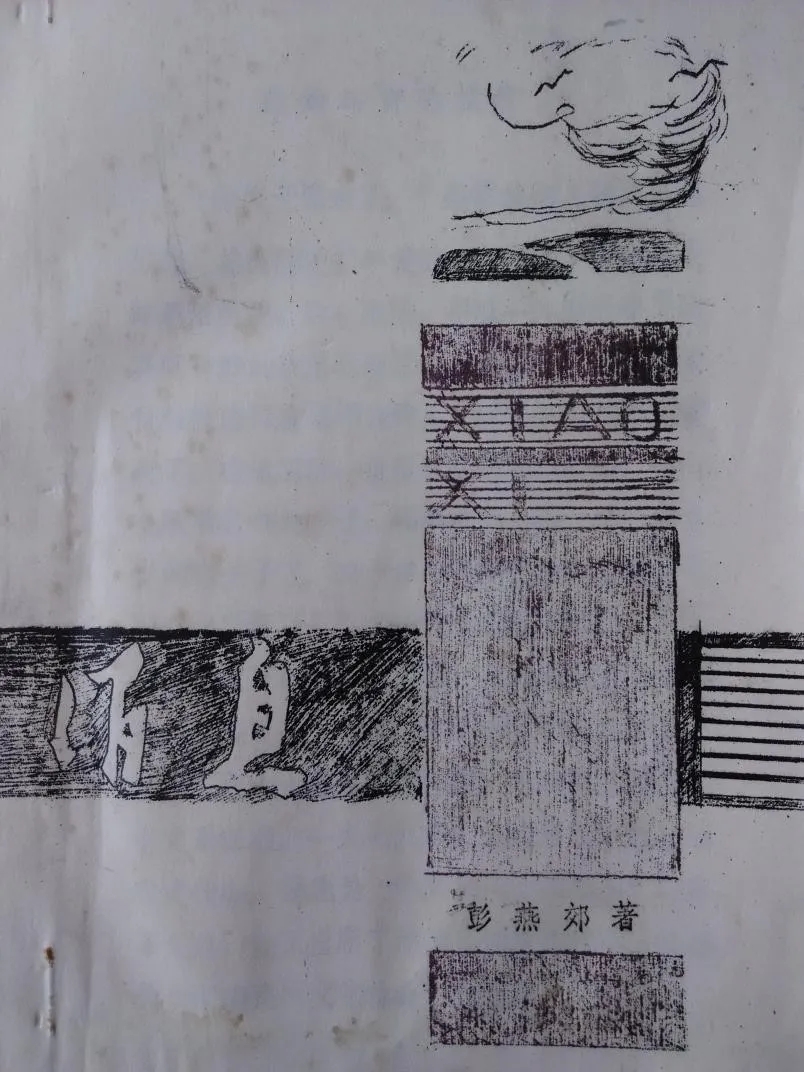
油印詩(shī)集《消息》,1980年
二、“衰年變法”:在探索中超越
在《彭燕郊評(píng)傳》中,著者劉長(zhǎng)華曾結(jié)合彭的自述“我愛(ài)疏離,又怕寂寞,我也需要熱鬧……”,和其剛剛走上詩(shī)歌道路時(shí)所寫(xiě)的《朝花》中的詩(shī)句“漸漸地,漸漸地我想起了/我是如何被生活所折磨/掙扎中我是如何固執(zhí)地/熱愛(ài)著生活”,認(rèn)為“這種少年老成充分地表露了彭燕郊自小就有既想逃離世俗卻又不甘愿疏離的多維性和矛盾性”[9]。在我看來(lái),“多維性和矛盾性”同樣可以作為剖析彭燕郊晚年詩(shī)人心態(tài)的一個(gè)重要角度:一方面,彭燕郊是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邊緣人,但另一方面,彭燕郊在藝術(shù)生活上卻是一個(gè)責(zé)任感極強(qiáng)的進(jìn)取者,兩者以對(duì)立統(tǒng)一的方式集中在彭燕郊身上,后者是對(duì)前者造成的“存在感”缺失給予了有效的補(bǔ)充并最終使其獲得一種“生命的價(jià)值”[10]。
或許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為深入地理解彭燕郊為何服膺胡風(fēng)的名言“詩(shī)人和戰(zhàn)士是一個(gè)神的兩個(gè)化身”。在彭燕郊看來(lái),“詩(shī)人需要的只是做個(gè)詩(shī)人,做一個(gè)作為藝術(shù)創(chuàng)造者、一個(gè)精神勞動(dòng)者的詩(shī)人,因?yàn)樗吘故巧鐣?huì)的人,他和戰(zhàn)士都是一個(gè)神的化身,他也是戰(zhàn)士,不同于一般戰(zhàn)士的戰(zhàn)士”[11]。同樣,也只有這樣,才能理解彭燕郊為何會(huì)在重返詩(shī)壇之后、可以享受生活之時(shí)仍然要“衰年變法”,因?yàn)椤安弧儭⒉惶剿鳎扔诜夤P”[12]。當(dāng)然,作為一個(gè)熟悉詩(shī)歌創(chuàng)作規(guī)律的詩(shī)人,彭燕郊深知任何一種探索都離不開(kāi)特定的時(shí)代。是以,在明確“歷史規(guī)定性”的制約下,他說(shuō):“一個(gè)詩(shī)人必須是站在為人類的美好明天斗爭(zhēng)的最前列。”[13]他的寫(xiě)作一如他詩(shī)中描述的那樣:“水是/要有自己的路的/……因?yàn)槭詹蛔∵@個(gè)勢(shì)頭/因?yàn)橹荒芤还蓜诺?向前跨出這一步,闖出這一步/那確實(shí)是/非常之自然,非常之自如,非常之合乎情理/非常之稱心如意的傾瀉,飛濺,散落”(《瀑布》),始終處于探索進(jìn)步的狀態(tài),并以此成為時(shí)代詩(shī)歌藝術(shù)高度的明證。
“衰年變法”作為一個(gè)動(dòng)態(tài)的過(guò)程,主要經(jīng)歷了以下三個(gè)發(fā)展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jì)80年代中期的“轉(zhuǎn)折”。彭燕郊曾自言:“80年代中期,調(diào)子忽然沉重起來(lái),是有什么預(yù)感嗎?不知道。只知道已經(jīng)在努力找尋或者說(shuō)開(kāi)辟一條新的道路了。開(kāi)始厭倦‘純粹’,純粹的美、純粹的詩(shī)等等,自己說(shuō)是‘變法’,想要的是不被認(rèn)為美的美,想寫(xiě)不是詩(shī)的詩(shī)。事實(shí)上幾年前就有這種沖動(dòng),這時(shí)候已經(jīng)接近決堤之勢(shì)。”[14]寫(xiě)于這一階段的《鋼卷尺》《繆斯情結(jié)》《三葉》《距離》《最后一個(gè)》《你我》《完人》《循環(huán)往復(fù)》《賞賜》,冷峻、焦灼、突兀,不時(shí)夾雜著碎片的結(jié)構(gòu),既顯示出“集聚的困厄和多余的勃勃雄心”(《鋼卷尺》),又隱含著“又一個(gè)終點(diǎn)帶給迷路人的喜悅”(《你我》),而這種“醞釀”已久的“變化”的目的是“追求一種‘完成’,一種‘完善’,實(shí)現(xiàn)自我”[15]。
第二階段,是20世紀(jì)80年代后期的“深化”。對(duì)于寫(xiě)于80年代后期的《罪淚》《心字》《放射》《碰撞》《芭蕉葉上詩(shī)》《湖濱之夜》《神話》《站穩(wěn)腳根》《傘骨》《話語(yǔ)》《新鮮》等作品,彭燕郊自述:“難忘的年代,強(qiáng)迫每一個(gè)人思考人類命運(yùn)的年代,除非逃避,除非自我蒙蔽,不可能不思考。終于明白:詩(shī),不單單是抒情;現(xiàn)代人的抒情,可以也應(yīng)該是思考的抒情。詩(shī)當(dāng)然應(yīng)該美,思考在詩(shī)里,應(yīng)該以詩(shī)的美表現(xiàn)。不容易做到,但應(yīng)該努力做到。思考要達(dá)到的是對(duì)世界的詩(shī)意的理解。”[16]對(duì)比以往的寫(xiě)作,彭燕郊可謂經(jīng)歷了一次詩(shī)藝層面上的“自我揚(yáng)棄”并越來(lái)越強(qiáng)調(diào)一種“內(nèi)心的審視”。他既追求詩(shī)歌技藝的精進(jìn),同時(shí)也反復(fù)追問(wèn)詩(shī)歌本身:“寫(xiě)的什么?寫(xiě)給誰(shuí)?……寫(xiě)些什么?寫(xiě)給誰(shuí)?(《芭蕉葉上詩(shī)》)透過(guò)這些語(yǔ)句和非整齊化排列的形式,人們不僅可以看到一個(gè)探索者的“自覺(jué)”,而且還能感受到風(fēng)格初變后的“焦灼”與“沉重”!
第三階段,是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lái)的“匯通”。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的彭燕郊首先感受到了時(shí)代語(yǔ)境變化的壓力,然而這種壓力在靜下心來(lái)思考之余,不過(guò)是個(gè)體的限度和詩(shī)人慣有的敏感與憂慮。“人們常說(shuō)的‘失落感’、‘三信危機(jī)’,我不能沒(méi)有,而且來(lái)得還更早些,早到半個(gè)世紀(jì)前就有了”[17]。既然思緒一貫如此,倒不如找尋“變”與“不變”之間的平衡點(diǎn),像《氣息》中描述的那樣,將所有經(jīng)歷、感受到的氣息融合在一起,包括“誰(shuí)也不知道的不屬于任何人只屬于我的氣息”,然后“氣息的涌動(dòng)剛剛開(kāi)始”。在此過(guò)程中,在探索中超越當(dāng)然是一次縱的拓展,但也同樣可以是一次橫的擴(kuò)張,“質(zhì)樸、平淡是可以和絢麗、奇突并存的”[18],彭燕郊的詩(shī)也隨即在內(nèi)容和形式上走向更為廣闊、立體的境界。
如果說(shuō)以上所述更多是從心靈史的角度反映了彭燕郊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lái)詩(shī)歌的“衰年變法”,那么,具體至文本,“衰年變法”又可以在意象和形式上找到相應(yīng)的主線。80年代之后彭燕郊的詩(shī)歌創(chuàng)作在意象上明顯呈現(xiàn)了從“樹(shù)”及一些植物向“光”及相關(guān)物象漸進(jìn)的趨勢(shì)。回顧彭燕郊創(chuàng)作的歷史:從30年代末期初登詩(shī)壇,“原野”和“土地”就是彭燕郊詩(shī)歌的重要主題,并由此形成了相應(yīng)的意象選擇和意象群。80年代復(fù)出后的彭燕郊相繼寫(xiě)有《畫(huà)仙人掌》《懷榕樹(shù)》《林語(yǔ)》《水杉》以及《巖衣草》《季節(jié)性》《小花》等作品。“樹(shù)”及植物意象的反復(fù)使用一方面使人聯(lián)想起彭燕郊寫(xiě)于40年代的那株“孤單”與“高大”的《風(fēng)前大樹(shù)》,另一方面預(yù)示著彭燕郊詩(shī)歌視野在多年之后的一種收縮。他期待將詩(shī)意聚焦于更為具體的物象之上,或靠得如此緊密、光影相間,或剛強(qiáng)與柔美并濟(jì)、在以小見(jiàn)大中波及廣闊的原野,有著“思考者的冷靜”、引發(fā)“詩(shī)人癡迷的幻想”。隨著寫(xiě)作的拓展,彭燕郊的詩(shī)在意象上開(kāi)始向“光”及其相關(guān)物象傾斜。《德彪西〈月光〉語(yǔ)譯》《漂瓶》《無(wú)色透明的下午》《螢光》《混沌初開(kāi)》以及反復(fù)浮現(xiàn)于詩(shī)中的“光”,使彭燕郊的詩(shī)歌由“實(shí)”而“虛”——“光”不僅凝結(jié)著希望、生命、思考和智慧,還包括詩(shī)人自我人格的建構(gòu),因?yàn)樵?shī)中的“我”也曾在“無(wú)色透明的下午”被其“凈化”,也曾在“混沌初開(kāi)”時(shí)浴“光”重生、表達(dá)“超越”式的“心路歷程”[19]。這種意象(群)的轉(zhuǎn)換,使彭燕郊的詩(shī)相對(duì)于過(guò)往和當(dāng)下的同時(shí)具有了主題學(xué)的意義,承載著彭燕郊詩(shī)歌創(chuàng)作的思想的變遷及其內(nèi)在指向。與之相應(yīng)的,還有識(shí)別起來(lái)更為顯著的形式的變化。“對(duì)話體”“樓梯體”特別是長(zhǎng)詩(shī)、散文詩(shī)的大量涌現(xiàn)與實(shí)踐,意味著彭燕郊渴望通過(guò)形式的變化和語(yǔ)言的增殖,來(lái)擴(kuò)展詩(shī)的表現(xiàn)維度,而其背后潛藏的自然是有話要說(shuō)、寫(xiě)作能力的增強(qiáng)以及對(duì)當(dāng)代詩(shī)歌想象力日趨匱乏進(jìn)行挑戰(zhàn)。
在晚年接受訪談時(shí),彭燕郊認(rèn)為“我理想中的好詩(shī)還沒(méi)有寫(xiě)出來(lái)”。彭燕郊計(jì)劃寫(xiě)一首比《混沌初開(kāi)》更長(zhǎng)的散文詩(shī)《眼睛》,以此來(lái)“折射時(shí)代”,另外還有一首敘事詩(shī)[20]。然而,由于2008年3月31日辭世,這兩個(gè)計(jì)劃并未完成。不過(guò),從其在耄耋之年依然期待通過(guò)寫(xiě)作回饋時(shí)代,可以說(shuō)彭燕郊對(duì)自己的詩(shī)歌創(chuàng)作是非常苛責(zé)的,他將詩(shī)歌視為生命,而探索與超越也就這樣成為其詩(shī)歌生命的伴生物。

彭燕郊的主要作品
三、“中國(guó)式現(xiàn)代主義”理論的建構(gòu)
彭燕郊不僅是一位詩(shī)人,還是一位詩(shī)歌理論家。20世紀(jì)80年代之后,年逾六旬的彭燕郊在回顧現(xiàn)代詩(shī)歌歷史以及不斷和學(xué)生們談詩(shī)的過(guò)程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詩(shī)學(xué)理論。其以現(xiàn)代精神為底蘊(yùn)的理論主張,不僅和他的創(chuàng)作相互促進(jìn),而且還豐富了中國(guó)現(xiàn)代詩(shī)歌的理論建設(shè)。
出于對(duì)詩(shī)歌現(xiàn)代意識(shí)的認(rèn)同,彭燕郊的詩(shī)學(xué)理論從辯詰“浪漫主義”開(kāi)始。80年代中期,當(dāng)人們還沉浸于激動(dòng)人心的年代并常常談及創(chuàng)造方法和文學(xué)思潮意義上的浪漫主義時(shí),彭燕郊就曾在香港《大公報(bào)》刊發(fā)一系列“告別浪漫主義”為主題的札記,這些札記后來(lái)收進(jìn)《和亮亮談詩(shī)》作為“今詩(shī)話叢書(shū)”之一于生活·讀書(shū)·新知三聯(lián)書(shū)店出版(1991),此外,他還寫(xiě)有《兩世紀(jì)之交,變風(fēng)變雅:語(yǔ)言苦惱》《兩世紀(jì)之交,變風(fēng)變雅:浪漫主義困惑》等文章。通過(guò)這些收入不同版本文集時(shí)有著不同名字的文章,彭燕郊先后梳理了西方現(xiàn)代詩(shī)歌和中國(guó)現(xiàn)代詩(shī)歌的發(fā)展歷程,逐步確立了自己的詩(shī)學(xué)理路。因19世紀(jì)以來(lái)世界詩(shī)歌的發(fā)展軌跡是“現(xiàn)代主義逐步取代浪漫主義”,所以彭燕郊選擇從浪漫主義談起。浪漫主義在反對(duì)新古典主義時(shí)具有積極進(jìn)步的意義,但隨著社會(huì)生活和文學(xué)的發(fā)展,浪漫主義逐漸暴露了自身的弱點(diǎn),直到波德萊爾以“文學(xué)史上罕見(jiàn)的真誠(chéng)和藝術(shù)追求勇氣,第一個(gè)進(jìn)入現(xiàn)代詩(shī)領(lǐng)域,翻開(kāi)了文學(xué)史新的一頁(yè)”[21]。波德萊爾的先鋒探索使之成為“新、舊文學(xué)交界處的分水嶺,現(xiàn)代文學(xué),首先是現(xiàn)代詩(shī)的源頭就在他腳下。”從波德萊爾開(kāi)始,現(xiàn)代詩(shī)人逐步擺脫、拋棄了浪漫主義,“拒絕把生活簡(jiǎn)單化或‘凈化’,拒絕空洞的歡呼或哀嘆”[22],現(xiàn)代詩(shī)歌以“思想的火花和痛苦的思索過(guò)程留下的一道道印跡”,代替浪漫主義高蹈而懸浮的簡(jiǎn)單抒情,“現(xiàn)代詩(shī)歌不同于浪漫主義及此前所有詩(shī)歌之處,是用思考代替了抒情的主體地位”[23]。從波德萊爾開(kāi)始,經(jīng)過(guò)魏爾倫、蘭波、馬拉美、瓦雷里、阿波里奈爾、布勒東到英美意象派和艾略特,再?gòu)陌蕴氐浆F(xiàn)在,“將近一個(gè)半世紀(jì)的現(xiàn)代詩(shī)歷程,已經(jīng)使它具有自己的新的特點(diǎn)”:“現(xiàn)代詩(shī)的藝術(shù)革新的第一個(gè)特征是感受和表現(xiàn)現(xiàn)實(shí)的新的方式和新的形象塑造方法”;“現(xiàn)代詩(shī)藝術(shù)革新的另一個(gè)特征是語(yǔ)言方面不斷的探索。語(yǔ)言革新和內(nèi)容革新緊相關(guān)聯(lián),隨著出現(xiàn)的是形式的革新。”[24]在彭燕郊看來(lái),現(xiàn)代詩(shī)豐富多變是其實(shí)驗(yàn)性的結(jié)果,而實(shí)驗(yàn)性的出現(xiàn)又是高速發(fā)展的現(xiàn)代生活在精神生活領(lǐng)域的反映。考察現(xiàn)代詩(shī)的藝術(shù)成就不能沿襲舊的美學(xué)標(biāo)準(zhǔn)和批評(píng)方法,只能依據(jù)現(xiàn)代詩(shī)本身提供的復(fù)雜內(nèi)容進(jìn)行客觀、公正的評(píng)價(jià)。在此過(guò)程中,“現(xiàn)代性是現(xiàn)代詩(shī)的基本特征,世界性或全人類性則應(yīng)該是現(xiàn)代性的主要內(nèi)容”[25]。
相對(duì)于西方現(xiàn)代詩(shī)的沿革,彭燕郊在梳理中國(guó)現(xiàn)代詩(shī)歷史時(shí)首先是將其納入世界視野之中。中國(guó)的現(xiàn)代詩(shī)出現(xiàn)于波德萊爾及其代表作《惡之花》產(chǎn)生劃時(shí)代影響之后,“魯迅是中國(guó)第一個(gè)真正具有現(xiàn)代意識(shí)的作家,魯迅是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的開(kāi)拓者。”在新詩(shī)方面,魯迅的“《野草》和《惡之花》一樣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可作為“開(kāi)一代詩(shī)風(fēng)”的經(jīng)典之作。“《野草》是自有新詩(shī)以來(lái)最富現(xiàn)代感、世界感的真正的新的詩(shī)。從實(shí)質(zhì)上看,《野草》一直影響著新詩(shī)的發(fā)展……始終是新詩(shī)的精神旗幟。”[26]出于對(duì)現(xiàn)代中國(guó)社會(huì)的了解和經(jīng)歷過(guò)的現(xiàn)實(shí)體驗(yàn),彭燕郊在談?wù)撝袊?guó)現(xiàn)代詩(shī)發(fā)展軌跡時(shí),使用了“中國(guó)式的現(xiàn)代主義”即“可以稱為現(xiàn)代的現(xiàn)實(shí)主義的現(xiàn)代主義”的概念。他將撥亂反正二十多年來(lái)新生的詩(shī)人作為當(dāng)今新詩(shī)的“主力”和“希望”,認(rèn)為“中國(guó)式現(xiàn)代主義詩(shī)歌構(gòu)建的任務(wù)必須由他們來(lái)完成”[27]。表明他一直是以發(fā)展的眼光考察中國(guó)現(xiàn)代詩(shī)的歷史:讓現(xiàn)代詩(shī)與中國(guó)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聯(lián)系在一起,探索其進(jìn)步的可能與規(guī)律,彭燕郊既看到了現(xiàn)代詩(shī)發(fā)展的普遍性,也注意到現(xiàn)代詩(shī)發(fā)展的特殊性,這種認(rèn)知方式有助于其現(xiàn)代詩(shī)理論客觀、公正、深入地展開(kāi)。
彭燕郊的現(xiàn)代詩(shī)學(xué)理論屬于典型的詩(shī)人學(xué)者式研究。其對(duì)于現(xiàn)代詩(shī)歷史的梳理,有明顯的實(shí)證特點(diǎn),有理有據(jù)。當(dāng)然,由于其間融入了詩(shī)人的體驗(yàn)和感悟,所以難免在感情充沛之余,有較為明顯的主觀色彩,其邏輯脈絡(luò)也時(shí)常雜糅在一起。不過(guò),無(wú)論怎樣,他的詩(shī)學(xué)理論有明顯的個(gè)人特色。在梳理現(xiàn)代詩(shī)歷史發(fā)展過(guò)程中,他相繼觸及了詩(shī)人、創(chuàng)作方法、特征等一系列關(guān)于現(xiàn)代詩(shī)的結(jié)構(gòu)層次,而以“思考——?jiǎng)?chuàng)造”為主線的詩(shī)學(xué)觀念,又使其詩(shī)歌理論具有相當(dāng)程度上的實(shí)踐價(jià)值。
“思考”不僅是彭燕郊詩(shī)歌的重要起點(diǎn),而且也是其理解現(xiàn)代詩(shī)的重要標(biāo)準(zhǔn)。“思考”會(huì)寫(xiě)出沉思的詩(shī)、成熟的詩(shī)。對(duì)于彭燕郊來(lái)說(shuō),“思考”可上溯至波德萊爾,“從波德萊爾開(kāi)始,詩(shī)人們由抒發(fā)轉(zhuǎn)向內(nèi)省,不是現(xiàn)代主義的美學(xué)方法教會(huì)詩(shī)人們?nèi)ニ伎迹乾F(xiàn)代人——現(xiàn)代詩(shī)人的思考教會(huì)詩(shī)人創(chuàng)造新的美學(xué)方法。”[28]“思考”是現(xiàn)代詩(shī)的重要特征,“現(xiàn)代詩(shī)必須要有思考……一個(gè)真正的思考者,思考的應(yīng)該顯示為一種人文關(guān)懷。我們現(xiàn)在缺少的就是人文關(guān)懷,就是對(duì)于人類生存現(xiàn)狀和未來(lái)的終極關(guān)懷。”[29]因?yàn)椤八伎肌保F(xiàn)代詩(shī)擁有了深度呈現(xiàn)不斷處于變化狀態(tài)的現(xiàn)實(shí)生活的能力。在《再會(huì)吧,浪漫主義》《兩世紀(jì)之交,變風(fēng)變雅:浪漫主義困惑》《虔誠(chéng)地走近詩(shī)》《學(xué)詩(shī)心語(yǔ)》等文章中,彭燕郊充分闡釋了“思考”之于現(xiàn)代詩(shī)的意義:“以思考為第一選擇的,思考成為第一沖動(dòng),正如抒情成為浪漫主義詩(shī)人的第一沖動(dòng),現(xiàn)代詩(shī)人在思考中獲得理性的升華,從而獲得自我靈魂約束的能力。現(xiàn)代詩(shī)人以思考為詩(shī)人性格特征,浪漫主義詩(shī)人則以情緒化的語(yǔ)言為性格特征,終于導(dǎo)致了不信任感,而現(xiàn)代詩(shī)人的啟示性語(yǔ)言則以思考引發(fā)思考,他們深知,思考是詩(shī)人的天賦,詩(shī)人的本分,詩(shī)人的歷史使命。”[30]在彭燕郊看來(lái),“思考”具有“反思的理性”,有助于深入地表達(dá)情感的內(nèi)涵與分量,從而使詩(shī)歌從浪漫主義的“抒情”及“情緒化的語(yǔ)言”,轉(zhuǎn)化為此在的“理性”的“啟示性語(yǔ)言”。這樣的詩(shī)歌理路的形成與詩(shī)人反思浪漫主義和現(xiàn)代主義的特質(zhì)和演變有關(guān),而從時(shí)代演進(jìn)的角度來(lái)說(shuō),又與詩(shī)歌創(chuàng)作需要適應(yīng)并反映社會(huì)發(fā)展和現(xiàn)實(shí)生活密不可分。
“創(chuàng)造”是“思考”的結(jié)果,并與“思考”共同構(gòu)成現(xiàn)代詩(shī)人最主要的素質(zhì)。對(duì)于現(xiàn)代詩(shī)人應(yīng)有的“現(xiàn)代意識(shí)”,彭燕郊認(rèn)為——
生活在精神活動(dòng)前沿的現(xiàn)代詩(shī)人,必然比一般人更敏銳,更親切,更全面地感覺(jué)到它,他的創(chuàng)作心理、創(chuàng)作過(guò)程和創(chuàng)作成果,應(yīng)該更生動(dòng)、更深刻地反映現(xiàn)代意識(shí)和他在現(xiàn)代生活中的意義和作用……
現(xiàn)代詩(shī)人的文學(xué)活動(dòng)應(yīng)該從傳承型、守成型變?yōu)殚_(kāi)拓型、進(jìn)攻型、競(jìng)爭(zhēng)型,只有自己不斷地鼓舞自己才能鼓舞眾人。[31]
“現(xiàn)代意識(shí)”要求詩(shī)人保持探索意識(shí),具有先鋒性、實(shí)驗(yàn)性的藝術(shù)品格,就其結(jié)果來(lái)看,是強(qiáng)化了現(xiàn)代詩(shī)的自由精神和創(chuàng)造力。“要有膽量寫(xiě)不像詩(shī)的詩(shī)”,“文學(xué)藝術(shù)的天性是自由,從創(chuàng)意到創(chuàng)造的全過(guò)程都彌漫著自由精神”[32]。唯其如此,現(xiàn)代詩(shī)才會(huì)不斷產(chǎn)生新的詩(shī)學(xué)形態(tài),維系自身持續(xù)發(fā)展的內(nèi)在動(dòng)力。
以“現(xiàn)代”和“自由”為型構(gòu),彭燕郊的現(xiàn)代詩(shī)理論與中國(guó)新詩(shī)的發(fā)展保持著內(nèi)在的一致性。“現(xiàn)代人應(yīng)該寫(xiě)現(xiàn)代詩(shī)。現(xiàn)代詩(shī)應(yīng)該不同于古典主義的、浪漫主義的詩(shī),是現(xiàn)代主義的”[33]。對(duì)于現(xiàn)代詩(shī)創(chuàng)作,彭燕郊強(qiáng)調(diào)晚近的現(xiàn)代主義,但卻從未機(jī)械地照搬,他的現(xiàn)代主義取義于魯迅為俄國(guó)詩(shī)人勃洛克詩(shī)集《十二個(gè)》中譯本所作的“后記”中的一段話,即“是在用空想,即詩(shī)底幻想的眼,照見(jiàn)都會(huì)中的日常生活,將那朦朧的印象,加以象征化。將精氣吹入所描寫(xiě)的事象里,使它蘇生;也就是在庸俗的生活,塵囂的市街中,發(fā)見(jiàn)詩(shī)歌底要素。”[34]因此,他的“現(xiàn)代主義”是傾向于一種具體做法意義上甚至是只可意會(huì)不可言傳而非枯燥理論上的概念。而就彭燕郊個(gè)人來(lái)說(shuō),盡管他的每一首詩(shī)都力求做到“不同”,但他仍覺(jué)自己“不夠現(xiàn)代”,為此,他更注重“探索”和“借鑒”“了解整個(gè)詩(shī)歌潮流的大方向”[35]。彭燕郊自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lái)的詩(shī)歌道路生動(dòng)地實(shí)踐了他的詩(shī)學(xué)理論,他的理論與實(shí)踐互為依托,既體現(xiàn)了彭燕郊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同時(shí)也反映了他對(duì)于新詩(shī)的深切的關(guān)愛(ài)之情和晚年成熟狀態(tài)時(shí)應(yīng)有的沉潛和內(nèi)斂,而其關(guān)于現(xiàn)代詩(shī)的理論也由此成為中國(guó)新詩(shī)一份重要的文化財(cái)產(chǎn)。

彭燕郊的書(shū)架,肖振鋒攝影
四、散文詩(shī)的成就與貢獻(xiàn)
20世紀(jì)80年代之后彭燕郊還在散文詩(shī)創(chuàng)作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誕生了經(jīng)典之作。彭燕郊于30年代末期開(kāi)始散文詩(shī)創(chuàng)作,終生對(duì)這一詩(shī)體形式保持濃厚的興趣。結(jié)合其創(chuàng)作履歷可知:彭燕郊的散文詩(shī)受到魯迅《野草》的直接影響,遠(yuǎn)溯波德萊爾、惠特曼、屠格涅夫等大師,其具體指向是為了更加自由地表現(xiàn)現(xiàn)實(shí),并最終為散文詩(shī)擺脫詩(shī)歌的附庸地位做出了自己的貢獻(xiàn)。“在中國(guó)詩(shī)人中,彭燕郊是富于創(chuàng)造力的。他的散文詩(shī),保留了來(lái)自鄉(xiāng)土的秀美而又肆意加以破壞。他不倦地行走,探索,帶著自由加于他的創(chuàng)傷,努力找尋一種契合于現(xiàn)代中國(guó)和個(gè)人命運(yùn)的藝術(shù)形式。”[36]
20世紀(jì)80年代之后彭燕郊的散文詩(shī)創(chuàng)作和其現(xiàn)代詩(shī)理論觀念一脈相承,都是在詩(shī)的范疇內(nèi)追求最大限度的自由及以此實(shí)現(xiàn)的創(chuàng)造性。彭燕郊在談及散文詩(shī)創(chuàng)作時(shí)既涉及詩(shī)的散文美,也涉及散文詩(shī)。“散文美應(yīng)該包含音樂(lè)性,但這不完全是靠押韻,不能像中國(guó)舊詩(shī)那樣依靠押韻來(lái)限制節(jié)奏。散文美的新詩(shī)節(jié)奏變得豐富了……散文美的特點(diǎn)并不沖淡詩(shī)味,而且搞得好,能使詩(shī)味更濃。因?yàn)楸磉_(dá)可以更自然,而自然是最難獲得的。”[37]強(qiáng)調(diào)詩(shī)歌的散文美,與現(xiàn)代詩(shī)可以破除詩(shī)歌寫(xiě)作時(shí)一定要押韻、有形式的固有觀念有關(guān),現(xiàn)代詩(shī)即使不分行仍可借助“內(nèi)在的結(jié)構(gòu)”達(dá)到詩(shī)的本質(zhì),而且一旦以這種方式抵達(dá),會(huì)帶給人更為強(qiáng)烈的詩(shī)歌體驗(yàn)。結(jié)合彭燕郊對(duì)于詩(shī)歌散文美的看法,我們不難引申出是不是詩(shī)的關(guān)鍵,在于寫(xiě)作者自身的藝術(shù)素養(yǎng)和其對(duì)于詩(shī)歌本質(zhì)的理解,外在形式上的散文化不是詩(shī)味淡薄的必然前提。與詩(shī)歌的散文美相比,散文詩(shī)的理解“應(yīng)該更寬一些”,“容量”也“更大”一些[38]。在彭燕郊看來(lái),散文詩(shī)出現(xiàn)與發(fā)展,“首先是詩(shī)歌母題的變化,從抒情的詩(shī)發(fā)展為思考的詩(shī),現(xiàn)代人的豐富、復(fù)雜的感受和思考必然帶來(lái)新的審美需求,于是甚至連自由詩(shī)也承擔(dān)不了這種負(fù)荷,滿足不了這種需求,這樣就從自由詩(shī)發(fā)展到散文詩(shī)。”[39]
出于對(duì)現(xiàn)代詩(shī)發(fā)展軌跡的思考,同時(shí)也出于對(duì)日趨碎片化生活的適應(yīng),彭燕郊對(duì)散文詩(shī)這一表現(xiàn)形式充滿了信心,他認(rèn)為新詩(shī)有往“散文去的大趨勢(shì)”[40],甚至認(rèn)為現(xiàn)代散文詩(shī)是“最具活力的新詩(shī)體”“能引領(lǐng)新詩(shī)邁上坦途”[41]。他將《野草》視為中國(guó)新詩(shī)的經(jīng)典,而其散文詩(shī)寫(xiě)作也不時(shí)閃爍《野草》的痕跡或者說(shuō)與之氣韻相通,這是其散文詩(shī)創(chuàng)作起點(diǎn)頗高并隨著時(shí)間推移可以不斷深化的前提。20世紀(jì)80年代之后的彭燕郊曾和他人一起編譯“現(xiàn)代散文詩(shī)名著譯叢”,這一工作不僅反映彭燕郊對(duì)散文詩(shī)的鐘愛(ài),而且也深化了他對(duì)散文詩(shī)的理解。80年代以后的散文詩(shī)是彭燕郊詩(shī)歌文學(xué)創(chuàng)作與現(xiàn)實(shí)互動(dòng)的結(jié)果,同時(shí)也是其心境的反映。“散文詩(shī)在彭燕郊這里屬于‘寫(xiě)心’的載體,因此進(jìn)入他的散文詩(shī)文本,是更有助于我們?nèi)轿弧⑸羁趶降亍螝v’他的精神世界,并加深對(duì)他的分行詩(shī)歌的體認(rèn)。”[42]
就具體創(chuàng)作而言,散文詩(shī)由于散文化的傾向更能反映彭燕郊的心路歷程。《E=mc2》寫(xiě)出見(jiàn)到多年不通音訊的朋友們,感慨生命的時(shí)光、歲月的流逝,同時(shí)也寫(xiě)出一種“專注的、向內(nèi)的神情”,還有曾經(jīng)擁有過(guò)的“信念”和持續(xù)的“思考”,它們以生命的形式詮釋了愛(ài)因斯坦的定律。《漂瓶》是一曲“遠(yuǎn)行者”之歌:“漂流,無(wú)休止的攀登,望不到盡頭的,動(dòng)蕩、變幻的階梯,洶涌浪尖的野性撫摸和溫情拍擊。”“漂瓶”是“我”,“漂流”是經(jīng)歷,也是宿命,機(jī)遇與危險(xiǎn)并存。游歷張家界的組詩(shī)如《雨渡》《夜上天子山》《仙人橋》《觀景臺(tái),一種高度》等,總題可稱之為“爽籟清游”,雖是寄情山水,但“寄的是人的情,沒(méi)有這個(gè)情,哪里有詩(shī)。”[43]還有《夜路》《風(fēng)信子》《蛇睛》《螢光》等,讓人讀出《野草》的風(fēng)味:陰郁、晦澀、冷峻,或可見(jiàn)20世紀(jì)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社會(huì)語(yǔ)境迅速轉(zhuǎn)變?cè)谠?shī)人心靈上留下的投影。另外,彭燕郊散文詩(shī)創(chuàng)作中的“蕭颯氣氛”以及“憤世嫉俗”[44],一直被目為詩(shī)人的精神特征之一。
從藝術(shù)上看,彭燕郊認(rèn)為散文詩(shī)雖表面為散文形態(tài),但同樣具有音樂(lè)性特別是詩(shī)的節(jié)奏感。由于散文詩(shī)采用散文形式敘述、篇幅較長(zhǎng),所以只能依靠豐富和繁復(fù)的節(jié)奏來(lái)表達(dá)“現(xiàn)代人的生命困惑和精神創(chuàng)傷”[45]。比如,在結(jié)合具體作品后詩(shī)人曾指出:“我寫(xiě)《混沌初開(kāi)》,看起來(lái)像散文,但我很講究節(jié)律。我有一個(gè)時(shí)期寫(xiě)詩(shī)的時(shí)候,好像是在譜寫(xiě)一個(gè)交響曲一樣,一邊寫(xiě)一邊感覺(jué)就有旋律在伴隨著。就像在做一首交響曲一樣,講究?jī)?nèi)在的音樂(lè)性,情感的變化,音調(diào)的高低,也可以變調(diào),研究起來(lái)很有意思的。”[46]可以說(shuō),彭燕郊非常重視詩(shī)歌的節(jié)奏感,同時(shí)也必然要強(qiáng)調(diào)詩(shī)本身的語(yǔ)言使用和結(jié)構(gòu)上的渾然一體。他的散文詩(shī)因藝術(shù)而采用形式,而非從形式到藝術(shù),因而更強(qiáng)調(diào)非凡的腕力和現(xiàn)代性繁復(fù)甚至是混雜的精神品格。
當(dāng)然,最能代表彭燕郊散文詩(shī)創(chuàng)作實(shí)績(jī)同時(shí)也是確立其晚年詩(shī)歌地位的當(dāng)屬《混沌初開(kāi)》。以第二人稱“你”展開(kāi)敘述——“你已來(lái)到無(wú)涯際的空曠,界限已被超越,界限不再存在,悠長(zhǎng)的嘆息消失在悠長(zhǎng)忍受的終了。”像神話傳說(shuō)一樣,“混沌”是一種包容一切,無(wú)輕無(wú)重,取消時(shí)空界限的狀態(tài);“混沌”是起點(diǎn)也是終點(diǎn),無(wú)始無(wú)終。在這里“你”感受到無(wú)盡的孤獨(dú),直到被賦予生命的意義,然后是遭遇“第二我”,還有“非我”,最后是“光”的投入——“混沌初開(kāi),你將再次超越你自己。”
《混沌初開(kāi)》誕生之后,受到廣泛的贊譽(yù)。如公劉將其評(píng)價(jià)為“一部真正的長(zhǎng)詩(shī)……氣勢(shì)磅礴、光彩照人的長(zhǎng)詩(shī),記載了一個(gè)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中國(guó)文學(xué)家心路歷程的長(zhǎng)詩(shī)”[47]。詩(shī)人駱曉戈等則將其和道家文化和西方詩(shī)哲聯(lián)系在一起[48]。《混沌初開(kāi)》從1986年至1989年歷時(shí)三年,完稿時(shí)兩萬(wàn)余言,是一部當(dāng)之無(wú)愧的長(zhǎng)詩(shī),同時(shí)也堪稱中國(guó)現(xiàn)代知識(shí)分子的精神史詩(shī)。全詩(shī)分五個(gè)部分,想象奇特、汪洋恣肆、氣勢(shì)恢宏,讓人聯(lián)想到史前神話和今人對(duì)宇宙原初狀態(tài)的想象和推演。結(jié)合詩(shī)人的經(jīng)歷,《混沌初開(kāi)》是對(duì)其生命歷程和20世紀(jì)中國(guó)歷史進(jìn)程的一次總體性反思,但如果從“混沌初開(kāi)”、生命開(kāi)始加以推演,該詩(shī)則適用于人類歷史的反省和批判,同時(shí)也適用于每一個(gè)人的精神歷險(xiǎn)以及異化現(xiàn)象的叩問(wèn)。《混沌初開(kāi)》是彭燕郊對(duì)人類命運(yùn)特別是自我命運(yùn)的一次追問(wèn)和超越式的總結(jié),是彭燕郊詩(shī)學(xué)觀念、詩(shī)歌經(jīng)驗(yàn)的結(jié)晶,同時(shí)也是現(xiàn)代散文詩(shī)的巔峰之作,對(duì)于散文詩(shī)的發(fā)展和研究彭燕郊80年代以后的詩(shī)歌創(chuàng)作有著重要的意義。
在新詩(shī)史上,散文詩(shī)歷來(lái)發(fā)展不夠充分,其文體價(jià)值也常常受到質(zhì)疑。彭燕郊80年代以來(lái)的散文詩(shī)創(chuàng)作,接續(xù)了魯迅《野草》的傳統(tǒng),豐富了散文詩(shī)創(chuàng)作并極具時(shí)代性、實(shí)踐性的特質(zhì),因此可以這樣說(shuō):彭燕郊的散文詩(shī)大大提升了現(xiàn)代散文詩(shī)創(chuàng)作的實(shí)績(jī)與品格。
關(guān)于彭燕郊20世紀(jì)80年代之后詩(shī)歌創(chuàng)作還有很多話題,比如,將本文帶有修飾成分的“晚年”和薩義德在《論晚期風(fēng)格——反本質(zhì)的音樂(lè)與文學(xué)》中的“晚期風(fēng)格”[49],即可以指代一些偉大藝術(shù)家在生命臨近終結(jié)時(shí)其作品呈現(xiàn)出來(lái)的成熟狀態(tài)聯(lián)系起來(lái),或許會(huì)得出與以往文學(xué)史描述形成張力的結(jié)論。再比如,彭燕郊還是一位重要的“文藝組織者”,他在80至90年代,曾以籌劃者、組稿者和主編等不同身份,進(jìn)行了“詩(shī)苑譯林”“散文譯叢”“現(xiàn)代散文詩(shī)名著譯叢”和《國(guó)際詩(shī)壇》《現(xiàn)代世界詩(shī)壇》《外國(guó)詩(shī)辭典》的編撰工作,這些工作不僅是其為中國(guó)當(dāng)代詩(shī)壇的另一重大貢獻(xiàn),而且還與其詩(shī)學(xué)理論和創(chuàng)作有著十分密切的關(guān)系。只是限于篇幅,無(wú)法一一展開(kāi)。2008年3月,彭燕郊安靜地去世,留下很多未完的探索,每每回想起來(lái)都令人感慨萬(wàn)千、心生遺憾。彭燕郊是一位跨越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史的重要詩(shī)人和詩(shī)歌理論家,他的創(chuàng)作與觀念是現(xiàn)代詩(shī)歌一份重要的詩(shī)歌遺產(chǎn),不僅對(duì)于當(dāng)代詩(shī)歌創(chuàng)作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而且還對(duì)現(xiàn)代詩(shī)學(xué)理論建設(shè)有著重要的參考價(jià)值,值得我們反復(fù)閱讀、研究與思考。在其一百周年誕辰之際,筆者選擇其20世紀(jì)80年代之后的創(chuàng)作寫(xiě)下些許淺顯的文字,權(quán)作紀(jì)念這位始終于邊緣沉默的詩(shī)人,并以此表達(dá)崇高的敬意。
注釋:
[1]結(jié)合已出版的幾本有代表性的詩(shī)歌史,如洪子誠(chéng)與劉登翰的《中國(guó)當(dāng)代新詩(shī)史》(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3年版)、洪子誠(chéng)與劉登翰的《中國(guó)當(dāng)代新詩(shī)史》(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修訂版)和程光煒的《中國(guó)當(dāng)代詩(shī)歌史》(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版)等,“歸來(lái)的詩(shī)群”的基本義可理解為對(duì)自20世紀(jì)50年代起由于各種原因停止寫(xiě)作和發(fā)表作品的一大批詩(shī)人的統(tǒng)稱。“歸來(lái)的詩(shī)群”就成員來(lái)看既包括艾青、公劉等老一輩詩(shī)人,也包括對(duì)“七月派詩(shī)人群”和“中國(guó)新詩(shī)派群體”(“九葉詩(shī)群”)的重新確認(rèn)。無(wú)論從個(gè)體經(jīng)歷還是他者認(rèn)知的角度上看,彭燕郊都符合上述“標(biāo)準(zhǔn)”。至于說(shuō)《白色花》的出版,強(qiáng)化了“歸來(lái)的詩(shī)群”與“七月詩(shī)派”的關(guān)系,是因?yàn)椤栋咨ā纷鳛橐徊吭?shī)合集,標(biāo)志著“七月詩(shī)派”已恢復(fù)名譽(yù)、重返詩(shī)壇。
[2]如在彭燕郊口述、易彬整理的《我不能不探索:彭燕郊晚年談話錄》中,彭燕郊就認(rèn)為“我這個(gè)人,一輩子都是一個(gè)邊緣人物”。第64頁(yè),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
[3][12][13][19][20][29][35][38][40]彭燕郊口述;易彬整理:《我不能不探索:彭燕郊晚年談話錄》,第28頁(yè),第59頁(yè),第65頁(yè),第34頁(yè),第82—86頁(yè),第62頁(yè),第60頁(yè),第76—77頁(yè),第69頁(yè),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
[4][5][6]彭燕郊:《彭燕郊詩(shī)文集》(詩(shī)卷·下),第357頁(yè),第357頁(yè),第357頁(yè),湖南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
[7]龔旭東:《一朵充滿奇跡的火焰——彭燕郊綜論》,《理論與創(chuàng)作》2004年第5期。
[8][9][41][42]劉長(zhǎng)華:《彭燕郊評(píng)傳》,第200—201頁(yè),第7頁(yè),第243—268頁(yè),第268頁(yè),湖南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
[10][37][46]夏義生、唐祥勇、歐娟:《以詩(shī)歌表征生命的價(jià)值——彭燕郊先生訪談錄》,《理論與創(chuàng)作》2004年第5期。
[11][32][33]彭燕郊:《學(xué)詩(shī)心悟》,《彭燕郊詩(shī)文集》(評(píng)論卷),第291頁(yè),第296頁(yè),第298頁(yè),湖南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
[14][16][18]彭燕郊:《彭燕郊詩(shī)文集·后記》(詩(shī)卷·下),第358頁(yè),第358頁(yè),第358頁(yè),湖南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
[15]顏雄:《詩(shī)之苦旅——與彭燕郊先生對(duì)談》,《湘潭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4年第5期。
[17][43][44]彭燕郊:《彭燕郊詩(shī)文集·后記》(散文詩(shī)卷),第370頁(yè),第370頁(yè),第370頁(yè),湖南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
[21][22][23][24][25][26][28][31]彭燕郊:《再會(huì)吧,浪漫主義》,彭燕郊:《彭燕郊詩(shī)文集》(評(píng)論卷),第7頁(yè),第6—25頁(yè),第7頁(yè),第62頁(yè)、第65—66頁(yè),第68頁(yè),第82頁(yè),第14頁(yè),第106—108頁(yè),湖南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
[27]彭燕郊:《虔誠(chéng)地走近詩(shī)》,彭燕郊:《彭燕郊詩(shī)文集》(評(píng)論卷),第192頁(yè),湖南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
[30][45]孟澤:《〈彭燕郊詩(shī)文集(評(píng)論卷)〉序》,第4頁(yè),第25頁(yè),湖南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
[34]魯迅:《十二個(gè)后記》(1926),《魯迅全集》第7卷,第299頁(yè),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年版。
[36]林賢治:《〈彭燕郊詩(shī)文集(散文詩(shī)卷)〉序》,第8頁(yè),湖南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
[39]彭燕郊:《我學(xué)會(huì)了學(xué)習(xí)嗎》,彭燕郊:《彭燕郊詩(shī)文集》(評(píng)論卷),第286頁(yè),湖南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
[47]公劉:《靈魂的獨(dú)白——讀詩(shī)人彭燕郊新作〈混沌初開(kāi)〉》,《堅(jiān)貞的詩(shī)路歷程:彭燕郊評(píng)介文集》,趙樹(shù)勤選編,第416頁(yè),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
[48]具體內(nèi)容見(jiàn)駱曉戈:《尋找再生之地——讀彭燕郊近作〈混沌初開(kāi)〉》,《堅(jiān)貞的詩(shī)路歷程:彭燕郊評(píng)介文集》,趙樹(shù)勤選編,第375—380頁(yè),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
[49]具體可參見(jiàn)愛(ài)德華·W.薩義德所著的《論晚期風(fēng)格——反本質(zhì)的音樂(lè)與文學(xué)》中的相關(guān)內(nèi)容,閻嘉譯,“導(dǎo)論”第1—7頁(yè),生活·讀書(shū)·新知三聯(lián)書(shū)店200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