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大杰:為中國(guó)文學(xué)史書寫奠定重要里程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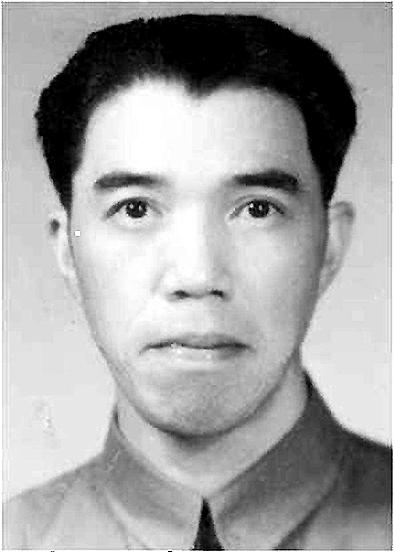
劉大杰(1904—1977),古典文學(xué)研究家。湖南岳陽(yáng)人。曾任上海大東書局編輯,安徽大學(xué)、暨南大學(xué)教授等。新中國(guó)成立后任復(fù)旦大學(xué)教授,并曾兼任中國(guó)作協(xié)上海分會(huì)副主席。早年從事小說(shuō)創(chuàng)作,以及外國(guó)文學(xué)的翻譯和研究,后致力于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史的研究。著有《中國(guó)文學(xué)發(fā)展史》 《魏晉思想論》 《〈紅樓夢(mèng)〉的思想與人物》等。

《中國(guó)文學(xué)發(fā)展史》
他被譽(yù)為“20世紀(jì)最有才氣的中國(guó)文學(xué)史家”,其代表作《中國(guó)文學(xué)發(fā)展史》一經(jīng)問(wèn)世,便被視為“文學(xué)史研究領(lǐng)域內(nèi)具有系統(tǒng)性、成就最為突出的一部文學(xué)史樣本,確定了中國(guó)文學(xué)史著作的基本范式”;他又是作家,創(chuàng)作過(guò)大量短篇小說(shuō)、劇本、舊體詩(shī)集;他還是文學(xué)翻譯家,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施尼茨勒等多位歐美重要作家的譯作都出自他手——這位文學(xué)園地里的“多面手”,便是劉大杰。
文學(xué)園地里的“多面手”:從作家、翻譯家到轉(zhuǎn)入古代文學(xué)研究
1904年,劉大杰出生于湖南岳陽(yáng)的一個(gè)鄉(xiāng)村。和同齡人比起來(lái),他的成長(zhǎng)經(jīng)歷異常艱辛,他在自己的一部長(zhǎng)篇自傳小說(shuō)《三兒苦學(xué)記》中有過(guò)記述:自幼失怙,家境貧寒,沒(méi)有受過(guò)正規(guī)小學(xué)教育,小小年紀(jì)便扛起了生活的重?fù)?dān)——種過(guò)地、放過(guò)牛、做過(guò)童工,但在極端艱難的條件下,憑借著自強(qiáng)不息的“苦學(xué)”,劉大杰考入免費(fèi)的旅鄂中學(xué),終于為自己的命運(yùn)鑿開(kāi)了一扇窗。
但走上文學(xué)道路卻絕非偶然,正如他所說(shuō):“母親死時(shí),我只有十二歲。她在秋夜紡紗的燈光下,教給了我兩本書:《唐詩(shī)三百 首》和《兒女英雄傳》,在我窮苦的幼年,得到了文學(xué)趣味的培養(yǎng)。”(林冠夫、林東海,《緬懷與思考》)1922年,劉大杰考入武昌高等師范中文系。那時(shí)的高師中文系群英薈萃,有黃侃、胡小石、郁達(dá)夫等著名學(xué)者。在高師,除了研究漢賦、《文心雕龍》、唐詩(shī)宋詞等“必修課”,劉大杰對(duì)新文學(xué)更感興趣,胡適之、魯迅、周作人、郭沫若、郁達(dá)夫等先生的文章和譯文都是填充他課余生活的精神食糧。為此,他還被視為“新派”,挨了系主任的一頓“教訓(xùn)”。(《追求藝術(shù)的苦悶》)
在高師,對(duì)劉大杰影響最深的是郁達(dá)夫。郁達(dá)夫主講“文學(xué)概論”和“小說(shuō)創(chuàng)作”,其中不僅有自己從事創(chuàng)作的切身經(jīng)驗(yàn),也介紹了國(guó)外新潮的文藝思想,對(duì)劉大杰很有吸引力。也正是在郁達(dá)夫的鼓勵(lì)下,他正式走上了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道路。那是在進(jìn)高師的第三年,當(dāng)時(shí)從家里逃婚出來(lái)、手中一文錢也沒(méi)有的劉大杰寄居在學(xué)校一間小房里,“心里充滿著說(shuō)不出的壓迫的情緒,好像非寫出來(lái)不可似的”。于是,他以逃婚為題材創(chuàng)作了小說(shuō)《桃林寺》,經(jīng)郁達(dá)夫介紹,刊登于《晨報(bào)副刊》,從此開(kāi)啟了他的創(chuàng)作生涯。
青年時(shí)期,劉大杰創(chuàng)作的小說(shuō)、戲劇作品有《昨日之花》 《三兒苦學(xué)記》 《她病了》 《十年后》《渺茫的西南風(fēng)》 《盲詩(shī)人》等。他的創(chuàng)作充滿著對(duì)底層人民的同情,并提出了一些尖銳的社會(huì)問(wèn)題,被稱為“問(wèn)題小說(shuō)”。郁達(dá)夫在《青年界》上發(fā)表評(píng)《昨日之花》的文章,對(duì)他關(guān)注現(xiàn)實(shí)的“問(wèn)題意識(shí)”予以肯定: “我看了劉先生的作品之后,覺(jué)得風(fēng)氣在轉(zhuǎn)換了,轉(zhuǎn)向新時(shí)代去的作品以后會(huì)漸漸產(chǎn)生出來(lái)了。”
在文壇里馳騁一陣,劉大杰意識(shí)到,“沒(méi)有深沉的文學(xué)修養(yǎng),沒(méi)有豐富的人生經(jīng)驗(yàn),想在文學(xué)上有什么大的成就,這是一件極難的事情”。(《追求藝術(shù)的苦悶》)在郁達(dá)夫的鼓勵(lì)和幫助下,他于1926年初赴日留學(xué),專攻歐洲文學(xué)。在日本的六年讓劉大杰系統(tǒng)性地掌握了世界文學(xué)知識(shí),深入研究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易卜生、福羅貝爾、左拉、蕭伯納等大文豪的思想和作品,“愈是讀他們的作品,愈是愛(ài)他們,也愈是愛(ài)文學(xué),想把自己的生命,獻(xiàn)給文學(xué)的決心,也就一天天地堅(jiān)定了”。他將研究重點(diǎn)轉(zhuǎn)向外國(guó)文學(xué)的翻譯與介紹,先后翻譯了托爾斯泰的《高加索囚人》、杰克·倫敦的《野性的呼喚》、顯克維支的《苦戀》、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癡》、屠格涅夫的《兩朋友》、雪萊的《雪萊詩(shī)選》等世界文學(xué)名著,并撰有《托爾斯泰研究》《易卜生研究》《德國(guó)文學(xué)大綱》《德國(guó)文學(xué)簡(jiǎn)史》《表現(xiàn)主義文學(xué)》《東西文學(xué)評(píng)論》等專著。 (林冠夫、林東海,《緬懷與思考》)
早年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經(jīng)歷練就了劉大杰的一支生花妙筆,世界文學(xué)翻譯與研究經(jīng)歷賦予了他開(kāi)闊的文化視野和深厚的理論功底,但這些都不是劉大杰最終的學(xué)術(shù)歸宿,而是他轉(zhuǎn)入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和中國(guó)文學(xué)史研究的“鋪路石”——正如復(fù)旦大學(xué)中文系教授陳尚君所說(shuō): “劉大杰先生既有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豐富積淀,又有對(duì)新舊文學(xué)和東西文學(xué)的融通理解和透徹體悟,涉足中國(guó)文學(xué)史這一開(kāi)墾未透的領(lǐng)域,他的文學(xué)才華和學(xué)術(shù)識(shí)見(jiàn),得到了充分施展的廣闊空間。劉先生晚年曾對(duì)友人說(shuō),他在涉足眾多領(lǐng)域,最后轉(zhuǎn)入研究中國(guó)文學(xué)史,才找到了‘自己’。” (陳尚君, 《劉大杰先生和他的中國(guó)文學(xué)發(fā)展史》)
回國(guó)后,劉大杰輾轉(zhuǎn)于復(fù)旦大學(xué)、四川大學(xué)、安徽大學(xué)、大夏大學(xué)、暨南大學(xué)等校任職。抗戰(zhàn)時(shí)期,滯留上海、處于半失業(yè)狀態(tài)、生活拮據(jù)的他拒絕了一些學(xué)校要他講授日語(yǔ)的聘請(qǐng),潛心閉門著書。30年代后期,因覺(jué)得“文學(xué)思想的發(fā)展,魏晉時(shí)代是帶著革命的意義的”,劉大杰對(duì)魏晉時(shí)期的思想流派及演變進(jìn)行了專題探索,著成《魏晉思想論》一書;而后,經(jīng)歷數(shù)個(gè)寒冬酷暑的辛勤寫作,終于鑄就那部80多萬(wàn)字的傳世之作《中國(guó)文學(xué)發(fā)展史》(上下卷,分別出版于1941、1949年),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領(lǐng)域的學(xué)術(shù)地位。
理論特色、時(shí)代立場(chǎng)、個(gè)性化審美趣味,共同鑄就了一座文學(xué)史上的豐碑
關(guān)于《中國(guó)文學(xué)發(fā)展史》的學(xué)術(shù)地位,陳尚君這樣高度評(píng)價(jià):“博大深沉的劉著,正好為民國(guó)時(shí)期的文學(xué)史撰寫,畫上了一個(gè)圓滿的句號(hào),也為發(fā)軔于世紀(jì)初的中國(guó)文學(xué)史史學(xué)走向成熟,建立了重要的里程碑。”將時(shí)鐘撥回20世紀(jì)初,自“文學(xué)史”概念引進(jìn)以來(lái),思考如何將西方文學(xué)理論與中國(guó)文學(xué)傳統(tǒng)相結(jié)合成為一代學(xué)人的努力——自1904年首部國(guó)人撰寫的文學(xué)史著作問(wèn)世到劉大杰開(kāi)始寫作的20世紀(jì)30年代,林林總總的文學(xué)史版本已多達(dá)80多部。為什么劉大杰的《中國(guó)文學(xué)發(fā)展史》能夠從中脫穎而出,并產(chǎn)生如此深遠(yuǎn)的影響?
在復(fù)旦大學(xué)中文系教授駱玉明看來(lái),這部著作的成功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其“理論上的特色”: “在劉大杰先生之前,還不曾有人仔細(xì)和深入地研究過(guò)西方的文學(xué)史理論,并將之恰當(dāng)?shù)剡\(yùn)用于中國(guó)文學(xué)史的寫作。”其次是鮮明的時(shí)代立場(chǎng): “在劉先生看來(lái),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中蘊(yùn)藏著與‘五四’新文學(xué)精神相通的東西,這是它最可珍貴的內(nèi)容。”最后是劉著的“個(gè)性化特征”: “《中國(guó)文學(xué)發(fā)展史》正是各種文學(xué)史著作中最能顯示個(gè)人學(xué)術(shù)風(fēng)格和個(gè)人審美趣味的一種。不僅語(yǔ)言富麗,敘述生動(dòng),富于感染力,書中的議論也每帶有激情。可以說(shuō),史家的理性與詩(shī)人的感性在此書中是共存的。” (駱玉明, 《劉大杰〈中國(guó)文學(xué)發(fā)展史〉(復(fù)旦版)感言》)
晚年劉大杰曾談起對(duì)自己影響最大的幾本著作:泰納的《藝術(shù)哲學(xué)》和《英國(guó)文學(xué)史》,朗宋的《文學(xué)史方法論》,佛里契的《藝術(shù)社會(huì)學(xué)》和《歐洲文學(xué)發(fā)展史》,勃蘭兌斯的《十九世紀(jì)文學(xué)主潮》。但對(duì)這些理論的應(yīng)用不是生搬硬套,用他自己的話說(shuō),是“把這些理論組織成為自己的體系,來(lái)說(shuō)明中國(guó)文學(xué)的發(fā)展”。受西方的進(jìn)化論和社會(huì)學(xué)影響,他認(rèn)為既然人類社會(huì)在不斷進(jìn)步,那么作為社會(huì)生活的反映,文學(xué)也必然是進(jìn)化的。探討造成每一個(gè)時(shí)代的文學(xué)思潮的“政治狀態(tài)、社會(huì)生活、學(xué)術(shù)思想以及其它種種環(huán)境與當(dāng)代文學(xué)所發(fā)生的聯(lián)系和影響”,是他所認(rèn)為的文學(xué)史家的任務(wù)。可見(jiàn),在劉大杰那里,文學(xué)史寫作不是對(duì)文學(xué)史實(shí)的簡(jiǎn)單時(shí)序羅列,不是主次不分的材料堆砌,而在于“求因明變”,尋找文學(xué)發(fā)展的內(nèi)在規(guī)律。這樣的文學(xué)史觀超越了他之前的文學(xué)史撰寫者,也為后來(lái)者確立了研究范式。
深受“五四”新文化熏陶,在劉大杰的文學(xué)史書寫中,張揚(yáng)個(gè)性、崇尚情感的現(xiàn)代意識(shí)是貫穿其中的鮮明紅線,也是他審視歷代文學(xué)思潮的標(biāo)尺——他看到了魏晉文學(xué)在文學(xué)史上繼往開(kāi)來(lái)的意義,在《魏晉思想論》中,他高度評(píng)價(jià)魏晉人身上那洋溢著的“熱烈的個(gè)人的浪漫主義的精神”,對(duì)于這個(gè)“浪漫主義”的內(nèi)涵,他進(jìn)一步指出: “魏晉時(shí)代,無(wú)論是學(xué)術(shù)研究上,文藝的創(chuàng)作上,人生的倫理道德上,有一個(gè)共同的特征,那便是解放和自由。”在他看來(lái),魏晉以來(lái)的浪漫主義為后來(lái)的唯美主義埋下了種子,因而他不顧傳統(tǒng)觀念的偏見(jiàn),充分肯定唯美主義文學(xué)的進(jìn)步作用;到了盛唐時(shí)代,他高度評(píng)價(jià)李白是“當(dāng)代浪漫生活、浪漫思想、浪漫文學(xué)的總代表”;而晚明公安竟陵派文學(xué)的浪漫精神,在他看來(lái)是“與五四時(shí)代的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精神完全相同”……在他的筆下,一部文學(xué)史,就是人類情感與思想發(fā)展的歷史。
在劉大杰的文學(xué)史書寫中,他作為作家的個(gè)性與才情也顯露無(wú)疑,他生動(dòng)活潑的筆法,讓他在評(píng)述那些偉大作家時(shí),能夠?qū)⑺麄兊慕?jīng)歷和性格刻畫得入木三分,有血有肉。他筆下的屈原,是“一個(gè)多疑善感的殉情者,缺少道家的曠達(dá),墨家的刻苦,和孔、孟的行為哲學(xué)的奮斗精神,加以他少年得志,一旦遭受著重大的打擊,就不容易自拔,于是牢騷郁積,發(fā)泄于詩(shī)歌,而成為千古文人了”;他筆下的李白,“是天才、浪子、道人、豪俠、隱士、酒徒、色鬼、革命家。這一切的特性,都集合地在他的詩(shī)歌里表現(xiàn)出來(lái)。他的腦中有無(wú)限的理想,但任何理想都不能使他滿足,他追求無(wú)限的超越,追求最不平凡的存在”;而他筆下的杜甫,“不是屈原式的殉情主義者”,“也不能在虛無(wú)空渺的神仙世界找著快樂(lè)”,“因此,他能用他的理智,去細(xì)細(xì)地觀察人生社會(huì)的實(shí)況,從自己的生活經(jīng)驗(yàn),去體會(huì)旁人的苦樂(lè)”……
但是,作為詩(shī)人的感性和熱情沒(méi)有湮沒(méi)作為史家的理性與冷靜,“寫文學(xué)史的人,切勿以自我為中心,切勿給與自我的情感以絕對(duì)的價(jià)值,切勿使我的嗜好超過(guò)我的信仰”,朗宋的這段話,劉大杰在寫史的過(guò)程中時(shí)時(shí)刻刻銘記于心。他說(shuō): “在文學(xué)史上的敘述上,你必得拋棄自己的好惡偏見(jiàn),依著已成的事實(shí),加以說(shuō)明。那些作家與作品,無(wú)論你如何厭惡,是如何僵化,他們?cè)诋?dāng)時(shí)能那么興隆的發(fā)展起來(lái),自必有他發(fā)展的根源環(huán)境,存在的理由和價(jià)值。文學(xué)史的編著者,便要用冷靜的客觀的頭腦,敘述這些環(huán)境、理由和價(jià)值。”他將文學(xué)看作是“一種有機(jī)體的生命”,有其生老盛衰的規(guī)律,因而即便是在他看來(lái)“簡(jiǎn)樸無(wú)華、干枯無(wú)味”的《周頌》、在現(xiàn)代人看來(lái)“僵化了的缺乏感情的死文字”的漢賦,他都結(jié)合當(dāng)時(shí)的時(shí)代背景給予了公允的評(píng)價(jià)。
這種客觀但又不失感性的寫法,仿佛讓讀者真正進(jìn)入了他所研究的文學(xué)家的時(shí)代,站在了他們的視角。這也鑄就了《中國(guó)文學(xué)發(fā)展史》這座文學(xué)史上的豐碑,正如陳尚君的評(píng)價(jià), “它是本世紀(jì)最具才華和文采、最客觀冷靜、體系完整而又具有濃厚個(gè)人色彩的文學(xué)史著作之一”。駱玉明也認(rèn)為, “此書不僅影響了后來(lái)多種同類型著作的撰寫,其自身也一直沒(méi)有完全被替代、沒(méi)有停止過(guò)在高校教學(xué)及普通讀者中的流行。總之,要論影響的廣泛與持久,至今還沒(méi)有一種文學(xué)史能夠超過(guò)它”。
聽(tīng)他講課是藝術(shù)的享受,“學(xué)生們都怕下課,希望他講得越長(zhǎng)越好”
上海解放后,劉大杰來(lái)到復(fù)旦大學(xué),擔(dān)任中文系教授、中文系文學(xué)教研組組長(zhǎng)、中文系代理主任等職。這是劉大杰人生中最后的也是停靠最久的“驛站”——他在復(fù)旦工作長(zhǎng)達(dá)29年,直到1977年因病去世。其間,中國(guó)文學(xué)史的教學(xué)和研究是他學(xué)術(shù)工作的“主旋律”,他多次主講“中國(guó)文學(xué)史”,還作過(guò)“唐代詩(shī)歌”和“紅樓夢(mèng)”的專題講座。在復(fù)旦中文系,劉大杰的才氣是有口皆碑的。若是放在今天,他一定是當(dāng)之無(wú)愧的“網(wǎng)紅教授”,淵博的學(xué)識(shí)、出口成章的文采,讓他的課總是場(chǎng)場(chǎng)爆滿,深受學(xué)生歡迎。
在復(fù)旦大學(xué)中文系教授吳中杰的記憶里, “讀大杰先生《中國(guó)文學(xué)發(fā)展史》,能使你感到一種審美的愉悅,聽(tīng)大杰先生講課,更是一種藝術(shù)的享受……講建安文學(xué),他從世積亂離的時(shí)代背景,講到慷慨多氣的文風(fēng),一直講到甄后如何漂亮,曹植如何傾倒,劉楨又如何以平視而獲罪。講課時(shí),他能隨口背出很多詩(shī)句,引用又恰到好處,令人折服。他講《紅樓夢(mèng)》,也能隨口背誦很多東西,就連黑山村莊頭烏進(jìn)孝上繳賈府的貨物清單,他都能背誦如流”。復(fù)旦大學(xué)中文系教授吳歡章也曾這樣回憶: “聽(tīng)大杰先生講課,同學(xué)們都形成了一個(gè)心理習(xí)慣,就是怕下課,希望他講得越長(zhǎng)越好,以致他的課總是上到下一節(jié)課的老師已經(jīng)等在教室門口才不得不打住。”50年代中期他受邀到北京大學(xué)作《紅樓夢(mèng)》的專題講座,聽(tīng)眾極為踴躍,連窗臺(tái)上都坐滿了人。學(xué)生們都說(shuō),從來(lái)沒(méi)有聽(tīng)過(guò)這樣生動(dòng)的學(xué)術(shù)報(bào)告。
1957年,劉大杰因腸癌動(dòng)了手術(shù),元?dú)獯髠浴皵嗄c人”自嘲。但他仍然堅(jiān)持著書立說(shuō),出版的著作有《〈紅樓夢(mèng)〉的思想與人物》 《中國(guó)古代的大詩(shī)人》等,譯作有屠格涅夫的《一個(gè)無(wú)可救藥的人》,并在各類報(bào)刊上發(fā)表大量學(xué)術(shù)論文,如《魯迅的舊詩(shī)》 《杜甫的道路》 《古典文學(xué)巨著〈紅樓夢(mèng)〉》 《〈儒林外史〉與諷刺文學(xué)》《關(guān)于曹操詩(shī)歌中的人道主義》《論陳子昂的文學(xué)精神》 《黃庭堅(jiān)的文學(xué)批評(píng)》等。其中, “他的《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問(wèn)題》一文,在國(guó)內(nèi)最先針對(duì)把整個(gè)中國(guó)文學(xué)史歸納為‘現(xiàn)實(shí)主義與反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公式提出質(zhì)疑,在學(xué)術(shù)界引起過(guò)廣泛的關(guān)注,在國(guó)外也有一定的反響”。 (陳允吉, 《劉大杰傳略》)
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的專題探索之外,劉大杰同樣精進(jìn)著自己的文學(xué)史研究。作為一位與時(shí)俱進(jìn)的文學(xué)史家,他一直在試圖學(xué)習(xí)先進(jìn)的理論方法、尋找更為合理的理論范式來(lái)解釋中國(guó)文學(xué)史。從20世紀(jì)50年代開(kāi)始,當(dāng)進(jìn)化論史觀變得不合時(shí)宜,劉大杰開(kāi)始反省自己先前的學(xué)術(shù)思想,力求用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研究工作的指導(dǎo)思想,加上“看到了一些從前沒(méi)有看到過(guò)的史料”,這就有了之后他對(duì)舊著的反復(fù)修改和補(bǔ)充。1957年,劉大杰出版了《中國(guó)文學(xué)發(fā)展史》的第一次修訂本,但在當(dāng)時(shí)左傾思潮影響下,這部著作不僅沒(méi)有得到承認(rèn),反而遭到猛烈的批判。但劉大杰仍在政治夾縫中堅(jiān)守著自己的研究立場(chǎng),上述提及的《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問(wèn)題》一文便是發(fā)表于這一時(shí)期。1962年, 《中國(guó)文學(xué)發(fā)展史》第二次修訂本出版,相比初版,這兩次修訂使得全書的結(jié)構(gòu)更加完整、材料更加豐富,如1957年版本就增補(bǔ)了之前忽略的“司馬遷與史傳文學(xué)”的重要章節(jié),再如增幅最大的清代文學(xué)部分,從初版的5萬(wàn)字增至1957年版的8萬(wàn)多字、1962年版的20多萬(wàn)字,得到了顯著的擴(kuò)充。盡管初版中劉大杰最顯才華個(gè)性的評(píng)論在后來(lái)的修訂中已改為嚴(yán)謹(jǐn)規(guī)范的敘述,但在許多學(xué)者看來(lái),與這前后多種集體編寫的《中國(guó)文學(xué)史》相比,劉大杰的版本仍然是最富個(gè)性的。1983年,教育部將《中國(guó)文學(xué)發(fā)展史》1962版本重印,作為全國(guó)高等學(xué)院文科教材。
因?yàn)椤吨袊?guó)文學(xué)發(fā)展史》的巨大影響力,晚年的劉大杰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賞識(shí)。1965年,劉大杰在復(fù)旦大學(xué)受到毛主席的接見(jiàn)和鼓勵(lì),后來(lái)二人保持通信,“今存于湖南韶山毛澤東故居的生前最后一封信,就是與劉先生談李白、李商隱詩(shī)歌的”。(陳尚君,《二十世紀(jì)最有才氣的中國(guó)文學(xué)史家——記劉大杰先生》)“文革”中,劉大杰對(duì)《中國(guó)文學(xué)發(fā)展史》進(jìn)行了最后一次修訂,作為特殊政治時(shí)期的產(chǎn)物,這一版本并不成功,“不僅受到了許多朋友嚴(yán)肅的批評(píng),也使他自己在臨終時(shí)感到十分痛苦和遺憾。”(陳允吉,《劉大杰傳略》)
1977年,劉大杰因病逝世,享年73歲。縱觀劉大杰的一生,他的學(xué)術(shù)道路是極不平坦的。在那個(gè)特殊的年代,他傾注畢生心血的《中國(guó)文學(xué)發(fā)展史》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時(shí)代的烙印,但他為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和文學(xué)史研究所作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xiàn),仍為后人所銘記——他的為人為學(xué),常為復(fù)旦中文系的老先生們談起,化作一段段學(xué)術(shù)佳話在校園里流傳;他的著作,被當(dāng)作教材在復(fù)旦的課堂上使用,至今潤(rùn)物無(wú)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