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yǔ)言的力量與隔閡——2020年美國(guó)與加拿大文學(xué)回顧
內(nèi)容提要 2020年是艱辛的一年,非裔美國(guó)文學(xué)拋卻“后種族時(shí)代”泡沫,以現(xiàn)代視角回溯歷史,關(guān)注個(gè)人與族群的精神世界,表現(xiàn)出強(qiáng)烈的現(xiàn)實(shí)觀照;移民文學(xué)穿越空間與時(shí)間的維度,陳述物理與精神的隔閡,實(shí)現(xiàn)了藝術(shù)手法的多種創(chuàng)新;災(zāi)難文學(xué)構(gòu)想災(zāi)難的源頭與形式,展現(xiàn)不同群體面對(duì)災(zāi)難的迥異表現(xiàn),引起關(guān)注;摹寫(xiě)親密關(guān)系的作品則探討人的復(fù)雜身份屬性與被社會(huì)定義的角色擔(dān)當(dāng)。與“文化熔爐”美國(guó)相比,加拿大文壇則相對(duì)平靜,種族、移民、身份、家庭等話題依舊是寫(xiě)作熱點(diǎn)。
關(guān)鍵詞 美加年度文學(xué)研究 族裔文學(xué) 移民文學(xué) 災(zāi)難文學(xué)
一、與現(xiàn)實(shí)互動(dòng)的美國(guó)文學(xué)
新冠疫情、種族沖突、民主危機(jī)、全球化進(jìn)程倒退……2020年或?qū)⒊蔀槿祟悮v史上標(biāo)志性的一年。這一年的美國(guó)文學(xué)擔(dān)承起現(xiàn)實(shí)的重任,危機(jī)倦怠與撫慰療愈相互織就,在追溯困境、尋找出路中展現(xiàn)語(yǔ)言的力量。
(一)非裔文學(xué)的使命書(shū)寫(xi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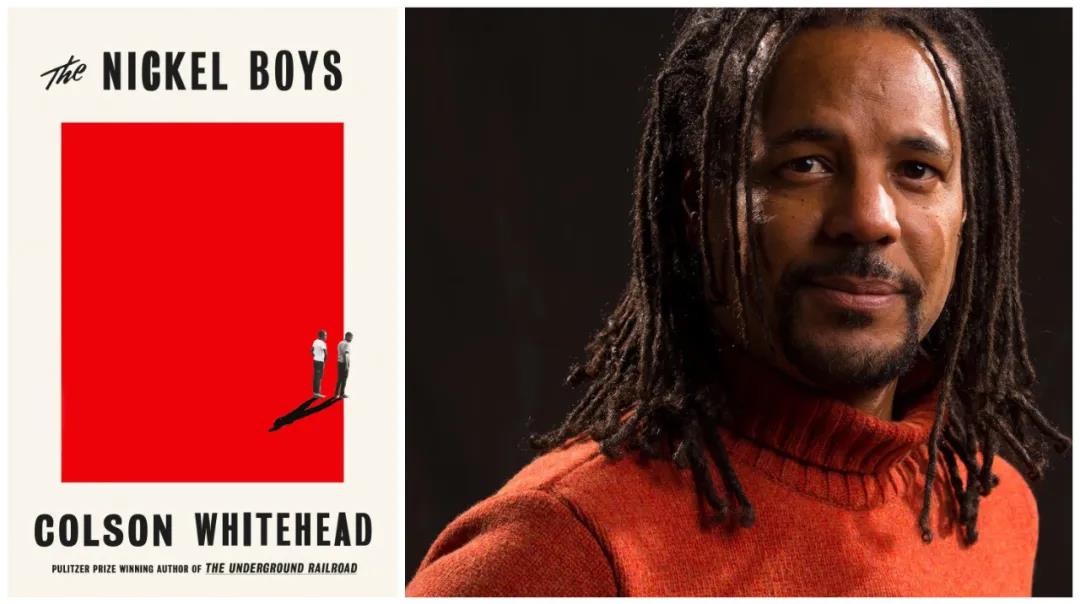
(《尼克男孩》與科爾森·懷特黑德,圖片源自Yandex)
自發(fā)端起,非裔美國(guó)文學(xué)的題材、旨?xì)w就一直處在不斷變化之中,通過(guò)早期奴隸敘事、哈萊姆文藝復(fù)興、黑人藝術(shù)運(yùn)動(dòng),非裔文學(xué)探索了其應(yīng)有的社會(huì)角色、功能、藝術(shù)性等問(wèn)題,在嚴(yán)肅的政治性訴求與藝術(shù)性的自由書(shū)寫(xiě)間游移。21世紀(jì)黑人民權(quán)運(yùn)動(dòng)以來(lái),黑人文學(xué)逐漸走向多元化,“黑人性”標(biāo)簽淡化,“后種族時(shí)代”似乎已經(jīng)來(lái)臨。然而,在特朗普治下,種族問(wèn)題再次突出,愈加嚴(yán)峻的種族形勢(shì)令非裔文學(xué)打破“后種族時(shí)代”的幻影,表現(xiàn)出強(qiáng)烈的現(xiàn)實(shí)觀照。2020年弗洛伊德事件更是將矛盾推向高潮,讓美國(guó)思想界掀起了關(guān)于“政治正確”的論爭(zhēng)。新的社會(huì)語(yǔ)境下,非裔美國(guó)作家以現(xiàn)代視野重新發(fā)現(xiàn)歷史、書(shū)寫(xiě)歷史,不再采用先輩作家的種族集體敘事、政治敘事、主觀情感敘事等形式,而是以個(gè)人日常生活敘事為主,注重對(duì)個(gè)人心理、族群精神世界的描述。新生代非裔作家科爾森·懷特黑德(Colson Whitehead)的《尼克男孩》(The Nickel Boys)回到吉姆·克勞時(shí)期,講述一所少年教養(yǎng)院里發(fā)生的虐待案,尤其是黑人少年受到的殘酷待遇,透過(guò)兩位少年的內(nèi)心世界詰問(wèn)現(xiàn)實(shí)。《尼克男孩》源于真實(shí)案件,原型是佛羅里達(dá)州北部的少年管教所亞瑟·G.多爾茨男校(Arthur G. Dozier School for Boys)。多茨爾男校成立于1900年,一度是美國(guó)最大的管教學(xué)校,收管被拋棄的和行為乖張的少年兒童。學(xué)校自成立來(lái),多次曝出虐待丑聞,但直至2009年政府才啟動(dòng)全面調(diào)查,由此,持續(xù)一百多年的虐童案才被真正翻開(kāi)。沉重的歷史圍繞兩位黑人少年埃爾伍德和特納展開(kāi),敘寫(xiě)這對(duì)好友截然不同的心理狀態(tài)與人生信仰,其中一位面對(duì)黑暗現(xiàn)實(shí)卻始終抱有希望,另一位則憤世嫉俗,懷疑一切。懷特黑德回到歷史的種族主義現(xiàn)場(chǎng),探尋其在當(dāng)代的延續(xù),于他而言,書(shū)寫(xiě)歷史就是書(shū)寫(xiě)當(dāng)下。他的筆觸平實(shí)而克制,不為渲染歷史傷痛,更在意于探討歷史如何被隱沒(méi)、扭曲,以啟發(fā)當(dāng)下困境。懷特黑德說(shuō):“埃爾伍德和特納代表了我個(gè)性中兩個(gè)不同的部分,埃爾伍德是樂(lè)觀的、充滿希望的那部分,認(rèn)為只要我們足夠努力,世界終將更好。特納則是我的另一面,這個(gè)國(guó)家以種族滅絕、謀殺和奴隸制為基石建立,永遠(yuǎn)都不會(huì)好起來(lái)了。這也是人們普遍面臨的困境:當(dāng)現(xiàn)實(shí)令人沮喪如何保持希望?……”。《地下鐵道》后,懷特黑德原不打算再寫(xiě)這種主題沉重的書(shū),然而多茨爾男校事件以及特朗普上任后對(duì)少數(shù)族裔的種種政策,令他“認(rèn)為自己有必要思考我們?cè)谶@個(gè)國(guó)家中到底處在何種位置”。《尼克男孩》贏得文壇認(rèn)可,斬獲2020年普利策小說(shuō)獎(jiǎng),也讓?xiě)烟睾诘鲁蔀槠裎ㄒ灰晃贿B獲普利策獎(jiǎng)的小說(shuō)家。
暢銷書(shū)《母親們》的作者本里特·本尼特(Brit Bennett)再出佳作《消失的另一半》(The Vanishing Half),入選《紐約時(shí)報(bào)》2020年十大好書(shū),探索了歷史遺留的“種族冒充”(racial passing)現(xiàn)象。“種族冒充”是美國(guó)黑人文學(xué)傳統(tǒng)的母題之一,也是美國(guó)社會(huì)的獨(dú)特現(xiàn)象,歷史上許多淺膚色黑人通過(guò)冒充白人來(lái)獲得更好的生存機(jī)遇,為此冒充者需要付出巨大代價(jià),不只是身份許可的轉(zhuǎn)換,更要在精神上背棄原有的生長(zhǎng)紐帶。小說(shuō)講述一對(duì)淺膚色非裔雙胞胎姐妹不同的人生選擇與后果,她們的人生選擇究竟有無(wú)對(duì)錯(cuò),作者沒(méi)有給出答案,而是將問(wèn)題拋給了讀者。
《真實(shí)生活》(Real Life)是美國(guó)作家布萊登·泰勒(Brandon Tyler)的處女作,入圍2020年布克獎(jiǎng)決選名單。小說(shuō)圍繞一位黑人酷兒的成長(zhǎng),揭開(kāi)當(dāng)下社會(huì)存在的隱性歧視,探索人在孤獨(dú)和欲望夾縫間的掙扎。主人公華萊士是生物化學(xué)專業(yè)博士生、黑人酷兒,他體形肥胖,敏感內(nèi)向,童年曾遭親人性侵,出于自我保護(hù)故意疏離身邊的同學(xué)。小說(shuō)的動(dòng)人之處在于精準(zhǔn)呈現(xiàn)了華萊士獨(dú)處時(shí)內(nèi)心的纏結(jié),以及隱性的種族歧視、性取向偏見(jiàn)、童年創(chuàng)傷給他帶來(lái)的難以言說(shuō)的傷痛和孤獨(dú)。這些隱性的歧視通常為受害者帶來(lái)持續(xù)性創(chuàng)傷。在一段欲與導(dǎo)師傾訴的心理描寫(xiě)中,我們可以清晰感覺(jué)到主人公明明每個(gè)毛孔都在申訴抗議、結(jié)果卻無(wú)一言可發(fā)的悶屈困頓:“一方深坑在他身下展開(kāi)。他可以說(shuō)說(shuō)丹納對(duì)自己講過(guò)的話。告發(fā)她有種族偏見(jiàn)且仇視同性戀。他可以說(shuō)說(shuō)入學(xué)以來(lái)經(jīng)歷的一切……有千百萬(wàn)件事可說(shuō),然而他知道沒(méi)一件能引起重視。對(duì)她、對(duì)周圍所有人來(lái)說(shuō)這些都無(wú)足輕重,沒(méi)人關(guān)心他的感受,除非他的情緒影響到了他們。”保羅·門德斯評(píng)論這部作品道:“這是一部校園小說(shuō),然而但凡熟悉19世紀(jì)奴隸敘事的人都能聽(tīng)到后院里叮當(dāng)作響的鐵鏈聲。泰勒簡(jiǎn)潔、細(xì)致、敏銳地審視了當(dāng)下美國(guó)的種族關(guān)系。”
短篇小說(shuō)集《教堂女士的秘密生活》(The Secret Lives of Church Ladies)將目光投向黑人女性,講述黑人女性的欲望與信仰,九個(gè)短篇涉及黑人女性情感關(guān)系中的背叛、隨意性行為和同性戀等話題。《教堂女士的秘密生活》是作者笛莎·菲利揚(yáng)(Deesha Philyaw)的處女作,入圍2020年國(guó)家圖書(shū)獎(jiǎng)決選名單,菲利揚(yáng)幼時(shí)就開(kāi)始參加教堂活動(dòng),小說(shuō)集里的女性形象出自她長(zhǎng)期以來(lái)對(duì)教堂女性的觀察,她們通常裝扮保守,講話謹(jǐn)慎,虔誠(chéng)信仰上帝。然而,人總是復(fù)雜的個(gè)體,束縛之下迸發(fā)的欲望往往更加驚心動(dòng)魄,在欲望與信仰的拉扯間,有的人矛盾沮喪,也有的人在信仰中找到慰藉與指引。
(二)移民文學(xué)的藝術(shù)創(chuàng)新
美國(guó)移民文學(xué)在空間與時(shí)間兩個(gè)維度反觀移民離散生活,尋找身份與文化的認(rèn)同,具有鮮明的民族文化符碼,同時(shí)又展露出開(kāi)闊的世界性眼光。2020年美國(guó)的移民文學(xué)以新穎的藝術(shù)手法,參與社會(huì)討論,豐富了文學(xué)的藝術(shù)形態(tà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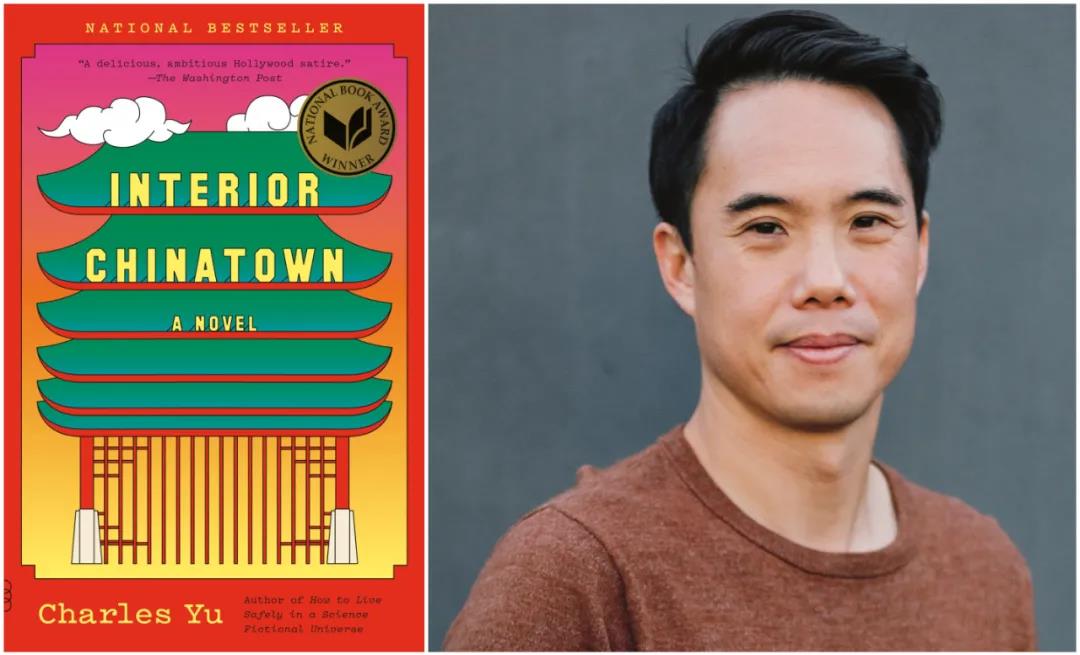
(《唐人街內(nèi)部》與游朝凱,圖片源自Yandex)
《唐人街內(nèi)部》(Interior Chinatown)以其深入的思考和精巧的結(jié)構(gòu)成為本年移民文學(xué)不可忽視之作,獲得國(guó)家圖書(shū)獎(jiǎng)。作者游朝凱(Charles Yu)祖籍中國(guó)臺(tái)灣,在美國(guó)出生、長(zhǎng)大。做過(guò)律師、是HBO《西部世界》等熱門美劇的編劇,目前專職創(chuàng)作。除《唐人街內(nèi)部》外,他還創(chuàng)作了長(zhǎng)篇小說(shuō)《如何在科幻小說(shuō)的宇宙中安全生存》(How to Live Safely in a Science Fictional Universe)、短篇小說(shuō)集《三等超級(jí)英雄》(Third Class Superhero)、《對(duì)不起,請(qǐng),謝謝你》(Sorry Please Thank You)等。
《唐人街內(nèi)部》透過(guò)主人公吳威利在演藝圈打拼的歷程,指出亞裔移民在美國(guó)的失語(yǔ)狀態(tài)以及美國(guó)社會(huì)對(duì)亞裔的刻板印象,包括外貌上的、精神上的。“在黑人和白人的世界里,初入拍攝行業(yè),大家(指亞裔演員)都從‘亞洲人’做起。誰(shuí)跟誰(shuí)都沒(méi)什么差別。除非你是位女士,那你的起點(diǎn)就能變成‘漂亮的亞洲女人’。這就是我們。兩個(gè)詞:亞洲家伙。[……]這兩個(gè)詞界定了你,壓扁你、圈禁你,將你困在這里。”值得注意的是,游朝凱還觀察到了促成這種困境的內(nèi)部源頭,群聚唐人街的亞裔因語(yǔ)言文化原因往往不愿走出舒適圈,少與外界交流,這種狀況更強(qiáng)化了亞裔的弱勢(shì)地位,形成惡性循環(huán)。對(duì)于亞裔的身份困境,游朝凱在小說(shuō)中秉持的是極為嚴(yán)肅的態(tài)度。小說(shuō)多個(gè)章節(jié)伊始引用了記者、社會(huì)學(xué)家、歷史學(xué)者如歐文·高夫曼、菲利普·蔡等關(guān)于種族問(wèn)題的觀點(diǎn),第六幕“亞洲人口失蹤案”更是不惜筆墨醒目地列出了美國(guó)19世紀(jì)以來(lái)不斷更迭的移民政策。游朝凱在接受美國(guó)國(guó)家公共電臺(tái)采訪時(shí)坦言:“寫(xiě)這本書(shū),以及將它以這樣的筆法呈現(xiàn)出來(lái)的動(dòng)機(jī)是,我想捕捉那種無(wú)法成為戲劇中心的感覺(jué)……想到這樣的故事的時(shí)候,我正處在這樣的人生階段:從事電視行業(yè)多年,年歲漸長(zhǎng)……父母皆已年邁,移民美國(guó)多年……孩子也漸漸長(zhǎng)大,到了能夠提出‘我們真的是美國(guó)人嗎’這類問(wèn)題的年紀(jì)。成為美國(guó)人到底有什么評(píng)判標(biāo)準(zhǔn)?”
在敘事手法上,得益于編劇經(jīng)歷,作家別出心裁地采用劇本形式,將主人公出演的劇本與主人公由劇本衍生出來(lái)的第二人稱的意識(shí)獨(dú)白相互嵌套,以七幕劇本為架構(gòu),結(jié)合主角的演藝生涯,一層層推進(jìn)完成述寫(xiě)。作家以嫻熟的技巧將劇本內(nèi)容與主人公心中的自白鋪展開(kāi)來(lái),過(guò)渡自然,完全沒(méi)有跳脫之感。如第四幕劇本里,就在吳威利的演員之路要取得成功時(shí),他被安排“死”掉了。遇到這種情況,必須45天后才能接戲,因?yàn)椤爸辽傩枰@么長(zhǎng)時(shí)間,大家才能忘記你那張臉。雖然你們亞洲人幾乎都長(zhǎng)一個(gè)樣”。這樣的答案引出了吳威利的內(nèi)心獨(dú)白,45天沒(méi)戲拍,對(duì)以此糊口的亞裔演員來(lái)說(shuō)無(wú)疑雪上加霜,可導(dǎo)演才不會(huì)在乎你家里生病的寶寶、挨餓的孩子、沒(méi)錢買藥吃的老母親……只要你死了,就什么也不是。接著吳威利心思一轉(zhuǎn):有些人卻不認(rèn)為這是個(gè)頂要命的遭遇。只要你的媽媽“死”了,她就能做回你的媽媽了:接你放學(xué)、陪你看電視、聽(tīng)她練習(xí)口語(yǔ)準(zhǔn)備下一個(gè)角色……不知不覺(jué)間,作家將吳威利成長(zhǎng)環(huán)境的細(xì)小關(guān)卡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第二人稱的視角仿佛是作者開(kāi)設(shè)的另一現(xiàn)場(chǎng)舞臺(tái),讓講述者直面讀者,體驗(yàn)感強(qiáng)烈。這樣的架構(gòu),模糊了劇本和現(xiàn)實(shí)的邊界,對(duì)作者和讀者來(lái)說(shuō),都是一種新奇的體驗(yàn)和挑戰(zhàn)。
探索移民問(wèn)題的《故鄉(xiāng)挽歌》(Homeland Elegies)同樣采取了別具一格的敘事形式,模糊了現(xiàn)實(shí)與虛構(gòu)的邊界。這部小說(shuō)講述巴基斯坦移民家庭與故土難以割舍的紐帶,以及“9·11事件”后他們?cè)诿绹?guó)的生活。作家將自己的名字賦予主人公,二者同名——阿亞得·阿赫塔(Ayad Akhtar),這是阿赫塔有意為之,以促成錯(cuò)覺(jué),混淆讀者對(duì)現(xiàn)實(shí)與虛構(gòu)的判斷。作家的巧思顯然起了效果,讀書(shū)網(wǎng)站Goodreads上,閱讀本書(shū)的讀者討論最多的就是:這究竟是回憶錄(或者社會(huì)學(xué)、政治學(xué)著作)還是小說(shuō)?阿赫塔說(shuō):“我希望能找到一種方式,表達(dá)難以區(qū)分現(xiàn)實(shí)與虛構(gòu)的困惑,這種困惑越來(lái)越成為我們現(xiàn)實(shí)生活或非現(xiàn)實(shí)生活的特質(zhì)。”阿赫塔以獨(dú)到的角度,刻畫(huà)出這個(gè)國(guó)家里深陷債務(wù)危機(jī)的民眾、被資本剝奪的夢(mèng)想、表演型人格的總統(tǒng)、惶惶不可終日的移民生活以及“9·11事件”給這個(gè)國(guó)家乃至世界帶來(lái)的持續(xù)性災(zāi)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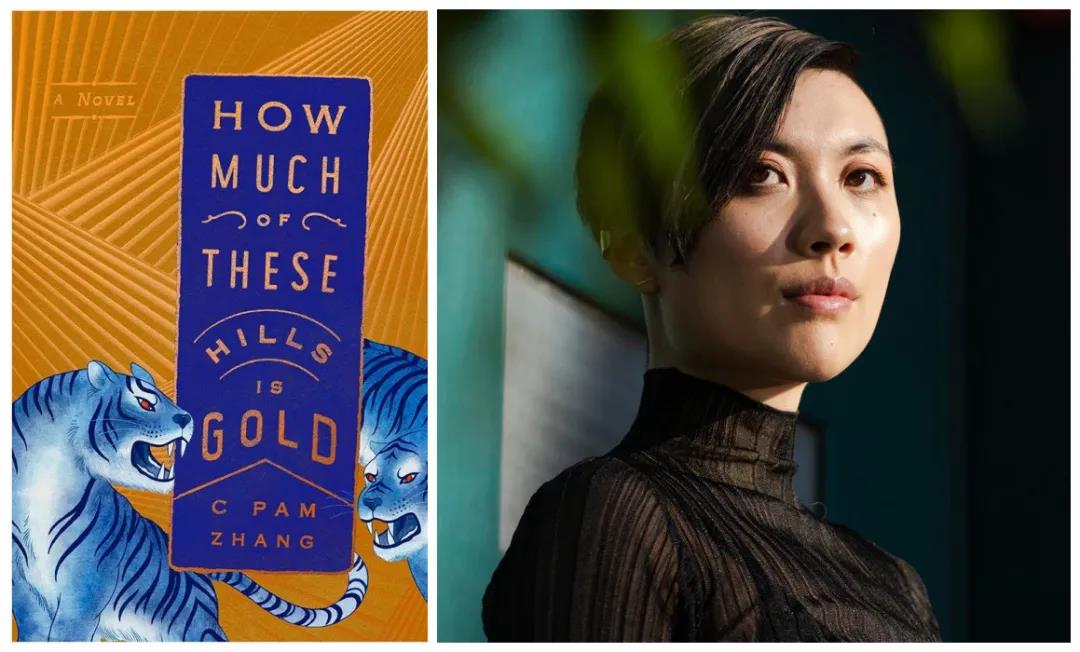
(《山里有多少黃金》與帕姆·張,圖片源自Yandex)
此外,帕姆·張(C. Pam Zhang)的《山里有多少黃金》(How Much of These Hills is Gold)關(guān)注美國(guó)文學(xué)中罕見(jiàn)的群體——西部淘金的華人,講述一對(duì)失去父母的貧困姐弟在西部荒地掙扎求存的故事,填補(bǔ)了西部文學(xué)領(lǐng)域里華人敘事的空白。珍妮·康明斯(Jeanine Cummins)的《美國(guó)塵土》(American Dirt)寫(xiě)一對(duì)母子離開(kāi)墨西哥非法遷往美國(guó)經(jīng)歷的諸多磨難。1998年出生的作家張欣明(K-Ming Chang)的《動(dòng)物寓言》(Bestiary)則為移民文學(xué)帶來(lái)奇異色彩,小說(shuō)圍繞從中國(guó)臺(tái)灣移民至美國(guó)阿肯色州的三代女性(女兒、母親、祖母)展開(kāi):自從聽(tīng)媽媽講了虎姑婆的故事后,女兒長(zhǎng)出一條老虎尾巴,擁有了令她無(wú)法理解也不知如何使用的超能力。這部小說(shuō)探索了外鄉(xiāng)人、原住民、母親、女兒等諸多身份的意味,充滿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色彩。
(三)災(zāi)難書(shū)寫(xiě)與現(xiàn)實(shí)的共鳴
災(zāi)難文學(xué)通過(guò)創(chuàng)設(shè)不同的災(zāi)難圖景,將人物置于極端情境下,不論背景虛構(gòu)與否,都具有強(qiáng)烈的現(xiàn)實(shí)指涉意義。2020年新冠疫情來(lái)襲,災(zāi)難文學(xué)受到關(guān)注,產(chǎn)生了與現(xiàn)實(shí)的同頻共鳴。
《孩子們的圣經(jīng)》(A Children's Bible)是一部氣候小說(shuō),展現(xiàn)面對(duì)氣候?yàn)?zāi)難時(shí)一群孩子的表現(xiàn)。這是莉迪亞·米萊特(Lydia Millet)的第13部小說(shuō),她的作品關(guān)注現(xiàn)實(shí)、筆法靈活、富含黑色幽默,曾入圍普利策獎(jiǎng)短名單。《孩子們的圣經(jīng)》獲2020年國(guó)家圖書(shū)獎(jiǎng)提名、入選《紐約時(shí)報(bào)》2020年十大好書(shū)。小說(shuō)里,12個(gè)孩子隨父母去別墅度暑假,然而父母?jìng)兂商炜v情酒樂(lè)、生活無(wú)度,一場(chǎng)暴烈的颶風(fēng)來(lái)臨,大人們依舊無(wú)視現(xiàn)實(shí),孩子們則開(kāi)始了逃亡之旅。作家將他們遇到的災(zāi)難與《圣經(jīng)》中的場(chǎng)景相呼應(yīng),如諾亞方舟、從洪水中救出的動(dòng)物、馬廄中出生的嬰兒等,處處充滿了諷喻。不過(guò)作家并未過(guò)度渲染這些意象,也沒(méi)有將其寫(xiě)成一部脫離現(xiàn)實(shí)的神奇小說(shuō)。在孩子們眼中,《圣經(jīng)》是一本在廢棄房間里找到的古書(shū),一封來(lái)自遠(yuǎn)古世界的信函,但書(shū)里的奧義可一一解碼與現(xiàn)實(shí)呼應(yīng),上帝對(duì)應(yīng)自然,耶穌對(duì)應(yīng)科學(xué)……孩子們?cè)凇妒ソ?jīng)》中找到了當(dāng)下性的意義。
黛安娜·庫(kù)克(Diane Cook)的首部長(zhǎng)篇小說(shuō)《新荒野》(The New Wilderness)將故事起點(diǎn)設(shè)定于未來(lái)被霧霾污染吞噬的大都市,貝亞為了挽救女兒艾格尼絲的生命,與其他18位志愿者組成族群(Community),前往人類未曾踏足、未被污染的荒野之地,族群只能依靠狩獵、采集生存,人們慢慢適應(yīng)了這里的生存規(guī)則,同時(shí)也開(kāi)始了權(quán)利、資源的爭(zhēng)奪。這項(xiàng)試驗(yàn)意圖檢驗(yàn)人類是否能在不破壞環(huán)境的前提下生存,當(dāng)災(zāi)難來(lái)臨,當(dāng)個(gè)人主義侵蝕集體利益,我們?cè)撊绾翁幚砼c他人的關(guān)系。這是一部探索自然、社會(huì)、人性、母女關(guān)系的小說(shuō),極端環(huán)境下母親與女兒對(duì)自我、歸屬感、社會(huì)和他人認(rèn)知的分歧以及由此造成的情感裂痕與修補(bǔ)裂痕的努力,是這部小說(shuō)最為動(dòng)人之處。
《孩子們的圣經(jīng)》和《新荒野》都描繪了災(zāi)難面前,成人的缺位、孩童的勇敢,似乎有意展現(xiàn)社會(huì)舊有秩序和新秩序的差異,諷喻人類對(duì)環(huán)境已造成了無(wú)可挽回的傷害,須以新視角探討新出路。唐·德里羅(Don DeLillo)的《寂靜》(The Silence)則想象了2022年的全球斷電災(zāi)難,反思人類對(duì)科技的深度依賴。克里斯托弗·貝亞(Christopher Beha)的《自毀行為指南》(The Index of Self-Destructive Acts)從不確定的災(zāi)難預(yù)言寫(xiě)起,描述預(yù)言陰影下,與主人公薩姆命運(yùn)交織的道爾一家的人生選擇。世界末日也許不會(huì)到來(lái),而世間眾生卻在作繭自縛,走向自己親手打造的末日。魯曼·阿拉姆(Rumaan Alam)的《拋下這個(gè)世界》(Leave the World Behind)是一部沒(méi)有災(zāi)難的災(zāi)難小說(shuō),著力呈現(xiàn)當(dāng)人類處于信息孤島隔絕狀態(tài)時(shí)的各種反應(yīng),以及恐慌之下的親密關(guān)系、種族偏見(jiàn)。疫情期間,人們有更多時(shí)間與家人相處,這一年,探討家庭關(guān)系的書(shū)籍也格外引人注目。《母親,女兒,寡婦》(Mother Daughter Widow Wife)講記憶與女性身份構(gòu)建。《燒焦的糖》(Burnt Sugar)考察當(dāng)下社會(huì)強(qiáng)加于“母親”這一身份的復(fù)雜框定與期待。《荷蘭莊園》(The Dutch House)述寫(xiě)動(dòng)人的手足之情與復(fù)雜的家庭關(guān)系……
2020年美國(guó)文壇發(fā)生了幾樁重要的文學(xué)事件。瑞典文學(xué)院將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授予詩(shī)人露易絲·格呂克(Louise Glück),令美國(guó)文壇多有意外。一是距離上次美國(guó)作家摘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僅過(guò)去三年;二是格呂克較賠率榜上排名靠前的米蘭·昆德拉、村上春樹(shù)而言,相對(duì)冷門,處在許多讀者的閱讀視野之外。另一個(gè)事件與種族問(wèn)題有關(guān),2020年5月,非裔美國(guó)人喬治·弗洛伊德遭遇白人警察暴力執(zhí)法身亡,引起軒然大波。“黑人的命也是命”運(yùn)動(dòng)(Black Lives Matter)再次大規(guī)模興起,抗議運(yùn)動(dòng)逐漸演變?yōu)楸﹣y,波及美國(guó)全境乃至其他涉種族問(wèn)題的西方國(guó)家。該事件同樣引發(fā)了文化界的爭(zhēng)論,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約翰·班維爾、馬丁·艾米斯、J.K.羅琳等一百五十多位作家、學(xué)者、新聞從業(yè)人員聯(lián)名簽署《哈珀斯雜志》公開(kāi)信,呼吁在社會(huì)運(yùn)動(dòng)中要保持寬容自由的社會(huì)氛圍,杜絕極端主義的“取消文化”和“政治正確”,掀起了自由中間派、激進(jìn)派、保守派的激烈辯論。極端主義思潮同樣蔓延到文學(xué)領(lǐng)域,越來(lái)越多的文學(xué)作品因間或表露的不合時(shí)宜的思想傾向被禁,托尼·莫里森《最藍(lán)的眼睛》、哈珀·李《殺死一只知更鳥(niǎo)》等眾多經(jīng)典作品均在列,據(jù)美國(guó)圖書(shū)館協(xié)會(huì)報(bào)告,僅在2020年,273本書(shū)籍受到質(zhì)疑甚至下架。這一年與美國(guó)文壇相關(guān)的第三件大事是企鵝蘭登書(shū)屋宣布收購(gòu)西蒙與舒斯特出版社,在美國(guó)圖書(shū)市場(chǎng)形成一家獨(dú)大的局面,據(jù)估測(cè),收購(gòu)?fù)瓿珊筮@家公司將占去美國(guó)圖書(shū)市場(chǎng)30%的份額。收購(gòu)行為引起多方擔(dān)憂,美國(guó)作家協(xié)會(huì)公開(kāi)提出反對(duì),認(rèn)為此舉將導(dǎo)致作家書(shū)稿競(jìng)價(jià)方減少,版權(quán)預(yù)付金勢(shì)必降低;小型出版社也將受到?jīng)_擊,新作家亮相越來(lái)越難。獨(dú)立書(shū)店表示這次收購(gòu)將降低他們與出版機(jī)構(gòu)合作談判的砝碼,不過(guò),這同時(shí)意味著出版社將擁有與銷售商更強(qiáng)的議價(jià)能力,保證書(shū)價(jià)不被過(guò)分壓低。受疫情沖擊,美國(guó)大多數(shù)行業(yè)都停滯萎縮,圖書(shū)市場(chǎng)卻十分可觀。據(jù)《出版人周刊》統(tǒng)計(jì),這一年紙質(zhì)書(shū)銷量上升8.2%,為2010年以來(lái)最大增幅,其中青少年非虛構(gòu)類書(shū)籍增長(zhǎng)最多,而非虛構(gòu)類作品中,弗洛伊德事件促使有關(guān)種族與社會(huì)公平的圖書(shū)銷量增加了4.8%。
二、延續(xù)傳統(tǒng)的加拿大文學(xué)
相較美國(guó)文學(xué)熱切的現(xiàn)實(shí)觀照,加拿大文學(xué)相對(duì)平靜,族裔文學(xué)依舊繁盛,種族、移民、婚姻、親情等議題依舊是作家們寫(xiě)作的主要方向。
2020年加拿大吉勒文學(xué)獎(jiǎng)?lì)C給了詩(shī)人、短篇小說(shuō)作家蘇萬(wàn)坎·塔瑪翁撒(Souvankham Thammavongsa)的處女作短篇小說(shuō)集《怎么念Knife》(How to Pronounce Knife)。塔瑪翁撒出生于泰國(guó)廊開(kāi)的老撾難民營(yíng),一歲時(shí)和父母移民到加拿大,她的短篇小說(shuō)《彈弓》(“Slingshot”)曾獲2019年歐·亨利獎(jiǎng)。《怎么念Knife》由14個(gè)短篇組成,主人公都是移民,敘事落在家庭與工作兩個(gè)主要空間,描寫(xiě)因種族、階層、性別而生發(fā)出的權(quán)利不對(duì)等、人與人之間的疏離與錯(cuò)位,其中一些細(xì)節(jié)源于作者的親身經(jīng)歷。長(zhǎng)于寫(xiě)詩(shī)的塔瑪翁撒為小說(shuō)賦予了詩(shī)一樣的語(yǔ)言,小說(shuō)細(xì)節(jié)中常常流露微妙的心緒:演唱會(huì)后打算牽妻子的手卻落了個(gè)空的丈夫,躲在暗處偷看女兒的母親……塔瑪翁撒重視語(yǔ)言的力量,常借語(yǔ)言的隔閡來(lái)呈現(xiàn)移民生活的疏離之感:“我”因念錯(cuò)了knife的發(fā)音而受到同學(xué)嘲笑;長(zhǎng)篇大論講臟話卻因發(fā)音不標(biāo)準(zhǔn)而顯滑稽的老撾小孩;跟著肥皂劇學(xué)英語(yǔ)、最終脫離不幸家庭的主婦……語(yǔ)言只是符號(hào),但在移民語(yǔ)境中,卻意味著難以跨過(guò)的橫溝以及融入新世界的有力武器。
杰西卡·J.李(Jessica J. Lee)的《雙木成林》(Two Trees Make a Forest)則是一場(chǎng)故鄉(xiāng)追溯之旅。一封來(lái)自祖父的信啟發(fā)作家前往遙遠(yuǎn)的故鄉(xiāng)中國(guó)臺(tái)灣,追尋家族的痕跡,作者暢游在高山海岸間,記錄從未見(jiàn)到過(guò)的動(dòng)植物與風(fēng)土人情,并在此間呈現(xiàn)歷史與自然如何塑造家庭與個(gè)人。作家本身是一位環(huán)境歷史學(xué)者,她將學(xué)者的精準(zhǔn)與詩(shī)人的敏銳感性相結(jié)合,以動(dòng)人的語(yǔ)言講述故鄉(xiāng)的自然風(fēng)光和歷史過(guò)往,令作品成為一部跨越歷史、旅行、自然、回憶等體裁門類的佳作。巴基斯坦裔作家、攝影師薩姆拉·哈比卜(Samra Habib)的回憶錄《我們一直在這里》(We Have Always Been Here)集合了穆斯林、酷兒、女權(quán)、移民等多種元素。尼日利亞裔作家弗朗西斯卡·艾克沃亞斯(Francesca Ekwuyasi)的處女作小說(shuō)《黃油蜂蜜豬面包》(Butter Honey Pig Bread)依托非洲文學(xué)富有神秘色彩的意象“阿比庫(kù)”,講述尼日利亞母親與她的雙胞胎女兒在傳統(tǒng)思想與親情之間的掙扎。凱·凱洛(Kaie Kellough)的短篇小說(shuō)集《十字路口的多米諾骨牌》(Dominoes at the Crossroads)聚焦加拿大的加勒比黑人族群,探討種族、階層、成長(zhǎng)問(wèn)題,將個(gè)人和族群經(jīng)驗(yàn)與現(xiàn)實(shí)緊密結(jié)合,牢牢抓住了人們?cè)诂F(xiàn)實(shí)中常體驗(yàn)到的陌生感。
本土文學(xué)中最耀眼的要數(shù)吉爾·亞當(dāng)森(Gil Adamson)的《山村鄉(xiāng)巴佬》(Ridgerunner)。2007年亞當(dāng)森憑借《外鄉(xiāng)人》(The Outlander)獲加拿大圖書(shū)小說(shuō)首作獎(jiǎng),作為《外鄉(xiāng)人》續(xù)集的《山村鄉(xiāng)巴佬》在眾人期待中上市,甫一出版便拿下作家信托獎(jiǎng)、入圍吉勒獎(jiǎng)短名單。故事傳承西部文學(xué)傳統(tǒng),背景設(shè)置于1917年加拿大落基山脈之間,塵土飛揚(yáng)的西部歷險(xiǎn)故事通常令人血脈僨張,但亞當(dāng)森的西部世界多了些冷峻與莊嚴(yán),父子二人歡鬧的歷險(xiǎn)旅程,又為其增添了幽默與溫情。亞當(dāng)森搜集老照片、閱讀軍人日記檔案,歷時(shí)十年完成這部小說(shuō),以細(xì)膩獨(dú)特的藝術(shù)手法與真實(shí)的氛圍感營(yíng)造出一個(gè)獨(dú)特的西部世界,為讀者帶來(lái)沉浸式的體驗(yàn):夜晚靜默的貓頭鷹、草原看不到盡頭的公路、天邊聚集的雨云……常在安靜的氛圍中一點(diǎn)點(diǎn)鋪展開(kāi)來(lái)。“遠(yuǎn)處一輛卡車開(kāi)來(lái),空車,默默卷起一路的塵土。他看著車開(kāi)走,猜它要到哪去。農(nóng)場(chǎng)、谷倉(cāng),或者是屠宰場(chǎng)。[……]卡車右側(cè),一團(tuán)駭人的烏云懸墜大地,圈聚在離莫蘭好幾英里遠(yuǎn)的地方。站在遠(yuǎn)處看陰云雨雪多美呀,不必?fù)?dān)憂那天氣會(huì)影響到自己。雨,雪,雷電,都是別人在經(jīng)歷。”
受疫情影響,加拿大重要文學(xué)獎(jiǎng)總督文學(xué)獎(jiǎng)宣布推遲發(fā)布2020年度獎(jiǎng)項(xiàng)。加拿大文學(xué)女王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ret Atwood)發(fā)布近十多年來(lái)首部詩(shī)集《深深地》(Dearly),主題涉及自然世界、親密關(guān)系、政治議題、女性地位、神秘傳說(shuō)等。加拿大圖書(shū)市場(chǎng)與美國(guó)展現(xiàn)出高度相似性,青少年兒童書(shū)籍銷量最多;非虛構(gòu)類作品中,《應(yīng)許之地》占據(jù)銷量榜首;虛構(gòu)類作品銷量前兩位分別是《美國(guó)塵土》及迪亞斯·歐文斯2018年出版的《蝲蛄吟唱的地方》。
(原文載《外國(guó)文學(xué)動(dòng)態(tài)研究》2021年第4期,“年度文學(xué)研究”專欄,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