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yè)余小說家”丘吉爾和他虛構(gòu)的“權(quán)力游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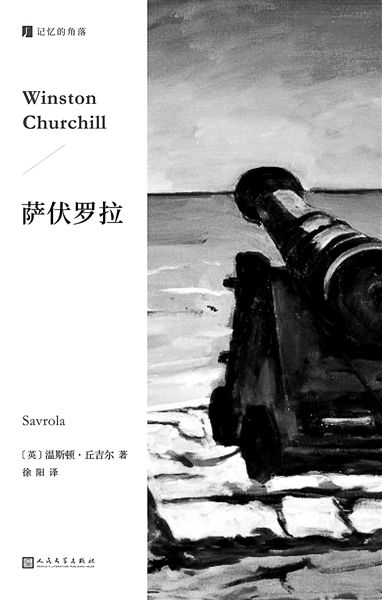
話說世紀(jì)之交,歐洲的政治形勢波譎云詭。地中海地區(qū)小國勞拉尼亞爆發(fā)了一場醞釀已久的政變。該國反對黨領(lǐng)袖薩伏羅拉年方三十二,得道者多助,始終面臨困難卻未經(jīng)多少坎坷,頗受上天眷顧。他的對手,勞拉尼亞總統(tǒng),雖然推行獨(dú)裁,卻是上一場內(nèi)戰(zhàn)的勝者,政治、軍事資源雄厚。雙方從暗斗到明爭,一同為看客們奉上了一場跌宕起伏、血脈賁張的大戲——這一切,均出自英國二十世紀(jì)偉大的政治家溫斯頓·丘吉爾之手。沒錯(cuò),《薩伏羅拉》正是丘吉爾被埋沒已久的唯一虛構(gòu)作品。
權(quán)力的游戲
剛拿到這本小說時(shí),我著實(shí)愣了一下:丘吉爾居然寫過小說?大家知道,他寫非虛構(gòu)是一把好手,憑借《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回憶錄》等作品獲得了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不過,丘吉爾在大學(xué)時(shí)已經(jīng)展現(xiàn)演講的才華,又是軍校畢業(yè)、經(jīng)歷過戰(zhàn)火,還做過隨軍記者,這么想想,他的確擁有小說創(chuàng)作的文字基本功和一手素材。
本書出版于1900年,時(shí)年丘吉爾26歲,是一位標(biāo)準(zhǔn)的“斜杠青年”,尚未步入政壇,卻已對政治展現(xiàn)出極其敏銳的嗅覺,當(dāng)然還有足以讓他日后獲得世界頂級文學(xué)桂冠的文字功力。他以接近專業(yè)的水準(zhǔn),為讀者“業(yè)余地”創(chuàng)作了這部《薩伏羅拉》,一場十九世紀(jì)末的“權(quán)力的游戲”。書中,作者既構(gòu)思了精彩詭譎的情節(jié),也很明顯地傾注了自己的感情。
英國現(xiàn)任首相、丘吉爾研究專家鮑里斯·約翰遜就認(rèn)為,薩伏羅拉很像是青年丘吉爾的理想化身。不過依我之見,書中其他人物也或多或少投射出了他青年時(shí)代的影子。此外,丘吉爾還在故事中融入了自己對政治乃至對哲學(xué)的深入思考,試圖通過虛構(gòu)來探討這些問題:歷史的惡性循環(huán)能否徹底打破?武力推翻獨(dú)裁個(gè)體之后,起義的人民及其領(lǐng)導(dǎo)人是否會(huì)重蹈覆轍?革命者在創(chuàng)造新歷史的過程中可否做到破中有立?……青年丘吉爾已經(jīng)擁有了指點(diǎn)江山的雄心。
《薩伏羅拉》的情節(jié)起伏跌宕,頗具張力,文筆則簡潔凝練、惜墨如金。總統(tǒng)和反對黨皆需考慮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群眾影響,自始至終同樣遭受這種擔(dān)心的折磨;每逢關(guān)鍵時(shí)間點(diǎn),下一刻總存在多重發(fā)展可能,扣人心弦;一支走到半路陷入進(jìn)退抉擇的艦隊(duì)(勞拉尼亞最重要的軍事威懾力)呈現(xiàn)出內(nèi)憂外患無法平衡的窘境;陣營界限模糊,無所謂實(shí)際意義上的“自己人”或“敵我”互動(dòng),表面陣營之下一直暗流涌動(dòng),推推搡搡。
除了框架性的節(jié)奏把控,作品中也不乏抓人的小瞬間:一位軍官正要向抗拒命令的中士開槍殺雞儆猴,軍政部長騎馬入場,來到士兵身旁打圓場,子彈就這樣憋回去了;保衛(wèi)總統(tǒng)府時(shí),中尉剛剛一擊斃敵,他身邊的中士立刻被敵人的子彈射中——丘吉爾精準(zhǔn)地刻畫了這一場景,中士贊嘆著中尉的槍法,自己也仔細(xì)地瞄準(zhǔn),專心致志的瞬間仿佛讓時(shí)間凝固,可倏然間,沒有尖叫,只有奇怪的聲響,他還沒來得及開槍,已經(jīng)血肉橫飛……簡短的幾句描述,人物形象、動(dòng)作、甚至聲音,栩栩如生地呈現(xiàn)在讀者眼前。
業(yè)余小說家
作為語言天賦和政治敏感度都極高的“業(yè)余小說家”,丘吉爾在《薩伏羅拉》里認(rèn)真嚴(yán)肅地組織了各位軍政人物的語言:在街頭激情演說和政壇微妙辭令之間切換自如的革命領(lǐng)袖、穿梭于官腔和閑談之間的霸道總統(tǒng)、能夠輕松應(yīng)對不同場面和人物的總統(tǒng)夫人、口氣冷硬利落的軍政部長、年輕活潑的軍官、圓滑謹(jǐn)慎的“墻頭草”秘書……作為親歷過殘酷戰(zhàn)爭的軍人和隨軍記者,他為讀者帶來了全景式的觀戰(zhàn)體驗(yàn)——巷戰(zhàn)、進(jìn)攻總統(tǒng)府、街頭突圍、海上炮擊等。首次經(jīng)歷戰(zhàn)爭的薩伏羅拉敏銳地觀察到各種細(xì)節(jié),與身經(jīng)百戰(zhàn)的軍官有著不同的體驗(yàn),形成完美互補(bǔ):薩伏羅拉和中尉穿越有埋伏的廣場,遇襲時(shí)中尉立即看清形勢,薩伏羅拉卻一頭霧水。另一邊,總統(tǒng)夫人在窗口似懂非懂地聆聽?wèi)?zhàn)況,越是不懂,越是不想錯(cuò)過任何一個(gè)細(xì)節(jié)——這種觀察也許與從未經(jīng)歷過戰(zhàn)爭的細(xì)心讀者同步;不必道破“子彈擦肩而過”等事實(shí)——當(dāng)事人那一刻還沒反應(yīng)過來,但我們都能通過音畫切實(shí)感受到。而作戰(zhàn)英勇、對政治卻絲毫不敏感的中尉,與手腕老練的薩伏羅拉、總統(tǒng)、秘書等同樣形成對比互補(bǔ),他這方面的后知后覺或與從未參政的讀者同步,或需委屈讀者放慢感知速度駐足觀看,但無論如何,透過他眼睛看到的政治資本、政治行為及其動(dòng)機(jī)都更加新鮮有趣。
當(dāng)然,如果我們一定要以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的標(biāo)準(zhǔn)來衡量丘吉爾,《薩伏羅拉》畢竟難以媲美第一流的文學(xué)。小說人物的多樣性未能有效地掩蓋某些角色的扁平。部分人物的設(shè)定稍有臉譜化的感覺,比如“偉大的民主人士”,很像古老史詩中帶上各自常用修飾語的英雄們。而且,那個(gè)年代的男性對女性的凝視似乎也是現(xiàn)代讀者無法忽視的,女性人物的扁平化尤為嚴(yán)重,以照顧他人為樂的老保姆與集美貌和心機(jī)于一身的總統(tǒng)夫人都被局限在傳統(tǒng)的性別角色中,雖然分別因其照顧者的奉獻(xiàn)精神或是交際手腕與美貌而得到男權(quán)社會(huì)的認(rèn)可,但是在關(guān)鍵時(shí)刻也只能無助而被動(dòng)地等待來自男性的拯救。此外,彼時(shí)的作者可能閱歷尚淺,似乎急于讓讀者理解角色,以至于故事中有些心理描寫和對話稍稍顯得多余,把本該微妙的人物內(nèi)心世界說沒了深意。
最讓我意難平的是結(jié)尾:盡管全書整體節(jié)奏感非常強(qiáng),最后兩段卻像是在草草為讀者捧出主要人物的未來走向。這同樣是一種“古樸”的做法,許多小說家都有過這種焦慮:擔(dān)心讀者會(huì)因?yàn)椴恢廊宋锏淖罱K命運(yùn)而慍怒——人物伴隨他們已久,理應(yīng)給個(gè)交代。或有讀者會(huì)認(rèn)為,《薩伏羅拉》的結(jié)尾旨在點(diǎn)出歷史和民心的變幻無常,但在我看來,它更接近于一種理想化的倉促“發(fā)糖”。這兩段曾是責(zé)編老師和我的共同“槽點(diǎn)”,然而我們只能如實(shí)呈現(xiàn),相信各位看官自有公論。
典型“直男爽文”
所以,《薩伏羅拉》或許不算“最好的”小說,但它絕對是一本“很好玩的”小說。責(zé)編老師曾跟我開玩笑說,這是一本典型的“直男爽文”。然而,這里有種網(wǎng)絡(luò)“爽文”絕不可能具備的歷史感和真實(shí)感,丘吉爾初露鋒芒的文學(xué)素養(yǎng)也會(huì)給閱讀帶來意想不到的驚喜。確實(shí),就像鮑里斯·約翰遜所說,在閱讀這本書的同時(shí),不斷對照薩伏羅拉和丘吉爾的形象,會(huì)帶來許多難以想象的閱讀樂趣。當(dāng)然,可能也有和我一樣的讀者,先撇開作者的身份,專心聽他講這個(gè)故事,再不時(shí)回過頭來感嘆一句:丘吉爾居然會(huì)這樣寫!
能夠翻譯丘吉爾在中文世界“被忽略”的虛構(gòu)作品是我莫大的榮幸。多輪修改,不僅是編輯部的要求,也是譯本的要求:優(yōu)雅、凝練而富于節(jié)奏感的語言是這部作品的重要特色,面對這樣一部作品,譯后一兩輪磨合是遠(yuǎn)遠(yuǎn)不夠的。它不僅需要“中間人”用眼睛去看,也要用耳朵去聽。翻譯前、翻譯中、翻譯后,我都會(huì)不時(shí)大聲念出文本,體會(huì)節(jié)奏和重心,聆聽語氣,聆聽“音效”。即便如此,我也只能是盡力而為。
看著由電腦里的文檔變成眼前精致的紙質(zhì)書,又是莫大的欣慰。作為書籍“顏控”,見到封面上選用了丘吉爾本人的繪畫(恰好還暗示了故事線索),見到目錄和內(nèi)文舒服的字號、頁邊距和行間距,我也收獲了意料之外的喜悅。作為中文版最早的讀者之一,我想說,這是一本手感很不錯(cuò)的公版書。責(zé)編老師說,做這套“記憶的角落”叢書,不僅是為了拾遺補(bǔ)漏,也是為公版書正名。能為這項(xiàng)大工程做一些微不足道的努力,參與一處發(fā)光“小角落”的修繕工作,我感到非常開心。在此與諸位分享一些“考古挖掘”體會(huì),希望有機(jī)會(huì)與讀者朋友們共賞這位“業(yè)余小說家”的有趣側(cè)面。
(注:本文作者為《薩伏羅拉》一書的譯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