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克·懷特和他的《特萊龐的愛情》

帕特里克·懷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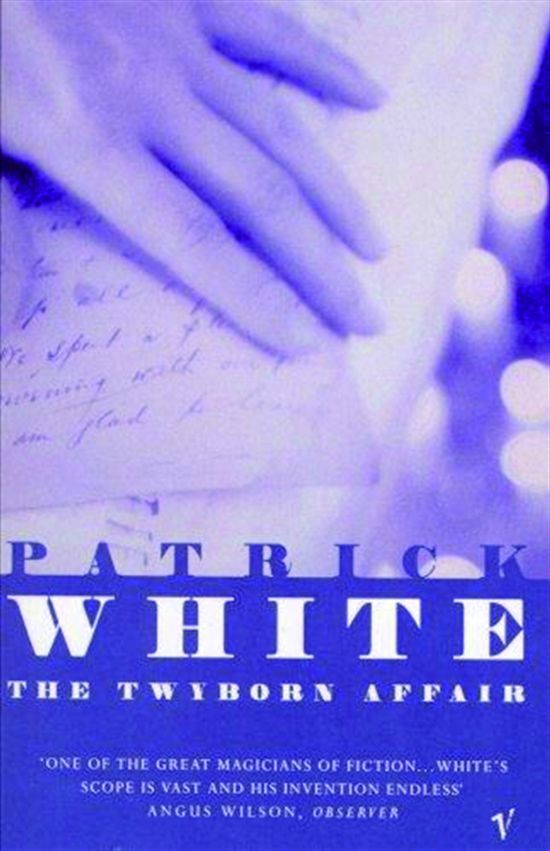
《特萊龐的愛情》英文版封面
1973年,瑞典皇家學(xué)院在斯德哥爾摩宣布:“本年度的諾貝爾文學(xué)獎授予澳大利亞作家帕特里克·懷特”,因為“他史詩般的、擅長刻畫人物心理的敘事藝術(shù),把一個新的大陸介紹進文學(xué)領(lǐng)域”。帕特里克·懷特是一位文學(xué)奇才,也是20世紀最重要的英語作家之一。他一生著述頗豐,主要著作有長篇小說《幸福谷》(Happy Valley,1939)、《生者與死者》(The Living and the Dead,1941)、《姨媽的故事》(The Aunt’s Story,1948)、《人樹》(The Tree of Man,1955)、《探險家沃斯》(Voss,1957)、《乘戰(zhàn)車的人們》(Riders in the Chariot,1961)、《堅實的曼陀羅》(The Solid Mandala,1966)、《活體解剖者》(The Vivisector,1970)、《風(fēng)暴眼》(The Eye of the Storm,1973)、《樹葉裙》(A Fringe of Leaves,1976)、《特萊龐的愛情》(The Twyborn Affair,1979)、《百感交集》(Memoirs of Many in One,1987)等12部;中短篇小說集《燒傷者》(The Burnt Ones,1964)、《白鸚鵡》(The Cockatoos,1974)和《三則令人不安的故事》(Three Uneasy Pieces,1987)等3部。此外還有自傳《鏡中瑕疵》(Flaws in the Glass,1981);劇本《重返阿比西尼亞》(Return to Abyssinia,1974)、《大玩具》(Big Toys, 1977)等。
帕特里克·懷特1912年5月28日出生于倫敦,半年后回到澳大利亞。他的父親是澳大利亞一位農(nóng)場主,母親也出生于富裕的農(nóng)場主家庭。懷特在澳大利亞鄉(xiāng)間度過無憂無慮的童年,13歲被送到英國接受傳統(tǒng)的英國教育,“在英國公學(xué)把自己熨燙得平平整整”。但他難忘在故鄉(xiāng)度過的快樂時光,痛恨被“熨燙”的4年。畢業(yè)后,懷特立刻返回澳大利亞,到牧羊場做“學(xué)徒工”。艱苦的生活環(huán)境不但磨礪了年輕的懷特,也為他日后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積累了豐富的素材。1932年,懷特再度到英國,在劍橋大學(xué)攻讀現(xiàn)代語言。在此期間,他閱讀了大量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文學(xué)作品,深受喬伊斯、勞倫斯、司湯達、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普魯斯特、蘭波、埃德蒙·威爾遜和亨利·詹姆斯的影響,為其從事文學(xué)創(chuàng)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1939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長篇小說《幸福谷》。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懷特服役于英國皇家空軍情報部門,在非洲、中東和希臘等地工作5年,1948年回到祖國澳大利亞,在悉尼遠郊的一座農(nóng)場和他的摯友——希臘人曼努雷·拉斯堪瑞斯過著牧羊人的田園生活。然而,這種平靜的“田園生活”只是一種表象。退避三舍、離群索居的日子喚起懷特對人生深刻的思索,使他爆發(fā)出巨大的創(chuàng)造力。如他所說:“我周圍是一片真空,而我的天性正需要這樣一片天地,以期滿懷激情地生活。”在這片天地,他創(chuàng)作了《人樹》《探險家沃斯》《乘戰(zhàn)車的人們》等重要著作,在世界文壇引起廣泛關(guān)注。上世紀60年代初,懷特從遠郊農(nóng)場搬到悉尼百歲公園馬丁路二十號,在綠樹掩映的書房寫下著名的長篇小說《風(fēng)暴眼》《堅實的曼陀羅》《樹葉裙》《特萊龐的愛情》……直到1990年9月30日在那幢和他及曼努雷同年“出生”的房子里與世長辭。
作為澳大利亞最著名的作家,帕特里克·懷特的作品具有鮮明的澳大利亞屬性。他的著作都涉及了澳大利亞歷史的重要方面,以極其生動的筆觸表現(xiàn)了澳大利亞生活的獨特之處——五彩繽紛的內(nèi)心世界的感知,鄉(xiāng)音土語的特殊結(jié)構(gòu),喜劇式的社會生活的精巧優(yōu)雅,以及澳大利亞人理念中陰郁的哲學(xué)思辨。帕特里克·懷特的小說剛剛面世的時候,讀者往往大惑不解,并且感覺到一種挑戰(zhàn)。因為在他之前,從來沒有一位澳大利亞作家這樣深刻地揭示這個國家的社會問題,以及這個國家的人們作為互不相同的個體內(nèi)心世界的沖突。帕特里克·懷特描繪的這幅澳大利亞的畫圖并不取悅于他的觀眾。他表現(xiàn)了這塊土地的美麗、友愛,也暴露了它的丑陋和破壞力。可是,經(jīng)歷了最初的抵制,讀者總是很快就意識到,懷特的作品充滿熾熱的感情,努力向真理的目標(biāo)求索。
懷特的創(chuàng)作方法對于讀者也是一種挑戰(zhàn)。他既植根于小說創(chuàng)作的傳統(tǒng),從諸如狄更斯、陀斯妥耶夫斯基、哈代這樣一些文學(xué)大師的作品中汲取營養(yǎng),又緊跟傳統(tǒng),熱情擁抱現(xiàn)代派藝術(shù)發(fā)展的大潮,從約瑟夫·康拉德、D.H.勞倫斯、詹姆斯·喬伊斯的著作中獲益。他以濃厚的印象派的表現(xiàn)方法、詩一樣的語言、意識流、黑色幽默,以及敘事技巧、觀點表述上的“支離破碎”,把現(xiàn)代主義的藝術(shù)技巧和創(chuàng)作態(tài)度引進到澳大利亞小說創(chuàng)作上來。他善于探索人的精神世界,在社會的荒原中尋找生命的終極意義,被認為是與喬伊斯、勞倫斯等齊名的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巨匠。
但是懷特小說的讀者遇到的最大困難或許是他帶有強烈個人色彩的想象力。他把世界看作光明與黑暗、善與惡、靈與肉無休止的沖突。他試圖將人類所有潛在的能力——從破壞力到創(chuàng)造力,從最崇高到最卑鄙,都包容在自己的作品之中。而他晚年創(chuàng)作的《特萊龐的愛情》更將他的這種努力推向極致。
帕特里克·懷特在自傳《鏡中瑕疵》中坦言:有時候我很納悶,如果我生來就是一個只愛異性的普通男人,生活該是什么樣子呢?如果我是一個藝術(shù)家,或許會是一個自負的、夸夸其談的家伙。當(dāng)我因為成功,而面對那面可以透視靈魂的鏡子夸耀自己的時候,也許會像歌德那樣,突然發(fā)現(xiàn)比被自己拋棄的門徒艾克曼還差。我的地地道道的男性的基因會使我獲得開拓性的快樂。作為父親,我可能是一個讓人無法忍受的老頭,孩子們會討厭我,小瞧我,看透我并非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我可能接受什么封號、勛章;死后甚至?xí)槲遗e行國葬,盡管由于根深蒂固的虛偽,我總會裝模作樣地拒絕。
如果我是個女人,一定會是個生殖能力很強的母親,不顧自己的辛勞,心甘情愿地為丈夫生出一大堆兒女。我會溫柔多情,也會妒火中燒;會因為某種原因和結(jié)果忿忿不平,也會因為難以避免的失敗暗吞苦水。或許我會選擇妓女的生活。因為我可以比女演員扮演更多的角色。我會把男性“觀眾”哄得團團轉(zhuǎn),讓他們以為我是他們手心里的一個可以任意玩弄的玩物。然后,當(dāng)他扣好扣子的時候,就把他那張妄自尊大的人皮撕得粉碎,再扔還給他。要么,我會是個修女,白皙的臉龐上掛著一絲淡淡的微笑,獻身于人們最需要的精神上的愛戀。
我心中那種既愛又恨的感情賦予我一種洞察人類本性的能力。而這種能力,我相信,那些不折不扣的男人或者女人是不會具備的。我這幢不倫不類的“房子”盡管東倒西歪,不堪一擊,但絕不會拿它去換那些自認為自己是地道的男人或地道的女人所筑起的“城堡”。
事實上,帕特里克·懷特一生都在這幢不倫不類的“房子”的擠壓中,竭盡全力地探求自我。而《特萊龐的愛情》就是這條探求之路上的一座豐碑。小說主人公尤多西婭(Eudoxia)/埃迪·特萊龐(Eddie Twyborn)/伊迪絲(Eddith)具有男性軀體和女性意識。像懷特筆下的其他人物一樣,她/他渴望擺脫壓抑的生存環(huán)境,尋找業(yè)已消失的自我。懷特的不同凡響之處在于用主人公不斷變換性別的嘗試描繪尋找自我的痛苦歷程。小說第一部以充滿詩意的筆調(diào)描繪了埃迪·特萊龐為逃婚,突然失蹤,“變性”為妙齡女郎尤多西婭,委身于年長其40多歲的希臘“皇室后裔”安杰洛斯,漂泊到一個法國小鎮(zhèn),過著遠離塵世的平靜安寧的生活。但是在這個他們自以為天之涯、海之角的地方,尤多西婭的母親伊迪·特萊龐的密友瓊·戈爾森太太突然出現(xiàn),徹底打破了他們的“平靜與安寧”。瓊·戈爾森太太是位女同性戀者,對尤多西婭一見鐘情,窮追不舍。尤多西婭生怕暴露“真面目”,和安杰洛斯匆匆逃離小鎮(zhèn),途中安杰洛斯心臟病突發(fā),猝死于法國邊境一家小旅館,從而解除了兩人始終壓抑的關(guān)系。小說第二部,主人公又“變性”為英俊瀟灑的埃迪·特萊龐。埃迪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立功受獎,以中尉的身份退伍回到澳大利亞,出現(xiàn)在驚詫不已的父母面前。但他始終無法和父母建立坦誠相待的關(guān)系,在家中小住幾日便獨自一人到澳大利亞內(nèi)陸博貢,成為父親的朋友大牧場主格雷格·盧辛頓的“牧場學(xué)徒工”。埃迪在博貢深受大家的喜愛,來牧場不久便與格雷格·盧辛頓的妻子瑪西婭成為情人。而與瑪西婭關(guān)系曖昧的牧場經(jīng)理唐·普勞斯因為和埃迪朝夕相處,兩個人建立了一種十分微妙的關(guān)系。這種相互矛盾的關(guān)系,使得埃迪在感情的漩渦越陷越深,痛苦掙扎不得解脫,最終只能離開博貢,再次失蹤。小說第三部,主人公又成女性。化名為伊迪絲·特里斯特夫人。此時,她雖然早已步入中年,但儀態(tài)萬方,風(fēng)韻猶存,吸引了英國上流社會的許多達官貴人。但伊迪絲“超然物外”,漠然視之。后來,在格雷文諾勛爵的資助下,伊迪絲在倫敦開了一家高級妓院,閱盡人間春色與丑惡。格雷文諾一直深深地愛著伊迪絲,伊迪絲也把他當(dāng)作情人與心靈的依托,但她無法向他吐露真情,無法揭穿自己的真實身份。只能在貌似奢華的幻境中苦苦掙扎,直到和格雷文諾最后一次見面,才明白不管他是男性還是女性,格雷文諾都深深地愛著她。彼時,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即將爆發(fā),格雷文諾從戰(zhàn)火紛飛的遠方,寫信給她:“如果我們有勇氣,本來可以光明正大、充滿人情味兒地彼此相愛。男人和女人并非人類等級體系中唯一的成員,盡管你我都宣稱自己屬于其中……‘愛’是一個被人用濫了的字眼兒,上帝已經(jīng)被那些更懂得愛的人驅(qū)逐。而我給你的愛將成為愛依然存在的另外一個證據(jù)。”
然而,格雷文諾“愛的證據(jù)”并不能給伊迪絲帶來希望的光明,也沒有照亮她在一片黑暗中尋覓的自我。小說的結(jié)尾構(gòu)思奇巧,震撼人心。尤多西婭/埃迪·特萊龐/伊迪絲的母親伊迪·特萊龐奇跡般出現(xiàn)在戰(zhàn)火即將燃起的倫敦,許多年未曾謀面的“母女倆”在一張夕陽照耀的長椅上“邂逅相逢”。
她們相互凝視著,伊迪絲的眼睛猶如藍色和金色的碎片,緊張地燃燒。但她們的決心沒有被那火焰融化。伊迪的眼睛猶如沒有光澤的黃玉,與困惑不安的老狗的眼睛無異。還是那張娃娃臉,皮膚柔軟、白皙。蒼白的嘴唇劇烈地顫抖,最后不得不轉(zhuǎn)過身去。
兩個女人繼續(xù)并排坐著,直到伊迪鼓起勇氣在包里摸索著尋找什么。她找到一截鉛筆,在祈禱書的扉頁上潦潦草草寫下幾個字。
她用顫抖的手把祈禱書遞給伊迪絲。那幾個潦潦草草的字映入伊迪絲的眼簾:“你是我的兒子埃迪嗎?”
……
她抓起鉛筆,在祈禱書的扉頁上劃拉了幾個字,那股野蠻勁兒連她自己都沒有感覺到。
書遞回到伊迪·特萊龐的手里,上面寫著:“不是,但我是你的女兒伊迪絲。”
兩個女人繼續(xù)坐在越來越濃的暮色中。
過了一會兒,伊迪說:“真高興。我一直想要個女兒。”
“母女相認”,這令人淚奔的一幕似乎為小說畫了一個圓滿的句號,然而文學(xué)大師帕特里克·懷特給出的是另外一幅畫面。與母親相認之后,伊迪絲決定將妓院移交給助手艾達,開始新的生命之旅。她脫下薄如蟬翼的長裙,撕掉胭脂涂抹的“畫皮”,恢復(fù)男兒身,以埃迪的身份去尋找母親。遺憾的是,她/他終究無法逃脫命運的羅網(wǎng),前往母親下榻的旅館路上,埃迪遭遇敵人空襲,慘死在血泊之中。母親卻在炮火連天的倫敦大轟炸中繼續(xù)做著與埃迪/伊迪絲團聚的夢:
……我絕不能讓伊迪絲失望,既然找到了她——伊迪絲/埃迪。無論從我身上掉下來的這塊肉是怎樣一個存在,現(xiàn)在都已經(jīng)回到她/他的歸屬之地。
坐在花園里,在白鷺的鳴囀和水龍頭滴答作響的水聲中一起晾干頭發(fā),我們終于體會到和諧的美好。
她喜歡鳥兒。晾干頭發(fā)等待伊迪絲/埃迪的時候,一只白鷺棲息在石頭鳥池邊緣,喙啄著池里的水。它弄亂羽毛,歪著頭看她,搖了搖小丑帽似的、絲絨般光滑的羽冠,把喙伸向太陽。
“把喙伸向太陽”,是《特萊龐的愛情》貫穿始終、令人難忘的意象。它象征小說的主人公雖然對自己追求的目標(biāo)并無把握,但從未停止過努力。而太陽下的現(xiàn)實是:無論他以男性的面目出現(xiàn),還是以女性的面目出現(xiàn),都將以失敗告終。
《特萊龐的愛情》另外一個顯著的特點是,為了表現(xiàn)主人公追尋自我的不懈努力,作者除了描寫他/她改變性別的嘗試之外,還有意識地變換主人公的生存背景、職業(yè)、身份。小說的時間跨度長達30多年,連接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第一部的背景是法國海濱小鎮(zhèn),第二部是澳大利亞中部牧場,第三部是英國首都倫敦。第一部主人公是“皇室后裔”希臘老人安杰洛斯的妻子;第二部是博貢牧場的“學(xué)徒工”、女主人瑪西婭的情人;第三部是高級妓院老板、格雷文諾勛爵求而不得的戀人。這就使得這部山水迥異的小說色彩繽紛,讓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小說涉及的文化背景、風(fēng)土人情、方言土語、生活習(xí)俗當(dāng)為帕特里克·懷特作品之最。再加上作者細致入微的心理描寫、時空顛倒的意識流動,讀起來撲朔迷離,云里霧里。所有這一切對于譯者都是極大的挑戰(zhàn)。在迎接挑戰(zhàn)、潛心翻譯的兩年里,特別感謝我的朋友、《兩只公雞》(Two Roosters)合作者——澳大利亞著名歷史學(xué)家、澳大利亞社會科學(xué)院院士、人文學(xué)科學(xué)院院士大衛(wèi)·沃克(David Walker)教授和他的妻子凱倫·沃克(Karen Walker)教授的熱情幫助。兩年間,每當(dāng)我陷入困境,不知所措的時候,便求教于他們。兩位教授總能及時相助,動用他們的知識寶庫,引經(jīng)據(jù)典,答疑解惑,使我柳暗花明,茅塞頓開。毋庸諱言,正是由于他們的鼎力相助才使我在翻譯這本書的過程中,避免了許多貽笑大方的錯誤,盡管華麗的文字背后一定還埋藏著許多令人汗顏的紕繆。還望專家學(xué)者、有識之士、熱愛帕特里克·懷特作品的讀者不吝賜教。文學(xué)翻譯實在是一門讓人常感力不從心、又愛又恨的藝術(shù)。這或許是我翻譯完這本書之后,發(fā)自內(nèi)心深處的感慨!
(本文為《特萊龐的愛情》譯者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