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吉訶德》:阿拉貝拉出走以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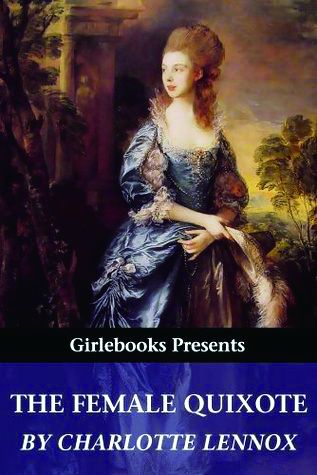
《女吉訶德》
《女吉訶德》,亦稱《阿拉貝拉歷險記》(The Female Quixote,Or The Adventures of Arabella),是18世紀英國女作家夏洛特·倫諾克斯(Charlotte Lennox)的代表作。該小說是對塞萬提斯《堂吉訶德》的戲仿,1752年出版后受到文壇名家塞繆爾·理查森、亨利·菲爾丁和塞繆爾·約翰遜的一致贊譽,認為其思想性與藝術性幾乎可以與同時期出版的《克拉麗莎》《湯姆·瓊斯》和《蘭登傳》媲美。該書在后世也產生了較大影響:簡·奧斯汀《諾桑覺寺》以之為范本;巴爾扎克在《幻滅》中曾借鑒其人物形象;福樓拜筆下的包法利夫人則堪稱“女吉訶德”的現代版——其悲劇精神可視為塞萬提斯與倫諾克斯的合體。
正如堂吉訶德因沉迷騎士小說而陷于“瘋狂”,小說女主阿拉貝拉閱讀了過多的法國浪漫小說,結果“走火入魔”。堂吉訶德錯將自己當成浪漫傳奇中的騎士英雄,阿拉貝拉則錯將自己當成浪漫故事中的戀愛少女(相信自己能用眼神“殺死”對方,并且堅信戀人有責任為之赴湯蹈火,同時又不得不備受煎熬)。當然,和唐吉訶德不同的是,阿拉貝拉不是與巨人風車搏斗,而是奮力反抗固化的社會觀念。
阿拉貝拉生活在幽僻的英國城堡,由鰥居的父親撫養(yǎng)成人。她自幼飽讀母親遺留的法國愛情小說——以斯居代里(Scudéry)夫人為代表,期待自己的生活也會同樣轟轟烈烈,浪漫而美好。父親在離世前宣稱,如果阿拉貝拉不與堂兄格蘭維爾爵士(Sir Charles Glanville)結婚,那么極有可能失去部分(甚至全部)財產。擺脫了父親的威壓,阿拉貝拉決定外出闖蕩。當她初次涉足巴斯和倫敦的時尚社會時,仿佛童話中人物“亂入”現實生活,鬧出了若干大笑話。在她看來,所有男人都心懷鬼胎、圖謀不軌——格蘭維爾接近她的目的只有一個:騙婚;他的競爭對手貝爾摩爵士(Sir George Bellmour)表面對她一味順從,事實上只為滿足他自己獵艷的虛榮心;甚至當格蘭維爾的老父親試圖勸說這位“未來”的兒媳婦盡早完婚時,也被認為對她心存“非分之想”。于是她益發(fā)堅定“不婚”的信念。
最能體現阿拉貝拉荒唐念頭的例子是園丁愛德華,他因為從城堡的池塘里偷盜鯉魚而遭毆打,然后被驅逐——阿拉貝拉卻堅信這是一位來自遙遠國度的王子,他假扮仆人,忍受凌辱,只是為了帶領她逃離是非之地。她的這一種執(zhí)念,最初只是將到她府上做客的男青年身體抱恙誤以為是為她害了相思病,后來則發(fā)展為處處“疑心生暗鬼”:晚上走在倫敦街頭,她始終相信不遠處馬背上的男人尾隨跟蹤并試圖誘拐她,于是鼓足勇氣,跳入泰晤士河,差點斷送性命。根據作者描述,當時她腦海中浮現的正是斯居代里夫人筆下的場景——她“將眼前的運河誤作臺伯河,向其全速奔跑,并縱身一躍,覺得自己就是克萊利亞(Clielia),并且也能像她一樣游過去。”——小說中的克萊利亞投身臺伯河,“以求保全自身,免受輕浮浪蕩的塞克斯都(Sextus)的侵害”,正是阿拉貝拉意欲效仿的對象。獲救之后,阿拉貝拉大病一場。醫(yī)生(同時也是一位教會人士)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向她解釋了社會現實和文學幻想之間的區(qū)別。阿拉貝拉如夢方醒:她“恢復了理智”,最終決定接受格蘭維爾的求婚,從此過上安寧幸福的家庭生活。
盡管小說“大團圓”式的結局與主流社會價值觀頗為契合,但小說人物展現出的“過激”言行,在保守人士看來無異于叛道離經,令人深感不安。尤其是阿拉貝拉面對一眾男性,不但缺乏應有的敬畏,反而自恃美貌和才智,頤指氣使,顯然有悖于上流社會紳士淑女的傳統道德觀。作為父權制社會的代表和象征,阿拉貝拉的父親首當其沖成為她反抗的對象。擔心女兒沉溺于浪漫幻想不能自拔,她的父親決定將此類“翻譯得很糟糕”的外國小說悉數焚毀。目睹這一場面,阿拉貝拉為那些“將被投進無情的火焰”的浪漫騎士的命運感到悲哀,甚至一度悲觀絕望想要自殺——在18世紀的文學作品中,“勇敢”的女性因生活打擊而自殺,乃是尋常之事。熟讀浪漫小說的阿拉貝拉對此心知肚明,自然也不缺乏這樣的勇氣;但她轉念一想,覺得比自殺更好的報復手段無過于拒絕嫁給父親中意的格蘭維爾——如此一來,他老人家定當死不瞑目。
平心而論,格蘭維爾出身名門,智勇雙全,對阿拉貝拉也一見傾心,始終如一。阿拉貝拉卻屢屢拒婚,頗有些無理取鬧。倘若一定要找出搬得上臺面的理由,只有一條,即格蘭維爾沒有做出“任何值得她去愛的事情”。從一開始,他就沒有按照“浪漫的程式”來追求她。他的情感過于“熾熱”,他的崇拜過于“親密”,所以她要求他遵守騎士的愛情規(guī)則(rituals),與她保持恰當距離以示尊重。格蘭維爾照此辦理。但他既不像小說中的騎士“為愛憔悴”(反而日益增肥),也沒有計劃冒險遠征,降妖除魔,然后在她的等待和期盼中凱旋歸來。
為了證明自己的魅力,同時考驗格蘭維爾的“忠誠度”,阿拉貝拉曾下令,要格蘭維爾殺死一名試圖“跟蹤并綁架”她的嫌犯,以此來展示他的“勇氣”。當旁人提出此舉可能涉嫌謀殺時,阿拉貝拉慨然回答:“英雄可以隨便殺死壞人;愛殺多少殺多少。”——浪漫傳奇中英雄人物從來不受人間律法的約束。她陶醉在浪漫小說編織的美妙世界,連衣著服飾,以及言談舉止都要一絲不茍地加以模仿。像堂吉訶德需要桑丘隨行征戰(zhàn)四方,阿拉貝拉也致力于找尋一名侍女,陪伴她開啟冒險之旅。她在一所教堂遇到“迷人”的格羅夫斯小姐(Miss Groves),結果卻發(fā)現,這位小姐15歲時便與家庭教師有染,后來又與一位已婚紳士產生婚外情(有兩個私生子以及一段秘密婚姻)。這一類道德觀念淡薄的女性往往為上流社會所唾棄,但阿拉貝拉對她卻無端生出幾分羨慕:根據描述,格羅夫斯小姐出身貧寒,打小“喜愛男性運動”——包括“翻越籬笆和橫跨溝渠”,這些粗獷的運動使得她擁有了與其性別不符的強健身體,甚至“帶有一絲陽剛之氣”。與此同時,這位小姐復雜的人生閱歷,更加堅定了阿拉貝拉闖蕩歷險的決心。
在經歷了一連串喜憂參半的鬧劇之后,阿拉貝拉遇到了年高德劭的伯爵夫人。當阿拉貝拉打算向伯爵夫人講述她的“歷險記”時,后者不容置疑地將她打斷:“歷險記,該詞通常意味著自由和放蕩,以至于人們很難恰當地把它運用于那些構成女性榮譽的歷史性事件。”在她看來,一個女人出生,長大,遇到一個男人,出嫁,這就是故事(history)的結束。由此阿拉貝拉與伯爵夫人展開了深入探討。與伯爵夫人觀點不同,阿拉貝拉認為道德善惡并無絕對標準,往往隨歷史背景而改變,因此固守道德教諭未必是明智之舉。自始至終,這場對話實質上與男人無關;而是涉及道德、文學、歷史等“嚴肅”話題——可謂是整個18世紀文學史中女性主導的最為有趣的談話之一。雖然伯爵夫人意在糾正年輕女子阿拉貝拉的“瘋狂想法”并試圖改造阿拉貝拉:“歷險一詞用到女人身上會有失傳統,因為好女人身上從來不會有故事發(fā)生……我從出生受洗,接受適當而實用的教育,直到得到我夫家的姓氏——這一切都是在我父母的建議下做的,我嫁給他也是得到父母的許可,自己心甘情愿的,而且因為我們生活得很和諧……這一切與跟我有著同樣地位、同樣理性、謹慎并有德行的女人沒什么不同。”然而事實上,這一番循規(guī)蹈矩的“道德經”并未能說服阿拉貝拉,相反,倒是后者的“瘋言瘋語”占了上風。值得一提的是,伯爵夫人此后從小說中消失,直至終章也未能再次露面,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倫諾克斯安排這一角色,無非是借人物之口表達作家本人對社會習俗的不滿和嘲諷。
這也正是作家倫諾克斯的高明之處:如同她筆下人物阿拉貝拉用浪漫小說為自己創(chuàng)造出“另一種現實”并退避其中——唯有在此間她的“瘋狂”舉動才有可能被接納。換言之,正是這種“瘋狂”給了她某種程度上思想和行動的自由,使得她能夠從充滿偏見的社會習俗中掙脫出來,展示出獨立自我的女性形象。倫諾克斯也借助于阿拉貝拉這一形象,“重新定義了女性的社會地位,認為女性主體具有絕對的、不容置疑的中心地位,而男性人物則在邊緣地帶打轉。”起初,格蘭維爾企圖教導阿拉貝拉成為一名傳統女性。但很快,角色便發(fā)生置換,老師變成了學生:阿拉貝拉時時教導格蘭維爾如何行事。事實上,整部小說中,包括格蘭維爾在內,沒有一位男性能在智力上與阿拉貝拉并肩。查理先生時時被她駁得啞口無言,見多識廣的歷史學家塞文斯先生也不得不承認阿拉貝拉比他讀過更多的歷史書——承認她“閱讀廣泛”、“記憶超群”、能夠“活學現用”且具有“良好的判斷力……如果她是一名男人,肯定能進下議院”——這既是對女性人物的美化,也寄寓了作家的社會理想。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當代評論家將阿拉貝拉背后的倫諾克斯譽為英國“最早的女權主義代表”(早于沃斯通克拉夫特《為女權辯護》約半個世紀)。
作家的激進姿態(tài)不僅受到男性同行(和讀者)的抨擊,也受到女性作家——包括“藍襪子”俱樂部成員——的質疑。蒙塔古夫人(Lady Montagu)是該俱樂部創(chuàng)始人,被譽為“藍襪子女王”,倫諾克斯則為其中一員。以蒙塔古夫人為首的女才子盡管學識淵博,但在兩性關系方面卻恪守傳統。她們指責倫諾克斯在書中的論斷,即女性擁有對愛情的絕對主宰地位:“多一點點順從和尊重,你的日子會變得更好過;你現在完全處于我的掌控之中”(阿拉貝拉語)。在她們眼里,這樣的言辭對男性是極大的侮辱和冒犯,有“顛覆”現行社會秩序之嫌。倫諾克斯筆下的阿拉貝拉受她所讀小說的影響,將當時所有社會機制看成是墮落的表征:高尚的英雄風范被遺棄,男男女女都把時間浪費在無聊的事情之上——訪客、打牌、跳舞,一切都是娛樂和消遣;無論是公開場合還是私人宴席的談話,無不充斥著誹謗和惡意的流言;社會階層固化:是出身和社會地位而不是道德品行決定了一個人能否出人頭地——盡管這些評論的確如實描述了18世紀中期英國社會生活的狀況,但阿拉貝拉的控訴卻普遍被當成一種“瘋癲”,正如倫諾克斯本人被視為“一位煽動者”。
除了小說創(chuàng)作,倫諾克斯在詩歌和戲劇方面也卓有建樹。1750年,她在《紳士雜志》(Gentleman's Magazine)上發(fā)表詩作《賣弄風情的藝術》(“The Art of Coquetry”),大獲成功。1750年代中期,她對莎士比亞戲劇源頭產生了濃厚興趣。在刊載于《莎士比亞畫報》(Shakespear Illustrated)第三卷的莎劇劇評中,倫諾克斯旁征博引,探討了莎士比亞戲劇的浪漫主義(古羅馬、威尼斯)元素,開日后浪漫派莎評之先河。與此同時,她認為莎士比亞戲劇也存在明顯缺點——剝奪了女性角色原有的威權,“褫奪了女性權力/力量(Power)和情感獨立,而這些在他援引的文學經典中原本有所體現”。這一番不自量力挑戰(zhàn)權威的言論,如同堂吉訶德挑戰(zhàn)風車,給她本人招致了巨大的麻煩(盡管約翰遜博士為之題詞背書)。她的戲劇《姐妹》(The Sister)——改編自她的小說《亨麗埃塔》(Henrietta)——首演之夜,若干“挺莎”的觀眾和戲劇愛好者聯合起來,大喝倒彩,最終只得黯然收場。
倫諾克斯這位被稱為“英國九大繆斯之一”的著名作家,晚年與丈夫分居后貧病交加,死后安葬于考文特花園(Covent Garden)附近一家無名公墓。正如18世紀詩人波爾維爾(Richard Polwhele)在名詩《無性的女性》(“The Unsex’d Females:A Poem”) 中預言的那樣:特立獨行的女作家往往被誣蔑成家庭和社會的“怪物”,不能見容于世。像她筆下的阿拉貝拉,從“讓愛做主”到“美德有報”,歷經磨難,終點卻又回到起點,令人扼腕嘆息。自小說《女吉訶德》面世至今已逾250余年,然而歷史似乎始終走不出“阿拉貝拉走后怎樣”這一怪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