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圍攻美因茨》:由此證之


《圍攻美因茨》德文版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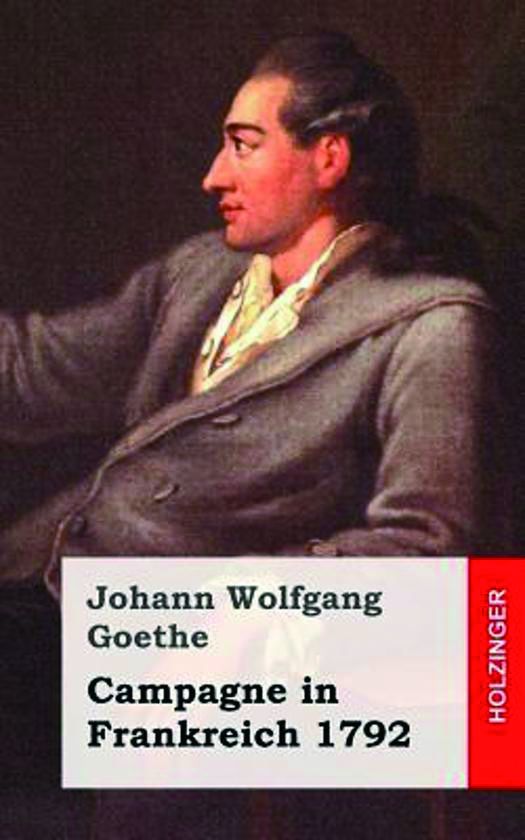
《進軍法蘭西》德文版封面
約200年前(1822年),歌德文庫里的兩部戰(zhàn)爭文學《進軍法蘭西》(Campagne in Frankreich)和《圍攻美因茨》(Belagerung von Mainz)首次刊印。《圍攻美因茨》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部。它有很大的回憶、自敘性成分,主要依據(jù)是歌德44歲那年的一次參戰(zhàn)經(jīng)歷和日記,故而可以將書中的敘事者與作者歌德直接聯(lián)系起來。那次戰(zhàn)爭是1793年春普奧聯(lián)軍對德國萊茵河畔城市美因茨發(fā)動的圍攻之戰(zhàn),起因是1792年10月,法國軍隊反擊普奧聯(lián)軍先前對法國的干涉,進軍德國占領(lǐng)了美因茨,聯(lián)合那里的革命黨人于1793年3月成立了一個“美因茨共和國”,還計劃要與法國合并。普魯士和奧地利又立即組織起一支聯(lián)軍包圍了美因茨,要恢復那里的封建秩序。歌德也參加了這場歷史上的“圍攻美因茨”之戰(zhàn)。
歌德參戰(zhàn)?匪夷所思。因為歌德自詡是“和平的孩子”,從來就是反對戰(zhàn)爭、反對暴力的。如法國爆發(fā)大革命時,歌德曾為此歡呼,但當雅各賓黨暴力行為傳到了他耳朵里,態(tài)度就發(fā)生了大轉(zhuǎn)變:“說我不能做法國革命的朋友,這倒是真話,因為它的恐怖行動離我太近,每日每時都引起我的震驚。”又如1813年拿破侖軍隊入侵德國,德國人紛紛行動起來保衛(wèi)家園,歌德卻持一種事不關(guān)己的態(tài)度,在把玩來自中國的玩意兒,在為他喜歡的女演員修改臺詞,得知自己兒子已自愿報名要去抵御法軍,還使用了低下手段進行阻止。在歌德看來,戰(zhàn)爭徹頭徹尾只是人類的禍害,不管以什么名義,即便是拿國家命運和民族存亡說事,也沒理由讓人們?nèi)ピ馐芫薮鬆奚?jù)托馬斯·曼了解,歌德說過這樣的話,“一家農(nóng)戶遭毀,才是一個真正的不幸和災難,而‘祖國淪亡’,不過僅僅是一種說法上的而已。”真讓人有些錯愕。
這樣一個極端和平主義立場的歌德怎么又去參加戰(zhàn)爭了呢?實際上,歌德是因為要陪伴他的君主卡爾·奧古斯特·馮·魏瑪公爵,才去參加了圍攻美因茨那場戰(zhàn)爭的。這個公爵帶領(lǐng)他的軍隊加入了去圍攻美因茨的普奧聯(lián)軍,歌德作為其樞密顧問還司管著軍隊事務,自然得跟隨。美因茨離歌德故鄉(xiāng)法蘭克福不遠,歌德青少年時期常去。1774年12月的一天,也就是在美因茨城內(nèi),歌德與當時還未親政的卡爾·奧古斯特一席暢談,決定了當時才20多歲的他的未來人生軌跡,歌德因此對這個城市很有感情。普奧聯(lián)軍對美因茨的圍攻發(fā)生在1793年的3月至7月。大約過了30年后,歌德才將當年參戰(zhàn)經(jīng)歷整理出來,寫成一個比紀實文學敘事上更為自由,所包蘊內(nèi)容上也更為豐富的小說類作品發(fā)表。
那時的歐洲/德國,不斷有大大小小的戰(zhàn)爭已經(jīng)發(fā)生、正在發(fā)生和將要發(fā)生。應此情形召喚,有人在注目戰(zhàn)爭方略,如卡爾·馮·克勞塞維茨就在這個時期寫了他的《戰(zhàn)爭論》(über den Krieg),有人則在敲打被戰(zhàn)爭陰霾覆蓋的人類社會進程。歌德屬于后者。圍攻美因茨之戰(zhàn)給他留下了夢魘般記憶。近30年過去了,戰(zhàn)爭血痕雖然早已干涸,歷史傷口并未因此愈合,記憶仍舊猶新。身為一個作家,歌德認為有必要記載下那場戰(zhàn)爭,既要清算戰(zhàn)爭之惡,也有要為自己傾吐之意。
與眾不同的戰(zhàn)爭文學
此時歌德73歲,透過拉開了距離的時空,已把那場戰(zhàn)爭看得更加清楚。但在魏瑪生活的特殊環(huán)境,已使歌德變得謹小慎微的中庸,溫言軟語的沉穩(wěn),如恩格斯對他的評價:“有時非常偉大,有時極為渺小。”這個時候的歌德,文字避開機鋒,不會去痛痛切切招惹當年發(fā)動戰(zhàn)爭的人和宮廷的不悅,但也不會放棄機會,找到適當途徑表達自己的意見。
這個背景下歌德書寫《圍攻美因茨》,用的是日記體文體,文本以“日期”分段保持了線性時間順序,各段敘事長短不一,以敘事者經(jīng)歷、見聞、所思、所感連綴,接榫中隱含的整部作品構(gòu)思,是人與戰(zhàn)爭時間的關(guān)系,或曰人在戰(zhàn)爭期間的所為。敘事敘述任達不拘,話里行間常埋藏有未直接言說出來的東西,對于熟悉那個時代的讀者而言那些暗指或暗示又都不難領(lǐng)會。宏觀和微觀交融,行營生活和戰(zhàn)爭戰(zhàn)事交替,選擇一些歷史人物、現(xiàn)場和情景,用“我”的視角連接事件與個人——歌德寫下的這部作品故事是零散化的,無慣常戰(zhàn)爭小說那種情節(jié)波瀾,曲折延綿。
此前在德國文學里,戰(zhàn)爭題材可謂就是金戈鐵馬弘揚圣武,為諸侯、領(lǐng)主等統(tǒng)治者所謂英雄雄才偉略寫意造像、樹碑立傳的同義詞。歌德的《圍攻美因茨》則完全不在這種氣象內(nèi)。開篇時刻,書中的“我”借他人之口重復了他以前(即在歌德上一部戰(zhàn)爭文學《進軍法蘭西》里)說過的話,“此時此地,世界歷史正在開啟一個新的時代,你們可以說,我曾親自在場”,給人一種似乎在跟著創(chuàng)造歷史的激情自信、躊躇滿志的感覺。但將作品一頁頁讀下來,讀者會發(fā)現(xiàn),在數(shù)個月的戰(zhàn)爭里“我”記載了很多,唯獨沒有記載戰(zhàn)爭統(tǒng)領(lǐng)的氣吞山河,也沒有記載戰(zhàn)爭出英雄的粗獷大氣。
歌德毫無英雄和英雄主義寫作用意,筆下的“我”只是在以戰(zhàn)爭的歷史線條和個人內(nèi)心的雙重角度記載著他的戰(zhàn)爭經(jīng)歷和日子。記載不論詳略,所定格出來的圖景顯示出敘事在暗地里服膺于歌德的一種反對戰(zhàn)爭敘事學。如,“今天是6月8日,我在繼續(xù)奮筆疾書我的《列那狐》;與最最尊貴的公爵一同騎馬去了達姆施塔特營地,拜見了封地伯爵,這位仁慈大人一直對我親切,見著他我滿心愉悅。晚上,茨魏布呂肯的馬克西米利安親王,還有封·施泰因上校,也都到頭領(lǐng)這里來了;幾人交談了一些事;最后說到即將開始的圍城,這已是公開的秘密。” 這個記載就表面日常的敘述暗藏機鋒,走筆恰到好處把歌德的軍營生活和戰(zhàn)爭立場透露得淋漓盡致。它有兩個層次,一是讓人看到在軍營里歌德念茲在茲的是他的文學,在用投入創(chuàng)作方式度過戰(zhàn)爭的日子,二是讓人看到在歌德眼里那個下令圍攻美因茨的普魯士“頭領(lǐng)”根本就不值得對他表示敬意,對他的名字予以一提。
以“毀滅”視角記敘戰(zhàn)爭
《列那狐》(Reinecke Fuchs)是歌德根據(jù)法國中世紀流傳的動物故事創(chuàng)作的一部長詩。詩中假托動物世界和形象,諷刺了德國宮廷的專制、盲目、強暴和強盜主義政策,諷刺了教會及神職人員的腐朽變質(zhì),諷刺了法國移民者的貪婪,對一個已經(jīng)運轉(zhuǎn)了上千年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秩序被歐洲人自己的政治頹敗、風氣墮落所毀滅,發(fā)出了一聲聲嘆息。同樣,《圍攻美因茨》與《列那狐》形成互文,背后隱逸的藝術(shù)智慧一是在用虛構(gòu)的方式脫離現(xiàn)實,二是在用非虛構(gòu)的方式講述隨軍。即是說,歌德在《圍攻美因茨》與《列那狐》之間設(shè)定了一種話語隱喻,既是在對戰(zhàn)爭時間和空間的超越,又使得對《列那狐》的提及充滿了啟示《圍攻美因茨》作品意旨的可能性。即是說,《列那狐》和《圍攻美因茨》在某種意義上是同構(gòu)性的,共同構(gòu)成了歌德對普奧聯(lián)軍圍攻美因茨之戰(zhàn)的拒絕,共同指向這場戰(zhàn)爭在歌德眼里同樣也是一片毀滅:邦國體制的毀滅,社會關(guān)系的毀滅,城市建筑的毀滅,個體生命的毀滅,古老文化的毀滅,悠久傳統(tǒng)的毀滅,人倫關(guān)系的毀滅,生存環(huán)境的毀滅,簡而言之是毀滅著一切的毀滅。
如對美因茨遭到的毀滅,歌德就記載哀嘆道,“這個用了數(shù)百年時間才建立起來的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這個各地的財富都曾往這里匯集的城邑,這個曾經(jīng)的擴展和鞏固信徒們信仰的圣地,現(xiàn)在已是棟塌房坍,華屋丘墟,成了碎片和瓦礫。”歷史上,普奧聯(lián)軍于1793年5月初完成了對美因茨的包圍,從6月底起開始對這個城市實施重炮轟擊。此前在1792年9月的法國馬恩省瓦爾密村戰(zhàn)役里,普奧聯(lián)軍曾被法軍以重炮重創(chuàng),不得不鎩羽而歸。現(xiàn)在普奧聯(lián)軍也使用這個戰(zhàn)法,對歌德來說這是在用重炮自己焚毀自己的城市。以幾個真實情形描述,歌德記載了炮火轟擊下的美因茨:城里的標志性建筑或搖搖欲墜,或付之一炬,或面目全非,不僅民居住宅在遭殃及,就連花果樹木也“無論怎樣說都是遭遇了毀滅”。記載表明,面對戰(zhàn)爭這個人類未能避免的事實,歌德是在用“毀滅”視角篩選記憶,書寫了圍攻美因茨那場戰(zhàn)爭。
戰(zhàn)爭對人生命的毀滅,歌德也有記載:“槍戰(zhàn)不久就停止了……夜間丟了性命的無套褲漢臥尸在地,狀似侏儒,衣衫襤褸,與我們威武的騎兵形成怪怪的對比;死亡已將他們統(tǒng)統(tǒng)放倒,不加任何區(qū)別。我們的好上尉拉·維埃是第一批倒下中的一員,還有封·福斯上尉,卡爾克羅伊特伯爵的副官,被射穿了胸部,大家清楚他已是命不久矣。”生命就如同草芥般消逝了或就要消逝,歌德的記載只撬動冰山一角,并不深入戰(zhàn)場寫出它的鮮血淋漓,也不展開生存與死亡的形而上思考,只以“夜間丟了性命者臥尸在地”的言說表明在他眼里戰(zhàn)爭的最真實形態(tài)就是每個丟了性命者都毫無區(qū)別地被收割了生命的死亡。時間隔了近30年,戰(zhàn)爭造成一片尸體,把死亡突然擺在還活著的人面前的體驗,對歌德來說仿佛仍在昨天。歌德這里唏噓的“死亡已將他們統(tǒng)統(tǒng)放倒”中的“他們”,也包括普奧聯(lián)軍的人,即是說也包括人們通常說的“自己人”。對“自己人”的倒下也云淡風輕,沒有哀慟,沒有沉重,沒有戰(zhàn)爭這一特定環(huán)境的愛與恨,只有為所有失去生命者感到的不值,顯然,歌德雖在隨軍普奧聯(lián)軍,骨子里卻是個保持距離的觀察者,思想上并未站在發(fā)動圍攻的普奧聯(lián)軍一邊,而是將自己最堅決的立場放在了不選邊站隊的一側(cè)。
特性獨立的歌德
不僅如此,歌德實際上甚至超越了戰(zhàn)爭文學的陣營規(guī)定性,還有對法國人英勇的暗示之筆,對“自己人”的表現(xiàn)則筆觸反諷,大喝倒彩:“河面上的響動吸引了我的注意:法國人的小船在奮力劃向小島,奧地利人的炮臺在不停向他們射擊。水面上跳彈紛飛,于我來說真是一出未曾見過的戲:首批炮彈射向河中,激起一些數(shù)尺高的水柱,尚未散落下來,已有第二批炮彈降臨,又致新的水柱飛起,強度與前批一樣,只是高度有些不同。然后是第三批、第四批,越往遠處水柱激起越矮,直至最后到達法國人的船前,只是繼續(xù)在對水面施加影響,偶然能對小船形成危險。對這出戲我怎么看也看不夠,這可是一發(fā)接著一發(fā)炮彈,一柱接著一柱水柱,與此同時舊的水柱還沒有消失的難得一見場面呀。”戰(zhàn)爭從來都是難以預料的例外狀態(tài),但戰(zhàn)爭是一出“戲”,一出奇觀意義上的、兒戲意義上的、荒誕意義上的“戲”,這在德國戰(zhàn)爭文學中屬于首次。
歌德這段言“戲”文字,有揶揄精神張揚,將冷眼看待戰(zhàn)爭如同在觀看一出戲碼的“游戲”觀鋪展到了極致。從美學層面看歌德這段話以形象跳蕩語言把真槍真炮的戰(zhàn)爭調(diào)侃化為啼笑間作的滑稽,從思想層面看它是在挑戰(zhàn)當時似乎神圣不可侵犯的對戰(zhàn)爭的思維模式。在普奧聯(lián)軍圍攻美因茨那個時代,在歌德所在的生活區(qū)域,崇拜英雄,謳歌強者,訴諸武力的普魯士軍國主義文化是社會的意識形態(tài)主流,是普遍的社會心理,是不容違逆的政治話語。歌德在其宮廷當臣的那個卡爾·奧古斯特公爵,歌德就形容他喜好軍事“如同魚對于水”。克勞塞維茨的《戰(zhàn)爭論》中就說,“戰(zhàn)爭是政治的繼續(xù)”,就在告訴人們戰(zhàn)爭似乎有著天然的合法性,即便不是在強化人們對戰(zhàn)爭的期待和膜拜,也是剝奪了人們對戰(zhàn)爭的思考和質(zhì)疑。《圍攻美因茨》則敞開了一個思想意識特立獨行的歌德,打破當時普遍的戰(zhàn)爭認同,用“戲”、“好笑”、“有趣”、“怪怪的”等字眼描寫普奧聯(lián)軍對美因茨的圍攻,令人感覺興味綿長,思路不羈。這不是歌德敘事語言上的俏皮,而是地地道道的顛覆和諷刺,表明在歌德眼里戰(zhàn)爭根本就是毫無意義。
因為戰(zhàn)爭除了毀滅生命和財產(chǎn)等外,它的巨大毀滅性還在于它使人的人性喪失,良知泯滅,社會的道德倫理全面崩潰。歌德清楚戰(zhàn)爭是人性的煉獄,《圍攻美因茨》里“我”就議論說,“人就是這個樣子,尤其是在戰(zhàn)爭時期,對于不可避免的,他逆來順受,對危險、緊急和煩惱間出現(xiàn)的空隙,他便以娛樂和尋歡來充填之。”說的是戰(zhàn)爭使得人的心理變得反常,行為變得乖戾,在死亡隨時有可能降臨頭上的焦慮下一有機會就尋歡作樂,放縱自己,致使傳統(tǒng)的規(guī)矩、約束、尺度等統(tǒng)統(tǒng)失去了說“不”的力量,致使人性上原來的“善”與“惡”平衡被打破,人性中的黑暗和殘暴釋放出來,人形同于獸。
在上一部戰(zhàn)爭文學《進軍法蘭西》中,歌德就記載了戰(zhàn)爭使得人性裂變之細末發(fā)梢的一件,在整個世界文學范圍內(nèi)都堪稱是個經(jīng)典:士兵收繳了牧羊人的羊,貌似付了錢,付給的卻是以在法國大革命中已經(jīng)掉了腦袋的法國皇帝路易十六名義簽押的代金券,實際上就是廢紙。牧羊人無奈又無助,只得眼睜睜看著他們的羊轉(zhuǎn)眼間已被宰殺:“他們像孩子般呵護的羊被急著要吃烤肉的士兵就在他們的腳邊破肚開膛了;我不得不承認,不曾有過比這還要殘酷無情的殘忍場面呈現(xiàn)在我的眼前,不曾有過比這還要更為痛楚至極的男人痛楚進入過我的心境。只有在看古希臘悲劇的時候曾讓人感到過如此的浹髓淪肌,里外蒼涼。”悲郁的筆調(diào),既是在為牧羊人哭泣,也是在為人類悲劇寫真。這部《圍攻美因茨》里,歌德也記載了平民百姓的非人遭遇,讀后同樣令人黯然神傷:“6月24日。正如預料的那樣,法國人和美因茨雅各賓俱樂部人感到了日益嚴重的給養(yǎng)壓力,便將老弱婦孺強行裝上馬車,往卡斯特爾方向驅(qū)趕。這些人來到城外,又被同樣冷漠無情地驅(qū)趕了回去。這些手無寸鐵的人吶,被城內(nèi)城外敵人驅(qū)來趕去的那個絕境,超出了所有的語言言表。”悲憫傾注的記載,再次表明在圍攻美因茨戰(zhàn)爭中歌德只允許他扮演一個角色,那就是他自己,一個反對戰(zhàn)爭和反對暴力的人,一個不選邊站隊的戰(zhàn)爭觀察者和一個人類悲劇的記載者。無論是對美因茨遭到毀壞的痛徹之情,還是對人性道德裂變感到的嗚咽之悲,皆出自于此。
人道主義基礎(chǔ)質(zhì)地
套用福柯說過的一個意思,重要的不是歷史講述的年代,而是講述歷史的年代,對先前的一段歷史進行講述的時間,一定層面上看比所講述的那段歷史還有其意義。戰(zhàn)爭過去了那么多年后歌德決定要寫《圍攻美因茨》,就有追求這個講述時間意義之意,用意就在于要用這部作品寫作來對抗有“戰(zhàn)爭熱”的當前。1810年,歌德公開了要將當年隨軍經(jīng)歷書寫出來的想法。他的秘書黎默爾記下了他給自己確立的如何書寫的主導思想:“如同往昔用人道主義對付野蠻人那樣,現(xiàn)在是用人道主義對付專制的時候了:要恰當描繪和這樣描繪士兵生活,讓士兵感覺到:不幸是作為命令下達給他的;當他獨自處事時,他的行為必須是一個人。” 士兵必須接受命令參加戰(zhàn)爭,這是士兵無力改變的“不幸”,但士兵應當如何左右自己的行為,便是歌德的思考。
歌德思考的是讓人道主義成為士兵思想的主導。《圍攻美因茨》里歌德寫“我”碰到一個帶著孩子逃出美因茨逃難在外的中年人,中年人談了要對美因茨革命黨人實施報復的想法,“我”聽后立即一臉嚴肅地告誡這個中年人一定要放棄他的這個念頭,“能夠回歸和平,返還家園了,就不要再用新的內(nèi)戰(zhàn)、仇恨和報復之事來污染,否則不幸就將周而復始永遠不止”。不能讓褊狹成為合理,人道主義才應當是指導未來生活的思維。以此點睛之筆,歌德瞬間將小說敘事升華到了一個新境界。完成了“他的行為必須是一個人”的給予,歌德在有史以來的德國戰(zhàn)爭文學中首次寫出了人道主義新意,給本身篇幅并不很大的《圍攻美因茨》寫出了大河般宏闊。
“我”不僅直接在宣告人道主義思想,還有對人道主義行為的敢為敢行。歷史上,1793年7月22日,法國人宣布投降,于24日和25日分批離開,26日,普奧聯(lián)軍開進了美因茨城。歌德講了進城后他做過的一件事。那是他看見一群人團團攔住騎在馬上的一男一女,叫喊著要打死他們,便趕緊上前喝開人群,那一男一女趁機逃離。“他們的不幸和仇恨并不給予他們權(quán)力,在我這里絕不允許發(fā)生暴力”,這是歌德記載的行為動機。歌德的朋友戈雷聽了這事后指責歌德的做法不妥,一是有可能讓眾人遷怒于他,給自己造成危險,二是那兩個美因茨革命黨人在法國人占領(lǐng)期間說不定犯下過罪行,不該讓他們未受懲罰就走了。歌德不愿以人道主義自夸,找了個理由解釋,但戈雷固執(zhí)己見,沒完沒了。歌德受不了那喋喋不休了,“我不斷以說笑的口吻指著房前場地上的清靜給他解釋,最終變得不耐煩,說:我寧可犯下不公正,也不愿忍受無規(guī)矩,這便是我的秉性。”顯然,所謂“秉性”只不過是歌德找的一句話來堵住朋友的嘮叨而已。有意思的是,上個世紀20年代,法國人將歌德這話剝離語境,翻譯成法語句子“plutot une iniustice qu'un desordre”(“寧可不義,不愿無序”),用來作為抨擊德國人就是個野蠻民族的證據(jù)。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其智慧、知識、文化的最高代表歌德都說自己是個并不在乎公義之人,由此推知,整個德國人群體難道不都是寧可不公正,也不能被所謂無規(guī)則的野蠻性充斥。還有意思的是,法國人掐頭去尾翻譯的這句話又被德國人回譯進了德語:“Lieber eine Ungerechtigkeit als eine Unordnung”(“寧可不公正,也不得亂秩序”),被一些不知原本上下文的德國人引用,成為他們批評德國人毛病的一件利器。殊不知,歌德這句話背后是戰(zhàn)爭語境下的人道主義境界彰顯,經(jīng)天緯地,嘆為觀止。
“卒章顯其志”
讀到歌德回憶他當年阻止私刑,讀《圍攻美因茨》已到其結(jié)尾部分。這里,歌德先是講述他進入美因茨后看見戰(zhàn)爭造成的傷痕累累,然后頗有意味地說,還在圍攻期間他就寫了一篇文章,卻被人嘲笑他寫這篇文章像個孩子和新手,而借嘲諷人之口表示了他對這篇文章的希望:希望人們對它發(fā)生興趣,希望它能在德國生發(fā)作用,還說它“對整個世界而言都是有益的和有意義的”。這是一篇什么文章呢?能讓歌德認為它如此重要,要對它進行如此鋪墊,要在全書結(jié)尾處作為壓軸將它提及,要如此“點撥”讀者對它引起注意?這篇文章必當是深意存焉。
歌德道出了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要促使一件難做的和宏大的事得以完成,須得由不同的人組成的社會合作為之,每個人都從自己的方面共同參與。”深層的文字往往大于作家。歌德這句話清晰表達,根據(jù)歌德在書中設(shè)置的戰(zhàn)后情景與語境,又有可從多個層面解讀的可能性和開放性。駐足閱讀,思索含義,層層遞進,剝筍抽蕉,歌德這是在說:必須認可和促進社會是多元結(jié)構(gòu)的,是由不同的人組成的,社會的建設(shè)需要不同人的合力,需要每個人的貢獻;又是在說:應當要摒棄紛爭和仇恨,對即便是先前的“敵人”也要予以和解的精神;就是在說:要在認可不同之中求得文明共存發(fā)展,共建文化社會;即是在說,還在一場血與火的戰(zhàn)爭期間,歌德就在思考和提出了對戰(zhàn)后人類社會應當如何修復和重建的問題。
所謂“卒章顯其志”是也。《圍攻美因茨》結(jié)尾處歌德這段話所涵的人道主義思想,在那個年代歷史情境下是彌足珍貴的,說它代表著人類至善境界也不為過。從比較文化角度,歌德這個人道主義思想與我國“和而不同”思想有息息相通之處。作為歌德生活時代的一個文化現(xiàn)象,我國儒家學說倡導的仁愛和以人類大同為崇高的思想,與歐洲思想家們倡導的理性主義、寬容精神和世界和諧理想有相互吻合之處;歌德閱讀過大量的有關(guān)中國書籍,自敘曾“全身心地投入對中華帝國的鉆研中”,被譽為是“魏瑪?shù)目追蜃印薄.斎唬@里無意定將歌德的人道主義思維與我國的“和而不同”思想聯(lián)系在一起,人道主義信念是歌德精神的一個本然存在。想說的是,有這樣一個人道主義觀念的歌德,有這樣一個走在別人前面為人類情況擔憂的歌德,有這樣一個在其他人還持冷漠態(tài)度時就已在捕捉將要成為未來發(fā)展重大問題的歌德,即便是德國處于伶仟、虛弱、破碎、四分五裂時期,它在精神上依然是偉大的、富有的和堅強的。
歷史似乎有這樣一個特性:不斷被人重復,直到教訓被人理解為止。如何理解歷史教訓,《圍攻美因茨》提供了一個啟示。這部作品記載了戰(zhàn)爭造成的一片狼藉,也給我們記載了一個面對狼藉思考未來的歌德。人道主義是這部作品一個特別而重要的精神底色,造就這部作品的閱讀回甘,是它能夠抵抗時間侵蝕的思想精魂所在。正是因為有人道主義思想灌注,歌德成名二百多年來他的不少作品還是被人遺忘了,惟這部作品始終讓人牢記著。二戰(zhàn)后的1946年,包括美因茨在內(nèi)的德國許多城市還是一片廢墟,《圍攻美因茨》被法國占領(lǐng)軍軍事管制委員會選中,編輯進一套“世界文學經(jīng)典叢書”,就在美因茨出版,以期對此前追隨了希特勒的德國人進行思想上的“再教育”。之后這部作品又在德國接連再版了數(shù)次,最近一次是在2010年。歌德書籍再版史上這樣情況不多,歌德這部卓然之書改寫了歌德書籍再版史。德國媒體上的評論早已將它評價為是部德國文學標高之作和世界文學不朽著作。標高和不朽者必然會隨著歲月流逝散發(fā)出歷久彌新的芳香,永不耗盡它所傳遞的作者精神囑托。作為外國人的我們可能不一定能夠從中完全感受到歌德書寫這部作品的出自心靈、為了心靈和創(chuàng)造心靈的文學高度,但應當是可以感受到歌德表達其中的人道主義思想深度。深度在于歌德將他的文學不僅保存了人類災難的真相,更在于指向修復災難后的人類社會。再次回顧歌德為《圍攻美因茨》確定的思想坐標:“現(xiàn)在是用人道主義對付專制的時候了”。說歌德將他的文學書寫作為了一種社會責任、政治行動和人類道義擔當,由此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