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石《二月》:彷徨的張力

柔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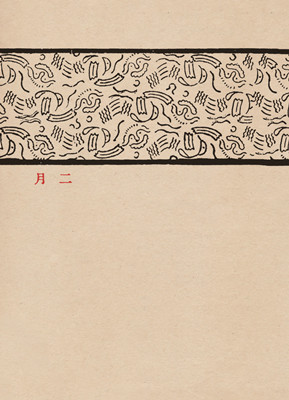
《二月》

1963年,謝鐵驪根據(jù)《二月》改編的電影《早春二月》劇照
《二月》是柔石(1902-1931)的小說代表作之一,在中國文學史上頗有影響。自1929年出版以后,引發(fā)諸家評議,反響熱烈,魯迅也曾撰文推介,各界對《二月》的分析、研究與討論一直持續(xù)至今。1960年代,小說《二月》被拍成電影《早春二月》,成為“十七年電影”的經(jīng)典作品。1980年代,亦出版了多種連環(huán)畫版“二月”,大大提高了小說的普及化與通俗化。進入新世紀以來,越劇《早春二月》、話劇《二月》等佳作頻出,讓觀眾感受到柔石作品的視覺與聽覺雙重魅力。本文即梳理近百年來《二月》諸般樣態(tài),考察其“彷徨的張力”,看《二月》是如何成為長盛不衰的經(jīng)典的。
一
1926年早春,柔石離開北京,向南回到“綠色的海濱”——上海,想找“做事吃飯的地方”,暫住嚴蒼山、汪靜之、童中岳等同學家中,與王方仁和崔真吾一起創(chuàng)辦學校而奔走于杭滬間。隨后,柔石經(jīng)王方仁介紹至鎮(zhèn)海中學教課,后任教務主任。期間“三·一八”事件使柔石“心內(nèi)的一腔憤懣,真恨的無處可以發(fā)泄”,于是“意識地野心地掇拾青年的苦悶與呼號,湊合青年的貧窮與忿恨”,遂作小說《舊時代之死》。
1927年柔石經(jīng)寧海中學吳文欽邀請,以“開展寧地之文化”之想法,“返里服務”,擔任寧海中學國文老師,兼授音樂與英文。隨后發(fā)生的“四·一二”事件則讓江南一片白色恐怖,柔石身陷入其中而周旋。
1929年,柔石經(jīng)歷了大革命的失敗,環(huán)境迫使他在思想上讓過去那種各行其是的自由主義色彩逐漸退卻。這時的他將自己在浙江那段教師生活融入小說里,創(chuàng)作了《二月》,帶有強烈的自傳色彩:鎮(zhèn)海縣為芙蓉鎮(zhèn),寧波市即海市,普陀山是女佛山,鎮(zhèn)海中學即芙蓉鎮(zhèn)中學。
《二月》以1926年前后作為時代背景,通過書寫青年知識人蕭澗秋、陶嵐等,以及在北伐戰(zhàn)爭中失去丈夫的寡婦文嫂及其一對子女的命運際遇,反映了大革命時期社會現(xiàn)實和知識人對所處時代的思考,人物形象鮮明、語言極富詩意、篇幅精悍有余味。雖然《二月》以戀愛為主題,但青年對時代的“彷徨”、對時局的“徘徊”,讓柔石的筆墨堅定地站在貧苦無依的寡婦孤兒這一面。可以說,對革命者的尊重與對弱者的憐憫,構成了蕭澗秋的性格底色。小說里文嫂及其幼子的雙亡,讓蕭澗秋心靈上受到了打擊:拯救弱小者和人道主義的寄托徹底被摧毀,他苦悶著、矛盾著,對未來更加彷徨,看不到路在哪里。另一方面,陶嵐與蕭澗秋之間感情糾葛,組成了《二月》的中心情節(jié),使讀者有了青春美感之閱讀體驗。陶嵐面對蕭澗秋娶文嫂為妻時,壓著內(nèi)心波瀾,只有一句“我覺得自己孤單”,恰似蕭澗秋說的“長陰的秋云里底飄落的黃葉的一個人”。
二
《二月》寫就后,柔石送交魯迅閱讀。魯迅很重視這部作品,對它有詳細的口頭批評,非常具體地指出優(yōu)點,也指出缺點,柔石非常悅服這種誠懇而具體的批評。他說這種批評才是對作者有幫助的批評。魯迅于8月20日撰文《柔石作〈二月〉小引》發(fā)表在《朝花旬刊》第一卷第十期。10月5日,魯迅校畢《二月》。11月22日,《二月》由上海春潮書局出版。
陶元慶(1893-1929),字璇卿,浙江紹興人。師從豐子愷和陳抱一等名家習西洋畫,國畫等亦有涉獵,為其從事書籍裝幀藝術奠定了美學基礎。魯迅的《苦悶的象征》《彷徨》《故鄉(xiāng)》等作品封面皆出自陶氏之手,與豐子愷、錢君匋并稱為中國現(xiàn)代書籍裝幀的三大家。1929年8月6日,陶元慶因病去世。故柔石《二月》封面成了陶氏遺作。《二月》的封面,陶元慶用上下兩段橫線,簡練地概括了畫面的空間,黑色線條勾勒出諸多人物的相貌,在類似河流中顛三倒四漂流著,滿幅畫面被緊張的情緒所包圍,將“二月”主題表現(xiàn)得恰到好處,又耐人尋味。畫面富裝飾感而柔弱陰沉,雖屬于西方的風格,但里面卻涵容著一種東方的飄逸的氣韻。
柔石拿到樣書立即寄贈妹妹一冊。12月3日,柔石又寄妹妹《三姊妹》小說一冊,扉面上還親筆寫著“前給你《二月》,你會懂嗎?現(xiàn)在送你這一本,很淺的,你可看看。”
《二月》出版以后,佳評如潮。《春潮書局出版物所得的佳評》一文摘引魯迅贊語:“我從作者用了巧妙的技術所寫成的草稿上,看見了近代青年中這樣的一種典型,周遭的人物,也都生動。”次年魯迅將《二月》列為“優(yōu)秀之作”之一再次予以肯定。魯迅的《柔石小傳》中總結“小說《舊時代之死》《三姊妹》《二月》《希望》”為柔石的“文學上的成績”之一。柔石女友馮鏗則說:“你把我的精神占領了去!坦白地告訴你:……自看你的《二月》以后,一種神秘的,溫馨的情緒縈繞著我。差不多每一件事物,每一個時間空間我的心里總是充塞了這樣不可救藥的情緒,弄得自己簡直莫明其妙,好像完全轉換了另一個人!”
歲月悠悠,業(yè)已證明《二月》的藝術生命力。自《二月》1929年由春潮書局出版外,還有廈門大學油印版(年份不詳)、1980年英文版、1982年德文版等,廣為流傳,成為具有世界影響的中國小說之一。
三
電影導演謝鐵驪尤為偏愛五四時期的小說,他認為《二月》不是“才子佳人”的憂郁生活,而是討論知識人面對革命,是順流而進,還是急流勇退,這恰恰反映著革命的人道主義。但謝氏改編《二月》時,對柔石略顯消極的結尾——蕭澗秋去了女佛山——做了修改,即讓蕭澗秋奔向革命。
謝鐵驪劇本《二月》于1962年2月16日完成,載1962年6月7日《電影創(chuàng)作》第三期。后來夏衍很重視這部劇,他認為原著小說中的“二月”,實質(zhì)上表達的是一種“春寒”。他又認為60年代的“二月”已無“春寒”之意。于是建議將片名改為“早春二月”,點出“早春二字比較醒目一些”,意即“春天快到了,但春寒還未盡”。此修改乃點睛之筆,叫“早春”而非“初春”,一字之差卻云泥之別,再一次體現(xiàn)了文藝體裁的標題都是極重要的。
1962年,夏衍在北京電影廠召開關于《二月》的討論會上說:柔石《二月》發(fā)表之時,由于當時的社會情況,原著及魯迅的“小引”都很隱晦,比如小說中沒有表現(xiàn)芙蓉鎮(zhèn)的地下激流,因為當時這些東西不允許反映在作品中。但夏衍認為謝鐵驪改編的時候,可以運用一些后景、道具以及通過人物的精神面貌,將當時的時代背景勾勒出來。夏衍是左翼電影運動的開拓者、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所以本身對柔石的《二月》應該也很喜歡的。夏衍對劇本的分鏡頭進行了細心修訂,比如說,謝鐵驪寫的劇本里原有一處,場景為“荷花地,外,夜,春”,夏衍則在“春”的地方畫了一個圈,并打上問號,旁邊注明“春天不會有荷花”。夏衍的批改臺本藏于北京電影制片廠,2000年為紀念夏衍誕辰100周年而影印出版,收入《夏衍手跡》。
1963年電影《早春二月》拍攝完成,可謂謝鐵驪最成功的電影作品,也最可代表其藝術風格。因為此片藝術上的重大突破,播映后引發(fā)強烈反響。1983年被葡萄牙第十二屆菲格拉達福茲國際電影節(jié)譽為“中國最美麗的電影”。1995年又被評為“中國電影90周年十大優(yōu)秀影片”。
《早春二月》里“蕭澗秋極想有為,懷著熱愛,而有所顧惜,過于矜持,終于連安住幾年之處,也不可得。”同時,“他其實并不能成為一小齒輪,跟著大齒輪轉動。” 細觀《早春二月》,其愛情色彩頗淡,更多描摹的是一種生活方式的找尋與探求,以及任何時代青年都會有的彷徨、苦悶與迷惘。《早春二月》在當時充滿了爭議,但在后世卻讓我們恍然大悟,在“十七年”電影史上留下濃重的筆墨。這使柔石《二月》在非常年代里實現(xiàn)了經(jīng)典的再生。
四
在20世紀中國的大眾傳播史上,連環(huán)畫無疑是一個無法忽視的文化存在。自上世紀20年代在上海誕生,到80年代急遽退場,連環(huán)畫以其“圖畫敘事”的媒介特質(zhì)和建構其上的通俗文化形式,深深地嵌入20世紀中國的社會文化底版之中,成為國人共有的文化記憶。
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80年代前后,至少有四種與小說《二月》有關的連環(huán)畫出版,發(fā)行量達180萬冊之多。
比如1979年有電影連環(huán)畫冊《早春二月》(文飄改編,中國電影出版社1979年版),是根據(jù)同名影片改編而成。封面極有特點,是陶嵐看蕭澗秋彈鋼琴的畫面,在中國還在“徘徊”的時期,描述青年人彷徨的電影用體現(xiàn)愛情畫面作封面,足見中國改革之端倪。
1980年出版有連環(huán)畫《早春二月》(姜文麗改編、邵殿英選片,遼寧美術出版社1980年版,印數(shù)530,000冊),亦由電影改編而來。
1981年則有連環(huán)畫《二月》(小戈改編,胡博綜繪畫,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1981年版),此冊特點是將結尾改為“陶嵐和哥哥去上海準備找蕭澗秋”,“河水總要流向大海,匯成那呼哨著的濤聲……”連環(huán)畫的題意所指非常明顯。
1984年,王良瑩改編、盛增祥繪畫的連環(huán)畫《二月》(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封面是蕭澗秋低頭趕路的苦痛表情,封底則畫著芙蓉鎮(zhèn)的橋和風中的柳樹,在內(nèi)容提要里稱“故事刻畫了舊社會知識分子在摸索前進道路上的痛苦心情,揭露了舊社會的黑暗”,頗具時代特征。
反映年輕人“彷徨”的通俗連環(huán)畫《二月》,其巨量發(fā)行、受眾群體、風格特征、藝術成就等方面都可以清晰地反映出經(jīng)典作品對社會文化傳播產(chǎn)生出的巨大影響力,在中國文化發(fā)展史上,還沒有哪種文化傳播形式或載體可以達到如此普及的程度。
時代在更迭,青年人的“彷徨”卻似乎成為一個亙古主題。2019年,話劇《二月》的導演李六乙接受《北京晚報》采訪時說:“柔石筆下的芙蓉鎮(zhèn)有太多值得思考的東西,其中的一些甚至比我們很多當代的作品更具思考價值,它關乎當下,無疑也關乎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