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yōu)槭裁簇毨?/e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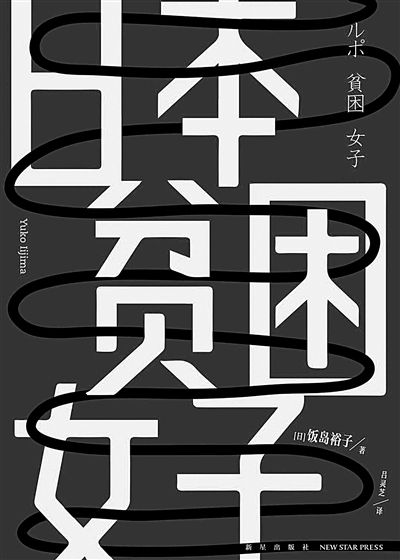
“上大學(xué)后我才發(fā)現(xiàn),有些事情再努力也沒(méi)用,女性會(huì)因?yàn)橥饷埠蜕聿谋粍e人指指點(diǎn)點(diǎn)。有的女性可以?xún)H僅因?yàn)槠量蓯?ài)就廣受歡迎。上高中時(shí),我還堅(jiān)信人只要努力一定有回報(bào),很久之后才明白過(guò)來(lái),原來(lái)世界并非如此。”
已42歲的川口澄子這樣說(shuō)。
在《日本貧困女子》(飯島裕子著,新星出版社)中,川口澄子的情況不算太差。她擅長(zhǎng)英語(yǔ),在大學(xué)當(dāng)了10年非正式雇傭(書(shū)中有見(jiàn)習(xí)生、合同工、臨時(shí)工、日工等多種職業(yè)分類(lèi),待遇不同,作者統(tǒng)稱(chēng)為非正式雇傭),一度收入不錯(cuò)。
在日本,非正式雇傭意味著隨時(shí)可能失業(yè)。21世紀(jì)以來(lái),20—40歲的就業(yè)者中,1/3屬非正式雇傭。其中,42%的女性如此,遠(yuǎn)多于男性(28%)。她們平均年收入147.5萬(wàn)日元(約8.6萬(wàn)元人民幣),只及男性非正式雇傭(222萬(wàn)日元,約12.9萬(wàn)人民幣)的2/3。
一旦成為非正式雇傭,便很難再成為正式工。“非正式雇傭—失業(yè)—為省錢(qián)與父母合住—自我迷失—找更差的非正式雇傭—再失業(yè)”成為一條標(biāo)準(zhǔn)的向下通道。
其結(jié)果是:日本女性依然要靠婚姻改變命運(yùn)。
川口澄子的月薪不足12萬(wàn)日元(約7000元人民幣),“沒(méi)有穩(wěn)定的工作,也沒(méi)有成家……我現(xiàn)在沒(méi)有一樣能讓自己踏實(shí)的東西,太痛苦了”,但她只能“假裝自己在享受獨(dú)身生活”。不論是官方統(tǒng)計(jì),還是社會(huì)救助,都不將她視為貧困者。
社會(huì)為何忽視貧困女子
在日本,“女性貧困”是一個(gè)很少被提起的議題。
一方面,女性貧困率“并不是最近幾年突然上升的,而是20年前就一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她們的貧困一直被視為個(gè)人問(wèn)題,而非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問(wèn)題。
表面看,日本女性可與父母同住,大大減少支出,而在文化上,男性絕不可如此。女性似乎享受了“優(yōu)待”,但也掩蓋了嚴(yán)重的家庭暴力問(wèn)題。
家庭暴力有時(shí)是直接的,有時(shí)是迂回的。因?qū)覍沂I(yè),27歲的小谷由紀(jì)長(zhǎng)期忍受父母的嘮叨,精神趨于崩潰,她不得不搬到網(wǎng)咖、漫咖、KTV去住,“存款花完之后,還睡過(guò)公園”。
在日本,單身女性在街上停留時(shí)間略長(zhǎng),會(huì)遭遇男人騷擾,許多貧困女子只好“想開(kāi)了”,從此在自我譴責(zé)、恐懼中度日,直到找到下一個(gè)非正式雇傭的工作。可非正式雇傭的收入太少,工作又很辛苦,一些貧困女子偶爾會(huì)想念“想開(kāi)了”的日子。
很多女性沒(méi)意識(shí)到自己貧困——住在父母家,暫時(shí)衣食無(wú)憂(yōu)。可一旦父母去世,她們立刻陷入困境(甚至有人餓死),代價(jià)是忍受親人的冷漠、語(yǔ)言暴力等。即使父母完全接納,宅女們也會(huì)因長(zhǎng)期無(wú)緣社會(huì),產(chǎn)生社交恐懼癥等。
作者特別使用了“關(guān)系貧困”一詞——她們目前生活無(wú)憂(yōu),貌似自立,甚至可以擁有奢侈品,但在社會(huì)性上,已落入赤貧。
條條大路通向女子貧困
陷入貧困的女性,多以輟學(xué)為始。
一旦輟學(xué),便很難再與社會(huì)建立聯(lián)系,隨之喪失自信,進(jìn)而失去外出的勇氣,落入越來(lái)越孤立的惡性循環(huán)。日本文化對(duì)女性輟學(xué)較寬容,認(rèn)為是“新娘修習(xí)期”,少有人探究為什么她們不愿繼續(xù)學(xué)業(yè)——部分女孩源于家庭貧窮;此外曾在學(xué)校遭霸凌,自我被徹底推倒。
霸凌的可怕之處在于,它會(huì)造成持久的傷害。有的女孩初中遭遇霸凌,短大(短期大學(xué),近似中國(guó)的大專(zhuān))時(shí)才輟學(xué)。此時(shí)已遠(yuǎn)離霸凌者,亦無(wú)法追責(zé)。
上世紀(jì)60年代起,日本經(jīng)濟(jì)騰飛,女性就業(yè)前景看好。1995年,日本雙職工家庭數(shù)量首次超過(guò)傳統(tǒng)的“男主外”家庭,很少有人意識(shí)到,其中存在結(jié)構(gòu)性的缺陷:
其一,女性只有擁有高學(xué)歷,才有職場(chǎng)機(jī)會(huì)。OL(辦公室女郎)受追捧,輟學(xué)女孩卻很難找到體面的工作。“高學(xué)歷=好工作”引發(fā)女性的“軍備競(jìng)賽”,考上大學(xué)本科的女生一度超過(guò)男生。
其二,當(dāng)時(shí)日本女性單身率不足2%,“結(jié)婚后就辭職”是常態(tài),男女之間競(jìng)爭(zhēng)相對(duì)較小。
1985年,日本通過(guò)《男女雇傭均等法》,主張男女就業(yè)機(jī)會(huì)均等,儼然是“文明一大步”。可隨著女性單身率的迅速增加,許多女性不再退出職場(chǎng),此外IT業(yè)發(fā)展,企業(yè)對(duì)辦公室文員的需求驟減,再加上全球金融危機(jī)的沖擊,女性就業(yè)形勢(shì)迅速惡化。
比如書(shū)中寫(xiě)到的草柳明子,原本是端“鐵飯碗”的公務(wù)員,因女性升遷極難,她先后四次被調(diào)換部門(mén),每次調(diào)換,都要花很長(zhǎng)時(shí)間適應(yīng)新工作。最后,她被安排到水道科,需要經(jīng)常外出,因不熟悉情況,她飽受同事指責(zé),不久,罹患“心因性反應(yīng)”——巨大壓力下的精神損害。
病假結(jié)束后,草柳明子依然難適應(yīng)新工作,申請(qǐng)調(diào)回原部門(mén),又被駁回。在部門(mén)領(lǐng)導(dǎo)逼迫下,她只好辭職。沒(méi)有正式工作,只好接受非正式雇傭。幾次求職失敗,她申請(qǐng)了精神殘疾人證明,得到就業(yè)照顧——在一家超市工作了5年。雖然月薪僅11萬(wàn)元(約6500元人民幣),她卻極為珍惜。
在采訪中作者發(fā)現(xiàn),草柳明子常聽(tīng)不清問(wèn)題,一旦明白問(wèn)題是什么,回答極具條理性。可見(jiàn),她不是能力差、智商低,而是太緊張。
日本經(jīng)濟(jì)長(zhǎng)期停滯,出現(xiàn)了許多“女人當(dāng)男人用”的黑心企業(yè),大多數(shù)貧困女子在職場(chǎng)中遭遇霸凌,使她們很難在職場(chǎng)中充分發(fā)揮。
難以掙脫的三重枷鎖
日本職業(yè)女性背負(fù)了三重枷鎖,即:文化枷鎖、社會(huì)枷鎖和制度枷鎖。
在文化上,日本女性從誕生第一天起,就被定義為家庭成員,而非獨(dú)立個(gè)體。
有的日本議員甚至公開(kāi)宣稱(chēng):“女人就是生育機(jī)器”。女性被看成“特殊的人”,被加以各種“區(qū)別對(duì)待”,卻被離奇地解釋成:這是對(duì)她們的“關(guān)愛(ài)”。不論女性在職場(chǎng)中怎樣的成功,都會(huì)被無(wú)視。日本女性平均工資遠(yuǎn)低于男性,在男人們看來(lái),純屬天經(jīng)地義。
在社會(huì)上,職場(chǎng)霸凌、家庭暴力被視為“教育”的一部分,得到容忍。
日本女性是非正式雇傭的“重災(zāi)區(qū)”,一到可以轉(zhuǎn)為正式工的年限,就意味著被解聘。政府試圖介入,但對(duì)300人以下的中小企業(yè),只能建議和警告,無(wú)法處罰。
因經(jīng)濟(jì)低迷,越來(lái)越多的日本男性因收入不足,只愿同居,不愿結(jié)婚,致使單親媽媽的數(shù)量增加。單親媽媽承擔(dān)著職場(chǎng)與育兒的雙重壓力,日本卻未建立匹配的社會(huì)支持體系。如果單親媽媽對(duì)孩子缺乏耐心,難免引起社會(huì)風(fēng)暴,成為千夫所指。總之,孩子是日本的未來(lái),單親媽媽則什么也不是。
男性可以用暴力結(jié)束同居關(guān)系,女性卻很難這么做,一旦被拋棄,她們往往陷入貧困。
在制度上,受“整體有缺陷,卻問(wèn)責(zé)個(gè)體”的思路影響,長(zhǎng)期無(wú)法達(dá)成解決方案。
貧困女子本是制度困境的結(jié)果,但女性們自己不敢主張,男性們又選擇性無(wú)視,導(dǎo)致問(wèn)題積重難返。從本書(shū)訪談可見(jiàn),大多數(shù)貧困女子因長(zhǎng)期加班,身體健康、精神健康受損,可她們喊累,卻遭指責(zé):還是沒(méi)融入到工作中,應(yīng)該多反省自己。為什么男員工就不抱怨呢?
男員工不抱怨,因?yàn)樗麄兊钠拮映袚?dān)了全部家務(wù)勞動(dòng),兩個(gè)人打一個(gè)人,職場(chǎng)女性怎么可能贏?
“一億總活躍”
問(wèn)題的關(guān)鍵,源于日本政治的道德自嗨情結(jié)。
日本通過(guò)《男女雇傭均等法》的1985年,還出臺(tái)了《勞動(dòng)者派遣法》,打開(kāi)了非正式雇傭的閘門(mén),企業(yè)的社會(huì)責(zé)任被大大削減。如果說(shuō),前者提供了“男女平等”的愿景,還算“進(jìn)步”的話,后者則為“同工不同酬”打開(kāi)方便之門(mén),將前者的努力清零。
在日本,同樣是女性,正式工與非正式雇傭之間差異巨大,前者有孕期照顧、豐厚收入和穩(wěn)定工作,后者則毫無(wú)保障,卻比正式工承擔(dān)更多工作。
如此擰巴,體現(xiàn)了現(xiàn)實(shí)與理想的分裂。
現(xiàn)代國(guó)家基于契約形成,但日本政客執(zhí)著于傳統(tǒng),熱衷壟斷道德解釋權(quán)。于是,在虛幻的“男女平等”的泡沫下,貧困女子成為犧牲品。
隨著越來(lái)越多的貧困女子不愿生育,日本連續(xù)出現(xiàn)11年人口負(fù)增長(zhǎng)。于是,日本又推出“一億總活躍”的育兒支持計(jì)劃,在結(jié)婚、生育、子女教育等給予補(bǔ)貼。時(shí)任官房長(zhǎng)官的菅義偉表示:“希望媽媽們以積極生育的意愿為國(guó)家做貢獻(xiàn)。”在中小學(xué)課本中,加入鼓勵(lì)生育的內(nèi)容。
制造這類(lèi)“現(xiàn)代迷信”,無(wú)非是想把女性留在“工作—結(jié)婚—辭職—生兒—撫養(yǎng)孩子”的、傳統(tǒng)的人生路線上,潛臺(tái)詞是:只承認(rèn)家庭,不承認(rèn)個(gè)體。
于是,超20%的單身女子將繼續(xù)作為犧牲品,她們的貧困與孤獨(dú),因?yàn)闆](méi)被看到,就被當(dāng)成不存在。道德的天空下,只有一個(gè)是正確的,其他都算歧途。這意味著:在走出中世紀(jì)之路上,日本還需更多跋涉。
解決問(wèn)題的前提是看到問(wèn)題、重視問(wèn)題,是回歸理性,多想解決方案,少套道德辭令。前車(chē)之覆,后車(chē)之鑒,《日本貧困女子》雖是小書(shū),所指卻是大問(wèn)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