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比·利希蒂希評(píng)《旅人》:新邏輯和舊秩序的爭(zhēng)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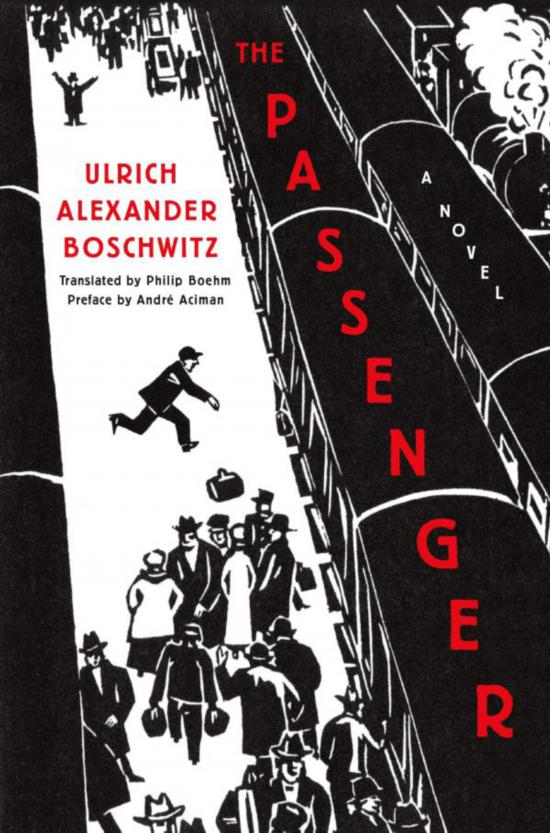
在過去幾年間,對(duì)二十世紀(jì)二十至五十年代的德語(yǔ)作家作品的關(guān)注迎來了一場(chǎng)非凡的復(fù)興。在一波翻譯熱潮的推動(dòng)下,這種文學(xué)的復(fù)蘇將漢斯·法拉達(dá)(Hans Fallada)、恩斯特·哈夫納(Ernst Haffner)、伊爾姆加德·庫(kù)恩(Irmgard Keun)、沃爾夫?qū)た埔僚恚╓olfgang Koeppen)、海因茨·萊因(Heinz Rein)、約瑟夫·羅特(Joseph Roth)、史蒂芬·茨威格等人的作品呈現(xiàn)在一代新讀者面前。
這些作家筆下的時(shí)代既狂熱又可怕,充滿了小資情調(diào)又洋溢著革命熱情,既快馬加鞭又閑庭信步,是現(xiàn)代性邁向脫軌那一刻的一幅快照。從整體上看,他們的作品展現(xiàn)了一個(gè)被那場(chǎng)戰(zhàn)爭(zhēng)深深創(chuàng)傷的社會(huì)——被怨恨填滿,被仇恨誘惑——并為下一場(chǎng)戰(zhàn)爭(zhēng)尋找受害者,一個(gè)被拖入深淵,然后被迫面對(duì)廢墟的社會(huì)。
現(xiàn)在,烏爾里希·亞歷山大·博施威茨(Ulrich Alexander Boschwitz)加入了這群被重新發(fā)現(xiàn)與重新塑造的作家行列,這位作家如果沒有被德軍潛艇的魚雷擊中,可能會(huì)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那是1942年,博施威茨時(shí)年二十七歲。他正乘船從澳大利亞駛往英國(guó),這是一段艱辛旅程的最后一部分,在這段旅程中這位年輕的猶太作家從他出生的柏林前往瑞典,然后是法國(guó),再到英國(guó),在那里他被作為“敵方外國(guó)人”關(guān)押,然后被運(yùn)往澳大利亞的一個(gè)拘留營(yíng)。
在他去世前,博施威茨用約翰·格蘭尼的筆名寫了兩部小說:1937年的《與生活平行的人》,以瑞典文譯本問世;1939年的《乘火車的人》,創(chuàng)作于“水晶之夜”后瘋狂的一個(gè)月中,以英文譯本問世。這兩本書都沒有產(chǎn)生多大影響,但博施威茨對(duì)后者寄予厚望,他對(duì)文字進(jìn)行了大量的修改,并將修改稿寄給了他在英國(guó)的母親。這份修改稿現(xiàn)已不存;而當(dāng)博施威茨死于海難時(shí),他攜帶的新手稿也沒能留下來。
五年前,德國(guó)出版商彼得·格拉夫發(fā)現(xiàn)了《乘火車的人》的德文原稿,并為之深深著迷。在征得作者親屬的同意后,他部分參考博施威茨自己的筆記,對(duì)這部小說進(jìn)行了修改,并將其以原名“Der Reisende”(《旅人》)在德國(guó)出版,而菲利普·博姆(Philip Boehm)的出色譯本也已問世。
我們應(yīng)對(duì)每一個(gè)參與其中的人心懷感激。《旅人》引人入勝地描繪了一個(gè)處于矛盾中的逃亡者,堪稱一幅強(qiáng)有力的黑色電影畫面般的肖像:在“水晶之夜”后恐怖的日日夜夜中,一個(gè)猶太人試圖在眾目睽睽之下藏身;對(duì)這個(gè)富有的柏林人來說,金錢已經(jīng)成了一種負(fù)擔(dān),他被逼入絕境但沒有身陷囹圄,他在移動(dòng)時(shí)最安全,而在被迫駐足時(shí)最受威脅。這本緊迫而充滿動(dòng)力一路向前的書,時(shí)常悲喜交加,夾雜著荒誕風(fēng)格的片刻和存在主義的猜測(cè),希區(qū)柯克式和貝克特式的戲劇場(chǎng)面交替上演。它具有匆匆寫成的小說的那種直截了當(dāng)?shù)奶刭|(zhì)。如果說原著是無(wú)序的,那么這個(gè)新版本則是凝練而節(jié)奏優(yōu)美的。
奧托·西爾伯曼是個(gè)商人,從事廢品拆卸與打撈業(yè)。他已經(jīng)把自己的生意簽給了他的雅利安人雇員貝克爾(現(xiàn)在正式成為他的“合伙人”),并且相信這個(gè)決定以及他的金融財(cái)富能夠使他絕緣于社會(huì)風(fēng)潮。但大屠殺已經(jīng)開始了,西爾伯曼如今成為了“長(zhǎng)著兩條腿的臟話”。但比起他的存在,他仍然更關(guān)心他的財(cái)產(chǎn),為此他派貝克爾去促成最后一筆商業(yè)買賣,然后趕回選帝侯大道來談判他的公寓的出售事宜——價(jià)格低廉得如同勒索。當(dāng)沖鋒隊(duì)抵達(dá)時(shí),西爾伯曼從后樓梯逃了出來。
西爾伯曼不確定自己是否在逃亡中(“今天肯定是有些事情失控了”),他在柏林四處奔波,在高級(jí)餐館吃飯,給妻子(并非猶太人)打電話。故事后面說明了她已經(jīng)逃去她的哥哥,一個(gè)納粹黨員那里。西爾伯曼被趕出一家深受他喜愛的賓館(伴以道歉),而在公共場(chǎng)合被熟人擁抱時(shí)他又深感忸怩不安。
西爾伯曼(小名斯坦因)“害怕(斯坦因的)猶太鼻子”。這將成為一個(gè)貫穿始終的主題。就像博施威茨本人(一半猶太血統(tǒng),從小是新教徒)那樣,西爾伯曼已經(jīng)被帝國(guó)猶太化了。從外表上看,他是一個(gè)雅利安人,而只要有半點(diǎn)機(jī)會(huì),他就會(huì)和他的同族人劃清界限。他后來在火車上曾抱怨說:“猶太人太多了。”在他想象中他對(duì)那些人說“如果不是因?yàn)槟悖麄兙筒粫?huì)迫害我”,然后他又突然抓住自我,反思自己“很容易被一般輿論所感染”。
西爾伯曼從柏林出發(fā),前往漢堡去找貝克爾,此人受他委托帶走了一大筆錢。路上他和一個(gè)納粹下了棋(并忍不住贏了),同時(shí)也繼續(xù)享用美餐。但“一切都發(fā)生得太快了”,他的權(quán)利正在蒸發(fā)殆盡。貝克爾硬生生地把他攆了出來,雖然留給他的現(xiàn)金足以裝滿一個(gè)手提箱。“沒有信仰的”貝克爾告訴他:“我是個(gè)正直的人。”西爾伯曼回到了他的殘破的公寓,并打包收拾了一個(gè)大行李箱。
從這里開始,這本書的節(jié)奏進(jìn)一步加快,我們處于兩難中的主人公登上一班又一班火車,在全國(guó)范圍內(nèi)曲折行進(jìn),但不知道下一步該去哪里,他急于離開這個(gè)國(guó)家,但又無(wú)法離開,他不再是德國(guó)居民,而是“德意志帝國(guó)鐵路”的人民。他遇到了納粹、猶太人和共產(chǎn)黨人,憤怒的人、恐懼的人和冷漠的人。他和女人調(diào)情,也并非一無(wú)所獲。他總是有像樣的酒喝。他弄傷了他的手指。他做出的決定是倉(cāng)促的、迷狂的、失敗主義的、不斷被推翻的。博施威茨以極其真實(shí)的筆觸描繪了一個(gè)被猶疑不決所撕裂的男人的肖像,以及當(dāng)他的選擇落空時(shí),他以良好的教養(yǎng)表現(xiàn)出的驚慌失措。
在西爾伯曼一路拖著他的行李箱(裝著帝國(guó)馬克)的時(shí)候,他與之前的資產(chǎn)階級(jí)生活之間的聯(lián)系變得越來越沉重。書中有極其喜劇化但又高度緊張的一幕,描述他偷偷摸摸地試圖拖著箱子越過比利時(shí)邊境,而當(dāng)他在自殺式的絕望中試圖故意被捕,但人們了解到他曾在前一場(chǎng)大戰(zhàn)中服役而將他釋放的那一刻,悲劇轉(zhuǎn)變成了鬧劇。雖然西爾伯曼并不是英雄,但我們也會(huì)發(fā)現(xiàn)自己在他尋求安全的旅程上投入了巨大的同情。他所遭遇的危險(xiǎn)之核心是他的平凡普通。
博施威茨特別擅長(zhǎng)表現(xiàn)新邏輯和舊秩序之間的爭(zhēng)斗。從某種意義上說,西爾伯曼并不抱幻想。他知道聰明的人早已逃之夭夭。而他也明白法西斯主義的沖動(dòng)。他曾經(jīng)想到,人們“前往證券交易所去體驗(yàn)一些情感。但如今公民的情感體驗(yàn)已經(jīng)綽綽有余”。當(dāng)貝克爾背叛他時(shí),西爾伯曼睿智地診斷出了原因:他的商業(yè)伙伴只是“覺得有義務(wù)證明他與時(shí)俱進(jìn)”。
同時(shí),西爾伯曼也在努力理解自己的新現(xiàn)實(shí)。當(dāng)他回到被翻了個(gè)底朝天的公寓后,他驚訝于并沒有任何東西被偷。“這說不通啊。”難道動(dòng)機(jī)是純粹的惡意?“他們甚至不認(rèn)識(shí)我。”就像他的手提箱一樣,他的理性成了這個(gè)“瘋了”的世界的累贅。他自我安慰可能是自己瘋了,然后有些遺憾地得出了結(jié)論,他沒有瘋。
《旅人》是一顆重現(xiàn)世間的寶石。它既是一部令人滿意的小說,又是一部重要的歷史文獻(xiàn)——正如格拉夫在后記中所寫,這可能是第一部關(guān)于“水晶之夜”及其影響的文學(xué)作品。通過奧托·西爾伯曼的眼睛,我們被推入了那個(gè)以政治與立法的手段實(shí)行的迫害轉(zhuǎn)變?yōu)槿轿坏纳婀舻臅r(shí)刻,我們的主人公的迷茫蛻變?yōu)榭植篮头纯梗噲D說服自己,情況一定會(huì)好轉(zhuǎn)。“遲早他們會(huì)再次放過我們的……歸根結(jié)底,事情并沒有那么糟糕。無(wú)論如何,我還活著。”
(原文發(fā)表于2021年3月26日《華爾街日?qǐng)?bà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