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的對(duì)話錄到底在思考什么
要說(shuō)清楚柏拉圖到底教了什么是件十分困難的事。他近乎完整保存下來(lái)的著作是極其復(fù)雜的,并常常包含驚人的矛盾。此外,除了少數(shù)像《申辯篇》這樣的特例以及一些書信之外,幾乎沒(méi)有柏拉圖的個(gè)人著述留傳,而只有對(duì)話錄。
柏拉圖對(duì)話錄是一種獨(dú)特的文學(xué)類型,難有一般類型可作參照。為了準(zhǔn)確地表達(dá)他的哲學(xué)思想,柏拉圖選擇了一種研究性對(duì)話的方式。以前無(wú)數(shù)以《論自然》命名的著作在以物理學(xué)或哲學(xué)方式解釋世界時(shí)用到感嘆號(hào)的地方,柏拉圖在對(duì)話錄中都用問(wèn)號(hào)。

柏拉圖
柏拉圖選擇這種極為特別的新方式表達(dá)哲學(xué)思想,有諸多理由。這種機(jī)智的提問(wèn)與詰問(wèn)方式是蘇格拉底的哲學(xué)風(fēng)格,柏拉圖深受其影響。而蘇格拉底沒(méi)有寫下文字著述,因此也沒(méi)發(fā)展出任何與其哲學(xué)風(fēng)格相應(yīng)的著述模式。他很少在哲學(xué)探討中下定論,而主要是指出他人觀點(diǎn)的不充分和謬誤。怎么才能將這種“否定性”哲學(xué)變成一種奠基其他眾多思想的“肯定性”哲學(xué)呢?
我們不確定柏拉圖開始寫作對(duì)話錄時(shí),他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了多少自己十分確信的道理。也許最初并不多。至少他早期的問(wèn)題與探討處于相當(dāng)真誠(chéng)的摸索階段。至少有16篇對(duì)話屬于他的早期作品,它們是些不完整的思想與未完結(jié)的探索—這比所有我們知道的早于柏拉圖的哲學(xué)家留傳下來(lái)的著述總和還要多。
除了蘇格拉底的詰問(wèn)方式之外,柏拉圖對(duì)話錄也許還有第二個(gè)可能的靈感來(lái)源。在雅典,人們相信有表達(dá)和宣揚(yáng)真理的能力的,除了哲學(xué)和智者之外,還有另一種完全不同的人—?jiǎng)∽骷遥?/p>
埃斯庫(kù)羅斯(Aischylos),古希臘悲劇之父,經(jīng)歷過(guò)第二次波斯戰(zhàn)爭(zhēng)。他參加了那場(chǎng)戰(zhàn)爭(zhēng)并將它成功改寫成劇本。他的兩位最著名的接班人歐里庇得斯(Euripides)與索福克勒斯(Sophokles)死于蘇格拉底審判的前幾年。我們可以在受人喜愛的阿里斯托芬那里看到,喜劇在柏拉圖時(shí)代的雅典備受歡迎。社會(huì)矛盾在這個(gè)代表世界的半圓劇場(chǎng)中作為現(xiàn)實(shí)縮影被演繹,人們從中品味劇中故事及其背后深意。悲劇和喜劇都是自由天空下的道德活動(dòng),它們的目標(biāo)是使人們震撼并因此得到“凈化”。戲劇的主題就像哲學(xué)那樣探討存在的本質(zhì):人是什么?人的存在意味著什么?命運(yùn)是什么?人與神之間的關(guān)系如何?什么是道德上的善與惡?我如何面對(duì)我的罪?我能期待什么樣的寬恕?換句話說(shuō),這些都是永恒的哲學(xué)核心問(wèn)題,康德在18世紀(jì)曾將其概括為:我能知道什么?我能期望什么?我應(yīng)該做什么?人是什么?
看看一位有名的劇作家會(huì)獲得多少贊美與尊崇,人們就會(huì)發(fā)現(xiàn)戲劇在雅典有多重要,影響有多廣泛。而對(duì)柏拉圖來(lái)說(shuō),這首先意味著一點(diǎn):競(jìng)爭(zhēng)!一方面,在晚期關(guān)于理想國(guó)家的討論中,他期望藝術(shù)的自由受到大幅限制;但另一方面,他又在寫作中吸收了許多戲劇修辭手法。他對(duì)“詩(shī)人說(shuō)謊”的冷酷斷言并不妨礙他將文學(xué)手段變成嫻熟的表達(dá)技巧。無(wú)數(shù)哲學(xué)問(wèn)題在他那里以回答的形式出現(xiàn)—反之亦然。豐富多彩的故事和神話突然憑空出現(xiàn),被用來(lái)闡釋或結(jié)束一個(gè)主題。想象的帷幕落下之后,仍然有不少問(wèn)題未下定論,留待聽眾與觀眾繼續(xù)思考。
因此柏拉圖的對(duì)話錄是一種結(jié)合傳統(tǒng)又非常獨(dú)特的藝術(shù)形式,盡管這種傳統(tǒng)是柏拉圖當(dāng)作競(jìng)爭(zhēng)對(duì)象猛烈抨擊的。就這樣,他把作為真理教育的哲學(xué)之英雄-道德式要求、智者修辭學(xué)的機(jī)靈敏捷,以及詩(shī)人戲劇的藝術(shù)性結(jié)合在一起。柏拉圖的哲學(xué)集智慧教育、演說(shuō)藝術(shù)與戲劇于一身。當(dāng)指責(zé)智者不誠(chéng)實(shí)和詩(shī)人說(shuō)謊時(shí),他在所有追隨者面前卻自認(rèn)以偉大的集大成者的形象出現(xiàn):演說(shuō)真理的藝術(shù)家和改編現(xiàn)實(shí)的劇作家。
柏拉圖并不是唯一一個(gè)撰寫哲學(xué)對(duì)話的蘇格拉底弟子,但他是唯一一個(gè)從中創(chuàng)造了世界文學(xué)的人。在古代哲學(xué)研究者中存在一個(gè)巨大的爭(zhēng)論,即柏拉圖的對(duì)話錄到底在思考什么。也許這些對(duì)話在阿卡德米或是其他什么地方被演說(shuō)出來(lái),可能還會(huì)像廣播劇一樣有角色分配。那么這一演說(shuō)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肯定是為了影響雅典社會(huì)與政治,從意識(shí)行為上改變盡可能多的人。對(duì)一些柏拉圖研究者而言,這些對(duì)話錄包含了未加粉飾的哲學(xué);而有些研究者只看到了訓(xùn)練課,他們認(rèn)為哲學(xué)的重要部分已經(jīng)丟失,因?yàn)閷?duì)話錄也許是被口頭表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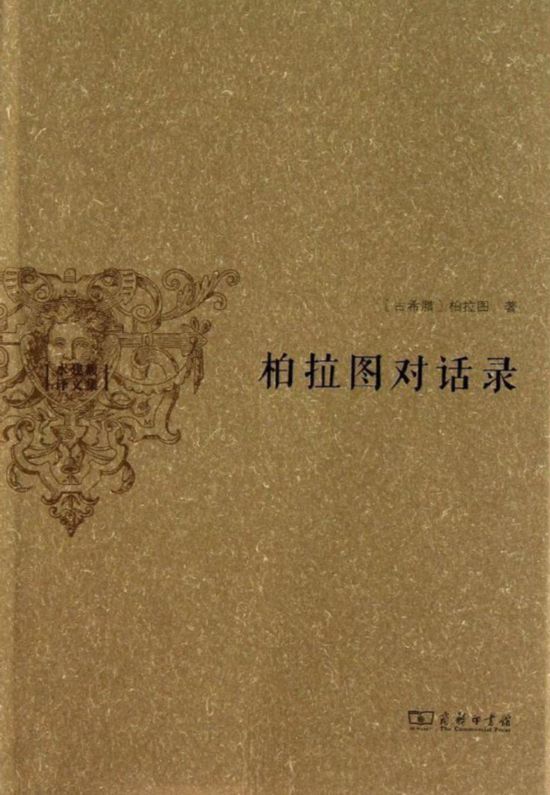
《柏拉圖對(duì)話錄》
以柏拉圖的名義留傳下來(lái)的文本數(shù)量多到驚人。如此驚人,并非只由于作品范圍之廣,還因?yàn)橐恍┲两癖徽J(rèn)為是柏拉圖作品的文本并非出自柏拉圖本人。今天被認(rèn)為真正出自柏拉圖之手的至少有24篇對(duì)話、《申辯篇》、少量的書信、一份哲學(xué)定義的匯編與一些詩(shī)歌。而大量“假”的柏拉圖作品有著完全不同的價(jià)值:一些可能是學(xué)生們編撰的柏拉圖思想梗概,其他的則可能是仿制品。
真正的對(duì)話錄卻也是一種獨(dú)特的“仿制品”。在對(duì)話錄中,蘇格拉底與精選出來(lái)的同時(shí)代重要的人,他們兩個(gè)、三個(gè)或四個(gè)一起討論關(guān)于神與世界的各種不同的問(wèn)題。因此這一古代脫口秀演員名單讀起來(lái)就像古代世界的《名人錄》。從高層政客和將軍阿爾西比亞德,高級(jí)軍官尼西阿斯、拉刻斯(Laches)、赫莫克拉提斯(Hermokrates)、美諾(Menon),到智者普羅泰戈拉、高爾吉亞(Gorgias)、希庇阿斯、歐緒德謨(Euthydemos)、色拉敘馬霍斯(Thrasymachos)、普羅迪科斯(Prodikos)和波羅斯(Polos),蘇格拉底的學(xué)生斐多(Phaidon)、斐德若(Phaidoros)、攸克里德和克力同(Kriton),詩(shī)人伊翁,偉大的老哲學(xué)家巴門尼德,柏拉圖的老師克拉底魯(Kratylos),柏拉圖的親戚阿德曼托斯(Adeimantos)、格勞孔(Glaukon)、卡爾米德和克里底亞,再到數(shù)學(xué)家泰阿泰德(Theaitetos)和忒奧多羅斯(Theodoros)。這些人中許多都是雅典以及古希臘其他地區(qū)有名甚至著名的人物,他們被放入對(duì)話錄中是因?yàn)樗麄兊拿诵?yīng)。也有些對(duì)話者像卡里克勒(Kallikles)、狄奧提瑪(Diotima)、普羅塔科斯(Protarchos) 和蒂邁歐(Timaios),關(guān)于這些人我們知之甚少。柏拉圖自己只出場(chǎng)了兩次。
幾乎所有對(duì)話參與者在柏拉圖讓他們于對(duì)話錄中出現(xiàn)的時(shí)間點(diǎn)上都已經(jīng)過(guò)世了。他們中的許多人在公元前4世紀(jì)的世紀(jì)之交前不久就已去世。這些對(duì)話在過(guò)去某個(gè)確定的時(shí)間和地點(diǎn)上演,在大約三十或四十年前。這可能就像我們今天一位在世哲學(xué)家讓他已過(guò)世的著名前輩阿多諾(Theodor W.Adorno)與其他也已過(guò)世的同代人相互對(duì)話。這場(chǎng)對(duì)話中阿多諾與約翰·福特(John Ford)和比利·懷爾德(Billy Wilder)就電影,與畢加索(Pablo Picasso)、斯托克豪森(Kanlheinz Stockhausen)、范德羅(Mies van der Rohe)就藝術(shù),與切·格瓦拉(Che Guevara)和胡志明就革命事業(yè),或者與薩特和羅素就社會(huì)公正等問(wèn)題進(jìn)行哲學(xué)探討。這就像一種復(fù)古脫口秀,它的腳本是一種腳本真人秀(Scripted Reality)形式——一種在生動(dòng)場(chǎng)景里演繹的偽事實(shí)。
場(chǎng)景也被打造得極其逼真。蘇格拉底的對(duì)話發(fā)生在監(jiān)獄中,在去往訴訟法庭的路上,在一場(chǎng)招待盛宴上,在運(yùn)動(dòng)場(chǎng)上,在私宅中,在梧桐樹下,在散步或徒步旅行時(shí)。這樣一種演繹哲學(xué)的方式極具啟發(fā)性。讀者或聽眾被深深吸引,進(jìn)入場(chǎng)景,身臨其境。柏拉圖沒(méi)有高高在上地訓(xùn)誡眾人,而是與公眾聊天。真理不是教條般地下定論,而是常常出現(xiàn)在對(duì)有疑點(diǎn)的智慧、行為與觀點(diǎn)的反駁中。在柏拉圖那里,哲學(xué)是一種尋找、追求與摸索真理的豐富多彩的動(dòng)態(tài)過(guò)程。這種哲學(xué)方式在公元前4 世紀(jì)初是全新的。那么為什么柏拉圖要這么做?它的意義又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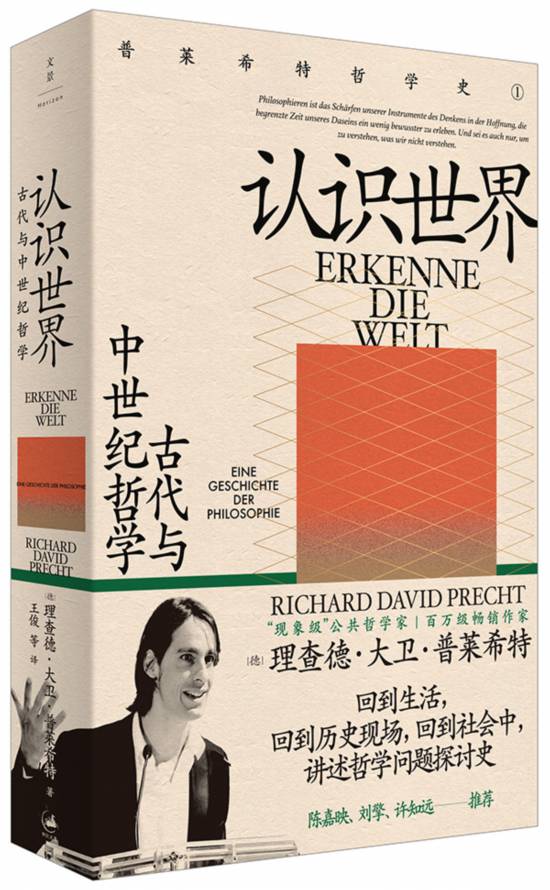
《認(rèn)識(shí)世界:古代與中世紀(jì)哲學(xué)》,【德】理查德·大衛(wèi)·普萊希特/著 王俊 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jì)文景,2021年4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