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毀滅 與戲子的誕生

克勞斯·貝克-尼爾森

《入侵》丹麥文版書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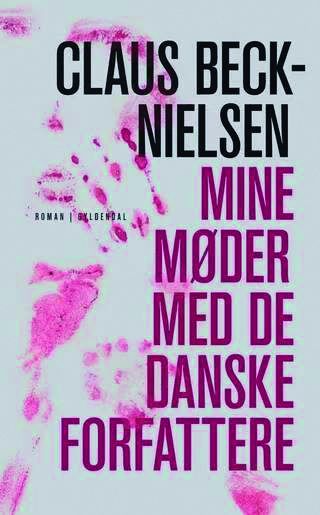
《我的那些丹麥作家的相遇》丹麥文版書封
克勞斯·貝克-尼爾森(Claus Beck-Nielsen,1963-)是丹麥當(dāng)代小說(shuō)家、劇作家、演員和音樂(lè)人。上世紀(jì)80年代后半期,尼爾森是一個(gè)搖滾組合的吉他手及歌手。90年代接受大學(xué)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訓(xùn)練。1997年推出第一本故事集,兩年后推出第一本小說(shuō)。2005年出版的《自殺行動(dòng)》、2008年的《君主》和2015年的《大撒旦的墜落》組成三部曲。《自殺行動(dòng)》讓尼爾森在2006年獲得北歐理事會(huì)文學(xué)獎(jiǎng)提名。2014年,尼爾森又借小說(shuō)《我與那些丹麥作家的相遇》再獲北歐理事會(huì)文學(xué)獎(jiǎng)提名。尼爾森獲得過(guò)若干獎(jiǎng)項(xiàng),他的書寫里有殘酷的自我揭示、痛苦的探索和怪異的前衛(wèi)。
自我的毀滅
2001年,克勞斯·貝克-尼爾森宣布了自己的“死亡”。此后進(jìn)行了一連串身份游戲。他使用過(guò)多種稱謂,包括將丹麥文學(xué)史上偉大的名字如安徒生和卡倫·布里克森與自己的姓氏連在一起。
尼爾森在2002年推出的《自我消滅》不算嚴(yán)格意義上的小說(shuō),卻很像配合身份游戲的文字記錄。全書由13篇相對(duì)散文化的書寫組成,采用他實(shí)際使用的各種假名來(lái)肢解自己,同時(shí)給自己分配出不同的人生任務(wù)。
對(duì)雖死猶生的尼爾森而言,2013年也是一個(gè)重要分界點(diǎn),在那一年里,“尼爾森夫人”成為“死去”的克勞斯·貝克-尼爾森的最新化身。從那時(shí)到現(xiàn)在,稱謂保持了持續(xù)穩(wěn)定。盡管如此,要評(píng)點(diǎn)尼爾森還是不得不在他和她之間轉(zhuǎn)換,在一副軀體和大腦的前世今生里轉(zhuǎn)換。
當(dāng)尼爾森依然是一個(gè)他時(shí),已經(jīng)借《自殺行動(dòng)》為首的三部曲嘗試了所謂平行的世界史的書寫。他聲稱這一平行的世界史的書寫旨在拓寬生命的深度和寬度。假如生命是一場(chǎng)終將不得不醒來(lái)的夏夢(mèng),尼爾森的自我毀滅為的不是死亡,而是以另一種乃至多種方式平行地活著。
出名的焦慮與自我的虛構(gòu)
尼爾森將自己活成了虛構(gòu)的一部分。他就是虛構(gòu),虛構(gòu)也逐步蛻變?yōu)樗囊环N真實(shí)。一方面他高呼打破固有的自我,一方面他也以虛構(gòu)來(lái)實(shí)踐清晰的自我建構(gòu)。
自宣布“死亡”以來(lái),尼爾森以其作品試圖表達(dá)對(duì)社會(huì)里必備的姓名及身份這一建構(gòu)的質(zhì)疑。他的藝術(shù)遺留品由一間所謂跨學(xué)科表演公司貝克維克(Das Beckwerk)管理,公司的影子總管和“已故”克勞斯·貝克-尼爾森在物理上百分百地重合。
沒(méi)有一個(gè)身份來(lái)安放“死后”的飄蕩魂魄的尼爾森,借這一間公司之口頗費(fèi)苦心地進(jìn)行過(guò)一番自我表白:克勞斯·貝克-尼爾森自1992年以來(lái),以作家、詞作者、劇作家、演員、翻譯、評(píng)論家和舞臺(tái)導(dǎo)演等身份生活……乍一聽(tīng)這會(huì)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好像這人不僅僅是個(gè)藝術(shù)家,還是個(gè)才華橫溢的藝術(shù)家,他的作品和行為使他脫離普通群眾的灰色薄霧,進(jìn)入閃亮的《丹麥名人錄》。
可事實(shí)是名人錄過(guò)于包羅萬(wàn)象……此外,丹麥?zhǔn)鞘澜缟纤^的“藝術(shù)家”比例最高的國(guó)度。毫無(wú)疑問(wèn),克勞斯·貝克-尼爾森像成千上萬(wàn)的丹麥年輕人一樣想成為一名藝術(shù)家……但寫作不一定能讓您成為作家,彈吉他不一定能讓您成為吉他手,表達(dá)和展示內(nèi)心與外在的自我不一定能讓您成為藝術(shù)家。實(shí)際上,在《丹麥名人錄》之外,在丹麥街頭,克勞斯·貝克-尼爾森根本不為人知,甚至在小小的丹麥也不為人知……克勞斯·貝克-尼爾森一生惟一做過(guò)的實(shí)事就是娶了個(gè)女人。他在丹麥沙灘上留下的惟一真實(shí)的痕跡是個(gè)孩子、一個(gè)叫艾瑪?shù)钠列∨ⅰhb于他的故事是世紀(jì)之交丹麥普通男人的故事,他的婚姻失敗了……在2001年秋,他如丹麥人所說(shuō)的那樣“走了”。一年后的2002年成立了貝克維克,負(fù)責(zé)管理和發(fā)展克勞斯·貝克-尼爾森的生活和作品,貝克維克的宏偉任務(wù)是將普通人的失敗變成杰作,將休閑觀念變成異象,將普通人的生活和故事變成世界歷史。
這段自白背后站著一個(gè)絕不甘心只做普通人的家伙。原來(lái)的姓名承載的是普通的血肉之驅(qū)。婚姻及其失敗被歸結(jié)為普通男人的故事。這個(gè)普通男人將自己弄死的時(shí)候,包藏了讓歷史名人誕生的野心,堅(jiān)信自己可以在新生的名人體內(nèi)復(fù)活。
克勞斯·貝克-尼爾森或許就是個(gè)狂人和野心家。所有的人乃至他自己都不難對(duì)他的言行投以疑惑的目光。但他到底還是迎著目光、硬是把自己活成了一個(gè)現(xiàn)象,一個(gè)散發(fā)著當(dāng)下歐洲的時(shí)代情緒的現(xiàn)象。他的意志狂野,而血肉之軀日漸消瘦,甚至脫形到讓他自己擔(dān)心,是否身軀不再能成為精神和心臟的容器的地步。
在“死去”已經(jīng)兩年之后,尼爾森書寫了自傳《克勞斯·貝克-尼爾森(1963-2001)》。這是個(gè)古怪的自傳,同時(shí)也未標(biāo)出作者姓名。不標(biāo)作者顯然是因?yàn)樯矸轄顟B(tài)的尷尬,同時(shí)也成了標(biāo)新立異的一個(gè)手段。自傳詳細(xì)記錄21世紀(jì)之初的那場(chǎng)行為藝術(shù):在哥本哈根街頭,一個(gè)面色蒼白的中年男人自稱失去了記憶、無(wú)家可歸。不久,尼爾森果真離婚了。回頭看,他的街頭表演倒像一場(chǎng)企圖突圍婚姻的強(qiáng)烈沖動(dòng),也像是要發(fā)泄精神上的喪家之苦。生活的真諦并非都能解密,即便當(dāng)事人有時(shí)也不能,除非果真借助上帝的視角。
無(wú)論如何,尼爾森抱怨自己在丹麥不為人知,這實(shí)在是夸大其詞。這抱怨里透露的是他對(duì)于出名的過(guò)度焦慮。成名焦慮從根本上說(shuō)也包含死亡焦慮和被遺忘的焦慮。這樣的焦慮人人都會(huì)有,只是程度不同,而在尼爾森這里,顯然演繹到了極端的地步。
身份的清除
“死亡”了的尼爾森躲在他的那家叫貝克維克的公司背后。這間公司聲稱他們的主要工作就是將尼爾森從個(gè)人身份的負(fù)擔(dān)中解放出來(lái),引入無(wú)名的、幾乎可稱為“空”的新存在形式。如果都采用這一存在的新形式,那么人人都可成為另一個(gè)人。按照這一思路,尼爾森的自我毀滅便不單是炒作,而兼具清除身份、找尋人類存在新形式的深意。
然而,世俗世界無(wú)法配合尼爾森的操作,熟人仍像他活著時(shí)一樣和他說(shuō)話。這游蕩的魂靈不由得感嘆,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的人類根本不肯放開(kāi)個(gè)人身份。
似乎是萬(wàn)般無(wú)奈,又好像是蓄意謀劃,在這個(gè)游魂的指令下,2005年,哥本哈根一處教堂墓地里豎起一座新墓碑,上頭刻著克勞斯·貝克-尼爾森的名字和生卒年份,沒(méi)有什么遺體埋在墓中。貝克維克公司也就是古怪地活著的尼爾森本人煞有其事地為這奇怪死亡的合理性到古希臘羅馬的故事里引經(jīng)據(jù)典。事情還沒(méi)完。2010年秋,貝克維克公司又與哥本哈根的一幫教會(huì)人員、哲學(xué)家、歷史學(xué)家和市民合作,給10年前死去的尼爾森舉行葬禮。一具蠟像在小教堂里躺了10天,供人做最后的告別。這一次,克勞斯·貝克-尼爾森真的死了,死的不是自然人,而是身份。伴隨這個(gè)人的“死亡”,貝克維克公司關(guān)閉。克勞斯·貝克-尼爾森的匪夷所思的死長(zhǎng)達(dá)10年,又后事不斷,尼爾森以其擅長(zhǎng)的編劇和表演力毫無(wú)倦意地演繹著自己的生死劇。
尼爾森這個(gè)人棄用原來(lái)的姓名,號(hào)稱要消除身份,卻沒(méi)有銷毀迄今積累出的演員、作家、藝術(shù)家標(biāo)簽,相反不能排除他以姓名消除游戲強(qiáng)化藝術(shù)家形象的成分。消除的盡頭是樹立,他擺開(kāi)一座迷路園,繞來(lái)繞去,卻只還是一個(gè)出口和入口。這個(gè)人很難被埋葬,即便名字已從丹麥人口登記系統(tǒng)里刪除,依然有原來(lái)的社會(huì)保險(xiǎn)號(hào)。在私人領(lǐng)域,尼爾森很難向當(dāng)時(shí)才6歲的女兒解釋,自己到底叫什么、是否活著。不過(guò)他也表示:“還好,一切都沒(méi)有回頭路了。”這句話里有慶幸、也有無(wú)奈。也許證實(shí)了一點(diǎn),世上沒(méi)有絕對(duì)自由,人生無(wú)處沒(méi)有枷鎖,每一項(xiàng)選擇都要付出代價(jià)。
性別是個(gè)機(jī)會(huì)
很難說(shuō)尼爾森的生死、姓名和話語(yǔ)中哪個(gè)更真,比較確實(shí)的也許只有瞬間的情緒。為尼爾森舉行國(guó)家認(rèn)可的葬禮時(shí),尼爾森走動(dòng)著的形體也在葬禮上,在哥本哈根市內(nèi)、距安徒生銅像并不太遠(yuǎn)的地方。這走動(dòng)的形體是否暗自承認(rèn),自己操控著一出《皇帝的新衣》,是否在內(nèi)心早已大笑不止,都不得而知。當(dāng)然也存在另一個(gè)可能性,因?yàn)槌两诰薮蟮膽騽∏榫w里,某些片刻,就連他自己也能被自己哄騙過(guò)去。總之,現(xiàn)場(chǎng)照片上,一張與被埋葬的克勞斯·貝克-尼爾森一模一樣的臉躲在別人的肩膀后,像躊躇的幽靈以略帶游離的表情看著眼前的人和事。2001年“去世”,2010年“埋葬”,2011年“復(fù)活”,2013年成為尼爾森夫人。尼爾森挑戰(zhàn)生死,還跨越性別。
在2013年,尼爾森撰文表達(dá)出做一個(gè)“超越性別”的人的心愿。希望性別不再是社會(huì)建構(gòu)的必需品,提出讓性別成為機(jī)會(huì)。改變性別在尼爾森這里成了改變身份的重要一環(huán),可以借改變性別讓自己有更多的可能性,可以成為另一個(gè)人。
本來(lái),每個(gè)人在一生中都在做不同程度的改變,就像牙齒,容易被人想當(dāng)然地以為是固定不動(dòng)的,其實(shí)一直發(fā)生位移。但尼爾森希求的改變更像拔牙,是擺脫過(guò)于固定的自我形象,在不懷疑自我存在的前提下扔掉固定身份。
必須指出的是,尼爾森憧憬的擺脫既定性別的愿景并非北歐正在討論的第三種性別合法化。在尼爾森看來(lái),第三種性別合法化不過(guò)是把給人歸類的盒子從兩個(gè)變成三個(gè),這遠(yuǎn)非擺脫身份的需求。擺脫身份的需求是更大的解放,暗含巨大的責(zé)任,同時(shí)意味著找到發(fā)展自己身體和潛力的途徑。盡管尼爾森的愿景里不乏閃光點(diǎn),可也不難想象這會(huì)導(dǎo)致世界無(wú)序和自身無(wú)序。尼爾森似乎也充分意識(shí)到自己的癲狂,并以積極的意味自稱是一個(gè)巫婆。巫婆就喜歡說(shuō)不該說(shuō)、不合適的話,拒絕成為同質(zhì)的“我們”的一分子。巫婆好制造爭(zhēng)端,以提醒人發(fā)現(xiàn)自我及生存環(huán)境里的弊端。
本來(lái),當(dāng)代北歐文學(xué)已經(jīng)慣于將越軌的靈魂和越軌的身體與絕不妥協(xié)的創(chuàng)造力相連。創(chuàng)造力是積極而不可缺的,尤其對(duì)作家而言。精神偏差乃至疾病被視為顛覆性的能量。這能量能打破自我身份的固定形式,從而帶來(lái)新的可能性。同時(shí)偏差總會(huì)引來(lái)污名和詛咒。
在健康問(wèn)題商業(yè)化、日常生活醫(yī)療化的當(dāng)下,自我以矛盾的方式試圖借助模棱兩可去敷衍社會(huì)既定的期望,同時(shí)在身體、性別、性等方面打破社會(huì)的規(guī)范體系。在北歐,一種幾可稱為精神病態(tài)的、逸出常規(guī)軌道的文學(xué)取向與自撰小說(shuō)浪潮差不多同時(shí)興起。在這些撲面而來(lái)的、基于自我經(jīng)驗(yàn)的文本里,瘋狂不再是個(gè)人生活缺陷,反之成為嘗試新身份、謀求文學(xué)爆發(fā)力的興奮劑。自我介于常人和抑郁者之間,在男人和女人之間,在嬉戲和癲狂之間。自我沉醉在極具挑釁性的雙重方向里,處于搖擺又尚未墜落的微妙平衡中。性別、身體、性乃至整個(gè)人生都已擲入一場(chǎng)不惜代價(jià)的實(shí)驗(yàn),同時(shí)投入了一場(chǎng)等待一夜暴得大名的豪賭。
說(shuō)到精神病態(tài),據(jù)說(shuō)厭食癥的病因就很復(fù)雜,而厭食癥與渴望和排斥的矛盾情緒相關(guān),也往往拒絕固定的性別認(rèn)同。尼爾森夫人的瘦削身體帶有厭食癥特征,試圖讓自己超越男性或女性,以一種尚未實(shí)現(xiàn)的性開(kāi)發(fā)身體潛能。于是 “性別是個(gè)機(jī)會(huì)”,可打開(kāi)、關(guān)閉、改變。
尼爾森認(rèn)為,在不至于懷疑自己是誰(shuí)的前提下,設(shè)法擺脫固定身份甚至有助于緩解被互聯(lián)網(wǎng)時(shí)代加大而非縮小了的民族主義、仇外心理和過(guò)度的自我專注。尼爾森贊賞不斷的、終生的轉(zhuǎn)變,持續(xù)地成為另一人。這個(gè)新的解放也要求每個(gè)人肩負(fù)巨大的責(zé)任,同時(shí)意味著可以找到發(fā)展自己的身體和潛力的更多方法和途徑。 正是在尼爾森等人的演繹下,以性別為主題的北歐作品在當(dāng)今不再是爭(zhēng)取具有特定性別主體和特定性別身份的權(quán)利的嘗試,而出現(xiàn)了要打破性和性別的既定規(guī)范聯(lián)系,打破性別觀念本身的新動(dòng)向。
無(wú)盡之夏
尼爾森夫人在2014年推出小說(shuō)《無(wú)盡之夏》。寫一個(gè)男孩和女友在夏日里來(lái)到一座丹麥莊園。在那里,也有女友的母親、一個(gè)丹麥貴族女子和葡萄牙男子的性愛(ài)和浪漫。小說(shuō)被看作生命的贊美詩(shī)和青年的頌歌。有意無(wú)意地追憶似水年華。無(wú)盡之夏是生活和愛(ài)情的隱喻。生活和愛(ài)情有夏天一般明亮而眩暈的光,足以讓人沉醉其間,忘記終將醒來(lái),而任何夏天都有盡頭。
延綿不絕的長(zhǎng)句子兀自滾動(dòng)向前,像表現(xiàn)欲極強(qiáng)的演員,并不在意讀者的忍耐力。結(jié)構(gòu)形成又消融,時(shí)間和空間時(shí)而清晰時(shí)而模糊。人物和故事演繹了夏和生的幻象。小說(shuō)里有這么一句話,可以說(shuō)是對(duì)文本恰好的自我評(píng)論:“就像這本書里的每一則故事一樣,故事本身必須不斷地被打斷,然后繼續(xù)播放,直到每一個(gè)故事都或多或少地抵達(dá)它悲慘的結(jié)局。”
尼爾森夫人自己則對(duì)這樣的開(kāi)頭自鳴得意: “這個(gè)可能是女孩,但對(duì)此還一無(wú)所知的小伙。這個(gè)可能是女孩的小伙,絕不會(huì)想要撫摸男人,絕不會(huì)赤裸著和一個(gè)男人在一起,并且拿自己的皮膚摩擦對(duì)方的皮膚,絕不會(huì),無(wú)論生活將多么令人興奮和令人作嘔,都永遠(yuǎn)不會(huì)。”
無(wú)盡之夏在時(shí)而遲滯時(shí)而迅疾的時(shí)間節(jié)奏里波動(dòng)。一群人的道路在殘酷的愛(ài)情嬉戲中交匯,命運(yùn)的閃電沖擊夏日的天空,領(lǐng)人走向始料未及的路。這個(gè)夏日里一切都有可能,也暗含致命因素。女孩的男友,那害羞的大眼而瘦削的男孩后來(lái)古怪地成了一個(gè)老婦。這老婦在生命的最后階段,用永恒的聲音講述無(wú)盡之夏,對(duì)生活里苦澀甜美的憂郁作出了精確又大膽的表達(dá)。這老婦似乎也就是背負(fù)類似的性別困惑的尼爾森夫人。冰島當(dāng)紅作家松(Sjón)也被這部200多頁(yè)的薄薄作品吸引,認(rèn)為這是“關(guān)于愛(ài)情、死亡、時(shí)間和命運(yùn)的,不同尋常且令人感動(dòng)的小說(shuō)”。除了松提及的幾點(diǎn),尼爾森夫人探討了性別、性、身體等主題。
此前尼爾森也借用過(guò)卡倫·布里克森的名字。丟失的世界、貴族的垮臺(tái)、青春、愛(ài)情、性和死亡的確也是卡倫·布里克森的符號(hào)。不光是布里克森,瑞典作家塞爾瑪·拉格洛夫在其處女作《尤斯塔·貝林的薩迦》里早就有對(duì)往昔時(shí)代和往昔人物的浪漫謳歌。不過(guò)尼爾森沒(méi)有拉格洛夫的壯闊和浪漫,又比布里克森更歇斯底里。尼爾森夫人在扮相上越發(fā)靠近老年布里克森,其一或許因?yàn)檗D(zhuǎn)型后的女作家標(biāo)簽,其二或許因?yàn)橄荩欢祭锟松莸母词撬叱龇侵拗啊那胺蚰抢锶旧系拿范静『筮z癥,尼爾森的消瘦則和厭食癥不無(wú)干系。
入侵和邊界
一貫提倡打破邊界的尼爾森反對(duì)把人群分為“我們”以及“其他人”,反對(duì)自我認(rèn)定的固化。認(rèn)為所謂真實(shí)的“我”或“我們”都只是個(gè)幻象,并提出“我”可以不斷成為另一個(gè)“我”。成為另一個(gè)“我”時(shí),有可能擺脫原本具有的對(duì)其他人的偏見(jiàn)。這些話不難理解,比如人到中年就可擺脫少年人對(duì)中年人的偏見(jiàn);比如一個(gè)人陷入此前不曾想象的處境時(shí),終于理解某些原本不能接受的行為。然而尼爾森以自我設(shè)計(jì)和手術(shù)的姿態(tài)閹割自己,這種大刀闊斧的刻意改變還是并不多見(jiàn)。尤其是當(dāng)今的世界里,身份依然是人們?cè)谌粘^斗中必須攜帶的重要通行證,通過(guò)越來(lái)越先進(jìn)的技術(shù)記錄和驗(yàn)證身份數(shù)據(jù)已成常態(tài),尼爾森拼力擺脫身份帶來(lái)的實(shí)際問(wèn)題。一方面,每一個(gè)人對(duì)應(yīng)一個(gè)身份,另一方面,北歐社會(huì)自詡消除了階級(jí),而事實(shí)上“我們”與“他們”的區(qū)分在北歐依然和本能一樣重要且鮮明。
然而果真沒(méi)了身份,會(huì)是個(gè)什么處境呢?也許和沒(méi)有護(hù)照的難民有相似之處。2015年秋,大批難民從非洲流入歐洲。難民流中,混入了涂著大紅的唇膏、戴一頂紅色貝雷帽的尼爾森夫人。尼爾森夫人從希臘沿巴爾干路線穿過(guò)歐洲到丹麥,2016年便推出了小說(shuō)《入侵》。
本來(lái),2015年8月,尼爾森夫人正于郁郁蔥蔥的柏林創(chuàng)作劇本。新聞媒體上,難民消息突然鋪天蓋地,對(duì)危機(jī)和危機(jī)中的人一貫充滿興趣的尼爾森夫人起意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以自己的身體去感受。《入侵》被認(rèn)為形式很新穎,尼爾森夫人不僅是小說(shuō)作者,也是小說(shuō)人物。語(yǔ)言有時(shí)跳躍,有時(shí)冗長(zhǎng)而復(fù)雜。書名其實(shí)頗耐人尋味。在政治正確的當(dāng)下的歐洲,恐怕沒(méi)幾個(gè)人膽敢將難民流入歐洲稱為入侵,從副題看,“入侵”這個(gè)字眼兒可以指尼爾森夫人自己闖入了難民區(qū)域的行為。但更可能的是,它攜帶雙重意味,包括在當(dāng)今的歐洲語(yǔ)境下不可明說(shuō)、只可意會(huì)的。
在《入侵》這部小說(shuō)中,德國(guó)南部邊境的一座村落里甚至沒(méi)人愿意談?wù)撾y民,村民擔(dān)心的不是難民,而是自己和彼此,難民入境讓本來(lái)團(tuán)結(jié)的社區(qū)面臨分裂的危機(jī)。尼爾森夫人描述了自己與難民、移民、志愿者及普通公民的直接相遇。
尼爾森夫人的難民流親歷很可能基于這么一個(gè)野心,身處值得見(jiàn)證的一段歷史當(dāng)中,描述內(nèi)景,同時(shí)描述相對(duì)超脫的自身的平行運(yùn)動(dòng),借此獲得縱深感和歷史感。尼爾森夫人認(rèn)為,在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里,縱深感和歷史感尤為重要,因?yàn)槭澜缫呀?jīng)變得越來(lái)越平了,我們擁有事件和新聞的龐大網(wǎng)絡(luò),卻少有記憶。在難民營(yíng),尼爾森夫人成了在籬笆另一側(cè)工作和睡覺(jué)的志愿者。她沒(méi)有刻意成為也不可能成為和難民水乳交融的一部分,反之她相信差異能讓世界表現(xiàn)出所有的復(fù)雜性。
在歐洲,因?yàn)槎唐趦?nèi)難民的超負(fù)荷涌入,對(duì)陌生人的恐懼和排斥在增加。歐盟自成立以來(lái),多少涂畫出了一幅拆除了邊界的大同氣象。而在2015年的難民流襲擊下,人們驚覺(jué)邊界并未真正被拆除,只是一度隱形,如今羞于公然再現(xiàn),便默默移動(dòng)。無(wú)論各國(guó)的邊境檢查是否卷土重來(lái),歐洲各國(guó)的很多人已默默將邊界帶入內(nèi)心深處,這從右翼政黨的迅速壯大可見(jiàn)一斑。
這場(chǎng)難民流之后,因?yàn)椴豢爸刎?fù),北歐各國(guó)從敞開(kāi)大門轉(zhuǎn)而開(kāi)始推出嚴(yán)格的難民政策。尼爾森夫人坦言,《入侵》的書寫并非出于一個(gè)享受著一定財(cái)富的北歐人良心不安的自責(zé),而是出于對(duì)世界、對(duì)人的關(guān)聯(lián)的興趣。成為世上的一個(gè)人,成為觀察和行動(dòng)中的人是尼爾森夫人的追求。《入侵》也以切身體會(huì)揭示,自我的意識(shí)會(huì)出現(xiàn)在邊界破裂之處。
真實(shí)與虛構(gòu)邊界的消蝕
尼爾森通過(guò)一系列文字、行動(dòng)和表演,在真實(shí)與虛構(gòu)的邊界移動(dòng)。那本狠狠地釘死他自己的自傳,正是利用了媒體報(bào)道和日記描述他如何在2001年初哥本哈根的流浪者中度日,如何試圖以無(wú)身份的方式扣開(kāi)社會(huì)系統(tǒng)之門,如何成功地讓自己登報(bào),突然有一天,晚報(bào)上出現(xiàn)整版報(bào)道,出現(xiàn)了瘦削而蒼白的尼爾森的臉,外加大標(biāo)題“我是誰(shuí)”。雖說(shuō)這一出流浪者之歌是一場(chǎng)虛假表演,“我是誰(shuí)”的問(wèn)題還是很尼爾森,他喜歡研究自己到底是誰(shuí),也很享受讓大眾“看著我”。尼爾森的自傳是文學(xué)作品,它的產(chǎn)生模式卻有些不自然,仿佛預(yù)先設(shè)計(jì)好的某個(gè)東西的一部分。這小說(shuō)不是從生活中提煉出的,倒像有一個(gè)被隱匿的腳本,戲劇已如期演完,隨后腳本得到了公開(kāi)。
本來(lái),關(guān)于小說(shuō)的社會(huì)共識(shí)之一是,雖然故事和人物源于生活,小說(shuō)依然是虛構(gòu)的。時(shí)下的狀況則是,一方面社交媒體里假信息鋪天蓋地,另一方面,尼爾森一類的作家在現(xiàn)實(shí)和虛構(gòu)的邊緣主動(dòng)進(jìn)行演繹。比尼爾森更具商業(yè)成功性的挪威作家卡爾·奧韋·克瑙斯高的自撰小說(shuō)《我的奮斗》的暢銷,在北歐催生了大量模仿者以及越發(fā)鮮明的新型現(xiàn)實(shí)主義,這種現(xiàn)實(shí)主義有它的犀利,有它的魔幻,恰如真實(shí)的謊言。凡此種種已使讀者習(xí)慣于放棄區(qū)分事實(shí)與小說(shuō)、真實(shí)和虛構(gòu)。一個(gè)邊界已被消蝕。
戲子的人生
2018年,尼爾森夫人推出小說(shuō)《怪物》,聚焦于一對(duì)孿生侏儒,以帶有散文風(fēng)格的獨(dú)白,對(duì)歷史、時(shí)間、感官、生死的本質(zhì)進(jìn)行考察。書中寫道:“放棄,并且突然沒(méi)了目標(biāo)或決定,喪失對(duì)事物和自己的所有權(quán),只是讓自己屈服于那個(gè)新的、滑動(dòng)、扭曲、贖回或解放了的存在形式,就可擺脫自我。”
怪物最終以一種預(yù)見(jiàn)性的愿景,在一個(gè)全新世界中徹底轉(zhuǎn)變?yōu)橐粋€(gè)全新的人類:“你不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就是應(yīng)該做自己不知道的事,盡可能精確地去做,直到它成形并出現(xiàn)為止,這樣不僅你自己,而且整個(gè)世界都可以看到它是什么。”
可見(jiàn),尼爾森對(duì)于人的生存形態(tài)的文學(xué)探索還在繼續(xù)。這個(gè)作家的書寫得到評(píng)論界的矚目和贊賞,不過(guò)總體來(lái)看,尼爾森的書寫與其說(shuō)是靠文字出彩,不如說(shuō)是靠著性、難民等邊緣且熱門的話題,靠著作者和小說(shuō)的高度重合性在發(fā)光。這些書寫走在真實(shí)和虛構(gòu)的邊界消蝕處,是實(shí)況轉(zhuǎn)播式或行為表演式的,極具時(shí)代流行元素的寫作。
尼爾森以不同的性別和稱謂書寫撲朔迷離、雌雄難辨的故事。在一個(gè)真假毋需固執(zhí)地辨別、只需冷眼沉醉的新歐洲里,尼爾森所做的一切都是一場(chǎng)鄭重其事的表演,也是一段鄭重其事的生活——這是戲子的人生,是邊走邊演、在每一個(gè)陌生村口的戲臺(tái)上粉墨登場(chǎng)的戲子的人生。當(dāng)尼爾森將這一狀態(tài)意識(shí)化、最大化時(shí),多少也活出了一分跳脫。在人生的臺(tái)前臺(tái)后變換,展現(xiàn)雖將粉身碎骨也能怡然自得的無(wú)畏,這無(wú)畏里幾分是真,幾分是即便膽怯也極力展現(xiàn)出的逼真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