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社會》:幾千年來,人類怎樣應對不平等?
幾千年里人類文明發(fā)展進程中的不平等困局有可能被打破嗎?那些說起來讓人戰(zhàn)栗的戰(zhàn)爭、革命、瘟疫、國家崩潰在顛覆一個政權的同時帶來短暫的平等,而除卻這些暴力現象,有沒有一種制度、一種變革真的創(chuàng)造出平等的經濟與社會局面?
美國斯坦福大學人文學科迪卡森講席教授、古典學和歷史學教授沃爾特·沙伊德爾的作品引進中文版本,即《不平等社會:從石器時代到21世紀,人類如何應對不平等》(后簡稱《不平等社會》)。書中從根源上追溯了不平等的起源,并將其定義為是人類開始耕種、放牧,并把財產代代相傳發(fā)展至今的一種人類文明的顯著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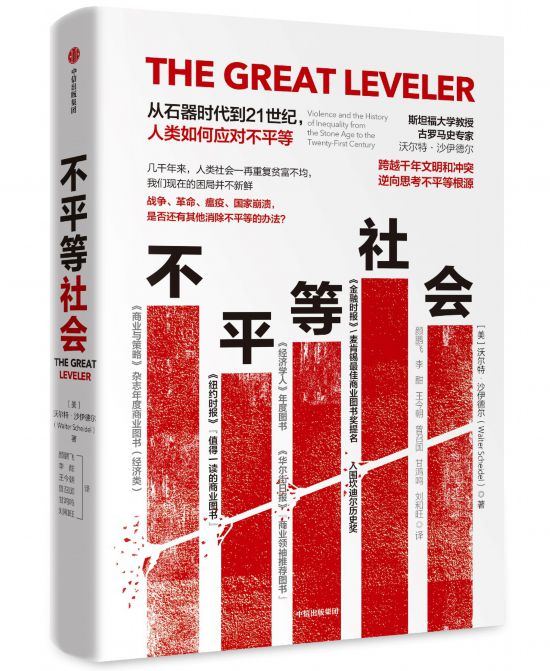
《不平等社會:從石器時代到21世紀,人類如何應對不平等》書影
在21世紀以后,隨著貧富差距在世界范圍內不斷擴大,經濟不平等問題影響到社會發(fā)展,以及被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關注,階級差異、不平等社會等問題被頻繁討論。然而,縱觀整個人類歷史,不平等現象并非是愈演愈烈、在當今世代才抵達的頂峰。根據數據統(tǒng)計,美國最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占比只是到最近才趕上了1929 年的水平,現在資產集中的嚴重程度要比那個年代的更為輕微。在“一戰(zhàn)”前夕的英國,最富有的1/10家庭令人震驚地擁有所有私人財富的92%,幾乎把所有人都排擠出去了,今時今日他們的收入占比僅略微超過全體的一半。
作者也指出,較高的不平等程度有一個非常長的譜系。各個國家國情不同,也存在許多特例,2000年以前,古羅馬最大的私人財富幾乎等于帝國平均年人均收入的150萬倍,然而,到大約公元600年前后的教皇大格里高利的時代,大莊園已經消失,給羅馬貴族留下的財富少到他們要依賴教皇的施舍來維持生存。
戰(zhàn)爭、革命、國家衰敗與致命傳染病矯正了社會不平等
是什么力量造成著社會的不平等,又是什么力量在打破著局面?作者提出,我們一直追求的社會發(fā)展中的穩(wěn)定和諧的局面恰恰會助長不平等,“文明社會并沒有讓自己適應和平的平等化進程。對于廣泛的社會范圍和不同的發(fā)展水平,穩(wěn)定都會助長經濟不平等。對于法老統(tǒng)治下的埃及,或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又或是羅馬帝國和現代的美國,都是如此。”
而恰恰是暴力性沖擊才能破壞既定的秩序,作者梳理出四種不同類型的暴力沖擊,分別是:大規(guī)模動員戰(zhàn)爭、變革性的革命、國家衰敗和致命傳染病。它們也分別構成了書中的二至五章,作者認為,這些力量對破壞既定秩序,壓縮收入和財富的分布,縮小貧富差距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沙伊德爾在行文中總是抱有一種沮喪的、悲觀的態(tài)度——他列舉各個國家不同歷史階段的發(fā)生的事件的案例來說明我們需要為了總是短暫的、不可避免會走向不平等的失序的平等付出怎樣的代價,比如戰(zhàn)爭和瘟疫之后,很容易想象的百廢待興,富人和窮人一樣被剝奪,而富人自然要失去更多,如瘟疫和饑荒造成的不平等其實是短時間內令數千萬人失去生命,矯正效果是短暫的。隨著人口恢復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抵消了這些好處。因此,瘟疫是一種既極其殘酷又最終不可持續(xù)的收入和財富不平等的壓縮機制。
如上所述,戰(zhàn)爭和瘟疫造成的社會不平等易于理解,其中瘟疫要造成社會的變革的前提條件是瘟疫蔓延相當嚴重,并造成很多人的死亡,在現代,即便新冠疫情非常嚴重,也并未撼動一國之根本。由此我們可以重點看“國家衰敗與系統(tǒng)崩潰”以及“替代性選擇”的部分。
書中,“國家衰敗與系統(tǒng)崩潰”部分,沙伊德爾認為,從當代視角來看,國家衰敗可以定義為是那些腐敗、缺乏安全保障、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崩潰,以及喪失合法性的國家。當然由于前現代國家首先是專注于檢查內部和外部的挑戰(zhàn),保護統(tǒng)治者的主要盟友和伙伴,征收執(zhí)行這些任務和滿足權力精英致富所需的收入,國家衰敗最好被理解為喪失實現這些基本目標的能力。對主體和領地的控制遭到侵蝕以及政府官員被類似于軍閥這種非政府角色取代是典型的結果,在極端情況下,政治權力甚至可能被下移至社會基層。
沙伊德爾舉的第一個例子是唐朝精英的毀滅,作者因襲了譚凱《中古中國門閥大族的消亡》中的觀點,談道:一份最為詳細的、對這個群體和它留下的大量的墓志銘的研究發(fā)現,在公元9世紀,住在長安的皇家知名成員,包括大部分的大臣和負責地方行政管理的最高級別官員,其中至少有3/5存在著緊密相連的親屬關系和婚姻關系。這個“高度封閉的婚姻和親屬關系網”控制了整個國家,在很大程度上為集團內部成員的個人利益服務。“從公元960年開始,一個新王朝宋的出現帶來了完全不同的家族。”
作者將中國歷史中一個屢次被討論的焦點“唐宋之變”解讀為“國家衰敗毀滅了位于社會金字塔頂端的財富,通過使富人致貧甚至消滅富人的手段來矯正財產的分配。”是直接針對統(tǒng)治國家的精英階層施加暴力而導致的相當程度的對于社會階層和財富的矯正。
令人質疑的和平性替代方案
所以暴力是“萬物之父和萬物之王”嗎?有沒有和平的替代性方案能產生相似的結果?
沙伊德爾也分析了很多改變階層關系的“候選方案”:土地改革、經濟危機、民主化和經濟發(fā)展。
其中,土地改革有很長的歷史,“在古希臘,土地改革和一些作用類似的措施——尤其是債務免除通常都與暴力政變相聯系。從古風時期到希臘化時期,這類記載延續(xù)了好幾個世紀。公元前7世紀的柯林斯的第一個暴君,在消滅或者驅逐其反對派成員之后奪走他們的土地進行再分配。公元前 280 年,在奴隸和制造業(yè)工人的幫助下,阿波羅陀洛斯在卡桑德拉城掌權。據說他沒收了富人的財產,并且在窮人當中進行再分割,同時提高了士兵的酬勞。”
因為在過去大部分的時間人和土地有高度的黏性,耕地也就一般代表了私人財富的數量。土地改革并非天生就與暴力相伴,在理論上,沒有什么會限制人類社會通過和平地調整土地所有權使窮人受益。“然而在實踐當中,情況常常會不同: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成功的土地革命幾乎毫無例外地都依賴于暴力的實施或者威脅。”沙伊德爾說,“表面上雄心勃勃的土地再分配計劃不斷被證實具有建立政權的特征,如同戰(zhàn)國和隋唐時期以及漢朝時的中國,具有統(tǒng)治者竭力壓低精英階層財富的背景。”
沙伊德爾對于我們一直堅信可以改變不平等的民主也持有不同意見:基于對184個不同國家觀測樣本的描繪,民主對市場乃至可支配收入不平等性的影響并不一致。民主在形成資源凈分配時的作用是復雜且異質性的,民主與平等化再分配政策之間的關聯性通常并不明顯。原因有二:如果民主被有勢力的選民‘俘獲’,平等化進程將會受到阻礙,同時民主化為經濟發(fā)展提供了各種機會,但也可能提高收入不平等水平。”
在歷史中,古代雅典民主制的演化似乎與動員群眾的戰(zhàn)爭糾纏在一起,在20世紀上半葉的特定時段,選舉權在很多西方國家的普及顯然與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沖擊有關。僅僅是這個原因,即使民主化看上去對于這些社會的物質資源分配有一種平等化的效應,這種平等化效應至少在部分意義上是由戰(zhàn)爭的壓力所驅動的。
目前已經有無數關于減少不平等的建議,如以累進的方式課稅、貿易關稅和創(chuàng)建全球財富登記制度等措施。“但是對任何一項現實的政策配置來說,其好處相對不大。更普遍的是,人們似乎對如何將這些建議變?yōu)楝F實,甚至對它們是否能夠產生重大影響出人意料地幾乎沒有興趣。然而,關于矯正,歷史告訴我們兩件重要的事情。一個是激進的政策干預通常發(fā)生在危機時期。世界大戰(zhàn)和大蕭條沖擊所產生的平等化措施主要是基于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換成不同情況它們可能就是不可行的。第二個教訓更加直截了當:政策制定只能有一定效果。歷史不止一次地證明,社會內部物質不平衡的壓迫是由暴力驅動的,這種力量在人類的控制以外,遠超現在任何可行的政治議程范圍。”作者提出。
“當未來變成歷史,人們可能發(fā)現,和平政策改革可能根本無法應對今后日益增長的挑戰(zhàn)。然而,有其他選擇嗎?我們所有珍視經濟平等的人都應該記住,它在巨大的悲痛中才會出現。”沙伊德爾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