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植芳:從歷史中來,到學問中去

賈植芳(1916—2008),山西襄汾人。現(xiàn)代作家、翻譯家、學者。1936年留學日本大學社會學科。因投稿結識胡風,成為“七月派”骨干作家之一。新中國成立后,歷任震旦大學中文系主任,復旦大學教授、圖書館館長,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第一屆副會長,上海比較文學研究會第一屆會長。專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和比較文學,是這兩個學科的奠基人之一。著有小說集《人生賦》,散文集《熱力》《暮年雜筆》,回憶錄《獄里獄外》,譯有《契訶夫手記》等。有《賈植芳全集》十卷存世。
【生活再動蕩也要握緊手中的筆】
◆哪怕生活再動蕩,賈植芳也“總是在人生道路上任何一個安定的瞬間匆匆忙忙抓起筆來,努力要留下一些人生的感觸”。甚至在化名避居青島安身小客棧的時候,因為“窮居無事”,便“潛心翻譯”。他從街頭舊貨攤上以買廢紙的價錢購進一批英日文外文書,用不到半年的時間翻譯了三本書:恩格斯的《住宅問題》、英國傳記作家奧勃倫的《晨曦的兒子——尼采傳》以及匈牙利作家E·維吉達的多幕劇《幻滅》。
【教授是假(賈)的,教書是真的】
◆賈植芳不是正襟危坐的老先生。他身上有著煙火氣,幽默感無處不在,說話常常妙語連珠,調侃起自己來更是毫不客氣。年紀大了,他說自己“走路用拐杖,談話要用助聽器,成了三條腿、三只耳朵的人,有時想想,覺得自己像個《封神榜》里的角色”。說到自己的工作,他說“我這個教授是假的,不是人人都叫我‘假(賈)教授’嗎?不過,我教書卻是真的,從來不賣假貨”。雖是玩笑,但從中能看出老先生的人生智慧和職業(yè)堅守。
【學術眼光充滿前瞻性和先鋒性】
◆賈植芳的學術眼光非常前衛(wèi)。他很早就具有了比較文學研究的思維——上世紀50年代的課堂上,已經在用這樣的思維方式授課;1980年代初,比較文學尚在復蘇之中,賈植芳已自覺運用比較文學的方法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展開研究。在翻譯上也是如此。他1940年代就翻譯了恩格斯的《住宅問題》。解放初期曾有人做過統(tǒng)計,復旦大學有兩位教授是譯介馬克思主義的先驅,一位是陳望道,另一位就是賈植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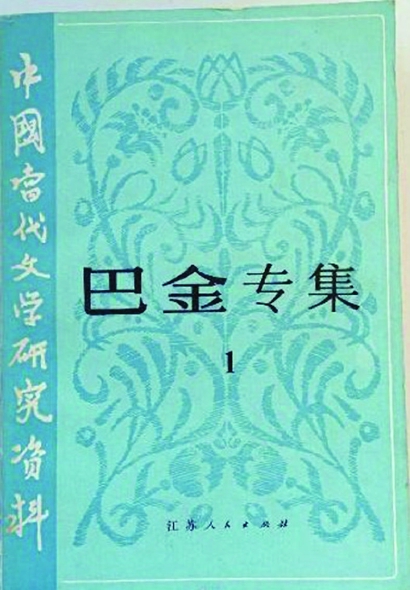
賈植芳代表作一覽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巴金專集》
大寫一個端正的“人”字
賈植芳為后人記住的,除了豐厚的學術遺產,還有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鏗鏘風骨。
在回憶文章《且說我自己》中,賈植芳說道:“在上帝給我鋪設的坑坑洼洼的生活道路上,我總算活得還像一個人。生命的歷程,對我來說,也就是我努力塑造自己的生活性格和做人品格的過程。我生平最大的收獲,就是把‘人’這個字寫得還比較端正。”這樣的話,賈植芳說過多次。在他心中,不論是要做“人生的主人”,或是追求生命的不平凡,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寫好這個“人”字。
“我只是個浪跡江湖,努力實現(xiàn)自我人生價值和盡到自己的社會責任,在‘五·四’精神的培育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識分子”,賈植芳晚年時的這番自我評價全面而深刻。他乘風破浪的一生,他的學術源起,“社會人”與學者的雙重身份都在這一句話中交代得清清楚楚。
在許多人的心中,賈植芳的存在如精神標桿,他那由風浪也撲不滅的風趣、磨不掉的傲骨,常為人談起。但內里對學問、對學科建設、對傳道授業(yè),他是極度認真的,從讀書上學,走上“知識分子”之路開始,賈植芳就時時提醒自己知識分子的責任。后半輩子,賈植芳以全副身心投入到他所熱愛的文學和教書育人的事業(yè)當中,在復旦大學中文系首創(chuàng)了現(xiàn)代文學和比較文學兩門學科,培養(yǎng)了一批又一批在學界赫赫有名的學者。
從 “淘氣王”到半生動蕩的“社會人”
如果在賈植芳孩提時代,問他的父母,這個小孩兒將來會長成什么樣子,“學者”大概是一個最意想不到的答案。1916年,賈植芳生在山西呂梁山區(qū)一戶家境殷實的地主家。因為總是闖禍,家里圖清靜,將5歲的賈植芳送入私塾,后來轉到鄰村小學就讀。天性不喜約束的賈植芳對教材上的刻板內容毫無興趣,父親趕集買來的新課本別在他腰上,買一次丟一次,還時常在課堂上淘氣。開始對書籍著迷,是賈植芳讀高小的時候,那時同學借他一本石印本《封神榜》,賈植芳一下子就被情節(jié)吸引住了。上初中時,賈植芳走出了閉塞的山村到省城讀書,那段時間他沉迷于各種借來的石印本小說,欽佩行俠重義的綠林好漢,佩服降妖鎮(zhèn)怪的神道。轉折發(fā)生于初二,學校來了一位北師大畢業(yè)的國文教師,指導學生們看新文學作品《吶喊》《彷徨》以及外國翻譯文學和一些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政治讀物,這對賈植芳影響尤深,“從這時起,我開始認識到文學是一種改造社會、改善人生的武器”。此后,賈植芳開始嘗試寫作、投稿,將對社會的觀察和剖析付諸筆端。1931年,賈植芳到北平一所由美國教會主辦的中學讀高中,雖然讀了兩年半就因個性反叛被校方除名,但這段時間,賈植芳打下了堅實的英語基礎。他開始看原版英語報紙和書刊,視野也隨之放寬,更多的中外文學作品、社會科學譯著列入他的閱讀范圍——在他宿舍的墻上曾掛過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克魯泡特金、馬克思的相片。
回望青少年時期,賈植芳曾自述:“我生逢中國社會內亂外禍交織、動亂不安的時代,這個時代也是一個中外文化交流、碰撞、融匯的開放性時代。在這樣的歷史環(huán)境里,我們一方面繼承了儒家‘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另一方面追求著個人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投入了中國救亡和改造的社會政治運動。”1935年,血氣方剛的賈植芳參加了“一二·九”運動,被逮捕關押,經當商人的伯父四處周旋才出獄。之后伯父匆匆將他送往日本求學,并叮囑他不要再碰政治。到了日本后,賈植芳并沒有遵從家里的意思學醫(yī)或讀銀行管理,而是在1936年夏天進入了日本大學社會學系,跟隨園谷弘教授學習研究中國社會,初衷是“想學點社會學專業(yè)知識,以便從中得到觀察、分析、描寫和反映社會生活的理論導引”。然而賈植芳最熱衷的依然是文學,尤其是外國文學,對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安特列夫代表的俄國文學尤其喜愛,甚至從舊書肆中搜購了他們作品的英譯本和研究俄國文學的論著來閱讀。賈植芳說,這些閱讀,對他有過很深的影響。
1936年10月,魯迅去世了。魯迅是賈植芳唯一始終崇拜的中國現(xiàn)代作家,他從不隱藏這份喜愛和崇拜,多次在公開場合尊魯迅為“精神導師”。暮年之際,飽經憂患的賈植芳每每重溫魯迅的早期作品,還能從中找到深切的現(xiàn)實感受。魯迅的去世,給年輕的賈植芳帶來不小的打擊。不久后他在東京內山書店發(fā)現(xiàn)堅持魯迅傳統(tǒng)的戰(zhàn)斗文學刊物《工作與學習叢刊》,非常驚喜,于是將自己的一篇小說寄送投稿。從此賈植芳與刊物主編胡風,也是魯迅親炙的弟子交上了朋友,后來成為胡風主編的《七月》《希望》等文學期刊的作者之一。
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賈植芳當即棄學繞道香港回國參加抗戰(zhàn),期間拒絕了家人替他安排的留在香港或去歐洲讀書的前程。后來談起這次人生十字路口上的抉擇,賈植芳說:“再想到自己幾經囹圄、傷痕累累的一生,我不能不感慨萬千……但選擇回國抗戰(zhàn),仍然是我的良知所決定的”,“我仍然會選擇自己應該走的路,終生不悔”。戰(zhàn)爭給青年賈植芳的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社會人”烙印:他在前線做過日文翻譯,也為后方報紙寫過戰(zhàn)地通訊……他不服管束的個性和刻在骨子里的良知使他不能容忍現(xiàn)實中腐朽與黑暗的一面,以至于幾次險象環(huán)生,幾次絕境逢生,整個抗戰(zhàn)期間在大半個中國顛沛流離。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賈植芳因在徐州搞策反被關到了日軍的牢房;1947年9月到上海后不久,因給進步學生刊物寫文章,又受了一年多的牢獄之災。多年在流轉生活中打滾,賈植芳養(yǎng)成了一種習慣和嗜好:讀各類有關中國社會、歷史、文化的書,以便能深入認識和了解這個國家的歷史和現(xiàn)實。1948年再一次從監(jiān)獄中出來,賈植芳便蟄居滬西鄉(xiāng)間一閣樓,用兩個月時間,趴在兩只箱子搭成的臨時書桌上,依靠借來的圖書資料——多半是日本學者的著譯,和他常年對社會的觀察,晝夜不停地編寫了一部20多萬字的社會學著作《近代中國經濟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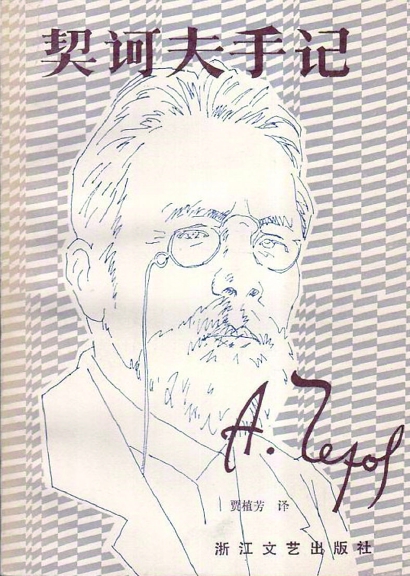
賈植芳譯著《契訶夫手記》
中國現(xiàn)代文學是與他的生命血肉相關的歷史
“賈先生是‘五四’的第二代。與前面一代的知識分子相比,他們是在‘五四’反封建專制主義精神激勵下成長起來的一代;卻在青壯年之際遭遇了抗戰(zhàn),失去了窗明幾凈的書齋,失去了從事縝密研究的環(huán)境。因此賈先生的文學知識積累不是書本到書本,而是活生生的感受。”著名學者陳思和曾跟隨賈植芳讀書,在他眼中,現(xiàn)代文學是活的歷史,某種意義上還在延續(xù);而賈先生是這段歷史中的人,現(xiàn)代文學與他的生命血肉相關。“他得到的知識、做人的方式、愛憎分明的性格,對傳統(tǒng)封建內容的批判,都有著五四新文學傳統(tǒng)的影子。新文學傳統(tǒng)的激進文學傳統(tǒng)里,代表性人物胡風、巴金以不同的方式繼承了魯迅精神,這種精神傳統(tǒng)又在賈先生身上得到延續(xù)。”所以,賈植芳的現(xiàn)代文學課,更像是當事人對人生觀察的分享,他講述文壇掌故與作家背景,關于現(xiàn)代歷史與文學的廣博見識和真知灼見,時常就貫穿在閑談中。作為賈植芳的學生,學者張新穎曾回憶,在他讀研究生期間,賈先生沒有給他講過一次課。“先生的方式就是坐在書房兼客廳里聊天。聊什么呢?沒有限定。這位瘦小的老人,能夠讓你充分感受海闊天空和人世滄桑。你在這里學習歷史和認識社會,全是通過具體可感的形式。”在賈植芳的又一位高足嚴鋒看來,賈先生的記述與回顧有著一種特殊的文化現(xiàn)場的意義,“他的這種‘目擊者’的證人式的研究法就是賈先生的獨門暗器,也是歷史和磨難贈予他的珍貴禮物”。賈植芳一些有趣的生活習慣都與他獨特的治學方式有關,比如他會去報攤上買小書小報,喜歡那些帶著原始的、粗糙的,甚至亂糟糟的社會生活氣息的真實的社會經驗,而不是被知識分子的趣味所整理、闡釋、概括和升華后的那些東西。
這些特質,都引向了一個看似偶然的必然:1950年,賈植芳從“社會”進入“書齋”,到震旦大學中文系任職,開始了以學術為業(yè)的職業(yè)生涯;后隨高校院系調整,調入復旦大學中文系任教授,并受命主持新組建的現(xiàn)代文學教研室——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學科史上,賈植芳是學科創(chuàng)建的元老之一。這一時期賈植芳對現(xiàn)代文學學科的貢獻,主要體現(xiàn)在學科架構、課程設置和人員調配這些“看不見”的基礎工作上。“他的工作為復旦中文系現(xiàn)代文學學科日后的長足發(fā)展奠定了良好基礎,今天看來,復旦大學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教學和研究所以能在全國乃至世界范圍內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是與賈植芳先生當年的開拓性貢獻分不開的。”賈植芳的再傳弟子張業(yè)松在一篇回憶文章里寫道。賈植芳一路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學科拓荒路上潛心耕耘,沒有料到的是,與胡風的友誼讓他陷入了一場長達25年的牢獄、“改造”風波。直到1980年底,賈植芳才獲得平反,重新回到教授位置,這時他已經60多歲。但他的精神銳氣未曾磨滅,在64歲到92歲留下了大量文字,這也是他一生中著述最為豐富的時期。
重啟學術之路的賈植芳接續(xù)了斷檔20多年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學科建設工作。當時,學科重建面臨的最為緊迫的任務,就是重新梳理和搶救基礎史料,還歷史本來的豐富面貌。1980年代初,賈植芳在全國范圍內率先啟動了大規(guī)模的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資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先后參與主持編纂《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資料匯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等大型資料叢書,并親自承擔了其中的《巴金專集》《趙樹理專集》《聞捷專集》《文學研究會資料》等書的編選工作。編纂這些大型叢書是一件為后學栽苗植樹的工作,為了將其做好,賈植芳留下了體量可觀的審讀和指導意見,并為專集撰寫編后記,字里行間透出的正是他對于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學科的復興和發(fā)展的建設性的思路。在賈植芳看來,研究性書籍的編輯工作應該嚴格從文獻學的角度、或者從歷史的觀點出發(fā),要突破文學研究中的一些積弊尤其是鉗制研究的非學術要求——在1980年代初提出這樣的想法,需要非常大的學術勇氣。
中國比較文學學科的奠基人之一
“1980年代初的時候,比較文學還剛剛在復蘇之中,賈先生談起來就好像已經思考多年了。”比較文學研究學者嚴紹璗曾在一次采訪中贊嘆賈植芳學術思想的前瞻性和先鋒性。賈植芳寫于1981年的長篇論文《中國新文學作家與外國文學的關系——以茅盾為例》已在自覺運用比較文學的方法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展開研究。“其實,應該說在1950年代初他給章培恒、范伯群、曾華鵬諸位先生上課時,就已經參透著當下比較文學學科倡揚的學術思想”,嚴紹璗說。曾有當年的學生回憶,賈先生講課常追根溯源,以異國文學相印證。講臺上堆一疊書,很多都是西方的著作,他當場翻譯給學生聽,學生的眼界豁然打開——賈植芳一直以來就反對孤立靜止、畫地為牢地自我封閉式地研究文學,“那是走古人研究四書五經的老規(guī)范:尋章摘句,咬文嚼字,只能是像馬克思所鄙夷的那種坐在書齋里連手指頭被燙傷都害怕的三流學者,或者像我們古人所形容的‘腐儒’,或‘書蟲’,那就不可能在原有的文化遺產基礎上進行創(chuàng)造性勞動”。
多年的翻譯經驗自然也是將賈植芳引向比較文學研究的關鍵。賈植芳譯著豐富,且主要集中在學術研究文章上:他1940年代翻譯了恩格斯的《住宅問題》,是馬克思主義專著的早期譯者。解放初期曾有人做過統(tǒng)計,復旦大學有兩位教授是譯介馬克思主義的先驅,一位是陳望道,另一位就是賈植芳。而對捷克作家基希的《論報告文學》的翻譯,更是顯示了賈植芳的前衛(wèi)眼光——報告文學這一戰(zhàn)斗文學樣式1930年代才引入國內,賈植芳作翻譯時,同類譯作寥寥。而對《契訶夫手記》的翻譯更是他譯著中濃墨重彩的一筆。在賈植芳眼中,翻譯文學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發(fā)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從魯迅起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作家,無不從翻譯文學中吸取到珍貴的養(yǎng)料……翻譯文學理應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一個有機構成部分”。這里其實透露出了賈植芳倡導比較文學的思想動因——他對中國文學的開放性的期盼,如他在《開放與交流》這篇短文中所說:“比較文學的一個基本精神就是開放與交流:以開放的眼光去研究文學的交流……比較文學研究的盡管是已有的文學現(xiàn)象,但它必然會帶來各國文學之間的交流。而且,這種交流是雙向的,即不僅有引進,還有引出。”
上世紀80年代,在賈植芳的倡導和推動下,復旦大學中文系恢復了比較文學的教學和研究,成為全國最早開設比較文學課程、最早設立比較文學教研室、最早獲得比較文學碩土學位授予權的高等學府。沒有先例可循。在賈植芳的手上,復旦大學的比較文學研究學科一點點“從無到有”。從資料梳理到理論評說,從建立學會到培養(yǎng)人才,他的工作逐步奠定了學科的規(guī)模、發(fā)展方向與品質。他當時主持的國家重點社科項目《外來思潮流派理論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影響》,在成書出版時改名為《中外文學關系史資料匯編》,是國內第一部較為全面和系統(tǒng)地整理中外文學關系史文獻的大型資料書,在學界影響深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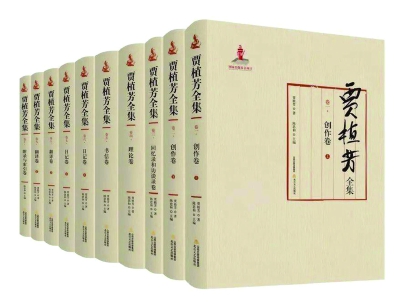
《賈植芳全集》
留下了學術遺產,也傳承了人格精神
曾有人借賈植芳的日記觀察過他的工作強度:“全力編《契訶夫年譜》,通宵達旦”(1983年3月30日),“昨晚譯書至晨六時始寢”(1983年10月24日),“未出門,今日五時始寢,趕譯論文”(1983年11月1日)……為什么要如此辛苦?老先生又露出了他嘻嘻哈哈的一面:“既然活在這個世界上,要活著就要消費,為了付飯錢,就得為這個社會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玩笑的背后,其實是他一以貫之的知識分子的擔當,還有來自青年時期的、從未熄止的理想之光。他有過另外一番剖白:“對我們這一代在‘五四’精神培育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識分子說來,凡是有助于社會進步和文化建設,即能促進中國由舊的傳統(tǒng)走向現(xiàn)代化的大小活動,總是習慣性地卷起袖子,奔上去,自覺地做些什么,即或是為之出生存身,吶喊幾聲,擂鼓助陣,都當成是一種義不容辭的社會職責。”帶著這一底色的賈植芳在青年時代形成了“當一個好事之徒的本性”,晚年更是甘做“寫序專業(yè)戶”,為把那些奮力于嚴肅的文藝著譯與學術著作的后輩學者推向學術文化界而搖旗吶喊。直到生命的最后,睡在病床上,賈植芳伸手能夠夠到的地方全是書,一顆心仍在掛念著病房之外的事。
“他是魅力型人物”,陳思和說,“我明顯感受到他那種強悍的、父性的人格對我的影響,這是一種整體的影響,包括后來我人生道路的選擇,都與此有關。他教給我怎樣做人,他并沒有具體地教我該怎么做,但他待人處世,看歷史,看現(xiàn)實,整體的精神深深影響了我”。深受賈植芳影響的不只陳思和。著名學者章培恒生前曾說過賈植芳對他的師恩是一輩子的,既在做人方面也在做學問方面。他坦陳自己在古代文學研究領域里面的“不正宗”正是襲自賈先生研究中國文學的方法和路徑:“如果沒有這樣的一種指導,我當然還會做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但是跟現(xiàn)在的情況,可能會很不一樣——而這一種很不一樣在我來看并不是我所希望的,我應該說正是我所害怕的”。在陳思和看來,賈先生傳授的是一種“知識分子的立場和精神”,即從正宗的主流的傳統(tǒng)規(guī)范中走出來,通過個人的獨立思考,重新審定研究對象。賈先生通過這種“精神傳遞”,“將優(yōu)秀學生的才華充分調整到了一個火山口,接下來就讓它自然地噴發(fā)了”。上世紀五十年代,短短幾年賈植芳就培養(yǎng)了章培恒、施昌東、范伯群、曾華鵬等學生,他們后來分別成為古代文學、文藝美學、現(xiàn)代文學等領域的領軍人物;而在八十年代重回教席后,賈植芳更是培養(yǎng)了陳思和、李輝、嚴鋒、張新穎等學術領域內著名的學者。“優(yōu)秀教師的判斷標準是能否培養(yǎng)出優(yōu)秀的學生,而不是自己是否有名。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賈先生是一名真正的教育家”,陳思和說。
“我理解的人生,不只是履行動物的本能要求……人生應該追求更高的生活境界——人生的自我價值和意義……應該通過博讀精覽,放眼人生、世界和歷史,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的真正位置,履行自己的人生責任和社會使命。”2002年,第五屆上海市文化藝術特殊貢獻頒獎典禮上,回顧過往,86歲的賈植芳說,我并未虛度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