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偉:作為詩和科幻的科幻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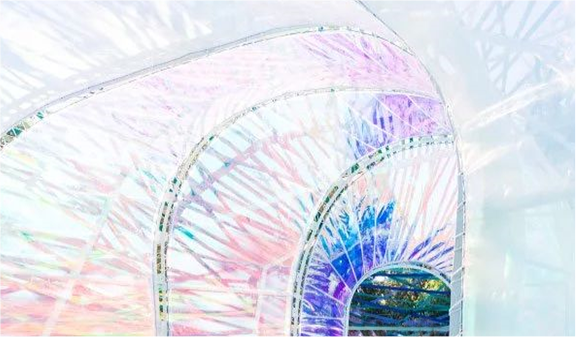
題記
作為一種文類的科幻詩首先是詩,具備詩的審美特質(zhì)。與此同時,科幻詩還具備科幻性。“相關或相似”原則可以標示出科幻詩的泛科幻性,認知陌生化能夠賦予科幻詩以內(nèi)在的科幻性,而與其他科幻作品的互文亦可為科幻詩注入源自外部語境的科幻性。
一 詩 性
正如科幻小說本質(zhì)上是小說,科幻詩在本質(zhì)上當然也是詩。或者說,科幻詩首先是詩,然后才是科幻詩。
分行的散文并不是詩。詩有其內(nèi)在的跳躍性,凝練、斷裂、留白,甚至蓄意拒絕邏輯的規(guī)訓。如果散文是小徑分岔的花園,詩就是隨機組合的星座,詞、句、意象彼此之間全依人為想象而勾連成圖。詩當然可以表意,可以傳情,也可以敘事,但畢竟不同于小說這種散文體的敘事文本。即便要講述一個科幻故事,詩也并非平鋪直敘。
哈瑞·馬丁松(Harry Martinson)的科幻史詩《阿尼阿拉號》(Aniara)[1]呈現(xiàn)了一個宏闊悲壯的太空故事,其敘事可謂相當完整。然而這部史詩中的敘事形態(tài),與一部同樣講述人類太空之旅的小說,迥異其趣。《阿尼阿拉號》的故事由103首詩展開,而這103首詩卻風格殊異,有娓娓道來者,有冥想哲思者,有插科打諢者,整個“敘事”進程層層斷裂,示人以莫大張力,熱切、驚懼、冷靜、憂郁、悲壯、詼諧、頓悟,凡此種種,皆閃爍其間。借跳躍形成張力,以場景、情緒、意象和象征對抗邏輯,這種反連貫的行文方式使得《阿尼阿拉號》深具詩的審美特質(zhì)。
二 泛科幻性
那么,科幻詩的科幻性又源出何處呢?
筆者對科幻有一個普泛的定義:科幻是呈現(xiàn)異于現(xiàn)狀之無限可能性的雜糅文類,其想象力與科學相關或相似。此定義也可用于界定普泛意義上的科幻詩。從最泛化的視野來看,凡是經(jīng)由“與科學相關或相似”的想象力呈現(xiàn)出別樣可能的詩,都可視為科幻詩。當然,此法無涉價值判斷,亦即,它只用來界定科幻詩的科幻性,而不負責測量科幻性的多寡,也不負責評判科幻詩的優(yōu)劣。
“與科學相關或相似”無疑是科幻詩對其科幻性最為直觀明確的展現(xiàn)。一方面,“相關或相似”意味著科幻性并不等同于科學性,聯(lián)結(jié)二者的是換喻(metonymy)或隱喻(metaphor)。科幻中的“科學”不是現(xiàn)實中的科學,而是在換喻的意義上與其相關,或在隱喻的意義上與其相似。這就免除了科幻對科學的絕對依賴,因此科幻中的“科學”不必精準、周延、可證、可行,質(zhì)言之,不必真實,只需可信。任何虛構(gòu)作品之可信,都并非源自真實,而是源自讀者與作品的契約——讀者擱置懷疑,作品敞開世界[2]57-59。
另一方面,“與科學相關或相似”,賦予了科幻詩區(qū)別于其他詩類的“科學”特征。準科學也好,類科學也好,偽科學也好,都是與科學相關或相似的話語,都可履契約之責,帶讀者走進虛構(gòu)作品的虛構(gòu)世界。不論這話語在作品中體現(xiàn)為術語、意象、隱喻,還是體現(xiàn)為世界設定、敘事策略、抒情模式等等,皆可為據(jù)。依此試讀下面這首詩,稱之為科幻詩應無不妥:
從太陽黑子到遺傳密碼
螞蟻金光閃閃 像星星
從宇宙到艦橋
到處是魔術師
到處是閃電
到處是鯨
到處是神經(jīng)過敏的時鐘
唇紅色的中子加速器里
水滴的艦隊 飛向異空
彼處有 光潔的電荷
橄欖形的螢火蟲
死寂的無云的天
和 甜的心靈①
上述界定方式,意在以最淺明的標記,為科幻文類劃定一個最寬泛的疆界。它在客觀上允許和鼓勵文類內(nèi)部的多元、差異、互動、流變,同時也正視文類內(nèi)部與外部的雙向滲透。如前所言,此界定方式并不司價值判斷之職,無關具體作品的優(yōu)劣評價。
三 內(nèi)科幻性
倘若只是堆砌科幻術語、意象、橋段,那無非為詩披上了一層科幻的宇航服——保身之物,而非科幻的肌理、血肉與骨骼本身。切身的科幻感源自文本內(nèi)在的審美邏輯。不妨來考察下面這首科幻短詩:
我看到了我的愛戀
我飛到她的身邊
我捧出給她的禮物
那是一小塊凝固的時間
時間上有美麗的條紋
摸起來像淺海的泥一樣柔軟
她把時間涂滿全身
然后拉起我飛向存在的邊緣
這是靈態(tài)的飛行
我們眼中的星星像幽靈
星星眼中的我們也像幽靈[3]
此乃《三體Ⅲ》中歌者文明的古老歌謠,雖是為小說敘事而穿插文中,但其本身未嘗不是一首科幻詩佳作。
詩中有諸多陌生化的表達。作為人類讀者,我們并不知道“我”和“她”的生物形態(tài)與文化特質(zhì)。為何是“她”,歌者文明的生命個體有性別之別嗎,又有幾種性別呢?為何要給她“禮物”,歌者文明也有饋贈的習俗嗎,個體之間饋贈禮物又有何深意?而這禮物是“一小塊凝固的時間”,時間何以凝固,何以帶有花紋,又何以涂滿全身?在歌者文明中,“飛”是一個修辭嗎,倘若并非修辭,那么這飛行所依賴的是肉身之翼、機械之助,還是波態(tài)傳遞?“存在”有“邊緣”嗎,歌者文明也思考存在嗎,對于他們(抑或她們、它們、祂們)而言,存在是哲學概念,還是具體之物?何為“靈態(tài)”,究竟是一道優(yōu)美身姿,還是一番宗教體驗?而“幽靈”又是否對他者的終極隱喻?
這種種表達,在不予解釋的空白與張力中,給我們帶來巨大的陌生感。然而,這一切卻又分明是我們能夠領會的,甚至讓我們身臨其境、感同身受。
我們“深知”這個純粹想象出來的異世界是“可能”的。在彼時彼處,彼文明的兩個個體——“她”和“我”,愛戀著彼此。“我們”對諸如時間這類物理概念有獨特的理解。“我”隨著“我的愛戀”以某種方式翱翔天際,去往某個天涯海角,與某些倏忽閃爍、似有似無的星星相對而視。這種可認知的陌生化,正是達科·蘇恩文(Darko Suvin)所定義的科幻。
蘇恩文承繼維克多·什克洛夫斯基 (Viktor Shklovsky)的“陌生化”(остранение)概念和貝爾托·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 “間離效果”(Verfremdungseffekt)概念,以 “認知陌生化”(cognitive estrangement)這一頗具結(jié)構(gòu)主義意味的美學特質(zhì)來界定科幻文學。他認為科幻之所以為科幻,并非源自科學或未來等主題內(nèi)容,而是寓于人般非人、現(xiàn)實般非現(xiàn)實、此世界般彼世界(this-worldly Other Worlds)[4]的美學屬性。
參照蘇恩文的思路,恰是在彼與此的相互挑逗之中,科幻詩具備了內(nèi)在的科幻性。詩中越是陌生晦澀處,反而越能撥動讀者共鳴之弦。
從另一個方向來看,以日常熟悉的語言和波瀾不驚的語氣來“低調(diào)陳述”陌生之意象與情境,同樣能夠促成認知陌生化的審美效果。筆者在此舉個極端簡潔的例子——源自兩歲孩童的“科幻詩作”Everyday Use(《日用家當》):
媽媽
你在早市
沒看著
賣火箭的嗎?②
這首由無忌童言無意而為的小“詩”,無非就是小孩和媽媽的日常對話,平實而直白。詢問早市小販出售的物品種類,比如,有沒有菠菜和西紅柿,幾家賣豆腐腦的,賣多少錢一碗……充滿了人間煙火味。
然而,不對!這煙火卻并非人間煙火。孩子問的不是菠菜、西紅柿或豆腐腦,而是火箭。家常聊天的慵懶句式中,暗藏著令人驚異的陌生場景和世界設定。把火箭當作日用家當出售的早市,是多么不同尋常的早市啊。這是未來某個年代的早市嗎?這是早已不在地球的早市嗎?這母親與孩子是和我們讀者同樣的人類嗎?又或者,“早市”與“火箭”乃是言此意彼的晦澀象征?
矛盾意象的巨大張力和凝練留白的闡釋空間,使得這幾行文字成為了“作為詩和科幻的科幻詩”。
四 互科幻性
倘若放眼外部語境,科幻詩的科幻性亦可來源于互文③。詩作對其他科幻作品的指涉,自然會為其本身賦予科幻性,不論這種互文指涉小到一個意象、一句引文、一處典故,還是大到模仿戲擬、框架嵌套。
韓松的《假漂亮和蒼蠅拍手》一詩,開篇便提到千葉:
“我有一個朋友,在千葉。”拍手說。
“那么她會神經(jīng)鉸接術。”假漂亮說。[5]
熟悉科幻的讀者當然知道千葉所指涉的正是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賽博朋克經(jīng)典《神經(jīng)漫游者》(Neuromancer)中的千葉。僅僅“千葉”二字,一下子就將讀者帶入了科幻的語境之中,為整首詩設定了科幻的氛圍和基調(diào)。當然,韓松的詩作也同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一樣,一端指向荒誕狂想,一端指向詭異現(xiàn)實,斷然拒絕文類的規(guī)訓。筆者曾在《科學外世界與科外幻小說》中展開過相關論述,此不詳論。
接下來讓我們再看看劉慈欣于《流浪地球》結(jié)尾處嵌套的點題之詩:
我知道已被忘卻
流浪的航程太長太長
但那一時刻要叫我一聲啊
當東方再次出現(xiàn)霞光
我知道已被忘卻
起航的時代太遠太遠
但那一時刻要叫我一聲啊
當人類又看到了藍天
我知道已被忘卻
太陽系的往事太久太久
但那一時刻要叫我一聲啊
當鮮花重新掛上枝頭[6]
此詩以沉郁頓挫、如泣如訴的語調(diào),反復吟詠出科幻版“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的心緒。然而詩中強烈的科幻感,更多源自其外部框架,亦即整篇小說的敘事。正是因為小說的科幻設定,詩中霞光、藍天、枝頭鮮花這些日常生活的普通意象,才變成了最令人動容的科幻意象,這首詩本身才變成了毋庸置疑的科幻書寫。
在劉慈欣探及詩歌藝術的短篇科幻小說《詩云》中,有個更為極端的例子:
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唉[7]63
如果單獨來看,這首“五言絕句”不知所云,無異于夢中囈語。然而放到其出現(xiàn)的語境之中,卻不同凡響、大有深意。在小說的敘事中,來自神級文明的宇宙藝術收集者 “李白”意欲寫出超越李白的詩,卻煞費苦心而不得,于是以技術之神的偏執(zhí)走了“另一條路”,即以窮舉方式“寫”出所有可能的五言、七言詩。用來儲存最終巨量作品的,是幾乎以全太陽系物質(zhì)制成的“詩云”。上文所引“五言絕句”便是“李白”的神級量子計算機“寫”出的第一首“詩”。而故事中的伊依對其做了磅礴、哀婉、最富詩意的解讀:“前三行和第四行的前四個字都是表達生命對宏偉宇宙的驚嘆;最后一個字是詩眼,是詩人在領略了宇宙之浩渺后,對生命在無限時空中的渺小發(fā)出的一聲無奈的嘆息。”[7]63在這個外層敘事框架的科幻語境下,這首“啊唉五絕”儼然化作科幻第一詩,展現(xiàn)出技術與藝術的交錯纏繞,引發(fā)了讀者的雙重哲思。
源自外部的互文因素與內(nèi)在的認知陌生化以及更普泛意義上的“相關或相似”原則,當然屬于三個不同的層面,因此既非相互對等,也不彼此矛盾,亦可共同作用,生成科幻詩的科幻性。
五 文類悖論
行文至此,不畏自唱反調(diào)。筆者素來反對侈論某一文類的本質(zhì),抑或不同文類之間的界線。文類本就是虛構(gòu)的建制[2]51,“何為科幻詩”這個問題與“何為文學”一樣,是無解的。這倒不妨礙我們談論和賞析科幻詩,因為界定何為科幻詩與品評何為好科幻詩,是兩碼事。當然,即便在這個表述中,不論“好”“科幻”還是“詩”,也都是要打引號的。
由此筆者提出如下10條觀點,是以作為對科幻詩這一文類的悖論式宣言。(一)科幻詩是詩;詩是無法精確定義的。(二)科幻詩是科幻;科幻是無法精確定義的。(三)科幻詩是無法精確定義的,這并不妨礙談論、賞析、研究和評價科幻詩。(四)科幻詩的評價標準與詩的評價標準無異,雖然并不存在所謂“詩的評價標準”。(五)科幻詩的科幻性可以從不同層面加以考察,如泛科幻性、內(nèi)科幻性、互科幻性,及其他。(六)科幻詩與現(xiàn)實世界的關系是相異、錯列、類比。不論泛科幻性的“異于現(xiàn)狀”、內(nèi)科幻性的“認知陌生化”,還是互科幻性的“文本指涉文本”,都否定詩作對現(xiàn)實世界的直接指涉或模仿。(七)科幻詩可以抒情、敘事、審美、思考、反諷、戲仿,等等。科幻詩當然也可經(jīng)由類比與現(xiàn)實世界發(fā)生聯(lián)系,或以文學述行(performative)對現(xiàn)實世界產(chǎn)生影響。(八)種種后/非人類所生產(chǎn)或參與生產(chǎn)的詩,可能但不必然具有科幻性。其具體詩作是否具有科幻性,可參照第五條。(九)科幻詩拒斥意圖謬見(intentional fallacy)。詩作科幻與否,與詩的寫作者/生產(chǎn)方式無關,與讀者對科幻文本的感知和界定有關。(十)現(xiàn)階段,科幻詩的預設讀者是地球人類。那么在或近或遠的未來,科幻詩也將拒斥感受謬見(affective fallacy)。
小冰、古戈爾·權(quán)斯萊特(Google Translate)等“詩人”“譯者”已經(jīng)出版了自己的詩集、譯詩集。陳楸帆2.0也與陳楸帆1.0聯(lián)“手”合“謀”,構(gòu)造出了層疊、纏繞、相互寄生的小說文本。換言之,后/非人類 “創(chuàng)作”或參與“創(chuàng)作”文學作品供人類閱讀,已成事實,而不再是科幻中描述的情境。
那么,不妨敞開心扉,面朝未來。由人類創(chuàng)作、以后/非人類為讀者的科幻詩,由后/非人類生產(chǎn)、以后/非人類為讀者的科幻詩,生產(chǎn)與接收一體化或無限分化的科幻詩,脫離了語言、脫離了編碼系統(tǒng)的科幻詩,及其他種種可能或不可能的科幻詩,將會呈現(xiàn)何種樣態(tài)?讓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簡介
郭偉,文學博士,北華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科幻文學方向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科幻文學、西方文學理論。
注釋和參考文獻
注釋
①本詩由劉慈欣編寫的“電子詩人”軟件生成,生成時間2020年6月5日21時29分21秒,所生成的文本經(jīng)筆者微調(diào)。
②本詩出自郭偉、郭弈茗著《此系集》,擬于近期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
③本文中的“互文”乃狹義用法,指文本之間明確的指涉關系。在更為廣義的結(jié)構(gòu)主義/后結(jié)構(gòu)主義用法中, “互文”乃普泛現(xiàn)象,一切“文本”都是“互文本”。
參考文獻
[1] 哈瑞·馬丁松.阿尼阿拉號[M].萬之,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 郭偉.解構(gòu)批評探秘[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
[3] 劉慈欣.三體Ⅲ[M].重慶:重慶出版社,2010.
[4] Darko Suvin. 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M].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
[5] 韓松.假漂亮和蒼蠅拍手[M]//韓松.假漂亮和蒼蠅拍手.南京: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
[6] 劉慈欣.流浪地球[M]//劉慈欣.帶上她的眼睛——劉慈欣科幻短篇小說集Ⅰ.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 2015.
[7] 劉慈欣.詩云[M]//劉慈欣.夢之海——劉慈欣科幻短篇小說集Ⅱ.成都: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2015.
本文轉(zhuǎn)載自《科普創(chuàng)作》202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