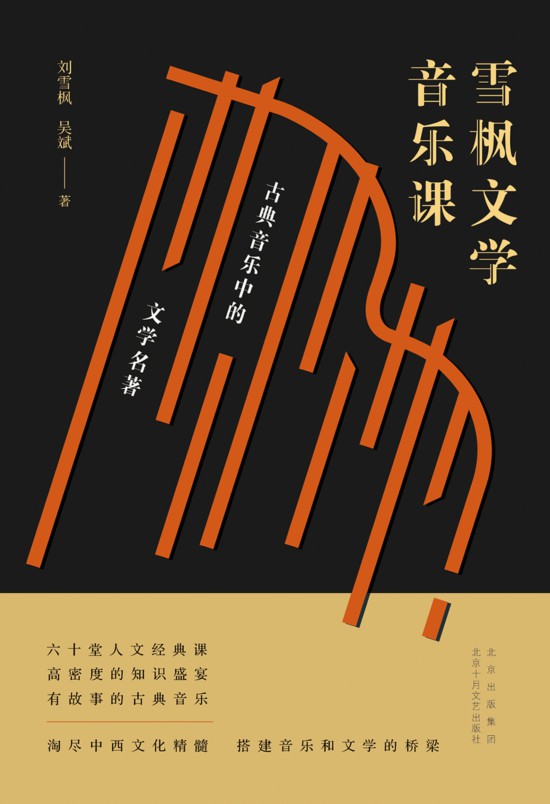《雪楓文學(xué)音樂(lè)課》:文學(xué)與古典音樂(lè)的交互結(jié)合
音樂(lè)藝術(shù)與文學(xué)、哲學(xué)、繪畫常常有非常緊密的關(guān)聯(lián),音樂(lè)家們熱衷于改編莎士比亞、《浮士德》,而很多文學(xué)作品也是從音樂(lè)中汲取靈感。只要你對(duì)文學(xué)故事感興趣,就會(huì)對(duì)同樣內(nèi)容的古典音樂(lè)充滿期待和好奇。無(wú)數(shù)改編自文學(xué)的歌劇、交響曲、交響詩(shī)、藝術(shù)歌曲背后有怎樣的故事?
最近出版的《雪楓文學(xué)音樂(lè)課:古典音樂(lè)中的文學(xué)名著》一書就選擇了較有代表性的多部中外文學(xué)經(jīng)典,從西方經(jīng)典戲劇、小說(shuō),到中國(guó)古典詩(shī)詞曲賦,并對(duì)改編自以上文學(xué)經(jīng)典的“有故事的音樂(lè)”進(jìn)行闡明。
劉雪楓是“音樂(lè)之友”創(chuàng)始人,音樂(lè)評(píng)論家,唱片收藏鑒賞家,文化學(xué)者。畢業(yè)于北京大學(xué)歷史學(xué)系中國(guó)史專業(yè),師從周一良、田余慶、祝總斌。曾任《愛(ài)樂(lè)》、《留聲機(jī)》中文版、《交響世界》主編及“京師愛(ài)樂(lè)叢書”主編。著有《貼近浪漫時(shí)代》《日出時(shí)讓悲傷終結(jié)》《交響樂(lè)欣賞十八講》等。
近日,“文學(xué)與音樂(lè)的天作之合——《雪楓文學(xué)音樂(lè)課:古典音樂(lè)中的文學(xué)名著》新書發(fā)布會(huì)”在北京舉行。作家歐陽(yáng)江河、格非,音樂(lè)家李南、欒峰,以及作者劉雪楓與各界讀者分享了《雪楓文學(xué)音樂(lè)課:古典音樂(lè)中的文學(xué)名著》的閱讀感受,并就“文學(xué)與音樂(lè)的天作之合”這一話題進(jìn)行了討論。

劉雪楓
做著文學(xué)夢(mèng)的音樂(lè)評(píng)論家
在劉雪楓看來(lái),這本書是圓了他小時(shí)候的一個(gè)夢(mèng)。他的父親是1950年代的音樂(lè)家,這讓劉雪楓從小就受到了很多音樂(lè)方面的熏陶,但是他真正的興趣還是在文史上,這和在小時(shí)候讀了很多書有關(guān)。“在‘文革’期間,圖書館大量的書都是禁書,外面人借不到。我小時(shí)候害怕吃藥,害怕打針,我父親就會(huì)誘惑我說(shuō)如果今天把這個(gè)針打了或者把藥吃了,下午就帶我去圖書館書庫(kù)。他有鑰匙,是一個(gè)管事的,可以讓我去挑一本書。到了今天,這是我對(duì)那個(gè)年代最美好的回憶。”劉雪楓談道。
劉雪楓畢業(yè)于北京大學(xué)歷史學(xué)系中國(guó)史專業(yè),但他目前更廣為人知的身份是音樂(lè)評(píng)論家。在他看來(lái),“音樂(lè)評(píng)論家”是一個(gè)嘩眾取寵的叫法,他作為“評(píng)論家”還是不夠格的,“只是長(zhǎng)期聽(tīng)音樂(lè),聽(tīng)完音樂(lè)有一些感想,正趕上有報(bào)紙、雜志約稿,從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jì)頭十年,年年開(kāi)各種專欄,最多的時(shí)候同時(shí)給七八個(gè)專欄寫稿,所以一發(fā)不可收拾,現(xiàn)在變成了音樂(lè)成為我的主業(yè)。但是文學(xué)夢(mèng)一直在做,所以在2017年年底有了這么一個(gè)想法,把跟中外文學(xué)名著相關(guān)的音樂(lè)作品做了一個(gè)梳理,做了一個(gè)比較詳細(xì)的比對(duì),從改編、戲劇化、音樂(lè)各個(gè)方面,寫出來(lái)這么一本算不上有什么學(xué)術(shù)價(jià)值,但是至少我覺(jué)得把它作為一個(gè)通俗的文學(xué)和音樂(lè)的入門讀物,還是可以做一個(gè)參考的。”
李南回顧了中國(guó)音樂(lè)雜志的發(fā)展:“在九十年代以前,我們國(guó)家除了《人民音樂(lè)》這樣的雜志以外,可能更多的是為主流音樂(lè),為國(guó)家的民族音樂(lè)、歌曲服務(wù)的,很少有人對(duì)中國(guó)古典音樂(lè)、西方古典音樂(lè)做一些評(píng)論、講解、引導(dǎo)。1992年的《愛(ài)樂(lè)》雜志就是在這種情境下應(yīng)運(yùn)而生的,這個(gè)雜志出來(lái)以后才涌現(xiàn)出一批真正對(duì)古典音樂(lè)評(píng)論的評(píng)論家。《愛(ài)樂(lè)》雜志有了以后,我和三聯(lián)的朱偉、劉雪楓一起寫各種各樣的文章,后來(lái)劉雪楓替朱偉當(dāng)了《愛(ài)樂(lè)》雜志的主編,我一直是編委。”
李南也表達(dá)了將文學(xué)和音樂(lè)勾連起來(lái)寫作文章的困難:“《愛(ài)樂(lè)》雜志剛成立的時(shí)候,我也曾經(jīng)嘗試過(guò)寫一些文章,其實(shí)挺撓頭的。比如柴可夫斯基有一首《曼弗雷德交響曲》是非常好聽(tīng)的一個(gè)交響曲,我寫樂(lè)評(píng)時(shí)覺(jué)得很困難,作曲家將拜倫的詩(shī)寫到了《曼弗雷德交響曲》中,但是又不是完全按照拜倫的意思來(lái)表達(dá)自己的意圖和感情的。”
格非認(rèn)為,劉雪楓是一個(gè)比較健康的音樂(lè)愛(ài)好者。他接觸的很多像他一樣喜歡音樂(lè)、對(duì)音樂(lè)迷狂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病態(tài)。“有的人專聽(tīng)巴洛克時(shí)期的,喜歡斯特拉文斯基的就排斥普羅科菲耶夫,非常復(fù)雜。你要問(wèn)他對(duì)一個(gè)問(wèn)題的看法,他想半天一個(gè)字不說(shuō),故作神秘,這樣的人非常多。但是只要問(wèn)劉雪楓,他總會(huì)給出直接的判斷,他要么說(shuō)很好,要么說(shuō)很爛,要么說(shuō)沒(méi)什么價(jià)值,他會(huì)直接把觀點(diǎn)說(shuō)出來(lái)。他如果沒(méi)有對(duì)音樂(lè)史、對(duì)文學(xué)史、對(duì)某些東西廣博的知識(shí)和精神的研究,要隨隨便便做一個(gè)判斷是非常難的,這是我喜歡雪楓的一點(diǎn)。”
“體系化”的現(xiàn)代音樂(lè)、文學(xué)、哲學(xué)在同一時(shí)期產(chǎn)生
歐陽(yáng)江河也一直關(guān)注音樂(lè)與文學(xué),他說(shuō):“我寫了好幾首跟音樂(lè)有關(guān)的詩(shī)。從杜普瑞到肖邦,到肖斯塔科維奇,尤其是舒伯特,還有皮亞佐拉,我都有涉及。我相信凡是熱愛(ài)古典音樂(lè)的人一定天然的帶有一種文學(xué)的基本的敏感,基本的素養(yǎng)。但是喜歡文學(xué)的人,對(duì)古典音樂(lè)還有點(diǎn)素養(yǎng),就不是天然的。但是無(wú)論如何,關(guān)于文學(xué)和音樂(lè)、文學(xué)和美術(shù)的關(guān)系,我一直認(rèn)為,如果你只搞文學(xué),完全不接觸古典音樂(lè),完全不接觸當(dāng)代美術(shù)的人,都有點(diǎn)土。” 歐陽(yáng)江河說(shuō)道,“劉雪楓把中國(guó)古典音樂(lè),不光是演奏,而且對(duì)它的感受、對(duì)它的敘述,包括作品的理解,包括版本學(xué),他把這些部分都引進(jìn)來(lái)。”
歐陽(yáng)江河也認(rèn)為:“蘇童曾說(shuō)格非的第一部跟音樂(lè)有關(guān)的《隱身衣》是一個(gè)杰作,而格非前年出版的中篇《月落荒寺》的寫作由頭也是他和劉雪楓去參加了一次音樂(lè)會(huì),這個(gè)小說(shuō)就是從那場(chǎng)音樂(lè)會(huì)開(kāi)始說(shuō)的。格非聽(tīng)完德彪西的一首曲子以后,把其中的感受擴(kuò)展為特別偉大的文學(xué)建構(gòu),我認(rèn)為《月落荒寺》有豐富的文體意識(shí)、文學(xué)意識(shí)的深度自覺(jué)的建構(gòu),很洋氣也很細(xì)膩。”
歐陽(yáng)江河認(rèn)為,文學(xué)性也是決定一位音樂(lè)家的造詣的重要考量標(biāo)準(zhǔn):“我很喜歡德國(guó)浪漫主義作曲家瓦格納,瓦格納除了音樂(lè)上的偉大以外,他的文學(xué)也太偉大了,他能把德語(yǔ)文學(xué),而且神話意義上的文學(xué),等于是原文學(xué),轉(zhuǎn)化為音樂(lè)語(yǔ)言,甚至是音樂(lè)文明。這個(gè)貝多芬都做不到,巴赫也做不到,盡管巴赫是西方音樂(lè)文明、西方知識(shí)的奠基人,但是瓦格納最后一百米達(dá)到的高度,迄今無(wú)人超越。”
格非說(shuō),自己身邊的很多人是拒絕聽(tīng)古典音樂(lè)的,因?yàn)樗麄冋J(rèn)為古典音樂(lè)是體系化的東西,“所以古典音樂(lè)怎么從自然的唱歌變成一個(gè)體系化的東西?怎么變成一門藝術(shù)?這個(gè)體系化的巨大結(jié)構(gòu)的東西是怎么誕生的?我想體系化的音樂(lè)可能是文藝復(fù)興到巴洛克時(shí)期出現(xiàn)。可是我看雪楓這本書的時(shí)候腦子里想到一個(gè)問(wèn)題,小說(shuō)不也是一個(gè)體系化的東西嗎?如果我們把今天的小說(shuō)跟古代的民間故事相比的話,或者跟荷馬史詩(shī)相比,現(xiàn)代小說(shuō)當(dāng)然是一個(gè)體系化的東西。”
“所以從這個(gè)意義上來(lái)講,為什么那么多人改編莎士比亞和《浮士德》?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莎士比亞出現(xiàn)的那個(gè)年代,也是小說(shuō)家塞萬(wàn)提斯出現(xiàn)的年代,而塞萬(wàn)提斯的出現(xiàn)就代表著現(xiàn)代小說(shuō)的誕生,同時(shí)也是斯賓諾莎現(xiàn)代哲學(xué)的誕生。幾乎在同一時(shí)期世界發(fā)生巨大變革。這當(dāng)中,不論是現(xiàn)代音樂(lè)、文學(xué),或者說(shuō)哲學(xué),都在一個(gè)體系化的,一個(gè)完全不同于古代社會(huì)的層面上展開(kāi)。”
一本寫給音樂(lè)愛(ài)好者的書
在李南看來(lái),把古典音樂(lè)功能化正在成為當(dāng)下的一個(gè)趨勢(shì)。“有過(guò)統(tǒng)計(jì),4億兒童,2億生活在城市,2億兒童里面85%以上的家長(zhǎng)會(huì)讓孩子到五六歲、六七歲的時(shí)候?qū)W一門課外技能,大部分有條件的家長(zhǎng)會(huì)讓孩子學(xué)音樂(lè),其次才是美術(shù)、舞蹈、體育等等,音樂(lè)是首選。所以它現(xiàn)在變成一種社會(huì)的需求,年輕人喜歡,但很少能聽(tīng)到年輕人說(shuō)我來(lái)聽(tīng)交響樂(lè)是想知道它的文學(xué)背景、知道它的歷史背景、知道它怎么樣怎么樣,有的人是獵奇來(lái)的,有的人是聽(tīng)說(shuō)這個(gè)好聽(tīng)。”
李南認(rèn)為,劉雪楓這本書肯定不是寫給從事音樂(lè)的人的,“而且在相當(dāng)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內(nèi),包括現(xiàn)在,真正搞音樂(lè)的人反而會(huì)反感這個(gè)東西,還會(huì)抵觸這個(gè)東西。因?yàn)楦阋魳?lè)的人認(rèn)為音樂(lè)就是音樂(lè),哪有那么多的背景,這都是矯情。” 所以劉雪楓這本書是寫給音樂(lè)愛(ài)好者的,是寫給音樂(lè)愛(ài)好者里面想去探究音樂(lè)更深層次東西的人的。
“我覺(jué)得這是一個(gè)挺費(fèi)力的事,現(xiàn)在這個(gè)社會(huì),有這樣的人做這個(gè)事真的不容易,這種學(xué)問(wèn)沒(méi)人做了。包括我們了解的,像《留聲機(jī)》雜志,國(guó)外一些著名音樂(lè)評(píng)論雜志,現(xiàn)在都已經(jīng)開(kāi)始往很市場(chǎng)化的、很前衛(wèi)的、很迎合的、很娛樂(lè)化的方向發(fā)展。現(xiàn)在突然出來(lái)這么一個(gè)人,而且在這個(gè)方面去寫這樣的書,大家看你都覺(jué)得奇怪。所以劉雪楓現(xiàn)在還在做這個(gè)事,讓我很尊敬。”李南說(shuō)道。
“用音樂(lè)寫文學(xué)容易,只要你這個(gè)作曲家有本事,只要作曲家有技巧,給你什么題材,就能寫出來(lái)。但是用文學(xué)說(shuō)音樂(lè)太難了,特別是載道的文學(xué),如果無(wú)標(biāo)題的,說(shuō)的天花亂墜、怎么說(shuō)都無(wú)所謂,但是載道文學(xué)更難,這是需要有功夫的。只有你對(duì)音樂(lè)的熟悉和對(duì)文學(xué)的熟悉要到相當(dāng)?shù)某潭龋拍馨堰@件事做到,否則的話你根本做不到。”李南也說(shu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