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布克國際文學(xué)獎獲獎作品《月亮的女人》: 從一個房間開始,以一個世界結(jié)束

阿曼女作家朱赫·哈爾西獲2019年布克國際文學(xué)獎
阿曼女作家朱赫·哈爾西(Jokha Alarthi,1978-)憑其作品《月亮的女人》(此處為阿拉伯語書名直譯。其英譯本書名為Celestial Bodies,譯者為Marilyn Booth)獲2019年布克國際文學(xué)獎。這是阿拉伯語作品首次榮獲該獎,一時間文學(xué)界的目光聚焦到長期處于世界舞臺邊緣的海灣小國阿曼,悠久的歷史積淀和溫和的文化氛圍使其在阿拉伯國家中獨樹一幟。
《月亮的女人》的阿拉伯語原版早在2010年便已出版,小說通過阿曼小村莊“阿瓦費”一家三姐妹的家庭關(guān)系、愛情故事和人生經(jīng)歷,反映了阿曼社會從殖民時代結(jié)束后至今百余年來的演變過程。描繪了被歷史洪流裹挾前行的眾生群像。《紐約時報》評論員認(rèn)為,《月亮的女人》本身是一座寶庫,是一團由盤根錯節(jié)的家族關(guān)系和家族發(fā)展軌跡構(gòu)成的混沌,它建立在秘密的引力之上。朱赫本人在采訪中承認(rèn)了對“代際小說”的興趣,她有意塑造眾多人物,從不同視角敘述事件以反映紛繁龐雜的現(xiàn)實,用一個個孤立的聲音拼湊出一段完整的歷史,這是一件“有趣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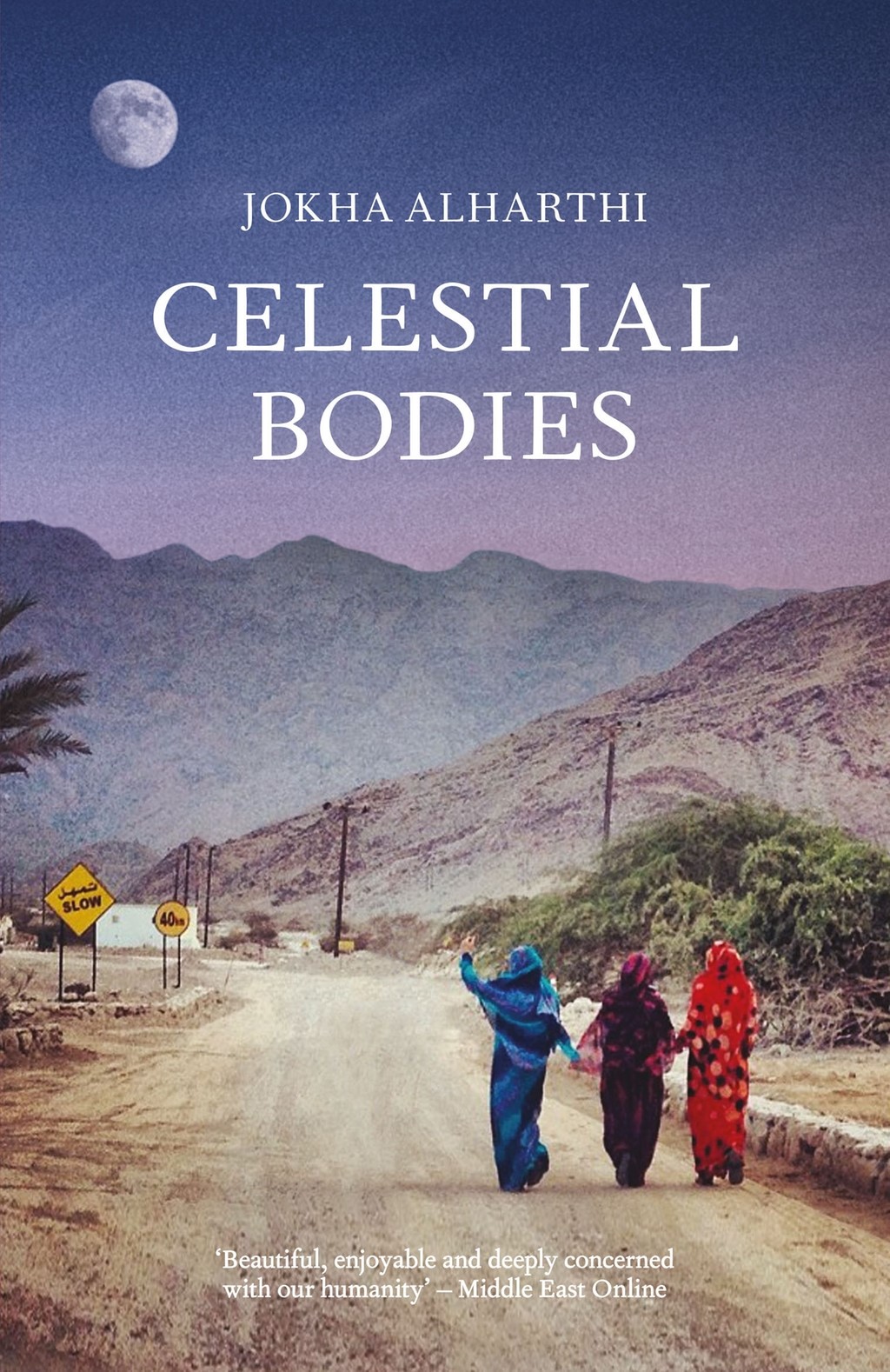
《月亮的女人》英譯版
舊時代的挽歌
“當(dāng)桑戈爾出生在肯尼亞的一個小村莊時,賽義德·本·蘇爾坦 正與英國簽署第二項禁奴貿(mào)易條約。在1845年達成的協(xié)議中,賽義德同意終止其在非洲和亞洲統(tǒng)治地區(qū)的奴隸貿(mào)易,英國海軍船隊有權(quán)在阿曼領(lǐng)海以及整個阿拉伯灣和印度洋截停阿曼船只進行搜查,并扣押和沒收任何違反協(xié)議的船只。”
小說中最早的故事始于19世紀(jì)末奴隸制下的阿曼。女奴扎莉法的爺爺、出生于肯尼亞的桑戈爾在販奴船只上死里逃生的故事讀來觸目驚心,但這僅是奴隸制暴露出的冰山一角。扎莉法被富甲一方的阿曼商人蘇萊曼買下時的價格甚至不及半袋大米,而她卻對這個“打開了她的身體和心靈”的男人癡情了一生。他給予了她公開的情婦地位,讓她不必像其他奴隸一樣過于操勞,卻也曾因一次“大爭吵”而將她強行嫁給另一個奴隸,仿佛她是一株可以隨時被嫁接到任何植物上的枝干。這種畸形的愛情在今天看來不可思議,卻是奴隸制社會中的必然產(chǎn)物,甚至在當(dāng)時還是令其他奴隸羨慕的處境。畢竟與扎莉法相比,她母親安卡布苔16歲便被軟禁侵犯、獨自生產(chǎn)的經(jīng)歷更為悲慘可怕。
然而,無論多么“浪漫”的主奴愛情故事,終究掩蓋不住奴隸制嗜血的本質(zhì),更比不上人性對尊嚴(yán)的渴望。時代的腳步轟隆而過,靠奴隸貿(mào)易發(fā)家的蘇萊曼垂垂老矣,當(dāng)年老病弱的他躺在病床上,叫囂著把扎莉法的兒子桑吉爾鎖起來時,桑吉爾正攜家?guī)Э谶h(yuǎn)走高飛。一切都宛如一個可愛的隱喻,舊時代再也無力阻擋懷揣夢想的新一輩奔向遠(yuǎn)方和自由的步伐。
評審團主席、英國歷史學(xué)家貝坦尼·休斯說,這部小說展示了“精巧的藝術(shù)和我們共同歷史中令人不安的方面”,同時又用巧妙的風(fēng)格“消除了關(guān)于種族、奴隸制和性別的陳詞濫調(diào)”。批評奴隸制和殖民主義的小說不在少數(shù),然而《月亮的女人》在記敘歷史的同時,并沒有將歷史生搬硬套,或者政治正確地塞進小說中,而是賦予了它人性的因素,為我們展現(xiàn)了普通人所面臨的艱難抉擇。當(dāng)親情、愛情與普世價值觀面臨沖突時,又有誰能凜然評判對錯?作為一名有使命感、正義感的作家,朱赫對歷史中常被忽略的邊緣人抱有深深的關(guān)切,她曾說:“傳統(tǒng)媒體和教科書出于各種原因——我認(rèn)為站不住腳的原因,企圖忽略阿曼非常重要的歷史時期。但作家意識到,對睜開眼睛看歷史的恐懼并不能讓人產(chǎn)生安全感。因此,他敢于點亮手中的燈,在一個又一個長廊里漫步,它的光亮將永存,而另一盞燈也可能以不同的方式照亮歷史的黑暗。”
要消解宏大敘事,不代表全盤拋棄宏大敘事,作家反對的是以宏大為代表的中心與邊緣的二元對立,警惕個體被群體、微小被宏大綁架的危險。所謂的家國、命運、主流、歷史,一定要融入到小人物的生活中去談?wù)摬庞袃r值,朱赫顯然意識到了這一點,沒有讓對歷史的解說喧賓奪主地?fù)屪邞?yīng)該聚集在“人”身上的目光。
時代的更迭令人猝不及防。戰(zhàn)爭中慘敗的伊薩流亡埃及,卻仍難忘拋棄他的故土,背負(fù)著“移民者”這個稱號宛如背負(fù)沉重的命運,但他的藝術(shù)家兒子哈利德卻不解他為何眼含熱淚地吟誦阿曼革命詩人阿布·穆斯林·巴哈萊尼的詩歌,甚至對他的革新思想不屑一顧,“畢竟,誰會來買這些書呢?”伊薩的負(fù)隅頑抗在一個和平年代顯得不合時宜,所謂“老兵不死,只是慢慢凋零”。阿卜杜拉還恪守著“不能談?wù)撌澄铩钡募乙?guī),而外面的新新世界已然鋪天蓋地遍布著人們張大嘴品嘗美食的廣告,他的兒子薩利姆及其同齡人已經(jīng)可以毫無顧忌地在麥當(dāng)勞里對食物評頭論足、挑三揀四。當(dāng)蘇萊曼和“可憐人”馬尼恩還堅守著“阿瓦費是我們的家鄉(xiāng)”的信念,他們的后輩正爭先恐后地涌向五光十色的國際化大都市馬斯喀特……
朱赫的祖父是阿曼最后一批古典詩人,也是朱赫在文學(xué)上的啟蒙者。童年的朱赫在祖父的沙龍里抓住了舊時代的尾巴,并將之真實地還原在紙上。新千年帶著新的風(fēng)向和新的迷茫吞噬了一切,但它將把人們引向何方還未可知。盡管今天的阿曼人不再像以前那樣擔(dān)心堅船利炮的殖民歲月,但放眼望去,馬斯喀特的酒店旅館紛紛掛起“此處只說英語”的標(biāo)識以彰顯其高端定位,誰又能說以文化侵襲為手段的一種新型殖民主義沒有在“暖風(fēng)熏得游人醉”的氛圍中興起?居住在高樓大廈里的人們無需再擔(dān)心被一場洪水淹死,但鋼筋水泥的現(xiàn)代化城市又出現(xiàn)了新的問題。
無論好壞,昨日世界已然故去,每一個古老的國度都需背負(fù)自己厚重的歷史繼續(xù)前行。朱赫以詩意的筆觸,將百余年來的種種變化凝練而真實地通過小人物的生活呈現(xiàn)出來,為落幕的時代做了一部深情的傳記。在她筆下,新舊兩個世界的轉(zhuǎn)換有一種詩意而神奇的美感,而伴隨著這種轉(zhuǎn)變的,是老一輩人的逝去與年輕一代的崛起。也許社會變革注定在老一代對新一代的震驚與不滿中完成,每一代人在上一代眼中都是“垮掉的一代”,但也正是這些“垮掉的一代”們,讓文明和文化生生不息地向前發(fā)展,破舊立新,繼往開來。
朱赫在《月亮的女人》里采用了典型的意識流寫作手法,時間的跨度伴隨著破碎的情節(jié),一如人們飄萍般的命運。僅229頁的小說中出現(xiàn)了多達三十幾個人物,且每個人物的故事都得到了一定的述說,讓人很難分清究竟誰是主角、誰是配角。作者仿佛意圖為我們描摹一幅時代轉(zhuǎn)型中的群像,而非以單個人物作為典型,一言以蔽之地將所有人的經(jīng)歷微縮于其中。這無形中給閱讀增加了些許難度,復(fù)調(diào)性的多聲部敘事讓無數(shù)“你”、“我”和“他”交雜在一起,稍有疏忽的讀者很容易迷失在多聲部敘事的海洋中和跳躍突變的時空里。然而,正是語流的交錯和斷裂,讓讀者得以與作者的思緒、人物的命運一道翱翔空中,俯瞰阿曼乃至阿拉伯的蒼茫興衰,在位于彼岸的文化中瞥見別一番洞天。
月亮般的女人們
“沉醉在她那蝴蝶牌黑色縫紉機旁的瑪雅,同樣沉醉在愛情中。”
小說開篇與《木蘭辭》的“唧唧復(fù)唧唧”異曲同工,待字閨中的女兒心事稚嫩而美好。從書名不難看出《月亮的女人》的主體人物是一群神奇的女性,而這顯然與朱赫本人的成長經(jīng)歷有關(guān)。“我在一群女人中間長大。她們中有人強大、耐心、無私,具有奉獻精神,也有人脆弱。每個女人都有一個美麗的故事,每個故事都不相同。我看到她們在愛,在恨,在做飯,在紡織,在生兒育女……”
小說中的女性性格迥異,但她們的故事同樣迷人。在她們身上我們能看到一些朱赫本人的影子,瑪雅的沉靜、阿斯瑪?shù)暮脤W(xué)、郝萊的倔強……似乎作者將自己的靈魂分成許多部分,裝進了不同女人體內(nèi),女性的脆弱與堅強、失望與憧憬,都被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
長久以來,我們對于阿拉伯女性的想象,往往是戴著面紗頭巾、順從地坐在丈夫身后一言不發(fā)的家庭婦女。然而,朱赫通過《月亮的女人》打破了這種刻板印象,塑造了一個個堅毅勇敢的女性。“在阿曼歷史中,我們有女學(xué)者、女法學(xué)家,女戰(zhàn)士和軍隊的女領(lǐng)導(dǎo)人,還有成千上萬無聲的女人在田野、房屋、牧場和學(xué)校里用默默勞作來證明自己的存在。”當(dāng)她們與男性比肩而立,其力量感與果斷干練的勁頭不遜色分毫,甚至可以說她們對人生和家庭有著更清晰明確的掌控。
瑪雅與丈夫阿卜杜拉同樣生活在家長的控制下,但兩人的選擇截然不同。盡管母親薩里瑪?shù)墓芙滔喈?dāng)嚴(yán)格,瑪雅卻始終用自己“內(nèi)在的世界”對抗“外在的世界”,努力逃離母親的掌控規(guī)劃自己的人生。而阿卜杜拉雖是一位事業(yè)有成的富商,但在瑪雅眼中他永遠(yuǎn)是“用成人的大衣偽裝自己”的小男孩,視獲得父親的認(rèn)可為畢生使命。同樣的,在阿斯瑪與哈立德的婚姻中,阿斯瑪看似是較為弱勢的一方,但與哈立德那時而熱情如火時而寂靜如冰的性格相比,她更善于掌控自己和他人的情緒,并運用這種能力擺脫了丈夫?qū)λ目刂疲安辉僭谡煞虻奶祗w內(nèi)運轉(zhuǎn)”,而成為獨一無二的“天體”。
小說中最值得一提的女子納吉婭,更是展示了獨屬于女性的風(fēng)采與魅力。成長在貝都因部落的納吉婭因其美麗的面龐而被稱為“月亮”,這動人的名字包含著作者對她的偏愛與欣賞。“月亮”有著桀驁不馴的性格和永不言棄的強大意志。她不滿學(xué)堂的種種束縛而早早退學(xué),卻憑借著強大的生意頭腦發(fā)家致富。和她無能的父親、病弱的弟弟、乃至逃避扭捏的情夫阿贊恩相比,納吉婭從始至終的率性而為、英姿俠氣更讓人欽佩。她在追求愛情時比任何人都敢于直視自己的內(nèi)心,卻又不屑于成為愛情的奴仆。“月亮才不會接受他人發(fā)號施令,我不是為了侍奉男人、聽命于男人而被創(chuàng)造出來的……他會偷走我身份的合法性,切斷我和弟弟、女伴們的聯(lián)系,他有時說不要出門,有時規(guī)定不要穿這件衣服,有時讓你過來,有時讓你走開……不不不,阿贊恩將會是我的,但我不屬于他。”鏗鏘有力的話語無異于女性的獨立宣言,畢竟一個女人可能是某人的妻子、某人的母親,但絕不是某人的奴隸,而更重要的是,她永遠(yuǎn)應(yīng)當(dāng)忠于自己。這樣的女子熱情奔放、勇敢倔強,有自己的人生哲學(xué),為了達到目的會想方設(shè)法,果敢堅決。精明、現(xiàn)實而強干的性格讓她如同風(fēng)一般,南來北往卻無跡可尋。然而,朱赫給了她一個撲朔迷離的結(jié)局,貝都因的大漠黃沙失去了光芒四射的月亮。這也證明了女性追求自由的道路并非一帆風(fēng)順,她面對的力量不僅來自于家庭或個體,甚至來自于整個社會。無論如何,“月亮”并非毫無瑕疵的滿月,但她不羈灑脫、追求自我的勇氣將照耀一個又一個女性在成見、打壓的荊棘中無畏前行。
隨著信息的流通和現(xiàn)代化的發(fā)展,越來越多女性被現(xiàn)實逐出對烏托邦式婚姻樂園的想象。當(dāng)伊本·哈茲米在《鴿子項圈》中暢想的那種靈肉合一的愛情神話被打破,女性真正的庇護所究竟在何方?如同伍爾夫在《達洛維太太》里借克拉麗莎之口說出,“人都有一種尊嚴(yán)、一種獨處的愿望,就算在夫妻之間也存在一道鴻溝。”朱赫在《月亮的女人》中隱約地指出了一條道路,大概“復(fù)樂園”就孕育在每個女性強大而獨立的心靈中。你有你的天體,我有我的軌跡,沒有人必須繞著他人運轉(zhuǎn),但我們可以偶然地相交,這便是最好的關(guān)系。
從房間到世界
“世界變得昏暗,我聽到汽車發(fā)動駛遠(yuǎn)的聲音。倫敦坐在方向盤后,穆罕默德在她懷中。我突然覺得他像一條魚。我走向洶涌的大海,直至海浪淹沒胸口。當(dāng)我張開雙臂時,穆罕默德像魚一樣溜走了。我衣衫未濕地回到了陸地上。”
小說在壓抑而超現(xiàn)實的場景中走向尾聲,這樣的結(jié)尾讓人意猶未盡。浩大天地中還有許多故事沒有說完,不知何日能再相會,有些故事在作者心里,而更多的則在讀者心里。朱赫說,“事實上我沒有完成這本小說,我放棄了,因為寫作對我來說是一項無法完成的工程……在某一刻放棄成為了拯救作品的選擇,它讓小說從我的場域走向讀者”。正是因為作者的故意放棄,讀者才無法放棄對作品的猜測和解讀,而這何嘗不是小說生命的另一種延續(xù),也許比一部小說更讓人激動的是一部沒有寫完的小說,它包含著人世間的萬千可能性。
小說以房間里的瑪雅沉醉在愛情與縫紉中開頭,以阿卜杜拉將兒子拋棄在海中結(jié)尾,夾在其間的是阿曼的百年浮沉。因此,貝坦尼·休斯評價道,《月亮的女人》是一本“從一個房間開始,以一個世界結(jié)束的作品”。
而朱赫寫作《月亮的女人》的經(jīng)歷又何嘗不是“從房間到世界”。“二十多歲時的我是一名外籍學(xué)生,用一種我不喜歡的語言(英語)攻讀博士學(xué)位,也是一個孤獨女孩的母親。寫作拯救了我。我?guī)е愢l(xiāng)人的臉龐、異鄉(xiāng)人的話語行走在街頭,看到成千上萬的故事與我同行,我邀請它們與我一起在霜寒中共飲咖啡。圣誕彩燈在窗外搖曳,積雪覆蓋屋檐,喚起了我關(guān)于沙漠和烈士祖先靈魂的記憶……鄰居邀請我去她明亮的屋子里喝下午茶,我腦子里卻想著姑媽那刷了深色墻漆、壁龕上擺滿古董器皿的房間。在寫作中,我愛上我的角色,與我的漂泊和解。”
誕生于愛丁堡一個小房間里的《月亮的女人》,最終走向了全球億萬讀者,誕生于孤獨中的文字,最終療愈了寫作者孤獨的心。也許這就是小說的魅力所在。一本本小說猶如一個個世界,人們漫步其中,流連忘返。而透過朱赫搭建的世界,人們得以望向一直被邊緣化的海灣小國阿曼,得以傾聽邊緣人的聲音。在日益強調(diào)多元對話的時代,我們愈發(fā)意識到,再微小的國家、再微小的個體亦有其尊嚴(yán)和價值,亦有發(fā)聲的權(quán)利和必要,而再微弱的聲音,亦有“從房間到世界”的力量。
細(xì)讀小說,字里行間總是透著一絲孤獨。阿贊恩在貝都因篝火晚會的裊裊余煙中心心念念的仍是他夭折的幼子,扎莉法在熱鬧的婚禮過后感慨的是不饒人的歲月,而薩里瑪在女兒出嫁的喜慶時刻感慨自己鬧劇般的荒唐婚姻。大概每個人的人生都總有那么一些不完滿,外人看來的和睦夫妻可能同床異夢,而矯健舞娘則為病痛所累輾轉(zhuǎn)難眠。這不就是人物們褪去主角光環(huán)后最真實的樣子,不就是我們需要應(yīng)對的真實生活嗎?種種瑣事,百味人生,但不為瑣事糾結(jié)困擾的人,也無法為瑣事開懷大笑。我們是否能與朱赫一道,與過往、孤獨和流浪的自我和好,讓精神回到家園。
寫作是一個由外向內(nèi)、再由內(nèi)向外的過程。阿斯瑪告訴我們,世界上沒有兩個靈魂與肉體緊密貼合的人。阿贊恩說,生靈即使在互相聯(lián)系時也是分離的。阿卜杜拉安慰離婚的女兒倫敦,愛情不再了但你還是一個成功的醫(yī)生。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但為了靈魂的自由,我們必須保有一份孤獨,讓它在自己的宇宙中有徜徉的空間。而孤獨并不意味著孤立無援,心靈之間的共鳴與回音仍可響徹天際。只要在自己的房間中深深地挖洞,終有一天我們體內(nèi)的聲音會流淌過長長的通道,與其他的聲音匯合。到那時,我們將一同聆聽這多聲部的靈魂奏鳴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