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珂:論沂蒙文學的“當代性” ——兼及沂蒙精神與沂蒙文學互源、互塑關系考察
論文概要:沂蒙精神與沂蒙文學的互源、互塑關系可概括為“三個互為”:互為表里、互為生發(fā)、互為塑造。習總書記有關沂蒙精神特質(“水乳交融,生死與共”)的科學界定,山東省委書記劉家義針對沂蒙精神所做出的詳細闡釋,在主題實踐向度和方法論上,為當代沂蒙文學特別是其中的革命歷史題材寫作指明了發(fā)展方向。但沂蒙文學對沂蒙精神的表達,并非空喊口號或直接作意識形態(tài)圖解,而是以語言(美學形式)與形象(審美想象)打動人,感染人。沂蒙精神與沂蒙文學互源、互塑的歷史突出地體現(xiàn)為對“當代性”的實踐。然而,由于作家們對其理解不同,從而在歷史演進中呈現(xiàn)了不同風貌。在“十七年”時期,其互源、互塑模式整齊劃一,影響甚大,但也不乏弊端;在新時期,奉獻與覺醒作為沂蒙文學的兩大主題,使得沂蒙文學、沂蒙精神深入人心,但又因藝術創(chuàng)新力困乏而難有持續(xù)的發(fā)展力;九十年代以來,其互源與互塑止步不前,理性有余而靈性不足,創(chuàng)新亦相當乏力;新世紀以來,沂蒙文學以“臨沂詩人群”為先鋒,以趙德發(fā)、夏立君、江非、高軍等幾位實力作家為骨干,在認識論和方法論緯度上,為二者互源、互塑關系開啟了新路徑、新可能。
關鍵詞:沂蒙文學 沂蒙精神 “當代性” 互源
何謂沂蒙精神?有關這方面的界定、生成演變、價值與意義的闡釋,當以習總書記的闡述最具權威性、綱領性、指導性:“山東是革命老區(qū),有著光榮傳統(tǒng),水乳交融,生死與共鑄就的沂蒙精神,對我們今天抓黨的建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示作用……沂蒙精神與延安精神、井岡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樣,是黨和國家的寶貴精神財富,要不斷結合新的時代條件發(fā)揚光大。”[1]在此,他不但將沂蒙精神的特質高度概括為“水乳交融,生死與共”,還將之上升為黨和國家精神文明建設高度并予以診視,并特別強調“要不斷結合新的時代條件發(fā)揚光大”。對近,山東省委書記劉家義撰文指出,“水乳交融,生死與共”的沂蒙精神“深刻揭示了沂蒙精神的科學內涵”,“充分揭示了沂蒙精神形成的深層原因”,“生動詮釋了黨和人民生死相依的血肉聯(lián)系”,“深入回答了‘我是誰、為了誰、依靠誰’的永恒課題”[2]。從習近平的講話到劉家義的撰文闡釋,這就分別從國家到地方(省)層面完成了對“沂蒙精神”特質、價值及意義的科學界定與最新闡釋。更為關鍵的是,關于如何踐行沂蒙精神,無論習總書記強調“要不斷結合新的時代條件發(fā)揚光大”,還是劉家義號召“用心講好沂蒙精神的感人故事”以及“傾力打造沂蒙精神的文化品牌”,在筆者看來,都無不強調要以主體觀念、發(fā)展眼光、創(chuàng)造性思維凸顯其當代品質。毫無疑問,這種界定或闡釋在方法論和主題實踐向度上為山東文藝特別是沂蒙文藝指明了發(fā)展方向,而作為沂蒙文藝重要組成部分的沂蒙文學當然更當率先垂范。
何謂沂蒙和沂蒙文學?一直以來,專家學者們對其外延與內涵的界定或闡釋并不一致。一種是側重從地理或人文地理學上的界定,比如:“在地圖上,山東至今沒有沂蒙山這樣一座山,說‘一群山’也似乎不完全確切,開始有‘南沂蒙’、‘北沂蒙’之分,指從沂水到蒙陰一帶的一片山區(qū);進而可以說指整個魯中地區(qū)。再后魯中、濱海、魯南合并為魯中南地區(qū),‘魯中南地區(qū)’,看來可以說是‘沂蒙’的廣義概念。建國后,魯中南地區(qū)撤銷,不管專區(qū)、地區(qū)和城市怎樣變化,也不管有的縣市單立(如萊蕪、日照),或有的縣市劃歸了鄰近地市(如沂源),仍大體以老魯中南地區(qū)為范圍(中心又是臨沂市地區(qū)),還是較為合情合理的。”[3]一種是打破地理邊界而側重從文化角度所做出的界定,比如:“沂蒙文化的區(qū)域,以今天的行政區(qū)劃來看,包括今臨沂市、日照市全境及沂源、臨朐、新泰、諸城、驛城、贛榆、東海、新沂、邳縣等縣區(qū),即魯東南地區(qū)和江蘇部分地區(qū),史稱‘齊魯鎖鑰’,是南北地域文化互漸、交融的結合部。”[4]但不管哪種界定,從地理或行政區(qū)劃上來看,如今的臨沂、日照全境或曰以汶河、沂河、沭河、蒙山等核心地理范疇的延展區(qū)域,應是沂蒙文化生成與演進最為核心、最為本源的物理空間。依托這樣的地理空間或文化空間,經(jīng)由漫長時間沉淀或凝聚所生成的帶有區(qū)域共同體趨向的文學即沂蒙文學。地域性、民族性、現(xiàn)代性、革命文化/文學的主導性,作為界定或闡釋沂蒙文學外延和內涵的四個常見向度而在實踐中予以凸顯。比如,已故老詩人苗得雨認為“沂蒙文學,是民族傳統(tǒng)與革命傳統(tǒng)融匯在一起發(fā)展成的帶有地域色彩的一種文化藝術形態(tài)”[5]。他對“沂蒙文學”的界定至少包括地域性、民族性、革命文化的主導性這三重內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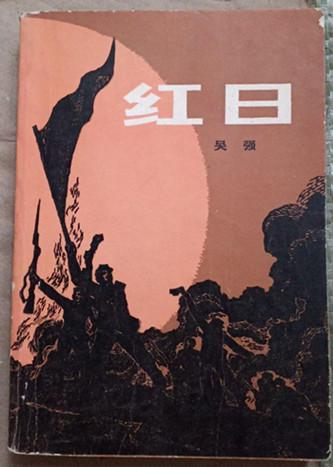
吳強《紅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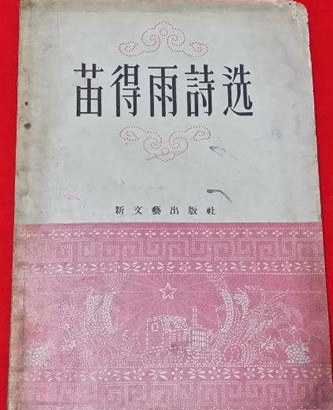
苗得雨《苗得雨詩選》

劉知俠《紅嫂》
沂蒙文學與沂蒙精神有何關聯(lián)?可概括三個“互為”:互為表里,互為生發(fā),互為塑造。或者說,二者本來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離。對作家而言:沂蒙精神是沂蒙文學表達的總主題,從方法論和主題表達向度上來說,不會存在多少爭議;實然存在的沂蒙精神與被概念化的沂蒙精神顯然是一種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前者是后者的背景、依據(jù)或基礎,后者是對前者的提純、概括或衍生。因此,“沂蒙精神”就是不斷被提純和概括的時間沉淀物或歷史衍生品。這就決定了作家們對沂蒙精神的理解與文本實踐并非囿于一點或一隅,而總是以聯(lián)系的發(fā)展的辯證思維不斷對之進行審視或建構,從而繼承并豐富其本體內涵。事實上,沂蒙精神既有其穩(wěn)定的一面,也有其不斷變化發(fā)展的一面,而就后者而言,它又總是與歷史演進的潮汐互為關聯(lián),誠如王萬森所言:“耕讀文化中,它是勤儉純樸和崇尚文明的;抗災和抗匪文化中,它是堅韌勇敢的;戰(zhàn)爭文化中,它是向往正義和敢于奉獻的;特別看到,在多災多難的歷史變遷和新舊交替的文化轉型中,它既是開拓進取的,又是和諧寬容的。”[6]然而,由于它與二十世紀中共革命歷史進程的“水乳交融,生死與共”,從而使得紅色革命文化一枝獨秀,并成為主導其他文化形態(tài)萌芽與演變的核心力量。由此以來,以中共革命和建設為中心所形成的紅色文化以及由此而孕育或衍生出來的沂蒙精神[7],不僅是當代沂蒙文化也是當代中國最具特色、最具影響力的地域文化形態(tài)。在此統(tǒng)攝下,作為沂蒙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沂蒙文學,不僅其精神之根當然會扎根于此并從中獲取豐厚的養(yǎng)料,從而生成眾多以帶有紅色風格的優(yōu)秀作家、作品,而且其對沂蒙精神的傳承或重塑——奉獻與忠誠,軍民生死與共——自也是題中應有之義。在“十七年”期間,以王安友的《李二嫂改嫁》、劉知俠的《鐵道游擊隊》、吳強的《紅日》為代表的一大批作品,以對沂蒙紅色革命歷史或沂蒙人民生活與精神風貌變遷史的書寫而成為國家宏大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很好的例證。其中,現(xiàn)實中的眾多“沂蒙紅嫂”一經(jīng)作家們的藝術塑造——劉知俠的《紅嫂》[8]影響最大——自從成為文學角色那一刻起,便已深入人心,并成為沂蒙文學的獨有標志;其純樸、高尚的女性品質和自覺的奉獻精神,亦大大豐富了沂蒙精神的本體內涵。如今,作為文化符號的“紅嫂”,不僅成為沂蒙文化、沂蒙精神的一張名片,昭示著革命戰(zhàn)爭年代千千萬萬沂蒙兒女為中國革命所付出的巨大犧牲,也作為黨和國家層面意識形態(tài)的組成部分,顯示了沂蒙與新生共和國之間的血脈相連、生死與共的精神共同體關系。1949年10月1日后,一個展新的、震撼人心的“當代”生成了。在整個“十七年”時期,作為一個地域的沂蒙文學、沂蒙精神,不僅從來也沒有缺席共和國宏大敘事進程,還以其后發(fā)優(yōu)勢成為中國最具活力、成就最突出、平臺最高的地域文學之一而備受矚目。沂蒙文學也就在這個時間范疇內,與壓抑中的現(xiàn)代性快速告別[9],從而快速開啟了真正屬于自己的文學史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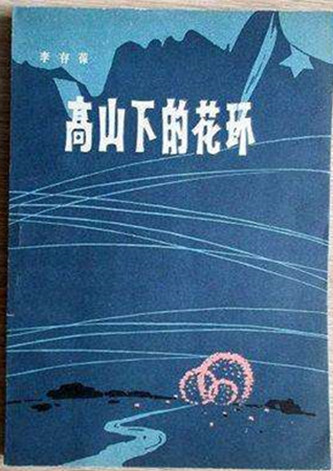
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環(huán)》

王兆軍《黑墩屯》

劉玉堂《鄉(xiāng)村溫柔》
新時期以后,真正推進沂蒙文學發(fā)生質變,并有效進入文學現(xiàn)場中心地帶的,則是以李存葆、劉玉堂、趙德發(fā)、王鼎鈞、王兆軍等作家?guī)в幸欢ǚ此夹曰騿⒚尚缘膶懽鳌H绻麤]有他們,作為史之意義的當代沂蒙文學就很難成立。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環(huán)》、《山中那十九座墳塋》、劉玉堂的“釣魚臺人物系列”和《鄉(xiāng)村溫柔》、趙德發(fā)的《通腿兒》和“農(nóng)民三部曲”、王兆軍的《拂曉前的葬禮》、苗長水的《非凡的大姨》都是該時期的代表作。從整體上來看,沂蒙文學與沂蒙精神密切關聯(lián)的主題向度突出表現(xiàn)在:對故土之愛(風物、風俗、風景,等等)和人性之美的書寫;對沂蒙老百姓和子弟兵無私奉獻精神的展現(xiàn);對人與時代關系的書寫中,側重揭示在社會轉向大潮下人們的覺醒意識。歷史理性與人文關照作為審視歷史與現(xiàn)實的現(xiàn)代性思維、方法,已逐漸被廣大沂蒙作家所采納。他們的寫作當然是典型的“當代性”實踐。沂蒙文學中人學思想、批判意識的萌生并逐漸展開,正是得益于這作家的探索與實踐。人性緯度或人道主義思想在文學中的展開,也即映照了現(xiàn)實中作為主體的人的解放。文學率先介入大時代潮流中,為沂蒙精神注入新質。這都充分說明,沂蒙文學又不僅深受紅色文化的影響,它還向其周邊和深處繼續(xù)拓展、深扎。同時,這也都表明,有關何謂“當代”或“當代性”的實踐,即從對“十七年”文學一體化規(guī)范的堅決貫徹(比如吳強的《紅日》、劉知俠的《紅嫂》),到八十年代以來對此種規(guī)范的大膽突破(比如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環(huán)》、王兆軍的《拂曉前的葬禮》),沂蒙作家都走在了當代文學發(fā)展的最前沿。
九十年代以后,特別是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間,沂蒙文學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對“當代性”的實踐最突出表現(xiàn)在宏大敘事逐漸退場,而代之以在詩歌、散文(含報告文學)、小小說等領域內個人化寫作風潮的興起。“當代性”與九十年代沂蒙文學、新世紀沂蒙文學的深度關聯(lián)突出表現(xiàn)在,彰顯個體之“我”在“時間”里的獨立性、主體性,以及由此而展開的對于沂蒙歷史與現(xiàn)實的再反思、再書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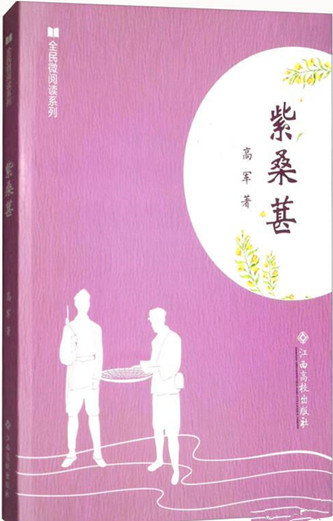
高軍《紫桑葚》

管虎電影《斗牛》海報
首先,以個人視角再述“紅色沂蒙”,重塑沂蒙精神的當代品質。沂蒙革命歷史堪稱沂蒙文學的素材庫。代表作有高軍的小小說、苗長水的沂蒙山系列、鐵流的《見證:中國鄉(xiāng)村紅色群落傳奇》《一個村莊的抗戰(zhàn)血書》、管虎的《斗牛》(電影劇本)等等。這種寫作集歷史考證、初心(信仰)追溯、可觀的閱讀(傳播力)于一體,也形成了沂蒙文學特有的當代品質。其中,高軍作為小小說領域內的領軍人物[10],創(chuàng)作了大量以沂蒙革命歷史、各類人物為題材的作品。個性化的人物,生動的細節(jié),好看的故事,有教育意義的主題,等等,構成了高軍小小說的幾個突出特征。他的小小說繼承了“紅色沂蒙”敘事傳統(tǒng),又不乏鮮活的“當代性”,比較充分地表現(xiàn)了以“紅色精神”為主導的沂蒙文化的地域魅力。管虎的《斗牛》從民間視角講述妞兒、九兒等沂蒙山小人物的抗戰(zhàn)故事,其對沂蒙精神的原生態(tài)呈現(xiàn),極具感染力。影片中的牛二雖是一個微不足道的鄉(xiāng)間小人物,但他照料那匹奶牛勝過關心自己,他用擠下的牛奶救活了很多的饑民,他機智地與土匪、鬼子周旋,他不拋棄信義矢志不移地完成部隊囑托下的任務。這部影片將沂蒙老百姓的樸實本色和人間大愛精神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

江非《一只螞蟻上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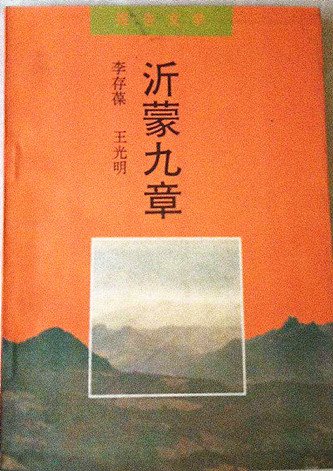
李存葆、王光明合著《沂蒙九章》
其次,視點下沉,將“我”自立為主體,并以此開啟書寫“新沂蒙人”的文學時代。如果說李存葆的《沂蒙九章》、高振的《沂水拖藍》等散文(含報告文學)率先垂范,展開對“新沂蒙”的書寫,尚處于由宏大敘事向個體書寫轉型中的話,那么,真正引發(fā)沂蒙文學發(fā)生巨變,徹底落實于個體表達,并在全國產(chǎn)生重要影響的當屬詩歌創(chuàng)作,即以江非、邰筐、軒轅軾軻、尤克利、辰水、老四、風言、瓦刀、也果、子敬、曹玉霞、梅林等為代表的“臨沂詩人群”,從對“口語詩”的探索與實踐開始,逐漸形成包容各種形態(tài)、風格的新詩創(chuàng)作格局,從而為沂蒙文學、沂蒙精神再次有效挨近或跨入中國當代文學的中心地帶,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其中,作為“臨沂詩人群”領軍者的江非對更新沂蒙詩歌的形象,對拓展沂蒙精神在“新時代”的內涵,更具有根本性的推動力。這是因為,與邰筐與軒轅軾軻的純粹“小我”視角、意識以及無根性寫作不同,江非在“小我”和“大我”之間[11],不僅較為完整地繼承自新時期以來的詩歌傳統(tǒng),還在對新鄉(xiāng)土(“平墩湖”)、“物自體”、內面風景等諸多視域的創(chuàng)造性書寫而自創(chuàng)一體,從而在詩歌史和文體特質上展現(xiàn)出更具可闡釋、可建設的價值。老四[12],作為“臨沂詩人群”80后代表,他以詩歌方式展開對人之本性(自然屬性、社會屬性)、個體心靈史(漂泊、孤獨、疼痛)和生活本質(荒謬、悖論)的探察,以及對以汶河、蒙山為中心的地域文化史,特別是深置于其中的人、事、物及其本源關系的深度開掘與書寫,都因別開生面、自成一景而備受業(yè)界矚目。從藝術實踐來看,其在地性、代償性、及物性、偏于形而上的寫作方式和美學姿態(tài),不受任何形式和修辭的羈絆且以精當把握和精準表達為特質的文本實踐,以及在都市與鄉(xiāng)土或中心與邊緣之間試圖建構新式空間詩學的藝術抱負,更使其在同代詩人群體中顯得卓爾不群。老四及其詩歌不僅有效、有力拓展了當代沂蒙文學的邊界并為其發(fā)展注入新質、新貌,也因生成了一種被稱為“老四詩學”的新范式——以詩學化的身體和身體語言探究生活與存在本質;以粗糲而沉重、尖銳而憂傷、通透而憂郁的話語風格而自成一體;尤長于對現(xiàn)實與夢想、溫暖與疼痛、和諧與悖謬等既日常又復雜、既統(tǒng)一又矛盾的“經(jīng)驗域”或“內視界”的深入開掘——而讓人對之寄予更多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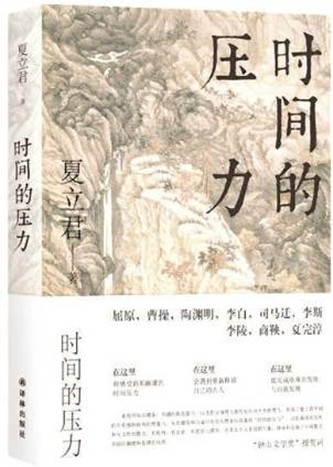
夏立君《時間的壓力》
再次,沂蒙文學的開放性、大氣象也初步彰顯。據(jù)筆者閱讀視野,在新世紀以來的沂蒙文壇上,能在寫作中展現(xiàn)大氣象、大格局的當屬散文家夏立君[13]。夏立君及其散文寫作,典型地體現(xiàn)了沂蒙文學或沂蒙精神“既有黃河文化的沉實,又有濱海文化的開放”[14]的特征。他對對中國古典文人的解讀,他的新鄉(xiāng)土寫作以及游記寫作,都無不貫徹著對“時間”與生命的本體性探討。這種審美姿態(tài)與藝術穿透力,在現(xiàn)當代沂蒙文學史上,也絕無僅有。人類從未放棄過對于時間的體悟與描述,但若要給“時間”下一個準確定義或者說對其外延與內涵做個準確界定,大概是一個具有相當難度且永遠也沒法完結的課題。與物理領域內的把握與界定不同,文學(作家)與時間的關系卻是具體的、形象的、可把握的:從孔子的“逝者如斯夫”到莊子“人生天地間,若白駒過隙”,從魯迅的“時間就象海綿里的水”到朱自清的“我的日子滴在時間的流里”,再到夏立君的“時間的壓力”、“時間之箭”、“時間會說話”,都可看出,他們的“時間”已非歷時的、一維的、不可逆的,而是共時的、多維的、可折疊的。作家們改變了“時間”的物理屬性,故可以自由出入任何“時間單元”。夏立君也是這樣一位自由出入于“時間單元”并以“時間”為伴侶、為攀談者、為靈感來源、為靈魂歸宿的文化探尋者、精神建構者、散文書寫者。或者說,對夏立君而言,時間作為一個歷史、美學與精神的符碼,構成了他及其文學實踐的源頭性的、統(tǒng)攝性的存在。他的《時間的壓力》、《時間會說話》亦然。“時間”以及“時間話語”是其最為核心的主題向度。他在修辭策略上對“時間主題”做了藝術轉化,即將時間的“直接呈示”轉化為時間的“空間表達”;而無論怎樣表達,表達什么,卻又都不脫離當代性視野。即,他將“劉家莊時間”、“長河時間”、“喀什時間”重疊或并置于當下,并在當代意識的燭照下,展開對鄉(xiāng)愁、生命、歷史、古人的再度書寫。這種書寫不僅直接表達一己所想、所念、所思、所憶,也對當代精神文明建設提供有益啟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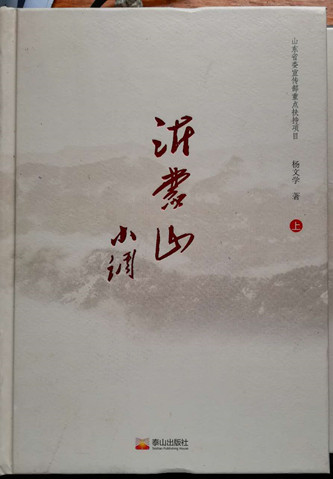
楊文學《沂蒙山小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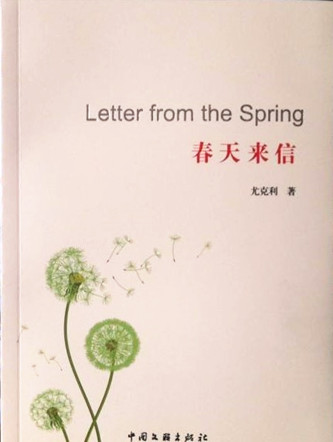
尤克立《春天來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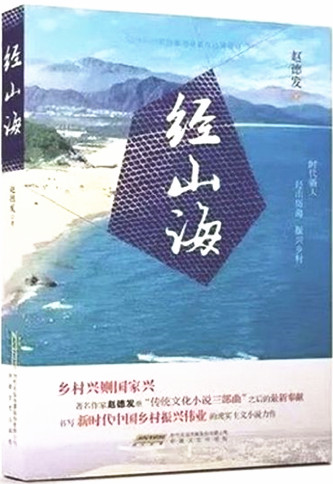
趙德發(fā)《經(jīng)山海》
新世紀以來,沂蒙文學的“當代性”實踐進入“快車道”,若單從沂蒙精神與沂蒙文學互源關系方面考量,我覺得如下四類寫作具有不可或缺的典范意義:一類是沂蒙當?shù)刈骷业幕跉v史經(jīng)歷和生命實感的代償性寫作。比如,沂南的王秀云、尤克利、梅林、武慶麗[15],蒙陰的喬洪濤、彭興凱,蘭陵的辰水。他們從事寫作的原因,無非正如方方所言:“我喜歡它的理由只源于我自己的熟悉。因為,把全世界的城市都放到我的面前,我卻只熟悉它。就仿佛許多的人向你走來,在無數(shù)陌生的面孔中,只有一張臉笑盈盈地對著你,向你露出你熟悉的笑意。這張臉就是武漢。”[16]若將引文中的“武漢”改成沂南、蒙陰或蘭陵,并將之用來表述他們與這座城的關系,也大可適用。是的,他們之于故鄉(xiāng),因熟悉而愛,并因之而寫。這類作家因對“三畫”[17]的描寫和“四彩”中對于“自然色彩”、“悲情色彩”美學基調的實踐,以及更切近鄉(xiāng)土肌理的內涉型表達,而賦予沂蒙文學以更為純粹的質地,對沂蒙民間精神的傳遞、塑造,遠比其它作家展現(xiàn)得更為直接、充分、厚實。一類是沂蒙領軍人物著眼于歷史或時代的帶有穿越時空區(qū)隔的展現(xiàn)大氣象的寫作。比如夏立君的《時間會說話》、趙德發(fā)的《經(jīng)山海》。兩位作家的寫作分別展現(xiàn)了沂蒙精神中“沉實”和“開放”之特質,其對宣揚或重鑄沂蒙精神的當代性品質,都發(fā)揮了其不可替代的作用[18]。同時,這類作家的創(chuàng)作已大大超出沂蒙文學內涵與外延的框定,而進駐中國當代文學現(xiàn)場的中心地帶,從賦予沂蒙文學以嶄新形象,為新時代沂蒙精神的傳播注入活力。還有一類是非沂蒙籍的作家或遠離故鄉(xiāng)的沂蒙籍作家針對沂蒙題材(特別是革命歷史)所展開的再審式創(chuàng)作。比如楊文學的《沂蒙山小調》(上、下)、房偉的沂蒙抗戰(zhàn)系列短篇小說[19]、趙冬苓的《沂蒙》(電視劇劇本)、常芳的長篇小說《第五戰(zhàn)區(qū)》、王兆軍的《黑墩屯——一個中國村莊的歷史素描》、周朝軍的《九月火車》。這類作家再度聚焦、審視沂蒙革命歷史,以“真實,好看,有意味” [20]為審美追求,從而開拓了革命歷史題材寫作的新路徑、新可能。同時,他們視野開闊,常常打通現(xiàn)實與歷史、官方與民間之間的森嚴壁壘,轉而在藝術層面上將對沂蒙精神開掘或表現(xiàn)引向新征程。上述四類作家的寫作因受到讀者廣泛關注從而為沂蒙精神的廣為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
沂蒙文學的“當代性”實踐,不僅是對沂蒙文化、沂蒙精神展開溯源性書寫的歷史,同時也是不斷對其進行“保值”或“增值”的活動。如果從某一時段或局部來審視沂蒙文學“當代性”實踐的即時效果,以及沂蒙文學和沂蒙精神的互源關系,都可以說發(fā)揮到了極致,然而,“極致”并不意味著永遠有效。沂蒙作家總會深陷某種習焉不察的誤區(qū),即對“當代性”的理解總會定于一端而不顧其余。誠如陳曉明所言:“‘當代性’說到底是主體意識到的歷史深度,是主體向著歷史生成建構起來的一種敘事關系,在建構起‘當代’的意義時,現(xiàn)時超越了年代學的規(guī)劃,給予‘當代’特殊的含義。”[21]如以此標準來檢驗他們的創(chuàng)作,很難說他們都達到了“主體意識到的歷史深度”,且“超越了年代學的規(guī)劃,給予‘當代’特殊的含義”。實際上,任何形態(tài)的地域文學都離不開賴以棲身其中的地域文化。沂蒙文學作為一種深受多種文化影響的文學形態(tài),其內在構成、演變、影響也并非鐵板一塊。單就沂蒙紅色文化而言,其對沂蒙文學的支撐、塑造是顯而易見的;同樣,沂蒙文學深扎于沂蒙紅色文化的土壤中,并源源不斷地生成新文本,其對包括紅色文化在內的沂蒙文化/沂蒙精神的創(chuàng)造性繼承或反哺式塑造亦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沂蒙文學的生成與發(fā)展并非是自足性的,而淪為沂蒙紅色文化或“十七年”紅色經(jīng)典譜系中的附屬,即只有依賴“他者”力量,并被編入“他者”譜系時,它才獲得“新生”。比如,劉知俠的《紅嫂》、吳強的《紅日》、苗得雨的一些詩歌,等等,一旦離開主流意識形態(tài)闡釋,其實都很難獲得文學史的再度認同或者從中被闡釋出超越于時代與文本的新意來。這說明,在新時期以前,沂蒙文學與沂蒙紅色精神基本處于同步發(fā)展狀態(tài),其互源、互塑關系是高度統(tǒng)一的。由這種“統(tǒng)一”所造成的優(yōu)長與弊端,都已成為有目共睹的事實,即當愛黨愛軍、軍民魚水情、舍小我,顧大我(集體主義、共產(chǎn)主義)等帶有突出國家集體話語或革命話語風格的文學實踐,在以劉知俠的《紅嫂》、吳強的《紅日》、李存寶的《高山下的花環(huán)》為代表的經(jīng)典文本中,借助歷史激情和鮮活典型而得到一邊倒的集中表達后,其后續(xù)發(fā)展力終因主體對歷史體驗的不足或藝術理念的落后而難有可持續(xù)發(fā)展力。其實,對某種外在理念的貫徹或圖解本不應該是文學第一性要求——對文學而言,追求“藝術真實”、情節(jié)或細節(jié)建構上的合理合情、語言或文體上的探索,等等,永遠是第一位的——但沂蒙作家卻在這方面耗盡了心血。這種藝術實踐上的南轅北轍,以及密切關聯(lián)或直接圖解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鮮明的實踐向度,都使得沂蒙文學因缺乏藝術上的創(chuàng)新性而難以在文學史上擁有跨越時代的增值性闡釋價值。自1990年代以來的三十多年間,沂蒙文學趨向多元發(fā)展,迎合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宏大敘事、高揚精英意識的個體化寫作、皈依商業(yè)意識形態(tài)的大眾化寫作各有“市場”,但各自對“當代性”的理解與實踐又大都誤入歧途:迎合主流一脈重視圖解理念(比如“新時代”)贏得了“當局”,卻失去了“讀者”;精英寫作太確信“個人化”以及由此而生成的主體思想介入時代和精神領域的力量,結果也同樣因為讀與寫的不通約性而處于孤立狀態(tài);至于大眾化寫作一脈則徹底擁抱市場,把文學等同于“為人民幣”而寫作的交換活動,則已越出文學范疇而不在本論文討論的論題內。總之,該時期沂蒙文學對“當代性”的理解與實踐,同樣存在極端化傾向。那么,該如何糾正上述誤區(qū)呢?在今天,沂蒙文學對沂蒙精神的傳承與弘揚當有更大作為,其關鍵就在于對“當代性”的切實理解與創(chuàng)造性實踐。
其一,在認識論上,亟待深度拓展。沂蒙文學對沂蒙精神的表達,沂蒙精神對沂蒙文學的支撐,彼此之間的互源、互映、互塑從來不是單向或單線展開的,而總是以多向、立體、交互的感應模式而存在著,而發(fā)展著,故對沂蒙文學或沂蒙精神“當代性”的理解和實踐,既不能囿于對“十七年”和新時期兩類話語裝置的概念化框定,也要警惕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因消費文化復興而逐漸生成的歷史虛無主義與價值虛無主義兩類后現(xiàn)代思潮的負面侵襲,從而突破種種拘囿并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有實質性進展。事實上,因為沂蒙精神“既有黃河文化的沉實,又有濱海文化的開放”[22],那么,沂蒙文學對沂蒙精神的表達也理應更為自由和廣闊。但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兩者彼此間的交互關聯(lián)卻步履蹣跚,時常形同陌路。沂蒙作家對主流價值觀的顛覆與戲仿,曾一度成為“時尚”。這也在表明,從緊隨主流意識形態(tài)一路走來的沂蒙文學、沂蒙精神,在面向今天和未來時遭遇到了發(fā)展的瓶頸問題。新世紀以來,“開放”作為沂蒙文學和沂蒙精神最具時代特質的品質,只在詩歌和散文界少數(shù)幾位作家筆下得到有效呼應、實踐。對絕大部分作家而言,對“當代性”的理解與實踐并無多大起色——反復重復過往主題,建構力很有限,藝術手法很陳舊。在這種境況下,沂蒙文學與沂蒙精神的互源、互塑自然就是效力甚微。陳曉明說:“在文學上(和美學上),要認定‘當代’卻并不容易。80年代后期,為了對時代的審美變化加以把握,人們劃分出‘后現(xiàn)代’這種說法,相對于整個‘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顯然更具有‘當代性’,‘后現(xiàn)代’就是‘當代’,但是‘當代’不一定就是‘后現(xiàn)代’。這就是中國語境,‘當代’一詞表示的時間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包含了‘當代’中國特有的歷史感及其時間意識。[23]”中國語境中的“當代性”既表現(xiàn)為自“十七年”時期一體化實踐,也表現(xiàn)為自“新時期”以來一體化解體過程,而“當下”、“當前”、“未來”等也理應內在于其肌理之內。據(jù)此,筆者認為,沂蒙文學中的“當代性”更應當是一個綿延性的指向寬廣的時間意識,是將歷史、現(xiàn)實、未來統(tǒng)一于“當下”并以此反應、揭示或呈現(xiàn)時空存在之樣、之態(tài)、之謎的藝術實踐。我們強調文學創(chuàng)作要有歷史感、現(xiàn)實感,說白了,也就要求作家具備打通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的創(chuàng)造能力,從而完成對于歷史或現(xiàn)實的總體性觀照或預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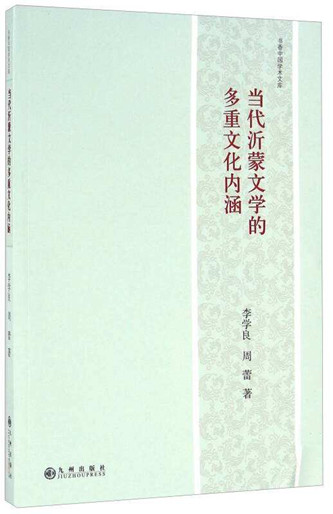
李學良、周蕾著《當代沂蒙文學的多重文化內涵》
其二,在方法論(美學觀念)上,亟待理念更新。沂蒙作家的文學創(chuàng)作又都有其明顯缺失——理性有余(主題的先入為主)而文學性稀薄。而更多時候,沂蒙作家所謂“當代性”的實踐又陷入另一種偏狹,即只注重“寫什么”上的大膽開掘,而忽略了在“怎么寫”上的藝術探索。也就是說,不是不能寫(寫什么),而是“怎么寫”依然是困擾沂蒙作家的首要問題——比如,同樣是紅色革命題材,王愿堅創(chuàng)作于“十七年”時期的那些短篇小說,在今天讀來,依然常讀常新,為什么呢?作為主旋律寫作的代表,柳青、孫犁、趙樹理、路遙等作家的作品在今天依然備受各階層讀者喜愛,其原因尤值得細細考察。而沂蒙作家在從事類似題材或主題的寫作時,卻總難以處理好這一問題。這其中有幾個誤區(qū)確有再次重提的必要。首先,對“真實”或“真實性”的機械式理解,即把文學真實等同于生活真實,而不是“藝術真實”。當前,強調扎根生活,加強現(xiàn)實題材創(chuàng)作,其前提是如何理解“生活”、作者、文本、讀者之間的互文關系。若四者不相容,一切寫作都無效或效果大打折扣。其實,扎根基層,熟悉生活,是從事現(xiàn)實題材寫作的基本前提;生活累積到一定程度,需經(jīng)過提純或審美轉化,是從事這方面寫作的關鍵;運用精當?shù)乃囆g形式,將之物化為獨一無二的語言文本,是昭示寫作成功的唯一標志;以文本為媒介彼此間生成對話與共鳴,是該文本能進入文學經(jīng)典化通道的必要條件。沂蒙作家對于上述四個環(huán)節(jié)的理解與實踐普遍不到位。其次,在革命歷史題材寫作中,把無限靠近那個“歷史真實”作為第一性追求而弱化或不考量文本自足性問題。其實,這一問題已被文藝理論家講得很清楚了——“現(xiàn)在有一種誤區(qū),寫的作家以為自己是在普及歷史知識,看的讀者以為可以增長歷史知識,這完全是誤會。歷史題材的創(chuàng)作屬于文學文化,它不提供真實的歷史知識,它提供所選定的歷史框架、歷史時限的真實的藝術形象,它的功能主要是審美欣賞,不是普及歷史知識。如果真想了解歷史知識,還是要去看歷史教科書。”[24]——此不再贅言。再次,在對歷史題材書寫中,不善處理或難以駕馭歷史理性和人文追求之間的藝術張力。最后,文體意識薄弱,探索與實踐能力相當不足[25],對“形式即內容”(“有意味的形式”)的美學理念還相當隔膜。這些弊端都非一朝一日所能克服的。然而,真正的文學從來都是少數(shù)天才作家的事業(yè),其在藝術實踐上的獨一無二性以及由此而昭示出的神啟般的偉力,只有留待時間去見證了。
注釋:
[1]《習近平在山東考察時強調認真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匯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強大正能量》,《人民日報》2013年11月29日第1版。
[2]劉家義:《弘揚沂蒙精神 傳承紅色基因》,《學習時報》2019年10月30日第1版。
[3] [5]苗得雨:《“沂蒙精神”永在》,《文藝報》2006年3月14日第2版。
[4]韓延明:《沂蒙文化生成和演進的歷史分期摭探》,《山東師范大學學報》2015年第1期。
[6] [14] [22]王萬森:《從文學視角觀察沂蒙文化》,《山東師范大學學報》2005年第5期。
[7]1990年,由時任山東省委書記的姜春云提出,即“愛黨愛軍、開拓奮進、艱苦創(chuàng)業(yè)、無私奉獻”。參閱周廣聰、張帆:《沂蒙精神16字來源》,《齊魯晚報》2011年7月27日第2版。
[8]《上海文學》1961年第8期。
[9]現(xiàn)代沂蒙文學的源頭可以追溯到新文化運動,即由劉一夢、王思玷等早期沂蒙籍革命者的小說創(chuàng)作,可看作是現(xiàn)代沂蒙文學的發(fā)端。以寫實性、批判性為特征的現(xiàn)代沂蒙文學在三四十年代被以革命斗爭和戰(zhàn)爭文化所改造。待到新中國成立,作為一個地域的“沂蒙文學”在整體上被納入“十七年”的語境中,從而出現(xiàn)由“現(xiàn)代性”向“當代性”的突轉。
[10]高軍,1962年生,臨沂沂南人,現(xiàn)為沂南縣作家協(xié)會主席。筆涉小小說、文學評論、文學史、諸葛亮研究等眾多領域。代表作有《紫桑葚》(小小說集)、《沂南文學史》、《諸葛亮十八講》。《紫桑葚》收入語文出版社出版的全國通用小學教材《語文》在全國十多個省區(qū)廣泛使用。
[11]江非,1974年生,臨沂河東區(qū)人,現(xiàn)居海南。著名詩人,參加過《詩刊》第十八屆青春詩會,出版詩集《獨角戲》、《紀念冊》、《一只螞蟻上路了》。
[12]原名吳永強,1985年4月出生,山東臨沂人,居濟南。中國作協(xié)會員,山東作協(xié)簽約作家。著有詩集《孤獨者說》《自白書》。曾獲2014“紫金?人民文學之星”詩歌佳作獎,黃河口駐地詩人。
[13]夏立君,1962年生,臨沂沂南人,著名散文家,現(xiàn)任日照市作家協(xié)會主席。著有散文集《時間的壓力》、《時間會說話》。《時間的壓力》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
[15]王秀云,小說家,著有《到山里拾柴禾》、《小城生活》;尤克利,詩人,著有詩集《晚秋》,曾獲“全國農(nóng)民十大詩人”稱號;梅林,詩人,著有詩集《農(nóng)事》;武慶麗,小說家,代表作有《失蹤》、《大水》、《向日葵》。其中,《失蹤》入選《中國當代經(jīng)典必讀2019年短篇小說卷》(吳義勤主編)。
[16]方方:《行云流水的武漢》,《文化月刊》2003年第5期。
[17]鄉(xiāng)土小說是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上影響最大的文類。丁帆曾用“三畫四彩”來概括其藝術特征:“三畫”即風景畫、風俗畫、風情畫;“四彩”即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悲情色彩。見《中國鄉(xiāng)土小說史》,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社,2007年版。
[18]夏立君的《時間的壓力》、趙德發(fā)的《經(jīng)山海》分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2019年“五個一工程”文學獎。作為土生土長的沂蒙作家,趙德發(fā)和夏立君的創(chuàng)作對踐行并弘揚沂蒙精神,做出了重要貢獻。
[19]房偉,山東濱州人,現(xiàn)為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近年來,他創(chuàng)作了不少沂蒙革命歷史題材小說,代表作有《小太君》、《副領事》、《肅魂》、《鬼子妮》等等,后收入小說集《獵舌師》,并以此獲得“第十八屆百花文學獎”(2019年)。
[20][24]童慶炳:《歷史題材創(chuàng)作的三向度》,《文學評論》2004年第3期。
[21][23]陳曉明:《論文學的‘當代性’》,《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第6期。
[25]相比較而言,劉玉堂的幽默味(比如“釣魚臺人物系列”)、趙德發(fā)的方言實踐(比如《通腿兒》)、夏立君的大文體探索(比如:《李白:忽然來了個李太白》、《屈原:第一個獨唱的靈魂》),軒轅軾軻的口語詩,等等,都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文章原發(fā)于《中國文化論衡》2020年第1輯,有微改。)


